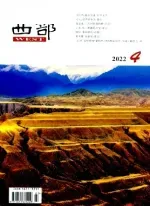收藏秘境(上)
2011-08-15丁建顺
文/丁建顺
收藏秘境(上)
文/丁建顺
一
吴越在政法学院的草坪上泊好车,走进教授楼的钱教授家。满头银发的钱教授将女弟子引进客厅,乐呵呵地说:“祝贺你获得了法制新闻奖,又荣升了文娱版的副主编。”
吴越觉得诧异,说:“这还是昨天的事,钱老你怎么也知道了?”
钱教授说:“大上海并不大的,圈内人士有点动作,过了一夜大家都知道了。
吴越说:“可我对文化娱乐圈还不十分熟悉呢。”
钱教授说:“你接手副刊后一定要沉下去,多看些艺术理论和书画作品,从采写展事新闻入手,写好每一篇报道,在短时间内把自己提升成行家。”
吴越说:“我来拜访钱老,就是想请你赐我几篇稿子,让我编好接手后的第一期专版。”
钱教授说:“近期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行情十分火爆,解读文章也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我写了一本《书画鉴赏与拍卖市场》的书,可以选几篇给你。”
吴越接过打印稿鞠了一躬说:“钱老,你这是帮我的大忙了。”
钱教授笑呵呵说:“我还要写一幅字送给你呢。”
吴越看钱老徐徐写了“积健为雄”四个大字,拍手喊好:“感谢老师的美意。”
等待墨迹风干时钱教授问道:“下午有什么安排?”
吴越说:“没什么事,我可以留在创作室为钱老拉纸吸墨,让老师写个痛快。”
钱教授说:“海华拍卖行的谢灵宇约我去看汤之丹的画,你没事就随我一起去看看吧。”
吴越问道:“汤之丹?就是前些日子他的后人为分家产闹上法庭的大画家汤之丹?”
钱教授感叹地说:“是呀,说起来真是作孽。上个世纪80年代末汤之丹过世时,几个儿女分遗产时抢着要屋里的红木家具并分了存折上的现款,而把他的画作视为圾垃,统统扔给了在大学里教美术的大儿子。这几年汤之丹的画价大涨,那几个儿女又坐不住了,要逼着老大交出父亲的画作平分。汤家老大自然不同意,说这些画是他们强摊给自己的,其他子女便把他告上了法庭。说来也是离奇,汤子丹好似料到日后会出现如此一幕,他在银行保险库里存了一口铁箱,每个子女都有一把钥匙,总钥匙则由老夫人掌管。汤家后人把长子告上法庭后,此事才浮出了水面。汤家老大拗不过众弟妹,于是同意在法庭上集齐了钥匙当众开箱,也同意将铁箱内的物件一律平分。谢灵宇接到了委托,他约我到法院鉴定铁箱内的字画。”
吴越叹了口气说:“汤之丹的在天之灵倘若得知,老先生也不知作何感想了。”
钱教授略顿了下说:“现在的人都心浮气躁的,像汤家长子那样的人倒也真不多了。还有那位海华拍卖行的谢灵宇也不简单,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老总,自己收藏宏富,还积下了上千万的资产,真像神话一样。”
门铃叮咚。吴越开门,一位身量高大的先生笑吟吟进门。
钱教授介绍来人就是谢灵宇,又说:“小吴记者是我以前的研究生。说来也是巧,小吴刚从法制新闻部调到文娱部,正愁着没文章编字画鉴赏专版。谢总,能带小吴一起去看看吗?”
谢灵宇很爽快地说:“请得动法制报记者是钱老的面子。吴小姐肯去自然最好了,把经过写成文章在报上一发表,拍卖汤之丹藏品的影响就更大了。”
三人乘电梯下了楼,谢灵宇引钱教授和吴越走向门庭外的一辆广州本田。
谢灵宇边驾车边问:“钱老,你估计那铁箱里会藏着些什么宝贝?”
钱教授沉吟道:“按常理而言,汤之丹是和上海的吴湖帆、刘海粟、谢稚柳等属于同一辈的书画大家,但汤之丹的子女多负担重,箱子里收藏着什么倒也吃不大准。”
谢灵宇很自信地说:“我推测是他自己的作品。”
吴越侧首问道:“谢总,你看到过那只铁箱吗?”
谢灵宇注视着前方:“我虽然接受了汤家委托,实情也并不知晓多少。”
吴越又问:“如果和传统的樟木箱一样大,你估计铁箱里会收藏多少件作品?”
谢灵宇回答:“如果那样大,铁箱本身就抬不动了。”
钱教授说:“装在箱子里的字画一般都是没有装裱的。假设铁箱只有樟木箱的一半大,压紧了装折好的字画,那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
谢灵宇微笑道:“看来这是一宗大买卖了。”
车到法院,谢灵宇引着钱教授和吴越推门进入一楼的民事调解厅。稍候,法官和书记员走进调解厅,在前边的高桌后入座。法官看大家神情肃穆地坐着,也不敲惊堂木,只是淡然地扫视了一下法庭问道:“铁箱已从银行的库房运来。大家钥匙都带来了?”
众人点头道:“都带来了。”
法官抬了下手说:“请把铁箱推来。”
法警推着铁箱把它送到调解厅中央指定的位置。那是一口比普通樟木箱略小的铁皮箱。法警向汤之丹后人收齐7把钥匙,按说明书依次开启连环锁,然后打开了箱盖。在场者都伸长头颈看,可箱子里一无所有。法警看到箱底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拾起来交给法官。
法官抽出信笺看了说:“这是一封汤之丹先生的亲笔信,需要在这儿念一下吗?”
众人回答:“大家都在,念吧。铁皮箱里既然没有东西,可把事情弄明白心里也好受些。”
法官一字一顿地念道:“各位子女:为父的只爱绘画不治他技,于当官敛财全然外行,然而一生清白。为父也曾勤奋作画,可画作都换了油盐柴米聊以养家。这口铁箱内一无所有,你们不要心怀怨恨。为父在此赠送各位子女四个字——清白传家。在场子女中谁继承了我的衣钵的,这口铁皮箱就归谁收藏字画。”
二
吴越拨通了章宝麟的手机。接听的语音有些疲倦,大约是在伏案写作。当吴越说她就是钱教授介绍的记者后,章先生马上热情起来,说他在小区门口等着。章宝麟登车后介绍说:“今晚收藏鉴赏联谊会邀请到会的范围很小。请客的严先生经营着一家酒店,生意蛮好。严老板倒也可以称为一位儒商,经营之余玩玩古董,收藏一些字画。据说近期低价购得一幅古画,今晚请客,就有一人乐不如大家乐的意思,把古画拿出来让大家欣赏把玩。”
吴越笑了笑说:“现在稍微看得上眼的名家字画动辄几十上百万的,他有这个财力收藏?想上海滩上酒店林立,有走红赚钱的,有打烊转手的,吃酒店饭其实也是极辛苦的。”
“严老板运道好,他经营酒店起步早,搞收藏也早,家里收着一些好东西的。就说今晚要展示的古画,据说收进的底价仅五十万,绝对是捡了个大便宜。这样的好事又被他撞着了。”
“不要是幅假画噢,是真的为什么不送到拍卖行拍掉,公开竞价,又热闹又可以多赚点钱。”
“字画流通除了拍卖行,还有许多别的渠道呢。譬如讲钱教授,他收藏书画喜欢淘,在上海喜欢跑城隍庙,到北京喜欢跑琉璃厂,也喜欢在书画圈子中交换,他收藏的乐趣在于集藏的过程。严老板要照看酒店的生意,他又不喜欢跑拍卖行和文物商店,于是就有画商掮客为其牵线搭桥。这种收藏法在生意人圈内蛮普遍的。”章宝麟笑笑说,“你刚刚涉足收藏圈子,是好是坏,是真是假,都不要轻易发话,省得人家笑你是外行。”
吴越笑着点头说:“晓得了。”
两人抵达徐家汇附近的星岛酒店时,门庭外泊着几辆轿车,应邀出席的收藏家已坐满一桌。严老板显然是个快活人,穿一件立领T恤,焗过油的黑发齐崭崭地梳向脑后。他连声问钱老答应来的怎么还没来?章宝麟打招呼说钱老晚上有事,与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商谈出书事宜。钱老虽然没来,但钱老是很支持我们工作的,派了他的得意门生,本市法制报的名记者吴越小姐出席我们的联谊会。严老板率先鼓掌,大家纷纷和她交换名片。章宝麟很热情地指点谁是谁谁,吴越一时也记不周全。她环视聚会场所,中间摆着仿红木的圆桌和靠椅,旁边还有一组沙发,墙上虽然挂的是名家画作,但一看即知是应酬之作,毫无气韵可言。这仅仅是一间较宽敞的酒店包房而已,她不知章宝麟所谓的宝贝古画藏在什么地方。
严老板端起酒杯说:“欢迎各位莅临本店,欢迎吴记者加入我们的队伍。来,干了!”
“干了干了。”大家笑哈哈地举杯,动作很大,其实只在嘴唇上碰一下而已。
吃了冷菜,接着端上来红闷乌参、清炒虾仁、糖醋黄鱼、草头圈子等等,吃得客人脸上渐渐泛出了红光,都说好多年没有吃到这么正宗的本帮菜了。
坐主席的一位老者说:“只要照这样的菜做,星岛酒店必定生意兴隆,赚到了大把大把的银子,严老板想买什么名画想买哪个朝代的,下单时手不会软的。”
严老板哈哈一笑说:“王老说得好说得好,但这桌菜是专门为朋友们烧炒的。本帮菜讲究用料,乌参选南货市场里最好的,虾仁是用活的竹节虾现剥的,二斤以上的野黄鱼难得觅到,等一会还要吃阳澄湖的清水大闸蟹,上正宗的鱼翅,原料加酒店毛利,如此一桌酒菜数千元的价,可不要吓退食客了。”
王老亦哈哈一笑说:“上海这么大,你对上海的消费水平要有信心嘛。”
大家依附着笑了一通。吴越觉得老者的语音很磁。
章宝麟凑近了介绍说:“这位王老也是上海本地人,抗战时去了延安,解放后留在北京做官,官不大脾气却很大,娶了北京人为妻,练了几十年,一口北方话居然讲得十分道地。听说他还拜启功为师,学习书法和鉴赏,离休后才回上海定居的。王老的书法虽属高人俗字一路,看东西的眼光却很凶,据说请他掌过眼的字画十有八九是靠得住的。”
吴越计算了一下,假如王老80岁,当年他去延安时还不满15岁呢。
待吃了酒酿圆子,随后端来一大盆各色水果。吴越想现在可以看古画了,不料严老板说中秋佳节快到了,又吩咐服务生送每人两盒自产自销的什锦月饼,然后下楼登车。
严老板的寓所在西郊的仙霞路一带,是个闹中取静的小区。一下来了五辆车,惊动值勤保安出来指挥停车。众人随严老板乘电梯上楼,吴越走进大门,才知道这房子是复式的,大客厅里摆的都是红木家具,墙上只挂着两件名家字画。大家围着博古架观赏,都说其中一只晋代的青瓷三足笔洗弥足珍贵,严老板却说是从地摊上随意淘来的。
待喝了茶,王老说:“可以了,是在客厅看吗?”
严老板笑笑说不,又请众人登上小楼梯。复式楼层里只摆着一只红木书案和两只老式硬木大橱,房间虽然空旷,四壁却挂满了名家字画。吴越随众人遂幅观赏,得到严老板允许后,她有选择地拍了几幅。从初次谋面到逐步熟悉,乍一看,严老板虽然快活却还有些俗气,但他的收藏却十分精到,墙上依次挂着任伯年和吴昌硕等海派名家的字画。
章宝麟指着满屋藏品,又拍拍两个大橱说:“严先生把所有的字画挂起来,恐怕可以开一家海派书画的美术馆呢。”
严老板笑笑说:“不敢讲,橱里实在也没啥好东西了。”
在王老的示意下,严老板撤去画案上的杂物,打开大橱,捧出一个长方形锦盒。
吴越看锦盒上的题签是:朱耷《水墨荷花图》手卷。严老板拿来几付汗布手套和一柄大号放大镜,自己戴上一付,然后打开锦盒,托起装裱一新的手卷,解下牙签,在画案上徐徐展开。
大家聚拢了仔细观赏,唯王老戴上汗布手套,拿起放大镜俯首研究起来。
严老板退到吴越身边,低声说:“钱老没来真是遗憾了,不然是要请教授题写引首的。”
吴越低声说:“今后总归有机会的。”
大家看了一会,说这《水墨荷花图》手卷怎么和看熟的八大山人的画有些两样,笔性好像硬了些。
严老板解释这是八大早期的作品,那时笔法还未定型,大家放心,他已请江西和北派的专家们都看过了,这握手卷足可以作他广海斋的镇斋之宝。
“是裱好了送来的还是你自己揭裱的?”王老抬首问道。
“送来时老裱酥得不成样子,是我送到朵云轩揭裱的。”严老板小心回答。
“这尺幅倒有些蹊跷。高28厘米是对的,裱过几次,每次总要勒去一刀。但宽度不对呀,丈二手卷是360厘米,八尺手卷是240厘米,这手卷怎么会是205厘米的呢?”王老量了下说。
“江西专家推测是传藏过程中被人割掉了一截。”严老板想了想说。
“割画一般只割引首,因为引首容易受污染或损坏,为什么连画尾也割去了呢?”王老的神色凝重起来。
“王老,这画难道有问题么?”严老板快活不起来了。
“不是有问题的问题。这画是真的,但不是八大山人画的。”王老哼了下说。
见众人齐刷刷地看着他,王老指点说:“纸是旧纸,笔墨也是老的,整幅画的风格也有朱耷早期作品的特征,按严先生的说法裱工也是老裱。但前一位藏家为什么要把引首和画尾都割去呢?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卖画者作假,把一幅临摹八大山人的作品去头去尾,冒充原作,如老裱的绫边再一看即知是老仿还是新仿;二是临摹者仿着玩玩,裁去摹得不好的首尾裱了起来,这给今天的画贩以可乘之际。从材质上看,第二种的可能性大一些。”
大家钦佩王老的眼力,也为严老板可惜,说这五十万岂不是打了水漂。见主人似遭霜打了黄瓜蔫蔫地,大家也觉得没趣,低声打过招呼,乘电梯下楼离去。
吴越送章宝麟回家。上了车章宝麟才说:“栽了,这回严老板栽跟斗了。”
吴越问:“严先生不是还收藏了那么多的海派作品吗?”
章宝麟说:“小吴你不知道,除了任伯年和吴昌硕的值钱外,其他的都还一般,有学术价值有艺术价值,但经济价值还不大。严先生的酒店规模小,五十万买进一张假画,说不定要弄得酒店关门打烊呢。”
吴越听了摇摇头,再也不说话了。才开了两个街区,章宝麟的手机响了,原来是刚才同桌的一位彭先生打来,请他返回严老板家的小区门口,说有要事商量。吴越在路边停了车,章宝麟问什么事这么急。彭先生说他想原价盘下严老板的《水墨荷花图》,只是要添那只博古架上的青瓷三足笔洗,他想请章先生做个中人。章宝麟说王老判定那手卷是假的,要一幅假画干什么呢。彭先生说这你就别管了,事成之后给百分之五的佣金。章宝麟说以后反悔了他可承担不了责任的,彭先生说这点规距他是懂的。
“怎么样?”章宝麟看着吴越问道。
“五十万的百分之五,赚头倒是不小。”吴越笑笑说。
三
吃了午饭,吴越取出数码照相机一帧帧翻阅,想从中找出一幅合适的写品藻文章。她选中了吴昌硕的《红梅水仙图》,正构思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写还是从收藏的角度写时,电话座机响了。吴越抓起话筒一听是钱教授打来,问她昨晚与收藏家们在一起的感觉如何。
吴越说:“感觉还不错。可我搞不懂的是,那手卷既然为赝品,为何还有人以原价盘下?”
“这里面玄机重重,有学术的有投资观念的,也有个人好恶的。”钱教授在电话里顿了下说,“你说的那件八大山人的《水墨荷花图》手卷,现在就放在我的画案上。”
吴越答应马上就去。她下楼驾车出发,到政法学院的工作室时,钱教授拿着放大镜还在画上俯首研究。钱教授抬首问道:“是你昨晚看到的那卷画吗?”
吴越仔细看画,那构图,那笔墨气韵,那泛黄发灰的画面说明确实是昨晚看到的那件手卷。她问道:“是章先生请你题的?”
“不是他,但与他也搭界。是他陪着一位——”钱老翻看名片说,“彭先生上门的,说润笔一万元,就在引首题‘朱耷水墨荷花图卷’。”
“嗬,还超过一字千金呢!”吴越笑着问,“你题还是不题?”
“不能题,不能为一笔润资坏了一世的英名。”钱教授凝重地说。
“对,钱老说得有理。最近许多报刊杂志在抨击某位鉴定家只管拿钱,无论真假他都题,把名声搞得很臭。”吴越由衷说道。
“你讲得有理,我也是这么考虑的。”钱教授笑笑说。他去贮藏室取来一轴八大山人的《芦雁荷花图》,解开锦带挂上墙,说,“这件立轴是八大成名后的作品。手卷临的是八大的早期作品,虽然有些差异,但大师级画家的笔墨灵性,前后还是相通的。”
吴越听了觉得茅塞顿开,凭着做法制新闻的直觉感到其中必有文章。现在的社会虽然富裕,但谁会一掷五十万元收藏一幅大家都认为靠不住的假画呢?她想到可以据此写一篇报道,把其中蕴藏着的新闻价值挖掘出来。
寻出昨晚收到的名片细看,只印着葚斋主人彭寅木和手机号码,据此也判别不出他的身份。她回想这位彭寅木的相貌,55岁左右,保养得很好,看人时尽管低眉顺眼的,但举手投足间又显露出几分倨傲……吴越相信他绝不可能是一位全职的收藏家,他一定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她对钱教授说想去采访这位彭寅木先生。
钱老说:“如果要获得确切的信息,请章宝麟安排,到这位彭先生的府上采访是最好的。”
吴越马上和章宝麟联系,过了一会儿他回电说彭先生同意接受采访,让她等在钱教授的工作室,他来接。吴越与钱老聊了没一会章宝麟就赶到了。他热情地与钱老师生打过招呼,把两篇书画掌故交给吴越。当他看到展开的手卷上还没有题字,神色便有些不解。
钱老让吴越把画卷起来,又从抽屉里摸出一个饱满的信封递给章宝麟,说:“画有点靠不住,我实在无法落笔,请把润资还给彭先生吧。”
章宝麟看看吴越又看看钱教授,只得尴尬地把手卷装进锦盒,与吴越一起告辞。坐进小车后,章宝麟苦笑着说:“看你的老师,送到手上的钱居然不要赚,叫我难做人了。”
吴越边扣保险带边说:“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钱老有自己的处事原则。”
章宝麟也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吴越。
吴越诧异地问:“怎么回事?”
章先生说:“就是昨晚的佣金。”
吴越笑着还给了他,说:“报社的收入挺丰厚,还有不少稿费,我怎么能收这钱呢。章先生搞收藏既辛苦花费又大,这点钱用在收藏上吧。章先生能为报社写稿,能带我出入收藏家的圈子,就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
章宝麟收了信封说:“你是我遇到的好记者之一。凡我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吩咐。”
“你与彭先生的关系怎么样?”吴越问。
“私人交情一般,因是收藏圈中的朋友,见了面还是很客气的。”
“彭先生给我的名片上只印着葚斋主人,看他的言谈举止,既不象一位民营企业家,也不像一个职业的书画掮客。说实在的,”吴越低声说,“凡是在名片上不给人确切信息的,这种人一般都靠不住,都想隐瞒点什么。”
章宝麟斟辞酌句说:“你分析得对,彭寅木有两张名片,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给你的那张是他的私人名片。”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概是公私有别,在私交圈子里发私人名片吧。”
吴越点点头,觉得这个解释还有些对头。她问道:“彭先生想在哪儿接受采访?”
章宝麟说:“到汇金楼去,彭先生已等在那儿,晚上请你吃饭。”
吴越在章宝麟指引下开车抵达酒店。进入包房,彭寅木已点好酒菜,他招呼吴越和章宝麟坐下,递上名片说:“请多多指教。”
吴越接过来一看印的是上海春晖投资公司总经理,问道:“这投资公司是独资还是合资的,是民营的还是政府的?”
“是政府的,我个人哪有能力开一家投资公司呀!”
彭寅木刚接口,章宝麟递上锦盒和信封,带着歉意说:“钱老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没有题引首。”
“喔,再想想办法吧。”彭寅木似乎没有觉得意外,他把锦盒随意放上空着的靠椅,对吴越说,“记者小姐,你说是吃了谈还是谈了吃,还是边吃边谈?”
吴越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彭先生设想了多种谈话的语境,倒有些诸葛亮的遗风。其实用不着这么正规的,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聊聊自己的经历,聊聊人生感悟,聊聊收藏观念和价值取向,聊聊收藏过程中的趣事逸事等等。”
“这还不正规么,这些话题足可以写一篇报告文学了,你们记者真会说话呀!”彭寅木看着吴越说,“我知道吴小姐的意思,你是否在想,这个彭某人花五十万买下一件膺品,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或者用北方话说是一根十足的棒槌?”
吴越笑着说,“怪不得坊间还在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老话呢。”
章宝麟插话说:“我们彭先生可是位大领导呢。”
“这里没有什么领导。”彭寅木摆摆手说,“王老鉴定这卷八大山人的《水墨荷花图》是赝品,钱老也认为此画不真而拒绝题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瞒吴小姐,我私下里玩字画已有些年头了,早期也吃过几次药,那注定是要交学费的。凡事都要上心做,上了心再下劲做,没一件做不好的。此后我自己看,也跟着朋友看,看过几百上千幅后,眼光多少也练了出来。”
吴越点点头说:“这倒和钱教授说他练眼力的经过一样。”
“钱老鉴定字画那才叫真有眼力,他是以学识修养为底蕴的,那像我这种民间收藏瞎弄弄的。”彭寅木喝了一口酒说,“昨天我看着《水墨荷花图》手卷慢慢打开,我的眼前一亮,那股拙朴的古气,那种大师级画家笔下才会有的逸气静气和高超的笔墨气韵扑面而来,我甚至可以感到八大山人作此画时的生命律动。我正暗暗嫉忌严老板运气这么好,竟能以如此低的价格收到八大山人的绝迹时,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王老鉴定此画为假,在场的收藏家都附和了王老的意见,严老板为自己看走眼而羞愧,为自己蒙受的损失而痛心。大家不欢而散后,我重返严家,提出以原价接盘,但要加上那只青瓷三足笔洗。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大手笔大手笔!”章宝麟感叹地说。
“我要这只晋代笔洗其实只是个幌子。现在这两样宝贝都成了我的收藏品。”彭寅木看着吴越,有些得意地说,“这也叫搏一记,凭自己的眼光罢了。宝石界有看石论玉的博弈,收藏字画为什么不可以博弈一次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