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茧[短篇小说]
2011-04-17张玉清
文/张玉清
一天早晨,庄永臣发现办公室的窗角织起了一只茧。那是一只蜘蛛茧,铜钱大,毛绒绒、灰扑扑,窗角的墙壁是白色的,因此这只茧待在那里不是很明显。
刚看见那只茧时,庄永臣内心的第一反应是要去摘掉它。它在那里很难看,也不雅,会让别人尤其是领导对房间的主人产生邋遢和缺少朝气的联想。他坐在椅子上,定定地盯了它两三分钟,却在将要站起来时,又打消了念头。这一是因为他懒得动,茧的位置在窗子的右上角,要去摘掉它,他得先站到床上再爬上窗台,伸直手臂去够它才能摘到,这明显是需要一个人兢兢业业去完成的一件事;再有是因为,庄永臣又意识到那只茧也是个小生命呢,那里面肯定孕育着等待出生的小蜘蛛,一时间动了恻隐之心;还有就是他忽然间心里有了一股豪迈之气,他妈的!我偏不摘它,我邋遢就邋遢,我没有朝气就没有朝气,我还怎么着我?
庄永臣坐在同事王芳的椅子上,盯着那个蜘蛛茧想:小东西,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吧。他这样想着,内心里感到自己是多么善良和富于人道主义,与这大楼里的许多人物比一比,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好人!
他拿过王芳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杯里的水还是王芳昨天下班时喝剩下的。他只喝了一小口,喝多了恐怕被她察觉。他喜欢在年轻的女同事王芳不在时拿她的杯子喝水,那杯口留有王芳口唇的芳香气,庄永臣喝水时有意让自己的嘴唇在杯口停留良久。
庄永臣喝过了王芳的水,细心地将杯子放回原位,然后才拔开门的插销,打开门,他的心里被一种暧昧的感觉弥漫着,小有快感。庄永臣回味着这小小的快感,拎了暖瓶去锅炉房打水。
他拎着水瓶走路,心思还在年轻同事王芳的身上。这是一种无聊的没有主题的心思,散碎、不连贯,并且随时可被无足轻重的事物打断。比如他走在楼道里脑子里浮现的还是王芳昨天下班之前补妆时,捏着一管唇膏专注地涂嘴唇的情景,走到楼门口推门时这情景就被门打断了,等到出了门,再次浮现的已是王芳拖地时撅起的屁股,那屁股丰满、青春、单纯……就是这样的心思,它们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在庄永臣脑子里徘徊,使他的脑子因此不会无所事事。应该说这样的思维有几分猥琐,却说不上淫秽邪恶,并且对王芳本人也没有什么危害。
至于用王芳的杯子喝水,按说存在一些卫生隐患,如果庄永臣有传染病将问题严重。好在庄永臣身体健康,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后果,顶多也就是假如让王芳知道了让她恶心得吐几回。但王芳不会知道,庄永臣一向谨慎,每次王芳上班,一般会看到庄永臣在捧着他的大杯子嘘嘘地喝茶,因此她不会想到庄永臣在不久前用过自己的杯子。王芳刚刚参加工作两年,资历甚浅,对庄永臣很尊重,每天上班一进门,总是冲庄永臣灿烂一笑,说一声:“庄科长早!”庄永臣嘴仍然拄在杯子上,说一声:“来了?小王。”王芳就拿来笤帚扫地拿来墩布拖地,这是她和庄永臣默认的分工,庄永臣每天早到一步打水,王芳则负责地面卫生。两个人属于政府办公室第九科,是最小的一个科,只他们两个人。
庄永臣走下大楼后门的台阶,看到一科的一个女的穿了裙子,他眼前一亮,用眼睛的余光瞄着人家的小腿和手臂,这两处裸露部位显得分外白净。庄永臣想,王芳什么时候也穿上裙子呢?
时间过得可真快,一转眼竟又要到夏天了。去年的夏天他的心里埋藏着一个期望,这是一个有关仕途的期望。那时政府办的一个副主任快到内退年龄了,而这一堆科长里面属庄永臣资格最老,按理他提副主任的希望最大。所以那时庄永臣的心里守着这个期望,连工作都十分卖力。哪知夏天一过秋天一到,却是资历远不如庄永臣的三科科长孙国起被提为了副主任。庄永臣深受打击,蔫了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每天除了偷偷地用嘴沾一下王芳的杯子,再也没有什么让他提得起兴趣。
今天一科这个首先穿上裙子的女人却仿佛触醒了庄永臣心里那蛰伏了的神经,他觉得委靡的心态一下子振作了。庄永臣眼前亮亮的,脚步也迈得大起来。
但他走出了十几步后却又眼前一暗,原因是迎面碰上了副主任孙国起。想避开是不可能的,从办公大楼通向锅炉房的路只有这一条,现在他们正处在半途中,何况孙国起已经看见了他,他不可能退回去了。庄永臣只好捏起脑瓜皮,迎上几步打招呼。
“国……国起,你打水啊。”
“啊,老庄,你好。”
“你事情那么多,让下边人打就行了,你主任还总是亲自打水。”
“没啥,反正早上事不多。”
两人对上这几句话,擦肩而过,听上去,双方都很客气很亲切。但庄永臣的心里尴尬得要命。
庄永臣倒不是对孙国起提了副主任不服,那是上级的意志,他岂敢不服?何况时间已过了好久,他的不满情绪已渐渐平息。庄永臣只是对与孙国起打招呼时的称呼感到尴尬。孙国起提了副主任的第二天早上,庄永臣与他在楼道里走了个碰头,庄永臣一看见孙国起,心里猛然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那就是他从今以后应该怎样来称呼孙国起。
孙国起年轻,又来得晚,从他到政府办那天起庄永臣一向是直呼其名的,就叫他“国起”。可是孙国起提了副主任,情形立即不同了,他已经是庄永臣的上级。在政府大楼里,一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下级称呼上级要称职位,比如“×县长”“×主任”,而上级称呼下级则既可以称职位又可以直呼其名或者叫一声“老×”。按这个规则,庄永臣见面打招呼应该称孙国起为“孙主任”。要说庄永臣在大楼里待了快二十年,对这规则早已适应,可面对孙国起他却感到很是别扭。两人相处这么久,从他刚进单位还是个小青年时起庄永臣就叫他“国起”“国起”,叫了这么多年,一时难以改口。
庄永臣一时间没了主张,还没等他拿定主意,两人的距离已经近在咫尺不能不开口招呼了。
“国……国起,早啊!”
“啊,老庄,你早!”
庄永臣站下,手忙脚乱,一点儿也不理直气壮。
孙国起没有停步,好像有什么急事要去办理似的。
庄永臣回过神来,有点儿后悔,他注意到孙国起已经对他改了口,称他“老庄”了,而过去孙国起对庄永臣的称呼一向是“庄科长”。正回味着,听到背后一个年轻女子脆生生的声音:“孙主任早!”听出来这是三科的小刘,庄永臣更觉后悔了。
庄永臣虽然后悔却并没有及时改正,那天上午他又碰到了孙国起三回,可他确实对这一声“孙主任”叫不出口。他比孙国起大了十岁,却要恭恭敬敬三孙子似地叫他“孙主任”?何况早上已经称他“国起”了,庄永臣觉得没法再改,就顺下来了。从此以后庄永臣也没有改,见了面就称他“国起”,但他却又总会在后面的话里想方设法再加上“主任”两个字,比如今天他就说:“你主任还总是亲自打水。”
就这样一晃半年过去了,庄永臣和孙国起之间的称呼还没有理顺,每次与孙国起走碰头不得不打招呼,庄永臣都觉得喉咙里鲠着什么东西。他平时尽量避免与孙国起走碰头,但两人之间还是不时的就有一回这样的细节。
这么多年庄永臣一直仕途不顺。
他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直接分配到政府办,应该说那是一个人前途无量的开始。在前后分到政府办的五个年轻人当中属庄永臣最为有才华,他写出的材料被领导打回重写的时候最少,一遇有县长讲话什么的大材料都由他来执笔,哪次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都少不了他,他偶尔还能写出一二首诗来在党报上发表,所有人都认为对他的提拔指日可待。可一个很小的事耽误了他的一生。
那时候办公条件比较差,政府办公楼里还没有空调,王副县长是个胖子,最怕热,喜欢对天气发表评论。那个夏天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天气,七月流火呀!”不知王副县长从哪儿学来了这么个“七月流火”,他显然很是喜欢这四个字,在好多个场合把它们表达出来,政府大楼里几乎每个人都听到过不止一回,这句话成了王副县长的口头禅。
庄永臣倒霉就倒在他比别人知道的多,或者是别人其实也知道但是人家不说。有一天几个科员私下里聊天,聊着聊着庄永臣不知怎么竟开始评判王副县长这句“七月流火”。他说王副县长这是用词不当,“七月流火”不是用来形容天热的,相反,这个词语要说明的是天气将要转凉。这是出自《诗经》里一首诗《七月》里的一句,全句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流火”的“火”并不是火焰的“火”,而是指火星……
是庄永臣过于大意了,他以为这种私下里的闲聊不会被王副县长知晓。谁料过了两天,王副县长居然在办公室里毫没来由地拍着庄永臣的肩膀说了句:“小伙子,有学问!好,好!”
说得大家都发愣,王副县长却不明不白地走开了,庄永臣浑然摸不着头脑。直到过了一个多星期,他猛然意识到王副县长已经好几天不说“七月流火”了,庄永臣霎时出了一身冷汗。
但这件事无可挽回了,它的负面影响很快凸现,一个月后有一件下乡工作,本该是别人的事,却派了庄永臣去。一去三个月,等到他完成了任务回来,与他同时分到政府办的刘全提为了科长,而在此之前这个科长的位子几乎被大家公认非庄永臣莫属。
这件事对庄永臣的教训极为深刻,他变得处处小心翼翼。“七月流火”之后庄永臣趴了四五年,与他前后分到政府办的几个人都提了科长,庄永臣却还是个小科员。直到王副县长退二线了,庄永臣才有了第二次提科长的机会。刘全提了副主任,科长的位子有了一个空缺,这回轮也该轮到庄永臣了。可就在领导们开会确定这个科长人选的前两天,庄永臣上厕所,怎么那么巧,竟遇上了新来的周副县长。庄永臣走进厕所时,周副县长已经站在小便池前有半分钟了,但还没有尿出来。因为周副县长有前列腺增生,尿等待,每次小便都费时颇长。庄永臣走上小便池,与周副县长恭敬地打了招呼,说了声:“周县长您好。”因为彼此不熟悉,也没多说别的。
庄永臣本想尿完就走,可他由于紧张,却像周副县长一样尿不出来了。两个人托着手里的东西,在小便池上比画着,一分钟过去了,却谁都没弄出一点儿动静,场面就显得有些尴尬。庄永臣汗都下来了,他意识到这样子很不好,副县长也许会不高兴,可他越是紧张越是尿不出来。两分钟过去了,两个人还在小便池上干着,此时庄永臣连哭的心都有了。副县长恼怒了,他显然也受了庄永臣的影响,平时他虽然有尿等待,可两分钟时间总够了。这尿等待本来就常让副县长尴尬,没想到今天竟在这小科员面前丢丑,可气的是他竟然就跟自己这样比着,丝毫不知进退。
周副县长好容易尿出来了,尿得淋淋漓漓迁延无力,一点儿不具副县长的风采。周副县长显然是不愿这样的情形在下属面前出现的,尿完走下便池时,他硬硬地看了庄永臣一眼。
副县长走了,庄永臣的尿却哗的一下就出来了,他气得狠狠地抽了那东西一巴掌。
就这一次,庄永臣落下一个毛病,以后只要跟副县长以上级别的人一块儿撒尿,他就怎么也撒不出来。从厕所出来,庄永臣后悔地想,他当时发现自己尿不出来时就应该灵机一动不尿了,及时退出,把撒尿的空间让给副县长,也许就不致惹恼副县长。可话又说回来,他那时紧张得连尿都撒不出来,大脑短路,又怎么会灵机一动呢?
这一次的科长庄永臣又没有提成,据说在讨论庄永臣的科长人选时,周副县长说了句“这人干不了正事”。
从此以后,庄永臣在仕途上一蹶不振。
等到命运多舛的庄永臣终于熬上了科长,他已是三十五岁。在行政部门,这样的年龄才当上股级科长,前途基本上无望了。在政府办,除了正主任马明,其余人都远比他年轻。当年与庄永臣同时进政府办的几个同事都弄个镇长局长什么的干干了,刘全已是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就连一个什么也不会干只会冲着领导媚笑的女的都当上了工会主席,工会主席虽然没用,但那是正经八百的正科级。
正副县长换了两三茬,现任的八个副县长有四个比庄永臣年岁小,庄永臣在政府办颇有了遗老的味道。这倒是有个好处,就是平时政府办的一些繁重的具体事务不再派他,有年轻人好使呢。如今早已有好几个笔杆子成长起来,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不着他了。因此庄永臣日子过得挺轻松,不像那些年轻同事那样紧张有压力。
可越是这样庄永臣越觉落魄,在行政部门混最怕的就是被闲置,那等于前途被空白。
庄永臣在锅炉房打好了两瓶水,拎回办公室,却见王芳已经到了。这有些不寻常,王芳通常都是在他打完了水之后才到。
王芳在拖地,显得比较兴奋,同时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果然,王芳拖完了地,随手关好办公室门,在庄永臣对面坐定。她用一分钟矜持了一下情绪,然后探过身来,压低声音,说:“庄科长,您听说了没?李主任要到司法局当局长了。”
“不可能吧?他一个学中文的,又不懂法律。”庄永臣对这消息有点儿漫不经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王芳脸上。那张脸干净鲜亮,闪着青春的光泽,让庄永臣心里感到舒适。
“怎么不可能?听说他有亲戚在市委给他使劲。”
“哼!”庄永臣相信了王芳的消息,但他气愤了。
“您应该高兴啊。”王芳见他这样子,小声说。
“人家升官发财,我高什么兴我?”
“李主任走了,这副主任就有了空缺了呀,您想啊,这一次是非您莫属呀!”王芳说。
庄永臣眼前一亮,对呀,这么明显的道理刚才他竟没有意识到,还要王芳来提醒,他真是让这么多年的挫折给委顿了。此时他也明白王芳兴奋的原因了:如果他提了副主任,王芳多半就能提科长。
可庄永臣又很快泄了气,这么多年,哪次不是非他莫属?可哪次也没属他。“唉,我哪有那好运气呢?”
王芳理解庄永臣的心情,说:“不能总是这么不公平吧。我看新来的赵县长是个正直的人,也欣赏您,上次您写的那材料,不是还受到他表扬了吗?说您的文笔不枯燥,有新意。您的文笔呀,就是比那帮人强!”
“要说文笔,我还真是谁也不怵,有的人啊,连话都说不顺溜,除了会喝酒,什么都不行,可人家照样升官!”

■美术作品:Lucian Freud
“就是,不公平。您这么多年,论能力、论资历、论贡献,谁能和您比呀?”
“唉,不提这些了,没用,这些在领导眼里都没用。我就等着混个退休了,现在五十就能退,我还有十年就行了我。”
“可我觉得,您不能松劲,以您的能力,先提了副主任,再到一个局当个局长,顺理成章。”
“我不做妄想哇。不过,小王,我要是提了副主任,咱第九科的科长就是你的!我——这虽然不是我说了算,但我有推荐权,到时候我及时推荐你,你在领导眼里的印象又一向很好。”
王芳低了头,不好意思地说:“我倒不在乎当不当科长,但您对我好我知道。”
这个上午没有事,庄永臣和王芳这样的对话就进行了一上午,两人一同走出办公室,都感觉比平时热络得多。说着说着庄永臣冒了句:“这天气热起来了。”
王芳说:“是呀,马上就是夏天了呢。”
庄永臣咽了咽唾沫,差点儿就说出来:“你该穿裙子了。”
王芳的消息在一星期后得到了证实,李副主任果然调到司法局当了局长。政府办副主任的位置再一次有了空缺,而这个空缺又在向庄永臣招手。
按照惯例,人事上虽然有了空缺,但领导不会马上就设法来填补,总要把这位置悬上一段时间,以便考察合适的人选。即便有了合适的人选,也要考察一下大家的耐心。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阶段,也许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意外的结果,诸如“七月流火”和“尿等待”这样的小事都会影响你一生的前程。庄永臣对此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他从李副主任调出的当天起,就比往常加了更多的小心。
庄永臣比任何人都更加认真地对待当前形势,他时刻告诫自己千万别出错,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在这种时候有没有成绩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别出错。他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是少干事少见人,少干事出错的几率就小,如果能够不干事,那就肯定功成名就了。少见人也是为了减少意外,这是庄永臣自己的教训,也是一个在仕途上混了好多年的老朋友给他的忠告。为此,庄永臣这些日子整天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下了班则关在家里不出来。为了少见人,他每天比过去提前了二十分钟到单位,以避免在楼道里遇见更多的人,为了避免在打水时碰见人,他谎称自己胳膊疼,把打水的任务交给了王芳。
庄永臣为了谨慎起见,甚至临时改掉了用王芳杯子喝水的习惯。
王芳终于在一天下午穿上了裙子,裸露出的小腿和手臂细腻白净,把屋子都照亮了。庄永臣感觉兴奋得很,心里像蠕动着一只肉虫子,有一种想跟谁做做爱的欲望。
赵县长对庄永臣确实是欣赏的,这天赵县长竟召见了他。
赵县长召见他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让他帮忙办一件很小的私事——请他翻翻书找一首咏鸡的古诗,要有点儿寓意不落俗套,再顺便找一个搞书法的人给写出来。赵县长解释道:“送一个朋友过生日。”
庄永臣从县长屋里出来,在楼道里碰上了马主任。这家伙显然是有意在等他呢,但却装成漫不经心地问:“老庄,县长给派任务了?”
一向在马主任面前很无能的庄永臣吐出了两个字:“没有。”
马主任不便多问,变得灰头土脸,讪讪地后退半步。
庄永臣也不多说,从马主任面前走过去,他心里想:你他妈的一向压制我,我还想你对我怎么着我?
庄永臣走出了半个楼道,马主任忽然从后面小跑着追上来,叫住他,有些讨好地小声说:“老庄,这两天有个大材料,还得你来弄,别人,没你这笔力!”
这要在平时,庄永臣得受宠若惊,可这次,他很冷静:“主任,那是不是过几天再说,我现在手头……”他沉下了不说。
“那是那是,你先办你的事。”
庄永臣感到扬眉吐气,回到办公室,意气风发。王芳正慵懒地趴在桌上发呆,一见庄永臣回来,立刻来了精神,迫不及待地问他:“庄科长,县长是不是找您谈话?”
庄永臣知道她说的谈话指的是啥,笑着说:“哪有这么快。赵县长是跟我说别的事。”
“啥事?”
“保密。”庄永臣觉得这事对王芳也不能说,不能大意。
“哼,对我还保密!”王芳扭了两下脖子,扬起了下巴。
庄永臣像电影上从事保密工作的革命者对待自己人那样说:“不要多问了,反正是好事。”
晚饭时庄永臣喝了一盅酒,他酒量不大,一盅足矣。借着酒劲,就寝后又跟老婆做了一次爱,之后,他还不想睡,又把今天得到赵县长召见的过程对着黑暗中的老婆叙述了一番。他兴奋得很,直到今天他才对这次提副主任的机会有了实在的信心。
老婆却没有政治敏感性,咕咕哝哝地说:“看把你美的,人家县长让你办了这么一丁点儿小事,能说明什么?能因为你为县长出这么点儿力就把主任给你?哪有这么便宜!”
庄永臣说:“这你就不懂了,县长要我替他办的事情虽小,但它表明了县长对我的信任。这件事谁都能办,为什么偏偏用我?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不是我要凭给县长办事来当什么副主任,而是以我的资历能力都应该来当这个副主任。可我以前为什么当不上?是因为领导不喜欢不信任我。现在赵县长信任我,我于是有希望!”
老婆方才明白此事的重要意义,嘱咐一句:“那你可要好好办这件事,一定要办好!”
“当然,我决不会掉以轻心。对了——”庄永臣忽然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你可记住,千万对谁也不要透露我为赵县长办的这件事情,一个字也不能露!”
“为什么?这又不是什么贪污腐败,就为县长办这么一件小事还怕别人知道?这都什么时代了,你太小心了吧你?你看看人家都怎么跑官的!”
“这事不怕别人知道,可是却怕赵县长知道。”
“咋?不是赵县长让你办的事嘛,怎么还怕赵县长知道?你把我说糊涂了都。”
“你懂什么?是这样,我怕的是赵县长从别人嘴里听到我在替他办事,那赵县长就会认为是我在把这事到处张扬,在利用给他办事拉大旗做虎皮,就会对我产生很坏的印象啊!现在坏人太多了,要严防别有用心的小人。”
老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咱可要严守机密,把事情办得神不知鬼不觉!”
老婆睡着了,庄永臣却又为此事分析了一夜,他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这次是真的抓住了机遇,他一定要把文章做足。经过更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虽然他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为赵县长办的这件事,但他却应该借机让别人知道赵县长对他的信任,这样才会更有利。他想,这事还真得运用点儿谋略。
第二天,庄永臣找到马主任请了两天假,说要去一趟省城。马主任问他有什么事,庄永臣平生第一次以沉默的方式来回答了主任的问话。
马主任没想到庄永臣居然敢不回他的话,他盯了庄永臣几秒钟,却软了下去,说了声:“那就去吧。”他联想到了昨天赵县长召见庄永臣的事,隐约感到庄永臣去省城与这有着某种联系。
庄永臣从马主任屋里出来,暗自得意。达到目的了,马主任这个老狐狸会意识到他在为赵县长办事,但只要不知道具体办的是什么事,就没法散布流言,也没法在赵县长面前搬弄是非。这老家伙会老实几天了。
赵县长交代庄永臣办的事情看上去虽小,却并不容易。你想啊,写龙写虎好入笔,写马写牛也容易,或高腾行天或威风八面或前程万里,顶不济还可以“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可这写鸡,要“有点儿寓意不落俗套”,何其难也。而庄永臣是立志要把这事做好的,决不能应付了事。于是他去了省城,到自己的大学母校,拜访当年的老师,求老师帮他在学校图书馆翻了一天古籍,总共找到了二十八首咏鸡的古诗。最终,老师从里面选择了一首符合赵县长心意的《咏鸡》,写的是:武距文冠五色翎,一声啼散满天星。铜壶玉漏金门下,多少王侯勒马听。
端的一首好诗也!
庄永臣一见此诗,双目放光,知道此事大功告成了。
庄永臣捏着录下了这首诗的一张纸片,又找到自己在省文联的同学,请同学帮自己求了省文联的一位书法家把诗写成了书法条幅。
回来后,庄永臣把条幅急急送到一家装裱店装裱,恨不得立即呈到赵县长手里。可店家告诉他,装裱一幅字画至少要一星期时间。庄永臣只得耐心地等待。
与庄永臣设想的一样,他走后马主任就来王芳这儿刺探情报。王芳对他去省城的事一无所知,主任一问,王芳很诧异。但这样一来就使此事变得更为神秘,也给了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通过主任和王芳的嘴,不少人都知道了庄永臣在为赵县长办事,但都属瞎猜,谁也不敢多问。
从省城回来以后,庄永臣感觉到同事看他的眼神以及与他说话的语气都有了微妙的变化。大家的眼睛都盯在了庄永臣身上,谁都认为这个副主任这一次不会再是别人的了。当然大家也都认可这种结果,确实,如果再不提庄永臣,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大家虽然认为庄永臣很没用,但对他的才华还是能达成共识的。有些行动惯于超前的人,几乎就是已经在把他当作一个副主任来对待了。与孙国起再走碰面时,孙国起不再叫他“老庄”,而是又像当初一样尊敬地叫他“庄科长”了。
那幅《咏鸡》装裱出来,庄永臣瞅个没人的空子给赵县长送了去。赵县长一看那上面的字就知道非一般人所为,看着落款问是什么人。庄永臣如实回答是省城的书法家,赵县长埋怨庄永臣道:“这么点儿小事,你费这么大心干吗。”
庄永臣赶紧表示说不费心,自己的同学与这书法家是同事。
赵县长高兴起来,读了上面的诗,越发喜欢,不禁小声诵了一遍,连声道:“好,好!”又转过脸对庄永臣说,他要这东西是要送给一个老领导。老领导一生清正,现已退休,因他属鸡,所以才要庄永臣找咏鸡的诗。没想到居然找到了这样一首好诗,老领导一定非常喜欢。
赵县长诚心诚意地对庄永臣表示了感谢,庄永臣激动得满眼泪花。
可是到了晚上,庄永臣兴奋地给自己的老师打电话,汇报说这首咏鸡诗县长非常喜欢,老师在电话那头惊诧地问:“你说这首诗是送给了什么人?”
“县长啊,我们县长。”
老师说:“你当时只跟我说是送人,却没说送什么县长。”
庄永臣说:“当时时间紧,没跟您细说。”实际上是当时他考虑老师平生最讨厌官员,怕说了老师不肯帮忙。
老师说:“可是这首诗,送什么人都可以,唯有送一个官员不太合适。”
庄永臣紧张了:“怎么啦?”
“你没看出来吗?那首诗的最后一句‘多少王侯勒马听’,隐含有小觑王侯之意呀!你把它送给官员,怕会惹人家不高兴的。”
庄永臣双腿一软,放下电话“啪”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
第二天早上,庄永臣战战兢兢来到单位,他的情绪非常沮丧,一直坐在座位上发呆。王芳看出了异常,关心地问:“庄科长,您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陪您去医院。”
温声软语的关怀就像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庄永臣内心的苦水顿时翻涌,他像一个长期被人压迫欺辱的孩子一样诉说起来:“王芳,我真是命苦哇,真是命苦哇,怎么什么事情一到了我身上就这样糟糕呢?我知道千万别出错,千万别出错,可终归还是出了错,还是出了错……”
王芳听得一头雾水,“庄科长您说什么呀?出了什么错?这些天不是好好的吗?大家都认为您这一次肯定了,难道又有了什么变故?”
庄永臣猛醒,意识到这是千万不能跟王芳说的。他立即收敛自己的情绪,慌乱地用手抹了把脸,强自一笑,对王芳说:“哦,不,不是,我说的不是指单位的事,是,是家里的事,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王芳狐疑地望着庄永臣的脸,“您跟夫人闹别扭了吗?”
“嗯,没什么没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庄永臣不置可否,此时他愿意王芳往这方面联想。
王芳忽然没心没肺地咯咯笑起来:“我知道了,一定是您这次去省城见到女同学了,哇,科长有艳遇了耶!是不是夫人在跟您闹离婚呀?要我说,这不是什么坏事。”
庄永臣又一次慌了神,要知道在仕途上这样的新闻同样可怕,它的危害甚至会比“七月流火”和“尿等待”更大,他赶紧摇着手制止王芳:“住嘴,住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王芳掩嘴而笑。
庄永臣面色严峻起来,郑重地说:“小王,我要求你,我严肃地要求你,可千万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你年轻,不懂得这里面的利害,这话要让别人听去,我可能就真的完了。刚才的话你可千万一个字也不要对别人讲,开玩笑也不行!这种事真假难辨,人们最爱捕风捉影,要是被小人利用,弄假成真……”
王芳听懂了此事的利害,变了脸色,说:“庄科长,我明白了,您放心,我对谁也不会说的,我一定替您严格保密。今后,我再也不会开这样的玩笑。”
庄永臣点点头,对王芳的态度表示满意,愣了几秒钟,又冤枉地说了句:“你这么一保证,倒像那事是真的似的,唉,我哪有那好运气呀。”
从这天起,庄永臣开始了好长一段时间忐忑的日子。他不知道赵县长是否看出了那首咏鸡诗里的深意,如果看出来,那他肯定又完了。这些日子里,他最想见的人就是赵县长,他想从赵县长的脸上、从赵县长对待他的态度上,判断出赵县长是否对他有了芥蒂。他甚至幻想赵县长再有一个老领导过生日,再来让他去找一首诗,要是那样就表明万事大吉了。可偏偏他好长时间也没碰见赵县长,赵县长也没有老领导再过生日。
庄永臣日夜忧患,人也消瘦,神也销蚀。他连对王芳都不再有兴趣了,随着夏天的燠热,王芳换上了一条裙摆刚刚扫到膝盖的短裙子,更为彰显女性身体的动人之处。可庄永臣对此却几乎视而不见,至少是无动于衷。
希望的曙光再现于一个雨后的早晨。这个早晨,庄永臣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却仍心情郁闷地来到单位,马主任急急地把他找了去,向他布置一项任务。省人大要来一个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基层实施情况的调查团,赵县长指定由九科负责接待任务,并由庄永臣负责写出汇报材料。马主任又有点儿不情愿地说,让庄永臣去赵县长办公室一趟,赵县长要当面给他交代这个汇报材料的调子。
庄永臣的心怦怦跳着,他双脚发软,像踩着棉花似地下了楼梯。从四楼来到二楼赵县长的办公室,轻轻敲门,战战兢兢进门。赵县长正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一见庄永臣进来,热情地微笑着打招呼:“庄科长,来来,坐坐。”
庄永臣不敢坐,怯怯地观察赵县长的眼神。他的心跳渐渐平缓,赵县长看他的眼神是明亮的信任的,看来赵县长并没有看出那首《咏鸡》的破绽,庄永臣的心放了下来。他偷偷地想,这些日子的紧张实在是有点儿风声鹤唳了。本来嘛,就是他这个中文系的高才生当初也没有看出那一层深意,别人更不大可能看出来了呀。
赵县长对庄永臣交代完写这个汇报材料的原则和一些注意事项,最后意味深长地叮嘱了一句:“庄科长,你一定要把这项任务完成好哇。”
庄永臣听得出赵县长话中的含义,他拼命点着头。
以往像这样接待省级来团的准备工作,至少应该是由一位副主任担当,现在让庄永臣牵头来做,足见对他的重用。庄永臣兴奋极了,一星期的准备时间,忙得马不停蹄。先是调查摸底,然后按领导写的调子将实际情况进行取舍加工,最后写成汇报材料。赵县长看了材料很满意。王芳也很兴奋,跟在庄永臣屁股后面干这干那。一向不被重视的第九科这一次显出了水平,这种平时需要四五个人完成的准备工作,两个人做得井井有条。调查团到来的前一天,庄永臣和王芳布置会议室,挂完了会标,扶正了桌椅,摆好了话筒,按级别高低放齐了写着与会者姓名的座次牌,这才算完成了最后一项的准备工作。已到下班时间,王芳走了,庄永臣却兴奋得不想走。他坐在会议室的主席台上,俯视着台下整齐的桌椅,忽然来了灵感。他把嘴凑到话筒上,“呼呼”吹两下,模仿一位他最佩服的领导的仪态,端正好坐姿,威严地望着台下,清了清嗓子:“吭,吭!同志们,开会了,开会了——”
浑厚的颇带领导风范的男中音,借了话筒的放大作用在会议室里盘旋回荡,让庄永臣心中充满了志得意满。
“吭,吭!同志们,开会了,开会了——”庄永臣把声音加大,又模仿一遍。为了声音不传出会议室之外,他把话筒的音量调小,这样就可以放开自己的声音了。
“同志们,开会了,开会了——”
终于找到当领导的感觉了,这天庄永臣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对着话筒不知把这句话说了多少遍,像幼童玩味一个简单重复的游戏,乐此不疲。
第二天调查团到来,先开了见面会,庄永臣的汇报材料让调查团很满意。接下来由他和王芳带着调查团去下面实地考察,都是事先已做好的安排,因此进行得十分顺利圆满。送走了考察团,赵县长当众对庄永臣和王芳做了口头表扬。谁都知道庄永臣提副主任是指日可待了。
不久以后的一天,王芳十分神秘地悄悄告诉庄永臣,他提副主任的材料已经报送到组织部待批了,剩下的事就等着领导谈话吧。
庄永臣还有点儿不敢相信,他知道这种组织程序是严格保密的,王芳怎么知道?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颤着声质疑王芳消息的可靠性。王芳做了解释,组织部干部组里有她一个同学。庄永臣才相信了王芳的话,他激动得端杯子的手都哆嗦了,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但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淌了下来。
庄永臣的表现让王芳始料不及,她能预想到他会高兴、会兴奋、会笑、会跳起来,甚至会高歌,可就是没想到他会哭。她知道他这是喜极而泣,那是激动的泪水,可她还是感到措手不及,一时不知道是该劝庄永臣别哭别哭,还是像鼓励一个人放声高歌一样鼓励他放声而哭。
庄永臣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放下杯子,用手掌胡乱擦着脸上的泪水,想自嘲地说句什么,可发出的声音也满是哭腔:“王芳,你看我,真,真,真……”他想说“真没出息”。
但王芳机灵地截住了他的话:“庄科长,您是真高兴了。”
“是啊,是啊,王芳,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消息。”
“以后呀,我还要您处处多关照呢。”
“一定,一定,不用你说,王芳,那是一定的。”
庄永臣非常感激地望着给他带来这好消息的王芳。
今天县委组织部要来宣布干部任命。
整个上午,庄永臣都在捧着一份中央文件认真学习,与王芳说的话也少了。王芳没人说话,显得无所事事,索性也拿了一份文件学习。可她看不进去,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她怨怼地看了庄永臣一眼,不明白他何以对一份中央文件这么有兴趣。其实庄永臣并不是对文件有兴趣,他只是心里在哆嗦。他紧张得好像大脑短了路,一会儿想发笑,一会儿又想流眼泪,一不留神还差点儿发出呻吟。他怕王芳察觉他的失态,所以捧一份文件做掩护。
庄永臣在努力喝水,不敢看王芳,当水终于再也喝不下时,时间很难熬。庄永臣想不能再这样,要让自己这紧张的状态轻松起来才行,必须开口说话,要找一个话题,找什么话题呢?情急之下他瞥见了窗角上的蜘蛛茧,此时此刻说蜘蛛的话题虽然没有意义,可总比没有话说要好。
庄永臣把遮在脸上的中央文件往右边一挪,露出半个脸,用中等音量的声音说:“咱们屋里有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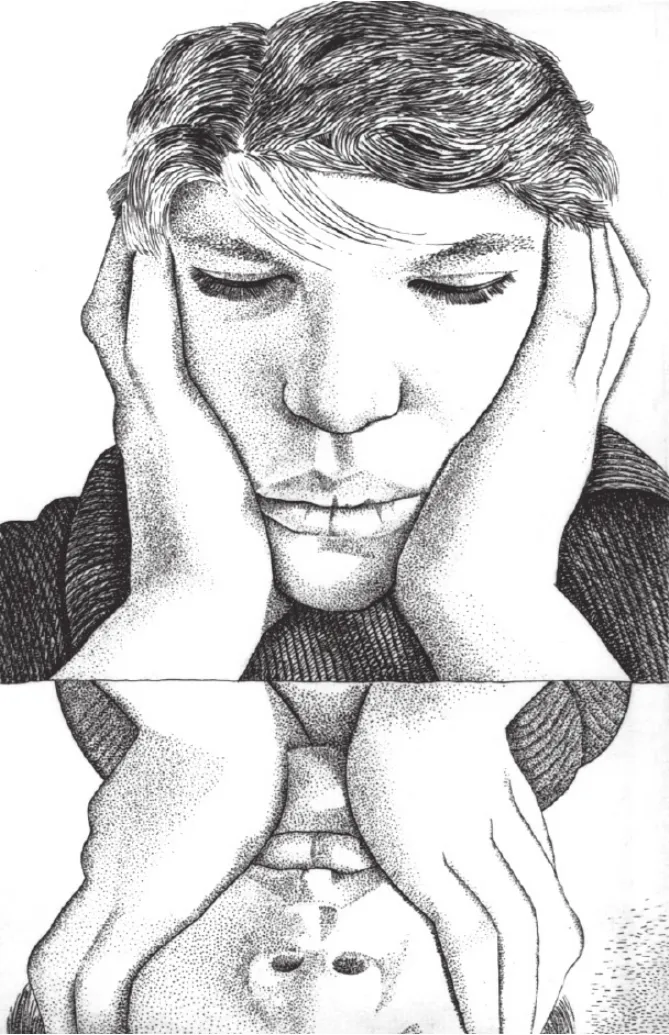
■美术作品:Lucian Freud
王芳没想到他看着书会突然说话,吓了一跳,没听清他说什么,她望着他。庄永臣重复了一句:“咱们屋里有蜘蛛。”
“哦,”王芳一时不明白庄永臣为什么说起了蜘蛛,她还以为有什么特殊意义,她疑惑地答了言,“不会吧?”
“会的,就是有蜘蛛。”庄永臣紧绷的心情放松了。
“哪里有?我怎么没有见过?”
“我也没有见过,但我知道有。”
王芳不由得露出了笑意:“您也没见过,怎么就知道有?”
“看那儿,”庄永臣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拧转身,伸手指向窗子的右上方,“因为有蜘蛛茧!”
“蜘蛛茧?在哪里?”
“那里,那里,王芳你看,就在那里。”
王芳顺着庄永臣的手势望去,果然看到了那个蜘蛛茧。“真的耶,真的是蜘蛛茧。”
“我早就发现它啦!”庄永臣兴奋地说。
“那您怎么没有摘掉它?难看死了。”
“那地方又没人注意,难看不难看没有关系。而且,我当时想,那里面包裹着小生命呢,我不忍杀生呀。”
“哇,会生出小蜘蛛的呀,好可怕!”王芳好像打了个冷战,仿佛那茧里已经爬出了密密麻麻的小蜘蛛。
“你害怕蜘蛛?”庄永臣问。
王芳横了他一眼:“女孩子谁不怕蜘蛛?”
庄永臣说:“那我把它摘下来吧。”说着就要行动。
王芳目测了蜘蛛茧的位置,知道摘掉它并不十分容易。她此时不愿意庄永臣爬上爬下地闹出过多的动静,况且那蜘蛛茧也没有迫切地马上就要生出小蜘蛛。她就制止了庄永臣,说:“先别弄了,不急。”
庄永臣此时听话顺从,于是作罢,说了句:“也对,今天,万一让领导看见了不好。等我闲着没事时再弄吧。”
挨到了上午十点,组织部的人终于来了,对庄永臣的任命终于正式宣布了。仪式简短而庄重,召集政府办公室全体人员在小会议室开了个会,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到会宣读任命,完成了最后一项组织程序。从这一时刻起,庄永臣就真的成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了。
大家都向庄永臣表示了祝贺,回到科里,庄永臣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私人的物品要带走,工作的事项要移交,杂七杂八,虽然李主任的屋子还没有腾空,他要想搬过去还要等待几天,但他现在就坐不住了。
王芳帮着忙。
“庄主任,您走了,我真不知道工作该怎么干,以后您可要多指教我。”
“那是一定,有什么问题你找我。科长的事先别急,总要等一等的,过些天就会有结果。你好好干,会有更大的前途。”
王芳答应道:“嗯。”
两天后的晚上,庄永臣请客,宴请政府办全体人员,高兴,热闹。庄永臣意气风发,逐一敬酒,大家由衷与不由衷地叫着“庄主任”,回敬着他,每个人都喝得尽兴,庄永臣更是喝得醉醺醺。
酒席散了,庄永臣回到单位,今天该他值班。
庄永臣从没喝过这么多酒,头昏沉得厉害,意识混沌,困意很浓,却又睡不着。政府大楼前面的消夏广场上,聚满了热闹的人们,有的在跳舞、有的在纳凉。舞曲音乐清晰地传来,平时庄永臣是很烦这吵人的音乐的,但今天他觉得它很悠扬、很动听。
他躺在床上,闭了灯,觉得有些飘飘然。外面很热闹,大楼里却寂静得很,另两个值班人员到三楼马主任屋里打牌去了。
身上热得很,庄永臣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他还感到了一点儿欲望,他躺不住了,晕乎乎地爬起身,脱下了内裤,让自己一丝不挂下了床,黑暗中走到王芳的座位上坐下来。
他趴在王芳的桌子上,嗅嗅王芳留下的气味,扭扭屁股,让皮肤最大限度地接触王芳坐过的椅面,这种接触让他的两腿间有一种满足感。这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值夜班时光着屁股坐王芳的椅子,让自己的光屁股接触王芳每天用臀部使用的椅子,能激发他更多的有关王芳的想象。
王芳这个小姑娘,真是很迷人啊,以后自己当了副主任,可要处处照顾她,对她好一些,说不定还能……
庄永臣晕晕乎乎的,思路散漫、飘动,有时像梦里,有时像现实。
他忽然想到了那个蜘蛛茧,那个织在窗角的蜘蛛茧。思路一动,他要把它摘下来。他曾经想过摘掉它,他也曾对里面的小蜘蛛产生过恻隐之心,但他现在不再动这样的凡心。
他明天就要搬走了,搬进副主任办公室。他不想在走后对这间办公室留有邋遢的记忆,他要意气风发地搬走。
何况王芳怕蜘蛛,他也答应了要为她把蜘蛛茧摘掉。他得在临走前做好这件事。
这样想着,庄永臣就从王芳的椅子上起来,走到床边。他得先站到床上,再从床上爬到窗台上,才能摘得到那个蜘蛛茧。爬窗台时,因为看不大清,他回身顺手打开了墙上的电灯开关。
庄永臣爬上了窗台,伸直手臂去摘蜘蛛茧。但他高估了自己的高度,或者是低估了蜘蛛茧的高度,反正是他伸直了手臂却还差一点点才够得着蜘蛛茧。
庄永臣踮起了脚尖,将身体尽最大努力地伸展。终于可以了,他的中指和食指的指尖能够触到蜘蛛茧了,他于是用指尖一下一下地抠。
应该是抠上四五下就能抠掉的,但他大约是在抠到第三下时,感觉到了一些异常。外面政府大楼对面的消夏广场上,乱哄哄的声音忽然好像被什么东西放大了。
庄永臣就着窗子向外望去,看见对面广场上的人们好像在聚拢,乘凉的不再乘凉,跳舞的不再跳舞。连政府大楼里的保安都跑了出来,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在争着看热闹,还有不少人在指指点点。
初时庄永臣并没有想到外面的异常情形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他还停了抠蜘蛛茧的动作也往外面张望。但几秒钟后,他发现人们指点的好像就是他这里的方向,他下意识地一低头,猛然发觉了自己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庄永臣脑袋里“轰”的一声,从窗子上掉了下来。
当然庄永臣是掉在了窗子里面,不是掉到窗外去,没有什么危险。
但庄永臣彻底地蒙了,他感到整个大楼都在坍塌,包括他仕途的大厦。他的眼前以及头脑里是一片无边的黑暗,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只有几个字眼像火花一样清晰地蹦出来:完了,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条怪诞的新闻通过广场消夏的人们的嘴,像炸了窝的马蜂,迅疾传遍全城——
昨天晚上,政府大楼里有人,据说还是个副主任,光着屁股跳上了窗子,对着广场上的人们跳舞!
留在人们印象里的庄永臣的形象是这样的:他以最大幅度伸展着身体,一只手臂上扬,奔放地指向右上方的某个目标,另一只手臂则为保持平衡而向身体的另一侧努力展开,那姿势,确实像是在热情地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