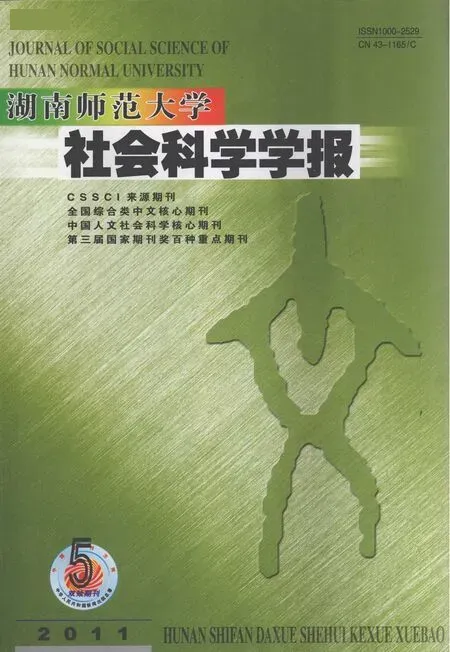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生产与社会变迁
2011-04-13吴果中
吴果中,汤 维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生产与社会变迁
吴果中,汤 维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舆论监督的话语演变是中国新闻改革及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考量。它是如何随社会变迁而形成特有的话语实践?它如何反映并建构了中国社会变迁过程和社会结构?这种话语生产如何呈现出中国新闻改革中社会化、历史化、制度化形构的各种矛盾和张力?通过对舆论监督的话语生产进行了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从官方话语形态到知识话语形态的转变。在“民意”与“官意”的结合话语空间,舆论监督实现了党政行政权力的延伸和补充。
舆论监督;话语生产;社会变迁
引 言
福柯的早期考古学研究中谈到,话语是建构性的,是从各个方面积极建造或积极构筑社会的过程:话语构建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福柯还认为一个社会或一个机构的话语实践是相互依赖的:文本总是利用和改变其他同时代的以及历史上已有的文本(即文本的“互文性”〔interextuality〕),而任何特定类型的话语实践都产生于与其他话语实践的结合,并受到它与其他话语实践关系的限制[1](P38)。在福柯看来,不同的话语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这种社会—理论意义的话语分析,经由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的开拓,将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两方面的内容连接起来,认为构成了话语与社会变迁关系话题的深刻探讨。在这两位学者的启发下,笔者试图以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基础,运用话语分析和社会政治思想相结合的框架,在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下分析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演变轨迹及其对社会制度的形构,表明舆论监督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如何建立国家与传媒的正当性协商。
在笔者看来,舆论监督话语生产的研究路径一般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话语的“客体”——舆论监督的产生、变化和再生产研究。因为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formations)的产物,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因此,“任何语言系统所能产生的、潜在的无限意义,总是遍布于特定时空并且本身也经由不同话语而得以呈现的社会关系之结构所限定所固定。”[2](P85)社会关系结构制约着话语结构,话语的“客体”是根据“某些特定的话语结构在话语中被构成的、被改变的,而不是独立存在于某个特定的话语中,也不是在某个独立的话语中被简单地涉及或谈论的东西”[1](P39)。那么,作为话语“客体”,中国舆论监督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舆论监督的主客体如何发生变化?舆论监督预期目的、操作方式和实际效果如何因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变更?第二,舆论监督的话语形态变迁。从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以“舆论监督”为目的生产的媒介产品来看,它们如何呈现了官方话语形态、知识话语形态等。第三,对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解释与分析。即大众媒介建构的文本如何体现政治权力拥有者与传媒实践者之间充满张力的合作。对于第一种研究路径的分析,已在拙文《中国舆论监督话语生产的历史演变》[3]中得以完成,在此不再赘述。
作为话语实践的舆论监督
知识政治学的观点认为,政治巩固的持久力量不是政权本身,而是由此形成的多元化知识。舆论监督的话语实践是一种知识文本被生产、分配的过程,又包含着文本如何转化为知识领域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从而影响政治形态和社会变迁。如何论述舆论监督话语实践的知识社会化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社会性的,都需要关联到话语从中得以产生的特殊的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1](P66)具体说来,大众媒介进行舆论监督的话语生产时,面对不同的知识形态,在叙述框架、内容选择、信息来源、逻辑分析核心术语等方面体现出固有的概念与逻辑以及不同的话语取向,从而构建不同的话语形态。
1.“文人论政”的知识分子话语实践
与西方报刊的“看门狗”(watchdog)作用不一样,中国舆论监督的最初形态是“文人论政”,即一批儒家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自办报刊,以报刊论证报国救国。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时报》,胡适派学人群的《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到陈独秀等的《新青年》、新记《大公报》、储安平的《观察》等等,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外国列强的入侵,民初的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等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社会背景,它们大量刊载了以救亡图存为主脉,以启蒙、革命、现代化为关键词汇,以科技传播、政治传播、政论、时评、杂文为主要表达手段的知识信息和言论信息,对民众实施启蒙以摆脱愚昧,对政府传播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以倡导变革图强,在报刊的舆论空间和言论阵地实现报国救国的愿望和政治理想,从而建构起了文人知识分子话语实践的独特体系。
以《大公报》为例。创办人英敛之以报纸是“国民之耳目,社会之回声”[4](P18)为办报理念,认为国民素质与报纸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他说:“近世欧美各国,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莫不设有报馆,为之鼓吹一切,发皇一切。故其国势膨胀,民智开通,殆非我国所能望其项背。”[5](P8)英敛之意识到报纸具有向上和向下两种舆论职能,而实行职能的关键便是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论。于是,《大公报》提出“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的口号,大胆揭露社会不公正现象。据其继承人胡政之回忆:“自清末民初,本报即有敢言之名,慈禧听政,本报曾有归政之主张。洪宪称帝,本报都曾予以指摘。”(《大公园地》1947年8月5日)无论是批判统治者的卖国行径和对革命党人的杀害,还是揭露黑暗官场和官僚专制体系,《大公报》都秉笔直书,毫不留情,始终把“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作为办报宗旨。民国时期,张季鸾等又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简称“四不”)的社训,其主持时期的《大公报》是一个无党派的独立的报纸,从总经理、主笔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不允许参加任何党派和任何社会团体,在国家权力体制外,独立地开展针砭时政、自由议政的舆论监督。
话语是社会变迁的反映和建构。为建构“文人论政”式的舆论监督话语形态,知识分子一方面按照自由、民主的理念,传播启蒙、革命的话语意义;另一方面,会随历史语境的变更调整自己的话语框架和叙事方式,以便客观地反映历史。拿《大公报》从1902年至1925年对孙中山的报道来说,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大公报》称其为“康梁孙文”、“革命党孙文”、、“逆匪孙汶(文)”、“革党领袖孙逸仙”,甚至将其革命同志称为“孙文之羽党”、“孙逸仙羽党”;而当孙中山辞职后,《大公报》的称呼转为“孙中山先生”、“孙公”、“孙中山君”“中山先生”等,将其革命同志称为“民党”。这种变化,呈现了复杂的政治局势对报人态度的冲击与改变,也蕴含了孙中山及其政党的实力与作为。称呼的改变,以及孙中山事迹在《大公报》版面上的频频出现,建构了孙中山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领袖地位。
“文人论政”的知识分子话语形态,由于标榜独立精神,无党无派,个人主义色彩浓厚,舆论监督话语体系常常分散且脆弱。
2.政经一体化时代的官方话语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state)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co-opt)进了党—国的体制,将他们定位成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6]。中国的舆论监督话语生产成为党和政府权力的组成部分,官方话语形态成为舆论监督话语生产的主要手段,是“由政府控制的,根据当前政策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有管理的舆论监督,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行政/领导监督”[7]。它立志传播承认政府存在的合法化知识,内容选择、符号表述和媒介内部结构都必须服从“命令型新闻体制”的政治规约,党和政府是舆论监督话语表达的主体,党报占据了媒介话语空间的中心地位。这种舆论监督话语实践历经毛泽东时代至改革开放前夕,以“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为典型代表。
3.新闻改革语境下的知识话语实践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计划经济的社会格局,也改变了媒介的生态环境。自此,市场机制进入新闻事业领域,尽管“事业单位”的制度属性没变,但“企业化管理”的经营属性,给媒介带来了相对的自主权,为媒介在官方话语形态之外,建构更多的与政治权利产生张力关系的规范知识,即知识话语形态营造了较大的空间,政治权利拥有者和传媒实践者有可能开展冷静的正当化协商和充满张力的合作。
媒介的知识话语实践主要体现在,自1978年以来的媒介改革实践中,都市报等大众化报纸大量涌现,以关注老百姓的民生新闻为话语对象,以日常生活为叙事基调,构筑民众所需的规范知识,回应社会的多元诉求,打破了党报独占媒介话语一元化的局面。1984年创刊的以舆论监督著称并率先实施异地监督的《南方周末》在90年代后期强化对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同期迅速崛起的时政类新闻周刊也挤入舆论监督队伍。它们更多地使用知识话语形态行使舆论监督。
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中知识话语形态的创建更是如火如荼。1994年4月1日开办了以深度报道为主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焦点访谈》,不仅采用制片人制和招聘制,激发了创作主体的竞争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在节目形态上采用演播室主持和现场采访相结合的结构方式,在“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框架下选题,“用事实说话”,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在官意、民意和媒意的结合部建构了“新公共空间”[7]。1996年5月17日,中国电视调查性报道的领军者《新闻调查》正式播出,选择揭秘性、可调查性的选题,采用“调查性纪录片”的形态、纪实的拍摄方式和故事化的叙事技巧,展现对新闻事件的调查和采访过程,在悬念和冲突中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2009年央视新闻频道改版,探索在目标定位、内容定位、形态定位的栏目体系里探寻贴近民众、民生和民声的路径,建构多元的知识话语体系,渗入到公民生活领域,从而实现对“行政/领导监督”的预防和抵制。
4.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监督话语实践的个人化与日常化
以上诸种机制在互联网语境下和新媒体环境下实现得最为透彻。网络的出现,在技术上完成了舆论监督主体向公众的回归,监督方式全方位化,舆论监督更需要创设多元的知识话语体系。网络媒介的公共性、公开性、迅捷性,无疑极大地挑战了单一官方话语形态的“行政/领导监督”,向知识类型的多元化及相互监视提出了强烈的呼吁并成为可能。同时,借助于互联网等新媒体,越来越多的个人可进行直接的个人表达以实施舆论监督。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的行动者利用结构性的规则和资源,进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积极行动,改变结构,从而推动社会的变迁。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舆论监督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结构化特质,“出现了大批具有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的行动者(agent),他们借助于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规则和资源,将舆论监督日常化和惯例化,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一些制度性关系的初步形成……”[8](P109)他们采用新闻跟帖、论坛发帖和个人博客以及微博等形式披露事实,发表意见,开展批评。更有甚者,他们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议程互动,共同设置舆论话题,推动或引领舆论监督的发展。
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监督的个人化和日常化趋势,创设了多元、复杂的媒介实践表征。如何重构网络舆论监督的媒介话语空间,如何以多元的知识话语形态消解、转换一元化的官方话语形态和制度建构,在多种话语形态整合的基础上实施舆论监督,这是网络媒介提出的尖锐话题。
舆论监督话语生产中的政治含义及意识形态
当对舆论监督文本进行阐释和分析时,舆论监督又成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话语,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在不同社会领域或不同机构背景中,不同类型的话语有可能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介入’(invested)。”[1](P62-63)由此看来,话语与社会体制之间的辨证关系决定了舆论监督的话语生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建构国家—媒介体制。尽管这种反映和建构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曾以“文人论政”和“报刊批评”的形式出现而直至中共十三大才被正名,具有与其他监督并列的身份,但舆论监督话语生产的意义及其对制度产生的影响不会消失,映射了中国社会诸多关系的历史性变迁。通过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实践演变轨迹可以看出:舆论监督在话语形态、主体转换和监督空间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特征:
(1)中国舆论监督话语经过了“文人论政”、“报刊批评”到“舆论监督”正当化的发展变迁,建构了不同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官方话语和知识话语分别占主体的三种话语形态。舆论监督的力度应来源于两方面:“用事实说话”和“对新闻事实进行意义建构式所展现的多元知识类型的话语空间”[9]。
(2)网络发达语境下,媒体舆论监督的独立意识与国家权力出现了正当化协商,并在技术支持下,舆论监督的主体日益转化为公众,媒体代表民众行使监督,舆论监督的话语在实践层面从“一元的党的‘喉舌’意识形态话语”向“多元的作为人民‘公器’意识形态话语”[10]转变,舆论监督对国家权力的干预越来越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民主进程。互联网时代媒体舆论监督话语体系的构建将会再次出现新的转变,舆论监督话语生产与制度建构又将开始新的一轮互动。
[1][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2][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 彬译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吴果中.中国舆论监督话语生产的历史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0,(3):81-83.
[4]英敛之.也是集续编·天津日日新闻三千号祝词[M].天津:天津大公报馆,1910.
[5]英敛之.安蹇斋丛残稿·安蹇斋文钞[M].天津:天津大公报馆,1917.
[6]陆 晔,潘忠党.成名的想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2008,(1):17-59.
[7]景跃进.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J].开放时代,2000,(5):59-68.
[8]许 静.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监督的结构化特征初探[A].巢乃鹏.中国网络传播研究[C].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9]齐爱军.舆论监督的三种话语形态[J].当代传播,2003,(6):53.
[10]雷蔚真,陆 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变迁: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线索[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6):163.
The Discourse Production of Chines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ocial Evolution
WU Guo-zhong,TANG Wei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The evolution of supervision by public is the key in deciding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How does it form the special discourse practi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How does it reflect and construct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How does the production of discourse embody the va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which originate from socialization,historiciz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reform of China News?Through the Foucaultian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on the formation of discourse of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this paper reveals that it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from official discourse to knowledge discourse.At the combination discourse space of“official expected”and“public opinion”,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achieved the extension and supplement for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power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discourse production;social evolution
G219.19
A
1000-2529(2011)05-0131-03
2011-04-18
吴果中(1969-),女,湖南安化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学博士;汤 维(1980-),女,湖南岳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彭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