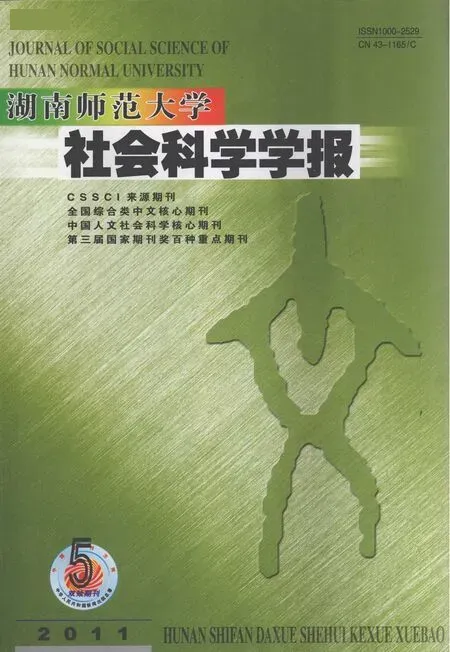辛亥时期胡汉民的排外观
2011-04-13李育民
李育民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辛亥时期胡汉民的排外观
李育民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辛亥时期,胡汉民提出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排外观。他认为,发生排外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汉族的种族思想、清政府实行的内外方针,以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胡汉民主张区分不正当和正当两种不同性质的排外,其判断标准是国际法。他认为正当排外便是主张国家权利,同时又认同合法的主权限制。在他看来,要达到正当排外的目的,其根本之计在于排满革命。胡汉民和革命党人致力于反清革命,而对如何解除帝国主义压迫问题有所忽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胡汉民;排外观;辛亥时期
晚清时期的排外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近代交往制度的引进,这一观念逐渐发生变化,辛亥时期尤为显著。该问题属中外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与革命派所进行的反清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涉及到对外方针和革命的前途。“迩者欧美各国相惊以支那人排外,支那人排外,撷一二事实以为证,而谋对待之策,吾国有志者亦颇怀隐忧焉。此真重大之问题,而与吾人增进世界平和之主义有密切关系者也,故亟论之。”①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骨干,胡汉民对成为清末热议话题的排外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排外观具有时代的特色,反映了革命党人和中国社会对外观念的演化。对此作一探讨,不仅可以深化对革命派的民族主义的认识,且有助于了解中国的对外观念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程。
一、排外现象的远因与近因
为什么会发生排外现象?胡汉民从各个角度作出了较深刻地分析,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现实背景。具体而言,其原因有三,即最远因、次远因和近因。
一是由于汉族的种族思想,即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传统意识,以及闭关锁国思想,并由此产生的反满思想的延续,此是排外的“最远因”
胡汉民认为,“排外者,其思想由来非一二日,其感触非一二事,徒论其目前之结果不可也。”国民狭义的“排外锁国之主义”,源自“内中国而外夷狄之思想”①。这一狭义的排外思想,“以锁国时代为盛”,及至“国际交通,内外平等之时代”,“则此思想必除”。但是,“其不能无所留遗者,必有物焉为梗于其心理,使其不能淡然忘也。”②
满族政权入主中原之后,传统的种族思想在新的背景下转为排外。胡汉民指出,清代明于今二百余年,“汉人种族之思想虽经尔虏芟夷蕴,崇之未尝绝也。”而开港以后,“文明输换,则民族的国民,益炳然发于人心。而非种之篡祚者,犹以时机未熟,而隐忍拥戴不能遽去,则愤思之深,无可宣泄。”因此,“其辩理心未纯,而任气或过者,则遇事横溃而不可以收拾,以为非我族类,其心皆异,仇满之怒迁而排外。”他认为,这一思想“严格论之,则是固不能无过”,但“所以造成此主观者”,则不无缘由。譬如某宅主人“被强胁于盗,踞其宅,戮杀其父兄,而奴其子弟。为宅主人者,日思光复,不得其间,而邻人有骤至其室者,则并恶之,其感情之过度也。”①
二是由于清政府实行的内外方针,加强或培植了排外情绪和心理,这是排外产生的“次远因”
胡汉民认为,清政府对外软弱,实行妥协方针,导致民众转而排外。“吾国人之排外,尚为口实于列邦者,则以其手段有时反于文明,而其结果不善也。”之所以致此,是由于清政府“国际之失败太多,持一‘宁赠朋友’之方针,而任意抛掷其权利”,“蹙削不堪”。列强各国“皆持其既得权而莫肯让步”,国人“内不得援于政府,又欲亟争之于外,此其所以允无当也。”这个“欲晓人以勿排外”的清政府,正是“发生排外之原因之人”。当外交之失败,“忧国之士乏于条理”,“不能得诸政府为救济之方,乃欲于国际上直接反对之。”①或因外人压迫愤而不平,“而内欲争之,政府不可得,则欲直接争诸外人,以愤激尤甚者,乃诉之于腕力而无所择”,这正是清政府“造成排外之原因”。国民之排外,“大者维持国家之独立权,小者亦主张其社会之权利”。如果“政府不为他人弱,受种种之干涉者,则排外之事皆可以不起。”政府对外屡屡“败失”,“国民乃承其流而救之,其为是非功过,殆亦不难于裁决”。闽粤间鄙谚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此言吾民气之未尝无可畏,而不良之政府官吏独不惜鱼肉之,以求媚于外,盖道其实也。”然民众心理,“既不能表现于上,而异族为制,外人得假之以为傀儡,以畏洋人之官,临畏官之百姓,则百姓以其畏官,故并畏洋人。”其时,“所谓畏百姓者,将不可复见”。列强“干涉人国,伤其国权”,而对于自主张权利者,“概斥之为野蛮,殆欲求‘予取予携,不汝訾瑕’者而后快,此偏私之论,不足凭也。”若“以闹教仇杀为诟病,疑我国民者狭义排外之恶性根者,亦未知其原因所由来也。”②
国人有野蛮排外之举,亦是清政府长期“贱外”、“排外”而酿致。胡汉民认为,“凡今世列国之竞争,咸以实益,其自怙而排斥他人者,以规律出之,未尝授人攻柄也”,但国民“未尽喻是”。“其所争亦恒在于实益,而意所拂逆,则将举一切报复之而弗顾。无实力以为盾,既郁愤不伸为浅欲所驱,又轻妄弗择”。不仅“所图失败,并令彼国得报我人以野蛮之名”。探其本源,国人之所以为此者,“政府始终为其戎首”。庚子以前,“政府贱外”,康熙时“曾命俄使以三跪九拜之礼,乾隆时代亦曾以胁英使,而累代夸为美谈”。“以侮人者自尊,其事正复无聊。然贱外之思想无所发乃发于此,至导义和团击戮他国代表者而极矣。”②清政府还实行“排外”,而其重要原因,“即以防汉”。“其排外也,端刚诸满奴初不自量,欲遂其豕突狼奔之志,而患外邦文明输入,使汉人有自由独立之思想,其亦一大原因也。”②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其排外政策一变为“媚外”,“前倨而后恭,辇毂细民,间亦揣摩成风气”。民众对此深为不满,“有激而动,遂逾常轨,故曰政府始终为戎首也”③。
因此,排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激成的。这一看法,在革命党人中非常普遍,如汪精卫指出,1644年满洲人征服支那,建立清朝,“专从事于鼓吹国人之排外思想”。欧美人“恒言支那人之排外思想,为其固有之性质,不知鼓吹激动此思想者实满洲人也。”这是由于“满洲人欲以少数之民族制御大国,永使驯伏其下,因而遮断外国之交通,杜绝外来之势力,其结果遂致使支那人有强烈之排外感情。”④
从这一角度,胡汉民认为,清廷没有资格降谕禁止国民排外。光绪三十二年,清廷颁发谕旨,谓“:乃闻近日以来,讹言肆起,适偶有不虞之暴动,遂突生排外之谣传,市虎杯蛇,群情惶骇。”要求各处学生“,应遵照奏定学堂禁令章程,束身自爱,尤不得干预外交,妄生议论。总之团体原宜固结。而断不可有视外洋之心。权利固当保全。而断不可有违背条约之举。”著各省将军督抚。“严饬该文武各官,认真防范。”⑤针对谕旨提出的排外问题,胡汉民予以严厉批驳,谓:“然其大旨只求媚外,抑以卸其责任,非真为吾民告。”并形象地说,这就如同先强占宅室的盗贼,“乃反出而任调和之责,问孰能听之者?”从排外的远、近各种原因来看,清政府“无有喻止我国民排外之资格”。其远因,“为此问题之根本,而无有虏廷容喙之地”。其近因,“无论不能应国民之请求,即应之而剜肉治创,盗铃掩耳”。彼“一度之交涉即一度伤国民之感情”,排外“虽事实上有不能不敛目之势,而不久而遇事辄发,其理然也。”而且,清政府之谕排外也,“其本旨诚为我国民告者,则其词或不正确而犹有节取之益,而无如其纯以之媚外而为卸责之地,则固尽人唾之而无与为听。”针对该谕将“排外”之举诬之为“奸人播弄”等语,胡汉民指出:“彼睹乎排外之事之不可遽已,根本问题之解决非其所能。而外人谪言日至,无以应之,则妨害其自庚子以来所改用之媚外政策,故假为是言,示言排外者以反对政府而起,为反对政府故而离间政府之邦交,则政府之不表同情于彼,断然可知。”然而,所谓排外之说所由起,系“外人就于最近之一二事实,而下可虞之判决,以交相警告”,实际上并“无所谓播弄者煽惑者”。谕中所说“奸人”、“匪徒”,“乌有奸匪而具播弄列国观听之能力耶?”谕中所谓“离间外交”一语,“隐然以奸匪为反对虏廷者之徽号”,试图使外人相信,“反对彼者,即为好言排外者”。其目的“不特以甘言而邀外交之顾盼,且欲藉排外之不可能,而压伏反动者之起也。”①
三是由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种种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权利,激起中国社会的反抗,产生近代权利观念和要求,这是排外产生的“近因”
胡汉民认为,当今之排外,与以往不同,“则浸进为权利之主张”。“今吾国人排外之观念,既恒以国际之失败而起,即时有见于国际法所特认保护之权利,不能与平等享有欲主张之而起也。”①也就是说,由于中国遭受列强的不平等待遇,起而要求国际法范围内的自国权利,由此产生了新的排外动因。胡汉民从各个角度揭露了列强侵害中国的独立权,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事实,指出,“必其国家能自由处理其内政外交之事,不受他之干涉,而后为能举国际上独立权之内容。”当今之独立国,如英、俄、德、法、美、日等,“惟行使其权利之过度,有侵妨他国之虞”。观诸我国,“则任外人为税官,亦国家行政权之自由也,而一国以约为担保,用其国人;一国又提议要求与之更代其权力,不啻足以左右我也。”如果“有一不洽于强邻之议者,则讼之外部,以排外为词,必使之去位而后已。”中国“不能自由”改正税法,“增设一税务大臣,而各国竟啧有烦言”,英国太晤士报“犹主张干涉”。除了一时一事之之外,还有种种“使吾国权常受制限”之干涉。如与各国结约,“而许认其有领事裁判权,则司法受制限,而不能与领土同其范围矣。”辛丑条约订立后,“对外主权益被侵削”,如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将大沽炮台及有京师至海通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等等,中国发展自己的自保权“无复有其自由矣”。这些均与中国主权有直接重大关系,而“其他间接之损失不与焉”。从中央到地方,“遇事受人干涉,其结果辄牺牲吾民之权利或利益者,尤不胜算”。任何事情通过比较,便可看到差别,由此而产生不平。“夫事以相较相形而见绌,见绌则不平之观念所由伏也。而况以不法而举其权利、利益为外人牺牲,则以不平之鸣,尤非无因而起。”或谓,“世之言者,怯惕于外交之不竞,受排斥于人之不暇。”②
而震惊世界的义和团事件,“其总原因为排外,为受列强压迫之反动”。列强侵入中国,“以通商、传教为两大工具”,通商打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而内地失业落伍者日多”;传教又挟有势力以压一切平民,“则于信仰之外,更生反动。”因此,晚清时期“排外与仇教,几互为因果,各省闹教之案,几无岁无之”。由于“以列强为后援,其结果决无公平之判决,平民积恨已深。”中国人民“既惧且愤,故排外为义和团事件之总动机,为帝国主义压迫之反响。”⑥
自鸦片战争始,列强用暴力将条约强加给中国,用合法的方式攫取中国种种权益,从而引起反抗。胡汉民看到这一深刻原因,指出,“触发吾国民排外之感情,而使不能自己者,其条约乎?限制吾国民之行动,至不能主张自国权利,激而为野蛮不正当之排外者,其条约乎?”因为条约者“规定国家间之权利义务者”,作为一个国家,“有相当之位置”;订立条约,“亦宜有相当之权利义务”。“于是而相守相报相调和,其国家之交谊既日亲,其国民亦无不平之感而生其猜恶。”因此,“凡今之世,任外交者莫不主张自国之权利”。尽管条约谈判之始,“各不免为过度之要求”,而折冲既定,“则恒止于其范围”。与此相反而行者,“惟以强大临于弱小,其国之势力位置既不相当,则其条约难望以平等耳。”所谓“欧洲协调”,是“以六国(英法德俄奥意)握强权支配欧洲全局”。其趋势固不可争,“而至于国际交通平和,订约之际,则亦不必六国独蒙其利,而此外细国必承其损”。惟有中国外交,“则有令人诧绝者”。自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订立以来,“与订约者十余国,为条约大小百余次,乃几至无一非损以己益人者”。大者为领土权独立权之侵蚀,小者为铁路、矿产、航道等权利之授予,“使吾国民独处伤心”。在“穷于无告”的情况下,“或者引为国耻,欲雪其鄙我亡我之愤;或则知利源已涸,而思为亡羊补牢之谋。”近日外人所指为“排外热”,“其为后之属固多,而为前者亦复不乏。”后者“范围较狭,其问题解决亦较易”。“其据理以争者,或睹成效,则横溃无虞。”前者“则一切相反,其目的既不可达,抑郁冤愤之久,激而诉诸腕力,乃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些均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夫使我国条约,其为制限削夺于我者,不若是甚,则我国民之志必不若是也。”因此“,触发吾国民排外之感情者,条约为之也。”⑦
列强的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是排外现象的基本原因,其他革命党人亦从不同角度认识到这一点。如章太炎谈到反洋教,认为是由于基督教对中国造成危害,而不是因为它是异教,指出:“自海衅未启以前,谁以罗马教宗为悖德忘本而反抗之者?若夫韩愈、杨光先辈,以其私意抒之,简毕陈之庙堂,则于全体固无所与。且今世亦有以彼教为无君父,而视之如洪水猛兽者矣。”民众愤而排教,其意乃绝不在于彼是异教,假如“基督教人之在中国循法蹈义,动无逾轨,则人民固不以异教而排斥之,亦不以异种而排斥之。”其相遇,“与昔之天竺法师无异,虽以百千士人著书攻击,犹往日宋儒之辟佛而已,而人民不因是以起其敌忾之心也。”政府排教,“其意本不在异种异教,而惟集众倡乱之为惧。”日本德川时代曾杀基督旧教六万余人,“即以是故”。以其集众倡乱而排之,“则不必于异种之教”,“虽同种之白莲闻香亦然”;“不必于破坏宗法之教”,“虽儒流之党锢道学亦然”。因此,政府之排教,“以其合群而生变”;人民之排教,“以其藉权而侮民”⑧。
胡汉民所作分析,符合客观实际,既未忽略排外现象的历史根源,又着重揭示了现实中的各种原因。与某些革命党人着重强调清政府与排外的联系不同,胡汉民更注意到国家权利的因素,从这一角度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更加理性地认识排外问题。事实上,列强对华侵略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国家权利的侵夺,正是近代民众反抗斗争,也是排外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揭示原因的基础上,胡汉民进而剖析了不同内容和手段的排外,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二、区分两种不同的排外
从根本原因来看,排外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具有无可非议的正当性。但是,各国列强却将视此为排斥先进文明的一项罪责,常常以此诋毁中国,并要挟清政府压制民众的反抗斗争。由于以往排外多“以国际上不可能之手段,致授人以柄,不可收拾,于是相惊以排外为最不美之名词”。胡汉民认为此说“不可无以纠之”①,对此作了辨析,主张区分两种不同的排外,肯定为维护国家权利而排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其所撰《排外与国际法》一文,从这一角度作了详细的论析,提出了权利排外的基本思想。
胡汉民认为,有不正当和正当两种不同性质的排外,“晚近我国民排外之观念,与前兹排外之观念,有绝异者。前兹之排外锁国之主义也,内中国而外夷狄之思想也。今兹之排外,则浸进为权利之主张。”其事体有三:一是“对于过去者,为回复”;二是“对于现在者,为保持”;三是“对于将来者,为伸张”。至于“将来之伸张,姑不具论”,就“过去”和“现在”而言,中国在“国际上种种失败,希望其回复”,即挽回被侵害的国家权益;并“维持现在之状态,而不使更为陷落”。作为一国国民者,“必不能无是思想”,因此“以不正当之排外言,则其中有仇外贱外之观念;而自正当之排外言,则主张自国之权利,而于其必需者排除外国人,不使共有之之谓。”即使是当今有着先进文明的欧美国家,也存在正当排外。“其法律之对外人者,以平等主义为原则,然立一二之制限为其例外,仍不能免,是此种正当之排外,未能悉湔除也。”国人排外,“尚为口实于列邦者,则以其手段有时反于文明,而其结果不善也。”之所以如此,“良由前兹虏廷于国际之失败太多,持一‘宁赠朋友’之方针,而任意抛掷其权利。”中国“既已蹙削不堪,而在外人则皆持其既得权而莫肯让步”。国人“内不得援于政府,又欲亟争之于外,此其所以允无当也”①。
两种不同的排外,即正当与不正当排外,区别的依据和判断标准为国际法。胡汉民所说正当的排外,是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而应有权利属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如果在此范围之外,便可以排斥。“权利者,法律所特认保护之特定行为也。”国际上所享之权利,系“国际法之所特认保护之特定行为”。因此,主张国内之权利者,“不可以不知国内法”;主张国际之权利者,“不可不知国际法。”狭义的排外主义,“与国际法不相容”,因为它与“国际法认有平等权交通权”“大背戾”。为伸张自国权利而排外者,则其权利观念“既当从于国际法之观念”,其行使求济及扩张之行为,“亦不可不一依求国际法而行动”。从国人排外观念来看,“既恒以国际之失败而起,即时有见于国际法所特认保护之权利,不能与平等享有欲主张之而起也。”其主张或过或不及,“则因其思想之不健全,洎欲达其主义而误用国际法上所不容认之行为,是尤弱点之著见者。”有鉴于此,胡汉民“纵举国际法上所特认保护之权利,以告我国民”,“使知国际上之权利为满政府所掷弃牺牲者”,“使知吾人所当主张之权利与其不必主张者”,以及“使知何者之行为为国际法所不容许,而不可不避者”①。
含有贱外仇外观念的“狭义之排外”,即不正当排外,“为与国际法为不相容”。而在“必需之范围”之内,“主张自国之权利者,无所刺戾于法也。”从国际法来看,国家要素有三:即人民、土地、主权。“主权依于领土范围而自由行动,对于内部,则存在于其领土内之个人团体,皆使服从。而对于外部,不受他之干涉。”此即为学者所言“国内法上主权与国际法上主权”,后者“即独立权”。所谓独立,“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国际法专家某氏从国家主权出发提出国际法之三大原则,其第二、三原则谓,“各国于法律上不能干涉他国之内政”,“领土者与其国之管辖同其范围”。独立权由此二大原则而来,“夫既与其领土同其管辖之范围,则于其范围内不许他权力之存在可知也。”②
因此,“各国不能干涉他国之内政,为法律之制限”,如果“反之而有违法以干涉他国内政者,其被干涉之国必有排斥干涉之权利,为法律所容忍保护可知也。”也就是说,排斥外国人干涉内政,是国际法所允许的。此如同国内法上,“个人于其权利所得利用享有之范围内,则他人不得反其意思而侵妨之。若有反其意思而侵妨之者,则法律许予其被侵妨者以排斥之之权利,而加以保护。”在国际法上,“国家之有独立,犹国法上个人之有自由。”国内法上的个人自由权,与国际法上的国家独立权,其性质是相同的。国内法所认其个人之自由,“则必不受他之个人之干涉,故个人亦为独立。”而国际法既认国家之独立,“则亦必不受他国之干涉,而其行动乃为自由。”两者的差别,在于维护这种权利的机关不同。“个人与个人共立于国家一大团体之下”,若遇他人侵妨其权利,“大半于自助之外,恒救济以国家之权力。”而国家间平等并立,“则更无居其上者之机关与制裁,而舍自力自助之外,几无防卫救济之道”。正是在此意义上,“主张自国之权利,而于其必需者排斥外人不使共之者,不惟不戾于国际法,而且为国际法所特认保护也。”如果“使于其必需排斥者而不能,则无以保自国之权利,即无以为独立也。”正是国际法承认国家有独立权,“即可云认有非干涉之原则”,当“遇适用此原则之时,则断可云有排斥外人之权利。”②
在肯定正当排外的基础上,胡汉民进而提出,对排外问题的认识不能绝对化,不能因为国际法“保护”维护独立的“排外”权,而“可以绝对主张者”。立言者就某一论点,“而可以绝对主张者,天下几无有也。”人之行为或不行为,“固各应于其地其时其事,而为是非优劣功过焉,为绝对消极论者之不可,犹绝对为积极论者之不可耳。”就排外而言,一方面,“衷于贱外仇外之观念而滥用之,则悖于国际法之平等权、交通权,而其为害之结果可以召亡,昔之言排外者所不免”。另一方面,尽管这种排外是不正当的,但不能“惩羹吹齑,因咽废食,以排外为绝对不可能”。他强调,如果“欲使一国之人尽刊除此一观念,则又悖于国际法之独立权,而其为害之结果亦以召亡,又今兹恶言排外者之类也。”②
排外思想与维护国家权利密切相关,要主张国家权利,就不能摒弃排外观念。胡汉民指出:吾人并非绝对主张排外,“而以为彼贱外仇外者助”,其界限在于“主张自国权利,依于国际法行动”。如果他国违背国际法干涉内政,而如绝对消极论者一样,断然否定“排斥之举动”,则是“张强暴者之焰,相率以蹂躏国际法之独立权”,“若含俯仰随人之外无他策”。因此,如果国民均采取这一消极态度,否定排外,“则必欲尽锄其气,使不敢丝毫有峙抗外力之意志,养成媚外之风,厥失为尤大。”国民主张自国权利之观念,“实为国家维持国际法上独立权之要素。”如果“使国民咸不思主张自国权利,则国力必消沈,而无以自立于国际团体之内。”而主张自国权利,在权利彼此冲突,为外力所侵妨之时,“又必不能尽忘排外之观念”。因此,“欲维持其国家之独立,则必增长国民主张自国权利之观念”;而“欲增长国民主张自国权利之观念,则不能尽锄其排外之思想。”
此种排外思想,如何才能不“横溢滥用”?其道“莫如因利而正导之”。一方面,“使知国际法上有所谓平等权、交通权者,则彼自不为绝对的积极主张,以取野蛮之讥,而为国际所不容。”另一方面,“使知国际法上有所谓独立权者,则于其必需主张权利之时,能正用其排斥手段,以维持其国度。”若如此,“则何有于忧无意识排外者之违法召衅,而遂欲举一切排外之观念而刊除净尽者乎?”对于某些学者“惟虑一般国民知识蒙稚,而乏于条理,乃为说以正之”,胡汉认为“其言抑矫枉过正,无复条理”。对其认为“其间为之界说不易,惧煽动之余,招无远虑者之误认,不若为消极论之无过”之论,胡汉民认为“其说之脆弱而己”。他强调说:“吾人所主之排外,对于惟以闹教仇杀为排外者言,故有广义狭义之称,而又谓有正当之排外与不正当之排外,则其区别一衡准于国际法。其妨害于平等权、交通权,而用国际上不可能之手段者,不正当之排外也。其原本独立权应于必需而为自国主张权利者,正当之排外也。”因此,“好排外者与恶排外者,皆不可不知国际法上之独立权。知国际法上之独立权,然后可与言排外之是非得失。”②
这两种不同主义和主张的排外,性质是相同的,只是手段存在差异。胡汉民说,实际上,吾人所“主张权利为广义之排外”,与“仇外贱外主义”之狭义排外,“不过与有程度之差,非性质之异”。广义的排外,“其就积极之一方言,则主张自国权利。而就消极之一方言,此进而彼退,此盈而彼,则因其权利有排除者,而亦曰排外耳。”排外之主义不同,“达其主义之手段尤不同”,且影响主义的实现。如误用其手段,“则有与主义背驰者”。其主义不谬,“非仇外贱外者”,而所用手段“非国际上之可能,则结果与仇外贱外者无别”。而且,“人以感情之强,而蒙其辨理心,最易事也”。因此,“当其排外热度”高涨之是,“则有党同妒真,举反对者而皆目为汉奸奴隶者”。因此,胡汉民尤注意手段,担心手段影响主义的实现,“正所以求主义之必达也”①。
胡汉民主张采用正当手段,即文明排外,如抵制美货运动。“华人以美禁华工约为虐滋甚,乃有不用美货之议,渐见实行,以要求废约。此事准正义人道而行,未尝为野蛮无礼之举动。”甚至与欧美各国同盟罢工比较,“其性质虽相似而不同”。除了彼在国内,“而此则对于异国”之外,彼“涉于暴动激烈,而此则悉出平和”。而且,运动打破了西人所谓华人作事“始锐而卒怠”的陈见,“实行拒约,渐推渐广,而相与励守者,未之或怠”⑨。胡汉民又将野蛮排外称为“无俚之排外”,指出,“我不能教国民以真正之独立,而教以无俚之排外,是无异使习为无意职之破坏也,而以是期大目的之达,不亦远乎?”从这一意义来看,排外“为锁国时代之思想,今无所用。”⑩
主张自国权利,这是胡汉民提出的正当排外的核心,同时他又认同合法的主权限制。胡汉民认为,“独立权之实行,则对于其为侵妨者有排斥干涉之权利。然不审其内容,则或已被他国侵妨而不知所以防卫,或不知其界限而转侵他国此权之范围,进退皆失据也。”②所谓国家独立权,是“自由处理其内政外交之事,而不受他之干涉”,因此,独立权之行使,“为‘非干涉’之原则”。但是,尽管非干涉主义为国际法之原则,“而此原则又不能绝对无例外者。”如在条约规定之内,即使是侵害一国主权,亦不能视为干涉内政而排斥之。虽然国内骚扰和革命运动,“不能为外国干涉之论据”,但“干涉者实不止对于革命而为镇压之行为,且有至紧急危难之际须自救而用干涉手段者”。在他看来,“以非干涉为原则,而于紧急自卫之场合认一之例外,皆近世国际法发达之结果也。”⑪但“权利之行使”不是干涉,例如,“一国以条约而认许他国有领事裁判于其领域内,则彼国直行使其权利,虽侵此国对内主权,不为干涉”。再如,保护国与被保国护之间,“已得代行外交事务之权利,则其基于此之行动,亦非干涉也。”“惟既非国家本来之权利(原权),又未尝得他一国之承认,乃生所谓干涉耳。”因此,南昌教案之时,法调兵舰;广东铁路事件,各国亦调兵舰,此非干涉之现象,不过防卫之准备行为”。中法《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规定,“任凭派拨兵船在通商各口地方停泊,弹压商民水手,俾领事得有威权”。可见,“寻常地方小警,外国辄调兵船停泊通商口岸为保护者,乃依于条约之行动,决非干涉也。”由此,胡汉民得出结论,谓:“野蛮排外,使用国际法上不可能之手段,致危难于人者,召干涉者也。”而根据独立权,“应于必要而排外者,非独不为召干涉之理由,抑对于不法之干涉,为当然也。”⑪再如割台之后的抗日护台,尽管“抗日之师(如刘永福等)在内国为有名誉之举,而以国际法论之,比于海贼”。因为“政府既割让之于他国,人民无反抗之之理由。其反抗为政府所不认,则无异于无国籍之个人(谓不属于一国家主权之下者)暴动,而法律上无能为左袒也。”①
条约损害中国应有的国家主权,为什么必须认可呢?胡汉民根据国际法学者的理论,认为,“战后媾和之约,一方之国家不能免于胁迫,而其约亦不得为无效,故遂有谓国际法认国家之武力而成于强暴胁迫,亦为所容许者。”缔约时惟重代表者之自由意思,“故加强暴于其国家以成约者有效,而加强暴于代表者之身以成约者无效”,此在国际上已有先例者。“有以毁损一国独立之权利之条约,亦为不法无效者,然以国际惯例衡之,则未见其当。”“至我国与土耳其、埃及等有领事裁判权之国,亦为以条约让与者,故学者谓独立国为妨其自国独立权利之条约,亦其自由,则与前之违反国际法原则及国际惯例者异矣。”胡汉民认为,作为国际法范围的条约,与国内法具有同样的效力。国际法既确定为国家负遵守条约之义务,“国际法规同时为国家自身之法规,国际法上条约之效力,与国法上之效力无有区别,于国际上完全有效之条约,亦必为国内可得执行者。”⑫因此,将排外限于国际法范围之内,实际上就是认可条约对中国主权的限制。
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观念来看,违反条约“为断不能容者”⑫,如何收回中国所损害的权利,解决排外问题呢?胡汉民提出了根本办法,关于此点,下节详述,这里不赘。而在根本问题未解决之前,须采取“救济回复之方法手段,以为将来之预备”。胡汉民认为,我国“所失于外交,而独立权之被侵妨者”,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于条约而被制限者”,即前面所举关于领事裁判权及辛丑和约各款。二是“不由于条约而被干涉者”,即发布命令,任免官吏,中央政府及地方行政之受外人牵掣者。二者比较,就其事实之利害言,“则规定于条约而不能违反者,其事重”;就权利之关系言,“则直反于国家之意思而为所干涉支配者,其失大”。这是由于,条约“为双方合意之结果,犹非被国家以外之权力之制限”。因此“条约内容必为列举,而限于或之条件,于条约所既定之条件而践行之”。在彼为有权利,在我为负义务,“非若彼以一方意思而干涉者,直横躏我之国权而已”。
针对这两类情况,回复国权之道亦有二。一是对于任意干涉,“可主张国家独立权而抗拒之,无所踌躇”。二是对于条约之制限,“则宁忍以俟之而徐图其修正”。因为条约有拘束当事者之效力,“其效力未消灭,则纵在义务国损辱已甚,亦无如何”。至于各国交涉,“未尝不视国力之强弱以为进退,而相与结不对等之约者”。在胡汉民看来,这种“不对等”虽然与国家实力有关,但并非是刻意为之的侵略行为。“其被制限之一方,固为不利,而其他一方亦未必以制限人国国权为乐也。”即使是有,“亦为怀抱侵略野心者之少数,而其他则皆有其必要之原因,迫使不得不尔者”。而我须“为之解释焉,为之保证焉,使无复疑虑,而视其前约为无足重轻,然后可得而改”。壬寅年中英新订通商续约第十二款规定,“有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之语。”中日、中美条约皆有此语,“足知各国非必坚护此权”②。
胡汉民区分两种不同的排外,主张以国际法判断依据,以自国权利为正当要求,是中国对外观念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步,反映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胡汉民又局囿于传统国际法不合理的规则,认同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限制。而这种认同,又使得他所主张的正当排外成了无的之矢,未能提出真正解决产生排外原因的有效办法,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憧憬。这里所体现的矛盾,无疑是时代的局限,反映胡汉民和革命党人对各国列强的侵略性质认识不足,更与对排满与排外的关系的认识有关,这是下面所要讨论的。
三、根本解决在于排满
从维护自国权利而言,排外是正当的,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历史使命。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直接诉诸于对外斗争,还是采取其他手段?如其他革命派一样,胡汉民选择的是后者。在他看来,正当排外便是主张国家权利,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其根本之计在于排满革命。“夫以其激动国民排外心如彼,而其所以喻止排外者又如此,故吾人为国民深计熟虑,而得根本解决之惟一方法,曰:欲达吾人主张权利之目的,则莫如排满革命。”①
为什么要排满革命?理由有二:其一,由于清政府不能履行政府职责,坚持国家权利,这是“异族政府为谋不忠当然之结果”。胡汉民指出“:我不能有真正之政府,而以彼虏为代表,其无恶意之际,则沾丐余,所获无几。而其有恶意,则必以我利益为彼牺牲。吾国民前兹之对彼有所请求者,毋亦实力未具,不得已而思其救济之方法耳,而不见听用,亦无如何。故其所得,了不可知,今则并以为干预外交,妄生议论,更若不悛,必将以煽惑播弄之罪,而尸奸人匪类之名,是并此之言论自由而无之,则翻然改图,不待再计。”而且“,吾国人所主张权利,对于既往现在将来者”。就清政府的外交来看,“止有退步,而无进行”。其所以如此,“不出不为与不能之两点”。其“不为”,则“不可不代以吾民族之真正政府而扑此去之”;其“不能”,则“吾国人又何取此劣败无能力之政府以坐毙”。因此,国人若要主张一切之权利,“则对于满廷与为无实力之要求,不如行急激之改革”。从国际上言,“与其以无实力之要求,丐彼异族政府为我主张,不如改造共和立宪政府,而得以国民之心理表现于上而主张之”。正是由于“不得政府之为我主张与无主张之能力,然后有铤而走险之人改造政府,一反其所为。”①
其二,正当排外是维护权利,而从维护中国国民权利的角度来看,也必须排满革命。从狭隘的民族意识出发,胡汉民将满族排除于国民之外,认为,“吾国民所失于满洲之权利,未有大焉者矣。以与其他较衡,则一踞吾上而惟所鱼肉,一伺吾侧而有所觊觎,其轻重利害迥不侔也。”因此,“吾人言排外,则宜先求所以去满者,事之先后,次序当尔也。”如果“我不靖其感情,怒室色市”,而迁怒于外人,“使虏廷有所藉口,而谓夫持民族主义者,莫不好排外。”清政府“利用外人之感情,以延其将尽之残喘,是断非持民族主义者所愿出也。”再者,即使是对外“专主张国际上之权利”,“亦断非支离灭裂之举动之可以成功”。如无国力以随其后,“则多一排外,必多一损失。”清政府“更将有辞,诿为衅自我开,而不负其责任,是再失计”。因此,“必并力一致进行于革命”,“异族政府既去,然后可以靖全国民之气,不使横溢,即国际上之权利亦渐可副吾人之希望”①。
胡汉民列举种种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软弱妥协,毫不顾惜国家和国民权利方面,尤其是领土主权。自近代开埠以来,正是由于清政府“不能保持其领土主权,故而版图日削。”各国之获得中国领土,“大抵缘因于割让,其殒辱不待言矣。”其中中俄交涉最为“可怪”,自咸丰八年至光绪十年立约勘界,“无一次不削地者”。其“为割让耶?为赠与耶?其性质暧昧实甚,世界各国无有轻弃其领土如中国者也。”再如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前此各国间所未尝有者,而以我国为先例。其事未至于割让,而其失败殆有甚耳,吾国人因有引为病者。”清政府对此,“无丝毫顾惜领土之心,且于条约故为粉饰模棱,以留他日之争点,尤叵测也。”①关于租借地,胡汉民指出,“吾人敢断言满廷实已抛弃吾国此数地者予人,特各国之受之为不以割让之名义而已。”或据条约中“中国帝权不得损碍”及“租借地之清国主权无所妨”等语,为清政府辩护,而此正是“所谓外人以是欺彼政府,而政府亦是欺我国民者也。”因为,“所谓高权管辖权之皆在租借国,而我国无有乎?”所谓“高权”,“德文包行政、立法、司法之三权管辖权,于英法文或译为法权”。从威海卫、广州湾两租借条约来看,则包含行政、立法、司法之三权,显然“与‘清国主权不妨害’一语为矛盾”⑬。例如,德国强租胶州湾,“以杀两教士之案,遽用舰队占夺,而后提出要求。”有“言国际法者”,将此事比之为“海贼”行径,德国内部舆论亦“不尽赞成”。如果当时清政府“能执强硬态度,或得外交之援助,肯居中调停,不至遂为各国租借之滥觞。”然而,清政府“惊惶失措,不知所备,且惟知依赖虎狼之俄,浼其公使为缓颊不可得,正依违间,而条约已成立矣。”⑬
而且,清政府的愚民政策,又造成国人对领土主权的漠视。胡汉民痛心地指出,中国领土主权遭到如此侵害,国人竟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尤令人惊诧。清政府“举其不甚爱惜之土地以予人,已无足怪责。所奇者领域主权行使已变,已成割弃取得之实,而吾国民犹熟视而等诸租界之新辟。”此前割让台湾,此后中俄密约传闻“尚有一部之舆论,激昂以争诸政府”。惟此四国租借条约订立,“其时舆论寂然”。这是由于“权利之思想,犹未发达,未尝深考其约之内容”,而这正是“异族政府所愚弄”造成的结果。如今日,“民气不知若何激昂”。因此,“非改造政府,则于外交上权利之已丧失者,鲜能回复”。而且,“此非仅指其一二端而言,而遇重大之关系则尤信”。即如租借条约所损害的国家权利,“期限虽满,而难为回复”⑬。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国民不能直接收回领土主权,因此需要更换政府。清政府“累次丧失领土”,国民虽“痛心疾首”,却无可奈何。因为,彼为国际上承认之“行政机关”,“则其于国际上之行为,为国际团体之所容认,吾国民虽极欲反对,断无直接之效力也”。而“至革此恶劣之政府,谋善良之组织而施之以完备之监督,使其为代表于外者,能巩固我国家之主权而不致有削弱灭亡之惨焉,此则纯为国内政治之问题”。领土割让是外交上最大的屈辱,“而犹不能以国内人民之意志为直接之反对,则其他国际问题不可以个人行动而解决之,尤可知也。”当外交失败,忧国之士“不能得诸政府为救济之方,乃欲于国际上直接反对之”。其实力既不可知,“且由国际团体观察之,复无可居之名义”。被割让领土上之人民,“无有反抗之权利”,其他方面“不能以此而反对国际行为,更不待论”。由此可知,“戴异族无亲之政府,而一切政权,惟其专制,则人民与其财产之抛弃,为其任意,而人民之自顾,恒不免于危道耳。”①
胡汉民还列举了清政府的四大弊窦,说明该政权缺乏国际交往意识,为了排汉而排外,因此不能指望它回复国家利权。一是“昧于交通之义而不自量其力”,二是“蔑弃国际之道义而自取陨辱”,三是“有宁赠朋友无畀家贼之观念”,四是“以满入掌外交而非其任”。由于这四大弊窦,“满政府所收于各国条约之效果无足怪矣”。这四方面,“其根本实同”,即“排汉之心事”。“即其防遮外国之交通,鼓吹人民排外之思想,亦为压服汉人之政策。”此为中外所共知,“不惟我国先识之士能睹其隐,即外人之善觇国者,亦能知之言之也。”今日其锁国主义,虽“因于时势不能无所转移,其他则究以与我汉人利害相反,而不改其故步”。且外交“恒与国务为缘”,条约之改正,“尤必视内政之改革为准”。满人怙其政权,“不能与汉人同化,则终不能一日举内政革新之实”。因此,“充分回复利权之希望,必不能达诸今日之政府无疑也。”⑭正是由于缺乏国际法观念,清政府轻易舍弃了不应放弃的国家权益。一个国家,在外交上力图维护自己的权利,“贪益求多”,如果“不大反于国际法之法则,而得以条约为之(如为锁海之约及卖买奴隶之约,则反于国际法之法则而无效)”,而“既为当事者之合意,则国际间无不容认”。中国却不同,“所可怪者,任人设定势力范围之国,一无国际法观念,甘自侪于无主权之地域,又甘以被侵入国而与之合意结约。”其所获“外交之资源”,“不过千六百万磅之借款而已”。清政府处理这一荒唐之事,要么“饵于利而抛弃主权以达其‘宁赠朋友’之目的”,要么“不顾名义及将来之利害而惟利用外交之嫉妒心于目前”,二者必居其一①。
自国权利的丧失,是由于清政府订立了大量不平等条约,且因为它的因循粉饰而难以挽回。胡汉民认为,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限制,“尚不失其独立国之资格”。但“以受制限者与不受制限者较,则显有不平等之事实矣。况其结果,贻莫大之损失,为不可讳也。”②根据国际法,条约难以更改。“夫条约之性质效力如彼,而其为消灭之原因如此,然则我国之条约,至今日而思改正以四复既失之权利,其事亦可知矣。”近代中外条约,“既具条约之要件,而相互遵守者,已不生自始无效之问题”。若条约附有期限条件,“皆得因缔约国间之合意或延续其期限,或更新其效力,则旧约虽解而不解”。即如与各国所订通商之约,皆附有期限,“而及期重订,则每不过多一批准交换之手续,而于旧约实丝毫无改”,清政府“且以不更有所要求为幸耳”。未附期限条件之约,“我为义务国亟欲免除,则彼为权利国必力葆所获,吾国民所最思更改之约,即最难得承诺于彼方而为合意者”。因此,即使“遇有可主张废止之时机,而亦不收其功果”,如美禁华工约尤为“显者”。“覆辙已见,则来轸方遒,对于既往之补救为若是难,而当前之败失乃未有艾。所损愈甚,则国力愈伤,而回复之望愈迟,斯诚不能不痛恨于蔑弃我国家权利之异族专制政府也。”鉴于这些事实,他不禁问道:“谁生厉阶,至今为梗?”⑫尽管中英、中美、中日通商续约中俟条件成熟“允弃其治外法权”的规定,“可为收复法权之根据”。但是否得以实现,“亦视我后兹之法政为如何”,若如清政府之“粉饰伪令,则断不足以得外人之信用”,将为一纸空文。如商律新颁,“而粤汉铁路公司违律私举不问”,法令之下,“求其实行且难,安有如商约皆臻妥善之日”。若全倚此约为根据,则观埃及之故事可知。一八七三年,欧洲各国与埃及约,至一八八一年,如能修善法律,则撤回混合裁判权。“至期而埃及如故,遂延约为一八九九年,至期而埃及又如故,各国遂认为永久不撤”。清政府“徒事空文,吾惧其蹈埃及之覆辙”②。
针对清廷上谕对学生的警诫,胡汉民进而揭露了清政府坚持专制,压制舆论,导致外交失败的事实,谓:在中国,国际交涉“亦只当局者在任其折冲,学生何人,何拳何勇而能干预者”。“无亦对于政府有所要求,为忠告救正,不以国权行动,于外交无预,泛泛言论,尤于外交无预也。”所谓“妄生议论”,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如粤汉铁路之收回,如果不是学生有所议论,坚持其事,“则一二佥壬,猥琐自利,罔顾大局,此路之敷设权不为我有久矣。”清政府无知,担忧有识者之言影响舆论,“则其赠朋友之政策不能行”。“又惧民气因此而张,民族观念必严,而异种专制之难乎为继也,故首以束缚其言论自由者为务”。在国际交涉中,主张自国国权,“当事者有以国民之舆论为后援者”。如日俄最近谈判,俄于偿金问题,日于桦太半岛,“皆以恐伤国民感情为争论根据”。清政府“专横武断,先欲噤吾国民之口,至其折冲失败,权利蹙削,都不一顾”。政府“每开一谈判,即失一权利,缄结于前者,必不平于后”。订约之失败,“甚有不特丧所有,且恒以伏内外人冲突之因者”。总之,清政府此谕,“其舍欺饰外人观听外,他无所计及”①。
总之,胡汉民从各个方面说明:清政府实施传统的排外政策,甚至“利用义和团以仇外,历史几无其例”⑮。它与近代国际社会不相枘凿,不能维护国家权利,惟有排满革命推翻该政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完全达吾国民主张权利之目的”。“使我国异族政府既去,国家之独立权既复,则所谓支那人排外者,当不可见”②。胡汉民又以日本为例,说明排外必须排满的关系,谓:明治维新以前,“覆幕之论与攘夷论并炽,幕府既倒,而攘夷论熄。”此“犹我国以民族之观念,而并生排外之感情,即亦非满政府既倒,难使之平也。”日本自明治二十三年,各国撒去其领事裁判权,“其国权遂独立不受他之制限,故国民排外之事不见于三岛中。”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国家为国际法之主体,彼国家能维持其国际独立权,自由行动不受他国干涉,其版图内之人民财产,方共立于同一法律规则之下,无所不平,既无干涉之者,亦无容其排斥干涉者。”所余之排外,“惟于国法上待遇外人者,立一二制限,为平等主义之例外而已。”因此,“使我国异族政府既去,国家之独立权既复,则所谓支那人排外者,当不可见,非虚言也。”显然,“欲完全达吾国民主张权利之目的,非扑满革命之后不能收其功”。②正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其对于各国所丧失权利,一一能回复无遗,而今且日谋伸张不已也。如是则言排外者必日少也。”①
以排满为根本之计和首要之图,是革命党人的普遍意见。如吴樾肯定排外的必要性,谓:“我同胞之稍具知识者,见外人之据我士地,夺我利权,奴我子女,莫我曰排外,排外。夫然,不排外则不得复我干地,不排外则不得还我利权,不排外则不得归我子女。国不可无,则排外不可不有。排外之系于国,不如此其重且大乎。”但他提出,“居今日而不思排外则已,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愿我同胞一行之。”⑯或谓:“夫排外之特质,立国于天地之所极不可缺者也,特今日而言排外,当先用之于满洲。”因为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避免国家权利的丧失,消除产生排外的原因。“傀儡既覆,民国既立,彼欧美之列强见吾民族之实力若此,唯有敛手而退耳。”⑰
在某些方面,胡汉民与其他革命党人存在差异,但在排满这一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反映了革命党人将反清革命放在首位,以及试图解答或解决因革命与各国列强产生的矛盾。因此,他们极力撇清自己与排外的关系,或否认革命就是排外,或提出排外必先排满,或指出排满之后不会再有排外现象,等等。如汪精卫说,“吾人之革命,以排满为目的,而非以排外为目的。”⑱在他们看来,“非扑灭清政府,外交内治,皆无可言。故莫先于排满,排满之后,致支那于独立,与各国为平等之交际,然后外交失败之事,可不复数见,此为根本的救治。”因此,“果能排满,不必排外,而外自莫之敢侮,其主义明白如此。”胡汉民亦是如此,所撰《排外与国际法》,“即解决此问题者”⑲。诸如之类的看法,其中心就是要打消各国列强的疑虑,避免引起它们对革命的反对。显然,胡汉民和革命党人致力于反清革命,而对如何解除帝国主义压迫问题有所忽略,并未找到收回自国权利的方法,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所冀望的愿景,即排满以后便可以消除排外现象,实际上而且不可能实现。由于中外之间的根本矛盾没有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没有解除,中国社会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便不会因为政权更迭而止息。民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民的反抗更不断走向高潮,展开了规模更大、水平更高的斗争,孙中山也明确提出了废约反帝纲领。
注 释:
①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4号。
②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续)》,《民报》第8号。
③ 汉民:《清政府与华工禁约问题》,《民报》第1号。
④ 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6号。
⑤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55,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戊申,《清实录》第59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4页。
⑥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第45号。
⑦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续)》,《民报》第10号。
⑧ 太炎:《社会通诠商兑》,《民报》第12号。
⑨ 汉民:《清政府与华工禁约问题》,《民报》第1号。
⑪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续)》,《民报》第 9号。
⑫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续)》,《民报》第 10号。
⑬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续)》,《民报》第 6号。
⑭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续)》,《民报》第 13号。
⑮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第45号。
⑯ 《吴樾遗书·革命主义》,《民报》临时增刊《天讨》。
⑰ 阙名:《仇一姓不仇一族论》,《民报》第 19 号。
⑱ 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民报》第 6 号。
⑲ 《与日本东京朝日新闻记者书(东京志同来稿)》,《民报》第26号。
On Hu Han-min’s Xenophobic Views during Xin-Hai Period
LI Yu-m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Hu Han-min put forward the xenophobic views with times characteristics during Xin-Hai period.He supposed that the causes of the xenophobic phenomenon were due to the race thought of Han nationality,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Powers.Hu insisted the International Law was the standard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wo different natures of the xenophobia:the justifiable and unjustifiable.According to his opinion,the justifiable xenophobia meant claiming national rights and approving legal sovereignty limit as well.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justifiable xenophobia,the radical strategy was to put down Manzu’s revolution.Hu Han-m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members devoted to the revolution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but to some extent ignored the problem of how to remove the Imperialistic oppresses,which ultimately failed to solve the xenophobic views.
Hu Han-min;xenophobic views;Xin-Hai period
K257.21
A
1000-2529(2011)05-0016-08
2011-04-18
李育民(1953-),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校:文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