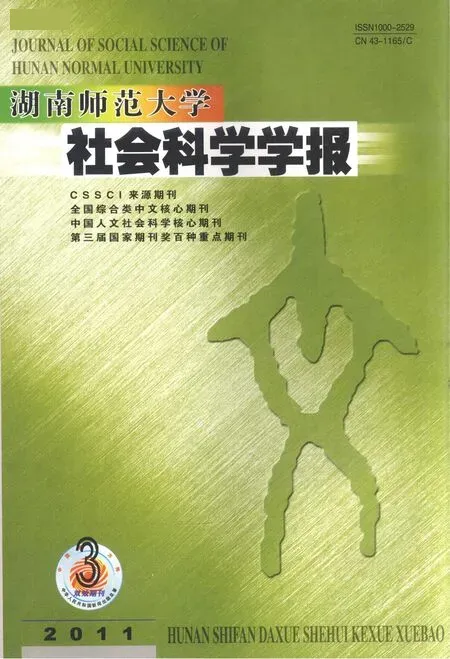文明演进背景下的人格模式探析
2011-04-13彭立威罗常军
彭立威,罗常军
(湖南师范大学 环境教育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文明演进背景下的人格模式探析
彭立威,罗常军
(湖南师范大学 环境教育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人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活动不断深化,积淀了原始文明的“族群人格”、农业文明的“依附型人格”和工业文明的“单向度人格”等三种不同的人格模式。进入生态文明时期以来,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已经进入协调互动的新时代。文明的转型,对人格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得生态人格的转型成为可能。
文明;人格;生态文明;生态人格
“人猿相揖别”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开始一步步地脱离自然、走向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文明。文明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它产生于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因为现存的自然并不直接满足人,人的生存离不开对现存自然的改变。人与自然的矛盾既是文明的催化剂,同时也是推动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
时至今日,人类已经经历了三大文明形态:原始文明形态——采集、渔猎文明;次生文明形态——农业文明;继生文明形态——工业文明。[1](P24)与此相应,人和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每一阶段均有其特殊的新质。正如恩格斯对自由所作的界定那样:“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P672)显然,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也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史,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人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活动不断深化,也积淀了不同类型的人格模式。
一、原始文明的“族群人格”模式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精神生产能力都非常低下。在物质生产方面,人类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是采集和渔猎。采集是向自然索取现成的植物性食物,运用自身的四肢和感官。渔猎则是向自然索取现成的动物性食物,这种活动比采集更为困难复杂,单靠人体自身的器官难以胜任,必须更多地制造和运用体外工具(首先是作为运动器官延伸的体外工具)。这两种活动都是直接利用自然物作为人的生活资料。尽管生产能力低下,但是为了维持自身生存,人类已经开始推动自然的人化过程,其代表性成果便是人工取火。“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3](P112)
在精神生产方面,人类最主要的精神活动是原始宗教活动。原始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其表现形式为万物有灵论、巫术、图腾崇拜等,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这种崇拜体现在原始人于自然界之外构想了一个超自然世界,并且认为自然界的秩序来自超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安排,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河土地、凶禽猛兽等自然事物和现象均为超自然神灵的体现。他们将自然力视为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采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
正是因为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生产力低下,自然作为一股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类对立,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动物一样屈从自然的权力。单个人无法从自然界获取自己需要的食物,无法抵御自然的灾害和野兽的侵害,因此,人们只能像动物一样聚集群居。这样一来,“个体只是氏族群体中的一个无独立性的‘粒子’,是‘无向度’的人,个体同群体分开是不可想象的,个体与祖先分开也是不可想象的……离开族群,人就不能战胜时时威胁人的生命的自然界,不能摆脱自然环境对生命活动的天然束缚,同时人离开族群,人也就没有归属,没有资格,乃至没有作为人的本性规定”[4](P55)。这种没有“作为人的本性规定”的原始族群仅仅具有“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5](P35),我们将这种人格模式称为“族群人格”。
族群人格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度的依赖性。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过度依赖、过分崇拜与无限敬畏,自身的主体性意识尚未觉醒,主观能动性受限,因此他们对自然的态度主要是敬畏。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他们无能力区别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无独立的意识和独立的个性,所以还谈不上有个人独立的人格。
这种族群人格,体现的是人类初级社会的人格形态,也可以说是人格的最初形态。由于这种初级性,一方面使得人与自然保持最基本的初级和谐,表现出社会的无主体意识的高聚合性;但另一方面,它又束缚和压抑了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独立性,使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缺乏自我的人格意识和自为选择的能力,没有独立的人格向度。因此,这种族群人格将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被扬弃。
二、农业文明的“依附型人格”模式
农业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出现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农业文明使自然界的人化过程进一步发展,这时期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物,而是通过创造适当的条件,使自己所需要的植物和动物得到生长和繁衍,并且改变其某些属性和习性。
马克思将农业文明称为“本来意义上的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都是先进的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初期,这些地方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推动了科学文化的繁荣,推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但是后来,它们中间有的中断,有的被沙漠吞噬,有的遗留荒野。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外族入侵、内部战乱、统治腐化等,但究其根本原因却是“生态灾难”,由于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突破了自然的承载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导致了自然环境恶化,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衰落或毁灭。恩格斯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文明是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6](P331)这就是说,农业文明的生态灾难根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在这一对抗中,人类从由对自然的敬畏和依顺发展为对自然的掠夺。
当然,在农业文明时期,在人类对抗自然的进程中,总体上还没有超出自然界的承受阈限。这种对抗体现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人有了基本的生存权利、弱小的自我意识和向自然索取的能力。然而,“取代原始族群共同体的是神权等级共同体或皇权等级共同体,人在宗教或宗法的等级关系中并未摆脱‘人的依赖关系’的生存状态,个人仅在其所处的等级地位角色中获得其有限的非自我性的人格权,人的性质还得在其所属的等级群体中获得给予的规定,即使皇帝或教皇也没有其真正的独立人格。”[4](P56)这种人格形态我们称之为“依附型人格”。
林语堂的中西方语言及文化功底颇为深厚,同时,他在译创工作中还秉承着“读者意识”的原则。所以,在林语堂的译创作品中,西方读者能够更加准确、清晰地了解到中华文化、中国精神、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西方读者通过林语堂的译创作品可以充分地领略到中国智慧的独特魅力。
“依附型人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身依附关系,即个人对于群体、社会和体制的依附,这是因为它在农业文明背景下社会自然经济和高度集权专制政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生产关系本身缺乏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的力量,而是通过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来维持社会的整体秩序的;二是自然依附关系,即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高度依赖,这是因为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较低,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尚停留在初级阶段,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十分低下,人类的生存境遇和文明延续极易受到自然生态的影响。
这种“依附型人格”之于人类自身的作用也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附,使得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个人与自然抗争的生命潜能得以发挥和增强,从而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扩大了的群体逐渐演化成为超个体、人格化的实体,反过来这种超个体和人格化的实体又对个体产生了束缚和压抑反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束缚了个人的创造性能力的发挥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农业文明尚属于人类对自然认识和变革的幼稚阶段,所以,尽管农业文明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这只是一种在落后的经济水平上的生态平衡,是和人类能动性发挥不足与对自然开发能力薄弱相联系的生态平衡,因而不是人们应当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人格也必然被扬弃。
三、工业文明的“单向度人格”模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人类文明出现第二个重大转折,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的出现使得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自然界不再具有以往的神秘和威力,因为自然对人无论施展和动用怎样的力量——寒冷、凶猛的野兽、火、水,人总是会找到对付这些力量的手段。人类再也无需像中世纪那样借助上帝的权威来维持自己对自然的统治,而是像弗兰西斯·培根宣告的那样,“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只须凭借知识和理性就足以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如果说在原始文明时代人是自然神的奴隶;在农业文明时代人是在神支配下的、自然的主人;那么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征服和驾御自然的“神”。
工业文明时代,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以来,机器化生产使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人类在开发、改造、利用和征服自然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甚至超过了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生产的机械化带来了思维方式的机械化,人们把社会、自然和人都看作机器,机械论的思潮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与在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力求顺从自然、适应自然不同,在工业文明时期,人们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征服者,人和自然只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7](P393)。这时,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大自然的奴役,成为自然的主人,并从权威、等级的服从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的自主、自尊和自由,获得人格的独立,物化的“单向度”人格得以形成和彰显。
这种“单向度”人格的形成,具有单纯立足于个人的利己主义倾向,一方面把人从生命本能的制约中解放出来,克服了传统农业社会人格对自然、社会的依附性,使人的创造性得以极大的发挥,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这种人格在向自然吹响进军号角的同时,却变成了向人类文明敲响的警钟,人们不再敬畏和崇拜自然,而是以自然界的征服者、主宰者和统治者自居,把人类置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忽视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忽视了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现实关怀,在文明的进程中迷失了自我。其结果是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工业文明,人类高扬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忽视了自己还有受动性的一面,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根源性、独立性和制约性。马克思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8](P167)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开发观念和行为准则违背了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法,而藐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9](P367)
因此,“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总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10](P4)
四、生态文明的“生态人格”模式
随着文明的推进,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文明应当把人类逐渐引入同自然相对和谐的状态,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工业社会并没有这样,而是不断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这种矛盾已经上升为对抗冲突,引发了人类存在的危机。人类要摆脱这一生态危机,它呼唤着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一场文明的全面变革,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总对策。[1](P30)
生态文明代表了时代的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已经进入协调互动的新时代。人类既不是自然界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界的主宰;既不是自然的膜拜者和臣服者,也不是自然的统治者和征服者。过去,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使天然自然变成社会自然,使天然生态系统变成人工生态系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当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超出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限度时,它又对自然生态平衡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由于作为主体的人是自然进化的引导者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者,整个人类和自然系统的动态平衡有赖于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所以,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期,人类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调整自身的行为,力求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生态文明的转型,不仅对人格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其转型过程当中,也使得新型人格的转型成为可能,我们称之为“生态人格”。生态人格是指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伴随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生态文明的发展,基于对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的把握和认识而形成的作为生态主体的资格、规格和品格的统一,或者说,是生态主体存在过程中的尊严、责任和价值的集合。
生态人格的提出是对生态文明转向的积极回应,是对人的发展完善的积极回应。生态化人格是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一种崭新的人格类型,是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现代生态人所理当具有的“资格”。一方面,这种人格是人类在与自然进行长期适应、改造后面对大自然时所产生的敬畏之心、珍爱之心。另一方面,这种人格是人类在面对当代全球化生态危机所要求的时代品质,不仅体现了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强烈意愿,而且也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种新型理想人格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同时还注重人与人的和谐,甚至还十分注重人类彼此之间利益的公平分配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生态人格是道德人格的一种新型要求,它是生态伦理原则与规范和生态道德素养内化为人的良知后形成的一种道德人格样式,是一个人对待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所持有的具有个性特征的确定的态度和立场。生态人格作为一种道德人格,体现为生态道德认识和态度、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意志、生态道德信念和生态道德行为习惯。
生态人格是一种崭新的、与生态文明相适合的理想人格模式,同前文谈到的原始文明的“族群人格”、农业文明的“依附型人格”和工业文明的“单向度人格”模式相比,至少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生态化人格是一种适时顺势的人格范式,具有最大的普遍性,生态化人格是适应生态文明所塑造成型的人格。我们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其次,生态化人格是一种立体的、复合的人格。过去谈人格都将其内容仅限定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则、规范和准则,几乎不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人格不仅在广度上将其内容涵盖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在深度上着眼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权衡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消除了自然的他者性,不再将自然当成人之外的甚至是与人相竞争的存在,而是将其内化为与人同生息、共繁荣的存在。最后,生态化人格还是一种自觉地、有意识地、能动地建构起来的人格类型,具有极强的自觉能动性。生态化人格是人类心态与自然生态相融合的结晶,是由内在的心态和外在的行动两方面共同支撑起来的人格。在人类普遍陷入精神危机,面临精神家园的丧失的现代,心态处于边缘化,陷入痛苦与矛盾中,变得不再健全。生态化人格的塑造正是人在面对困境时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得的唯一出路。
总之,生态人格的提出顺应了文明发展的需要,是对以往人格模式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它克服了原始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强烈的依附性,肯定其合理的主体性内核,并主张立足于个体的自觉与内省,自主性、创造性地塑造人格;另一方面,它又克服工业文明时代物化的单向度人格发展中形成的立足于个人的利己主义倾向,主张继承传统农业文明时代强调突显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人格特征。可以说,生态人格向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的实现迈进了前进的一大步。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一定能够创立一个完全新式的人类文明,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文明社会。
[1]刘湘溶.生态文明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4]张青兰.人格的现代转型与塑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梅萨罗维克.人类处在转折点上(刘长毅译)[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
[10]杨通进,高予远.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责任编校:文 建)
Personality Mode Prob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Civilization Evolving
PENG Li-wei,LUO Chang-ju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In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evolving,fo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making activity of the natural world,man has accumulated three different personality modes such as the“ethnic personality”in primitive civilization,“depending personality”i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and“single-dimension personality”i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When enter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r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has now entered a new era of harmonious relationship.Civilization transition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rsonality,and mak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personality possible.
civilization;personality;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personality
B82-058
A
1000-2529(2011)03-0014-04
2011-01-20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祛魅复魅生命境界——文化反思视野中的环境伦理与人格塑研究”(08CZX030)
彭立威(1972-),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环境教育中心副研究员,哲学博士;罗常军(1982-),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生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