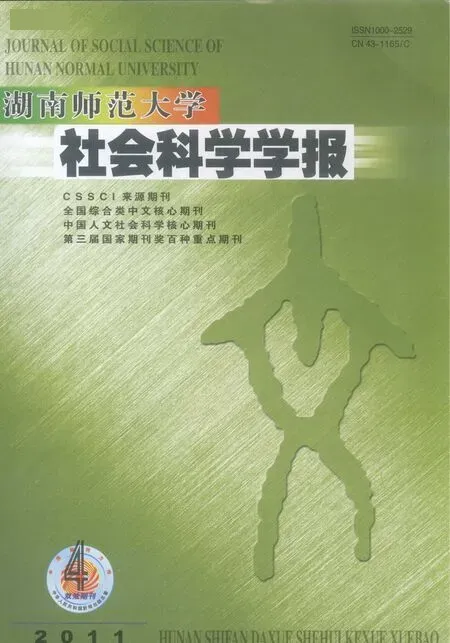论法律运行的司法最终原则——以“行政依赖”的克服为中心
2011-04-13向明,肖爱
向 明,肖 爱
(吉首大学 法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论法律运行的司法最终原则
——以“行政依赖”的克服为中心
向 明,肖 爱
(吉首大学 法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我国当前法律运行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行政依赖,有害于法治。应该将司法最终原则树立为法治的基本指导原则,将其贯彻到法律运行各环节,以司法裁判作为化解冲突和矛盾的终极手段。该原则的贯彻需要保障有效的审判独立,化解当前司法地方化困境,并且将可司法性作为立法质量的基本标准,便于社会权力通过司法对公权力守法进行监督。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和公平,应该强化司法程序化、透明化,可以在人大制度框架内构建我国的法官弹劾制度,落实司法最终原则,确保法院和法官守法。
法律运行;行政依赖;司法最终原则;法治
在专制性社会,“强力统治试图担当法律统治的工作。纵使我们倾向于给予十九世纪最后年代里所实行的法律统治以坏的评价,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对文明所做出的成就比今天强力统治对文明正在做出的要多得多。”[1](P8)法治是现代多元社会中社会控制的核心手段。改革开放后我国法治回应社会所需,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然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法治表现出在法律运行过程中过于依赖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现象,并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我国环境法治不彰也就是因为“一直走的是重立法和行政而轻司法、重空泛的实体权利规定而轻程序规范的路线”[2]。笔者认为应该发挥司法的积极作用,将司法最终原则作为法律运行的基本指导原则。
一、法律运行中的行政依赖
法律运行要“通过国家专门操作系统来推动和依靠社会主体遵守”[3](P196),表现为立法、守法、执法以及司法适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客观状态的法律规范,并逐渐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关系,形成法律秩序。法律运行是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以及各种社会权力相互作用的过程。世界各国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趋势对我国法治以及行政权良性发展产生很不利的刺激,因为本来我国就有“社会从属于政府”的传统。这使得我国法律运行表现出对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力的过分依赖,而无形中弱化了其他权力尤其是司法权在引导和贯彻国家意志方面的明显优势,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本文中的“行政依赖”源自行政心理学中的“行政依赖症”①这一术语,是指在法律运行的权力结构中过于重视行政体系,忽视或轻视其它权力尤其是相对保守和中立的司法权力的现象。我国法律运行中的“行政依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从法律的产生来看,我国奉行“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的总称”②,在这种国家主义法观念下,一方面,一出现某种社会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立法,却忽视了我国当前法律严重空置的事实。如2011年两会中,有代表提议对员工跳槽予以立法规定严格的责任,这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需要员工充分流动自由的规律,而且,在员工跳槽问题上,“员工”往往处于明显弱势,限制跳槽的立法难免“扶强欺弱”之嫌。另一方面,我国立法从动议和草案的提出到审议通过都对行政部门有过多依赖,结果往往使行政权力通过立法而获得新的拓展,使法外行政权力和利益固化,获得新的形式上的合法性。我国环境立法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环境法条款基本上是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较少对行政机关权力进行限制;环境法中呈现出“九龙治水”的现象,因为有环境监管权的各部门都努力在环境法中固化于己有利的权力,而推卸无利可图的环境监管责任。
另一方面,在我国立法体制下,行政部门可以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到2010年底,我国现行有效法律共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政府规章更是成千上万。因为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立法“宜粗不宜细”原则,法律成为“大、老、粗”的原则性宣示,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不得不形成对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的严重依赖,而政府规章又由更繁杂的政府规范性文件(其中不乏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红头文件”)“细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的“法治”其实就是由掌握行政权的各级政府部门以这些“红头文件”推行的,以至于形成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可以不懂法律但是不能不懂“红头文件”的怪现象。即使是人大行使立法权的立法,也存在强烈的行政依赖,因为草案基本上是由行政主管部门起草或提交,即使学者参与或主持起草,往往也会在行政部门之间的博弈中,学者草案的棱角几乎被磨蚀殆尽。所以说,我国立法实际上由行政主导并围绕行政权力的行使而展开。虽然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有权审查有关行政立法,有权宣布与宪法、法律、地方法规相冲突的政府规章无效,但是,《立法法》(第88条)并没有规定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部委规章的权力;对无所不在的政府“红头文件”根本就没有纳入人大审查和司法审查的范围。这实际上正是立法上行政依赖思维定势给行政权力运行留下了任性空间。
在法的执行和遵守方面的行政依赖,一是法律主要依赖各“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管”,其他有权部门“分工合作”执行,公民和企事业单位只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即“社会权力”只是行政权力的规制对象,缺乏基本的“执法”权力。法治发达国家基于对行政权天生趋向腐败的认识,赋予私人借助司法权监督、敦促行政权依法有效行使,这是运用“社会权力”“执法”的有效机制。但是在行政依赖的立法机制中,这种制度难以获得法律支持,“我们从来就不期望政府管理部门主动交出手中的权力——从维护并增大既得利益角度看,他们不想方设法增大手中的权力才怪。”[4]必须通过舆论监督、公民社会建设和法制进步,让他们不情愿却不得不归还属于社会和个人的权力与权利。二是守法主体在行政依赖的立法中主要是行政管理相对人,行政权力的运行似乎有着天然的合法性。这与法治发达国家首先规制行政权阻止其任性扩张的经验相背离,也违背我国“治民先治吏”的传统政治智慧。这种情况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有了很大改观,但是,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行政诉讼的艰难发展都表明,我国法律亟需普遍确立这样的观念,即行使行政权的公共权力机构更应该是守法主体。守法是公共权力机构的绝对性义务,应该通过法律机制使社会权力有足够的途径和能力与国家行政权力进行博弈,从而监督和督促行政守法。三是法律的执行和遵守忽视市场手段和社会手段。如我国的环境法中即使是“排污收费”、罚款等经济性措施也重在行政性管理和处罚,所以额度偏低,导致遵循市场规律的企业违法排污的成本远远低于其守法成本,于是环境保护领域的普遍不守法成为常态,即使一波又一波的“环保风暴”、“区域限批“和“挂牌督办”将行政手段用尽,也难改环境“总体恶化”的状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执法和守法的判断主要由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复议或信访等行政制度进行,忽视了司法权的本质功能。
运用司法手段解决法律运行中的行政依赖问题是各国通行的做法。我国实行人大下的“一府两院”体制,加强司法对法律运行的保障更具有实际意义:一是可以加强权力运行的程序性,有利于引导社会问题的理性化解决;二是可以加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强化法律规范的现实效力;三是在社会纠纷集中爆发时期避免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力成为“火药库”,将社会矛盾分流进入更具可预期性的专业解纷机构——法院,同时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能力和效率。因而应将“司法最终原则”作为法律运行的一项基本指导原则,使司法的程序性精神贯穿法律运行始终。
二、“司法最终原则”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指法院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对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关系享有最终审查、最终评断、最终裁判的权力”[5],王雪梅从分析行政最终裁决探讨司法最终原则[6],宋炉安基于行政诉讼引发对司法最终权的思考[7],王天林以涉诉信访为中心探讨司法最终解决原则[8]。“国内学者对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研究还相当匮乏,有也主要限于民事诉讼领域。”[9]尚没有从宪政原则意义上对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专门研究。司法最终原则应该是一项基本法治指导原则或宪政原则,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认可该原则,才可能摆脱技术层面的小修小补而高屋建瓴引导法治建设进程。
笔者认为,司法最终原则是指,任何个人权利的救济以及国家公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运行都应该坚持司法最终审查,以司法裁判作为化解冲突和矛盾的终极手段。即不仅应该将司法居于整个权利救济体系的中心和终极地位,使“所有涉及个人自由、财产、隐私甚至生命的事项,不论是属于程序性的还是实体性的,都必须由司法机构通过亲自‘听审’或者‘聆讯’作出裁判,而且这种程序性裁判和实体性裁判具有最终的权威性”[10](P225),并且,所有公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运行都应该贯彻司法最终原则。具体来说,该原则有如下主要含义:
一是以司法作为权利救济终极途径。法治社会具有多元化的权利救济方式,包括自决、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诉讼等,但是,在其他方式对权利救济失效的情况下,还有司法能提供有效的权威救济方式,司法裁判不可轻易更改,“判决一经确定,应不容恣意翻案,否则司法制度之安定性、可信性、吓阻性,以及司法资源之有效利用,皆将严重受损。”[11]做出最终判决后,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更改和违背该判决。当事人也不得就既判的法律关系另诉,不得就同一法律关系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本案相矛盾的主张。裁判的最终性在民族习惯法中也极受重视,“即使当事人受了冤枉,也不得反悔。凡是定了案的,即使是错判,公众也要按《约法款》的规定进行处罚……任何人不得违抗。”[12]维持一个最终的居间裁判的不可变更性是任何社会有序性的基本要求。我国涉诉上访案件不断增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司法判决的终极效力和公信力不足。
二是以司法作为权力运行冲突解决的终极途径。权力的运行总会发生多样的冲突,越是铁板一块的权力运行体制就越容易发生权力之间的血腥冲突。传统上,权力冲突往往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然而,在奉行法治的国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司法问题。因此,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助于司法的概念和语言。”[13](P310)这意味着即使是立法权力的行使也应该贯彻司法最终原则,如对立法的合宪性的司法审查;对行政权力的运行则更应该全面纳入司法审查,即使是为了保证行政效率,也必须通过具体机制,如美国对一些特别行政行为实行“穷尽行政救济”机制,而不能否定司法的最终裁决权力。此外,社会权力的运行也应该通过司法途径引导和规范,为其与立法权和行政权等公权力博弈提供理性平台,如使社会组织的成立与否具有可诉性、社会主体有权对公共权力的行使提起诉讼而不受制于“现实利益直接相关性”的传统民事诉讼资格限制,等等。
只有在整个法律运行过程始终坚持司法最终原则,本性被动、中立的司法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制约行政权力并使立法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运行规范化,宪政职能和法治目标才可能实现,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才能获得长效沟通渠道,避免公权力的内耗以及社会暴力的威胁和破坏,司法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14](P206)。人类历史早已证明了,只有司法具有总是用非武力方式提供最终的理性裁断的能力,只有司法权力是以个案解决的方式服务整个社会,并且其自身受制于最严谨的法律程序。
三、司法最终原则的实现
将司法最终原则上升到法治和宪政的基本原则之一,实质上是要求法律运行从当前的行政依赖转向以司法逻辑贯穿始终,其细致展开有赖理论和实践的系统研究。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初步勾画这一原则的实现。
1.司法独立与司法“去地方化”
司法“是人类社会由无序走向有序状态不可缺少的主导性结构”[15]。司法因为其独特的严格程序性以及基于个案审理的权力运行方式,迥异于上下一体的行政和采行议决方式的立法,司法内部不同法院、法庭和法官可以通过审级制度、审判庭和合议庭制度等产生几乎完全“外在”于审判者的监督机制,这是任何其他公权力机构都无法做到的。纵使像我国当前司法状况不尽人意,也不能否定审判独立的价值,一个国家必需有一个最终裁决的机构,相对被动和中立的司法无疑最为恰当。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见司法独立是我国的一项宪政制度。我国的司法独立主要是指人民法院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只是审判权独立、审判机关独立。然而,如果真正落实了这种审判独立,也能保证司法最终原则的实现。法院独立审判未能落实的主要原因,宏观上看,就在于法律运行整体上的行政依赖;从微观上看,就在于司法“地方化”严重,即地方法院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尤其是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必须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这样,法院维护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职能不可能不打折扣。贯彻司法最终原则、落实司法独立的宪政制度,首先要实现司法国家化或“去地方化”。司法国家化就是要摆脱目前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局面。可以通过修改《宪法》,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权属于国家”,并在《宪法》中恢复1954年《宪法》第7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6]同时,将法院和法官的利益与地方脱离,这样就能保障充分的审判独立,尤其是具体审判工作,法官只需要遵守法律,依法裁断。司法权也可以从裁决普通的刑事、民事纠纷发展到审查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尤其是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而形成“最终”的裁判权力。如果将司法辖区与行政区相错开,则司法“去地方化”更有保障。审判独立不仅无损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且因为司法仅仅对法律负责,不受地方政府控制,更能充分保障人大权力的实现,也就能保障国家意志贯彻到社会最基层,法律运行的行政依赖也就能得以解决。
2.在立法领域贯彻司法最终原则
立法包括权力机关制定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等的行为,也包括政府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行为即抽象行政行为,笔者认为应该将所有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甚至各种“红头文件”的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避免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层面以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误解甚至有意歪曲国家法律。但是司法必须始终坚持“告诉才理”原则,并且主要是通过解决个案纠纷对相关立法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免将法院沦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机关。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可以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框架内逐渐展开,也可以在民事、刑事诉讼中附带对有关行政立法进行审查。法院贯彻司法最终原则对行政立法的审查可以与人大行使立法权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变更和撤销并行不悖,法院基于个案的司法审查判定撤销行政立法,不需要人大审查批准。与此相应的是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必须坚持一个基本的原则即不得干涉法官断案,不得以人大决定否决法官判决,这种做法实质上会导致法律权威、国家权威的耗蚀。
从现行宪政体制看我国实质上实行的是全国人大下的一府两院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真正享有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立法权,因为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地方法规不得与行政法规相冲突,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受限于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的行政立法权。因此,对人大立法的监督,可以从现行宪法关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隐含的司法国家保留性的宪政基础,以及地方法规不得违背宪法和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在《宪法》未作有关修订之前,应该可以明确法院对地方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审查权。
最后,在立法领域贯彻司法最终原则,要求所有的立法不能仅仅注重行政上的可执行性,而是首先要考虑司法上的便利性,即要将立法的司法便利性作为立法质量的一个基本标准。
3.在执法和守法方面贯彻司法最终原则
执法主要是行政执法,因为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守法则是普遍守法,即所有公权力机关、法人、自然人以及作为社会权力的主要代表者——社会组织都是守法主体。吕忠梅教授指出,“执法主体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也需要设置司法审查加以监督和保证;执法相对人与执法主体间产生的争议也需要一定的途径加以裁断;执法者的不作为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必须设置司法程序,“这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解决纠纷所必需的机制”[17]。所有行政行为都贯彻司法最终原则,以有效约束和保障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除非法定情形为了保证基本行政效率而排除司法审查。行政主体是否守法不是由行政而是由司法进行最终裁判,更切实地保障行政主体守法。对非行政主体如各种组织以及个人的守法贯彻司法最终原则,主要是要拓展法院主管范围,完善司法制度等,并确保司法判决的终极效力,树立司法和法律的权威;有必要扩展社会组织的诉讼资格、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使社会权力能够通过司法渠道有序地监督执法和守法,这也有利于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造完善。最后,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不受监督、不负责任,因此在强调司法独立的同时构建适度的问责机制。应该通过程序透明化和判决公开等制度实质上使司法权力运行置于人大和社会的普遍有效监督之中,同时,可以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法官弹劾制度,在人大内按照基本的司法程序裁断法官责任,避免当前以行政绩效方式管理法官的行政化弊病,以将司法最终原则落实到法院和法官自身的守法,确保司法公正和公平的实现。
注 释:
① “行政依赖症”,即“人们对行政权力、行政机构、行政公务人员及行政行为的过度的和非分的依赖感,以及与之相应的对自身独立的自我意志、自我组织和自我活动能力等的严重缺乏和极度不自信。”参见姜继为,朱英群.论“行政依赖症”[J].中国行政管理,2006,(7):45-47。
② 国家主义法律观主要指:在本体论上,突出强调法律的国家意志论,使得国家法律越出理性批判的视野;在价值论上,看到法律价值的相对性而否定法律相对恒定的价值;在认识论上,强调“国家制定或认可”这一形式而忽略法的内容;在法律实践上却重实体轻程序。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M].法律出版社,2009:58。
[1][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肖 爱.我国区域环境法治研究现状及其拓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09-113.
[3]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熊丙奇.促进受教育权平等须推进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J].法学,2009,(11):20-24.
[5]张晓茹.浅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71-73.
[6]王雪梅.司法最终原则——从行政最终裁决谈起[J].行政法学研究,2001,(4):22-30.
[7]宋炉安.司法最终权——行政诉讼引发的思考[J].行政法学研究,1999,(4):48-56.
[8]王天林.中国信访救济与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冲突——以涉诉信访为中心[J].学术月刊,2010,(10):21-27.
[9]吴 俊.论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民事诉讼的视角[J].法治论坛,2008,(1):146-155.
[10]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1]王兆鹏.重新思考非常上诉制度[J].月旦法学杂志,2009,(170):114-115.
[12]罗康隆.侗族传统社会习惯法对森林资源的保护[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1):57-62.
[1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良果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4]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15]程竹汝.社会控制:关于司法与社会最一般关系的理论分析[J].文史哲,2003,(5):151-157.
[16]刘作翔.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J]. 法学研究,2003,(1):83-98.
[17]吕忠梅.水污染纠纷处理主管问题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9,(3):17-23.
On the Principle of Judicial Ultimate Resolu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Law——To Center on the Overcoming of“Administration Dependency”
XIANG Ming,XIAO Ai
(School of Law,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China)
In our country,the operation of law are too dependent on the administration,which is harmful to the rule of law.Principles of judicial ultimate resolution should b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rule of law,i.e.any individual’s rights and remedies as well as national public power community should insist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of final order to resolv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s the ultimate means of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The need to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and resolve the plight of the current localization of Justice and judicial convenience as a basic standard of quality of legislation;protection of social rights through the judicial and law-abiding public authority to supervise the judicial authority to protect resistance,impeachment of judges need to build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peration of law;judicial ultimate resolution;rule of law;authority of judiciary
DF0-052
A
1000-2529(2011)04-0075-04
2011-01-0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府际竞争背景下的区域环境法治研究”(09CFX039);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低碳时代的地方环境立法研究”(2010YBB269)
向 明(1966-),男,湖南凤凰人,湖南吉首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 爱(1971-),男,湖南绥宁人,湖南吉首大学法学院讲师。
(责任编校:文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