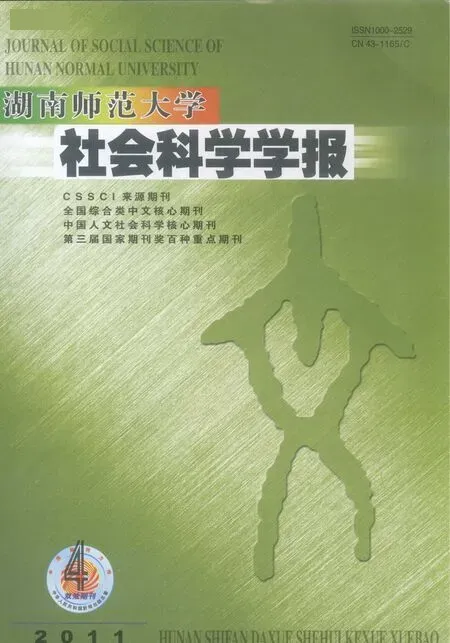论经济危机背后的道德危机
2011-04-13彭定光
彭定光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论经济危机背后的道德危机
彭定光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因其内在矛盾激化而出现的恶化状态,是所有经济因素和经济行为共同作用及经济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而且是自由主义道德观念推波助澜的恶果。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道德,虽然有如受到人们斥责的贪婪、失信、欺诈等,但更为主要的是由自由主义所提倡和经其论证而被合理化了的、且被经济活动主体普遍地奉行甚至被法律、经济政策等所制度化了的个体本位、自由至上和为己取向等道德观念。由于经济危机既是经济矛盾的呈现,又是道德观念危机的表征,因此,人们就应该从道德方面来思考如何防控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人为性;道德根源;自由主义道德;道德防控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制度,它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经济危机。然而,西方自由主义者却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不但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道德性,反而为之进行道德辩护,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提供了一整套道德观念。这套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道德观念,不但未能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改变资本主义的命运,反而加重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表明,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而且同时是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推波助澜的恶果。
一、经济危机是道德危机的表征
经济危机是什么的问题,是所有有关理论思考的逻辑前提。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此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西斯蒙第认为它是消费不足,凯恩斯认为是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哈耶克认为是投资过度,弗里德曼认为是货币信用过度扩张,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是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危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现在的危机主要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有人认为是若干经济体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的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有人认为是市场失灵尤其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有人认为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较多的人认为是生产(产品)相对过剩。除个别看法之外,这些看法在思维方法上主要有如下共同之处,第一,它们都没有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第二,它们都见物不见人;第三,它们都从数量角度来考察经济危机。这种思维方法直接导致了如下两个结果,第一,它们在理论上彼此区别甚至对立,不能自圆其说,各自都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在经济危机的应对方面,它们各有自己的思路与对策,使经济实践变得无所适从,甚至出现了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其最终效果是:应对危机的措施花样翻新,代价过高,经济危机却依然故我。
其实,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因其内在矛盾激化而出现的恶化状态。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非通常状态,是经济系统内在矛盾的激化状态。说它是一种市场经济运行状态,是指它并非瞬间爆发就立即结束,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处于某种状态,这种状态与非危机时期的常态有所不同,它标志着市场经济运行的恶化(而非只是经济指标的恶化),就如人一样,如果生病,其健康就面临危机,只有疾病痊愈才会恢复。说它是一种经济矛盾的激化状态,是指并非任何程度的经济矛盾都会表现为经济危机,只有当经济矛盾难以借助市场力量来顺利解决时才会转变为危机。
如此理解的经济危机,第一,意味着它具有整体性。这就是说,首先,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非通常状态,是所有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并不一定会因为任何单一的技术性因素或者经济资源的变化而爆发,如在当代工业化条件下,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几乎总是相对过剩,但经济危机却并未随时出现。其次,经济危机是各种经济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各种经济因素的运转都是由人来推动和实现的,因而,经济危机总是与人的经济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无论何种市场经济运行状态(不论是常态还是非常态),都是由人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因此,经济危机这一客观的经济运行状态必定有人的主观因素的参与。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独立的经济主体的行为都是理性的,都追求经由其理性权衡过的经济目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谁都未曾预料到的,他们的行为共同造成了非理性的后果,使市场经济的运行陷入了非常态,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见,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问题就出在单个主体的经济行为上,出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准确地说,是出在彼此对待的态度上。
第二,经济危机是经济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经济危机的发生虽然是难以预测的,具有突发性,但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在市场经济的常态运行中孕育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各种经济因素和经济活动主体所构成的整体,是在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中维持和发展的。其中的各种经济因素和经济活动主体必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出现不同的经济矛盾。这些经济矛盾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如影随形,存在于常态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往往被经济活动主体所轻视甚至忽略,表现得较为温和,且因为市场本身具有调和经济矛盾的一定能力而不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的继续运行。可是,市场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且市场调和经济矛盾并不是消除矛盾,而是在积累矛盾、深化矛盾。当经济矛盾突破一定的“度”,而市场机制对这些经济矛盾的应对又变得无能为力时,经济矛盾就会由潜伏状态走向公开对立,由可以调和变得不可调和。于是,市场经济的运行也就由常态转变成非常态,进入危机阶段。
第三,经济危机可能会转化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仅就整个市场经济而言是如此,而且就社会生活而言也是这样。这表明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间,或者说,经济矛盾的激化状态与社会矛盾的激化状态之间存在着某种事实上的关联,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人们践踏道德和法律的越轨行为,使人们丧失社会认同,甚至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这种可能性是否会转化为现实性,其前提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是否在经济危机时期走向了对立并被人们所明确意识到,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经济矛盾是否转换成了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是否演化成了人们之间争取生存条件的斗争。这就是说,“只要要求和意图的不可调和性尚未被社会参与者所意识到,冲突就是潜在的。……只要人们意识到那种不可调和性,冲突就会表现出来:不可调和的意图就会被认为是对抗的利益”[1](P36-37)。
由上述分析可见,经济危机是人们在其经济行为中没有及时而又合理地处理经济关系、化解经济矛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具有人为性的危机。由于经济关系的处理、经济矛盾的解决与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相联,与人们如何对待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态度有关,因此,经济危机就必定与经济活动主体的道德内在相关。可以这样说,经济危机是对道德危机的呈现。可见,经济危机既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经济矛盾、利益矛盾的呈现方式,又是其所具有的道德缺陷的呈现方式。
与经济危机有关的道德危机有两个层面。其一是经济危机本身内蕴着道德危机。这种意义上的道德危机既可能是市场经济欠缺道德的危机,又可能是市场经济道德在内容上的不合理或者错误,还可能是如麦金太尔所说的道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边缘化。其二是经济危机引发了道德危机。作为经济危机的社会后果,道德危机既可能是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认同危机,又可能是道德权威性的丧失甚至道德信仰的危机,还可能是个人道德自律精神的消解和其行为的道德失范。这两者虽然有所不同,前者往往被经济事实所掩盖,后者较易被人们所意识,但却都是有可能出现甚至同时出现的。就后者而言,它一旦出现,那么,如果经济危机越严重、持续时间越久,它就相应越严重,社会道德的自我修复机制就越难建立,道德的重建就越艰难。
本文所论及的道德危机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问题是它具体所指的是什么。当前有一种观念认为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经济没有或者缺乏道德所致的危机。这种看法虽然同主张经济与道德之间的“二分”论或者“划界”论的旨意有区别,但它毕竟承认了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存在着没有道德的情形,也许在主张这种观点的人的观念中道德是被视为外在于并外加于市场经济的东西。其实,市场经济是有其道德基础的,是会内生出某种道德的。因此,与经济危机有关的道德危机不可能是没有或者欠缺道德的危机,而是欠缺某种道德的危机。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边缘化。这种道德的边缘化无非是指道德相对于经济增长或者经济效率而言不被人们所重视。其实,在经济生活中,道德是否受重视与道德是否实际发挥作用并非一回事。经济活动主体可以忽视甚至排斥道德,但其经济行为却离不开道德,内含着道德。只要内含于各种主体的经济活动中的道德是合理的,那么,整个社会就不至于因此而陷入缺德的状态,经济矛盾也不至于变得激化。由此分析可以推知,经济危机所内蕴的道德危机,只是道德内容的不合理或者错误。
这种不合理的或者错误的道德虽然存在于经济生活之中,被经济事实和经济过程所冲淡甚至掩盖,被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追求的肯定所忽视,但它却可以通过经济活动主体处理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解决经济矛盾的态度具体表现出来。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相互对待的态度虽然是始终存在的,但它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却有所不同。在有的经济关系如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富者与穷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中,这种态度会直接地表现出来。如在此次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美国滥用自己所享有的发行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权力,通过美元贬值来缩减对其他国家的债务,直接地损害他国的利益,这表明美国在国际经济生活中过于自私和缺乏诚信。在有的经济关系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中,这种态度则是间接地表现出来的,即它不以经济活动主体一方对待“他者”的利益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而以他对待自己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实现出来。在此,经济活动主体虽然也意识到了自身利益的实现与“他者”的经济行为和利益的关系,但他直接关注的却是自己的独立经济行为,是自己与客观经济过程的联系,以为自身利益的实现是自己运用经济资源的直接结果[2]。经济活动主体独立地运用其经济资源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与“他者”联系起来,各种经济关系因此而得以建立,经济矛盾由此而发生。由于经济活动主体是依据自身利益的预期实现程度即预期利润率来作出其经济决策的,因此,他对其经济资源的实际运用是服从于他对何时、哪一经济部门更能获利的判断的,而不会服从于如何更好地满足大众的需要的考虑,不会包含着对“他者”的道德责任的承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扩大到在另一个前提下还显得远为不足的程度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3](P287-288)。当此时、此经济部门更能获利时,经济活动主体就会大量地甚至疯狂地投资、生产;当彼时、某经济部门的利润率达不到其预期值时,他就会减少甚至中断投资、生产。经济活动主体的这种投机行为是对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和整个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它造成了资本的过分集中和短期内某一生产部门的产品过剩,导致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就可能会诱发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发生的道德根源
经济危机不是被理解为有效需求不足、货币信用过度扩张、贫富差距、政府干预过度或者生产相对过剩等单一因素的危机,而是被理解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恶化状态、经济系统内在矛盾的激化状态,意味着凡是市场经济的各种经济因素和经济行为都与经济危机的发生有关。然而,这并不是说每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都是相同的,相反,其导火索可能完全不同,有时是投资过度、信贷失控、消费不足或者国际游资的冲击,有时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当、政府监管不力,有时是各生产部门比例的严重失调(主要是有的商品生产的过度增长),有时却是国家之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等的经济失衡。道德因素虽然不是这样的导火索,但它却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刻根源。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道德,并不是商品经济社会所存在的所有道德,而是其有缺陷的道德,是不合理的或者错误的道德,准确地说,是自由主义者所论证和提倡的道德。这种错误的道德使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陷入了危机状态,也使人类精神的发展误入了歧途。第二,这种错误的道德是基于私有制经济基础而形成的,是为私有制经济服务的,因而,它必定会反作用于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这就是说,这种错误的道德必定会被经济活动主体所奉行,它深藏于各种主体的经济行为之中,支配着经济活动主体对各种经济关系的处理、不同经济矛盾的解决。第三,迄今为止,这种道德虽然一直存在于经济生活之中,始终对市场经济发挥作用,但它并不能独立地导致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恶化的助推器。这就是说,不合理的或者错误的道德不会随时地引发经济危机,它对经济危机发生的影响要受制于客观的经济矛盾运动。
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道德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主要之处是人们在其经济活动中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的三个道德观念。
第一,个体本位。由于“把社会中的成员转变为个体是现代社会的特征”[4](P43),因而,个体本位的观念是人们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必定会形成的道德观念。其核心就是将个体特别是个人从客观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否定个人与社会的真实联系,倡导个体(尤其是个人)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身上,将自己作为其思考和行为的中心,以自我作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首先,这种观念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它认为,个体先于社会而存在,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更为本位、更为中心的存在,只有个体才是目的,社会只是个体达到其目的的手段。于是,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就会“完全以工具化的方式看待社会”[5](P216),只关心社会对达到其经济目的的价值,要求社会为提高经济效率和利润率而不断地调整自身,不会考虑其经济行为给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不会控制因其对巨大经济效益的追求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其次,个体本位观念强调个体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它对其多样性的强调,既强调整个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又强调这些主体有着多种层次,并强调多样性个体因其存在的客观性而具有维持其存在、满足其需要的合理性。它对其差异性的强调,既强调各种经济活动主体拥有的利益之间的差别性,又强调这些主体在实现其利益的活动方面的不同。正是因为它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强调,导致了经济生活的分化,造成了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与经济活动主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有着不解之缘。
再次,个体本位观念重视个体的独立性和时空有限性。它认为,所有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相对独立于社会和他人的个体,是“视自己为分离的个体……刻意凸显个人意识,强调独立的意志、个人需求和个人的愿望”[6](中文版序P3)的个体,并强调,个体的独立首先是如卢梭所说的“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7](P54),这种独立最终是个体在经济上的独立,经济独立是个体真正独立的根本条件。同时,它认为,个体总是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具有存在的社会历史性和生命的有限性。在市场经济中,个体的独立性和时空有限性最终会共同演化为占有性。因为,其独立性会使个体意识到自己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就如同存在主义者所比喻的被蜘蛛网所困的苍蝇,只能依靠自己;其时空有限性会使个体不再追求终极价值,只寻求现实的和瞬间的物欲满足,以此来消除自己对生命短暂的恐惧感。于是,个体就会借助或者创造相应的条件,不择手段地占有经济资源,毫无顾忌地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自由至上。自由本来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人类生活状态,是人追求其价值并能够被顺利地实现的生活状态。……自由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是一个价值概念”[8]。可是,主张自由市场的人却将其个体化和工具化。自由被个体化,指的是自由不再是人类及其个体的生活状态,而是被理解为只有个体才具有,是个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其所拥有的财产及其他东西的自主支配。自由被工具化,指的是“自由要么是促使效用最大化的手段,要么是保护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的手段”[9](P189)。自由被个体化和工具化的真正用意在于将自由作为一种权利。自由只被承认为权利,既意味着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有权对任何外来的控制予以抵制,这就是说,“自由市场是不受政府或个人小团体控制的市场”[10](P169),又意味着个体有权反对运用再分配的机制去实现平等。于是,自由就被当作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东西,不允许被任何社会力量所侵犯,相反,个体却有权对社会提出不同要求,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自由主义的内容往往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自由主义者可以今天反对教会,明天又拥护教会;在一个时期,他们希望政府对经济事务少干预,在另一个时期又希望政府多过问”[11](P581)。自由至上的观念在商品经济的运行中逐渐形成,因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推动而被提升为“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作为一种普遍的理念,成为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精神支撑。
自由至上的观念要求建立自由市场制度,要求经济活动主体享有全面而又充分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金融自由。它要求摧毁国家之间的金融壁垒,实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允许金融创新。表面上,国际游资的随意流动、低利率和金融工具创新都是经济自由的具体表现,其实,它们却是金融资本的拥有者攫取其最大利益的要求的表达,体现在国家层面,“保护和扩张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逻辑”[12]。且不说国际游资的随意流动和金融工具的创新等会影响他国的金融秩序和逃避国家的监管,仅就金融自由所创造的虚假需求来说,它就会成为生产过剩的主要杠杆,引发经济危机的发生。
其二是投资自由。投资自由是个体尤其是“个人的基本自由之一,就是持有并独自使用个人财产的权利”[13](P316),它主要包括不同经济活动主体即国内外资本拥有者都有权直接投资;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应该允许私人资本的投入,反对经济垄断尤其是国家对某些经济领域的垄断;资本投入有权自由地扩张和集结,反对政府的控制;投资主体有权自由地选择资本的投入或者撤出,不受接受投资方的约束。它有两个相辅相成的直接目的,即增加资本的流动性和使经济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可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为满足或者迎合资本持有者的谋利欲求,投资自由往往演变成了投机,投资由长期变为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意味着不负责任性,变成了对实体经济的不负责任。其结果是不但没有使经济资源通过市场得到最优的配置,反而可能使之最大地浪费,增加了经济风险。
其三是贸易自由。它要求本国在积极合理地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保护本国就业等为借口提高市场准入的门槛;反对滥用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要求实行低关税率。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贸易自由变成了发达国家倾销其过剩产品的一张王牌,造成了国家之间严重的经济失衡。
由上述可见,自由一旦被个体化和工具化,就会引发自由个体之间的经济摩擦,演变为反自由,以致“广大的人民群众实际上享受不到经济学家所设想的‘自由选择’。……垄断生产手段者或其经理成为暴君,为所欲为”[11](P58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求经济自由的个体的最高目的就在于实现其私利。主张经济自由的斯密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他指出:“不仅公众的偏见,还有更难克服的许多个人的私利,是自由贸易完全恢复的不可抗拒的阻力”[14](P42)。这就是说,自由至上必定会变成个体只对自己负责,不对整个社会和他人负责。因此,它就是个人主义精神的构成因素。这种“个人主义精神气质,其好的一面是要维护个人自由的观念,其坏的一面则是要逃避群体社会所规定的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为社会应做出的牺牲。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试图把上述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联合成一体”[15](P308)。
第三,为己取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有个体都是一个有其自身利益并与“他者”的利益相区别的独立主体。由于这种利益是个体得以独立和生存发展的前提,因此,“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16](P101-102),天生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为了应对变幻不定的市场,避免悲惨的命运,把握支配市场的主动权,个体就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打算,追求和增加自己的私人财产。可见,个体“一切的活动都可最终归结为自我保存。由自我保存就发展为利己。利己成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17](P431)。
由于经济活动主体的私利是通过社会来实现的,与“他者”的利益有关,因此,个体的为己取向就会在各个层面呈现出来。首先,它表现为个体对其最大化利益的追求。为了为自己谋取最大化的利益,经济活动主体往往会采取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扩大再生产和根据预期利润率作出经济决策等措施。获取和控制更多的经济资源,会膨胀或者放大个体的逐利欲望,引起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对经济资源的恶性竞争,导致泡沫经济,降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18]。经济活动主体扩大再生产并非为了满足大众的有限消费需求,而“只是为资本而生产”,即“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2](P278),其结果可能会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根据预期利润率作出经济决策,则会使投资者将其资本从前景暗淡的经济领域迅速撤出后大量地投入前景看好的经济领域,造成资本的过分集结,引发经济危机。
其次,为己取向表现为个体不愿意承担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责任。经济活动主体或者态度冷淡,“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13](P27)或者质疑、抵制政府的税收政策,要求降低税率;或者反对福利制度;或者制造股市楼市泡沫,扰乱金融秩序;或者向他国转嫁灾难,肆意破坏生态环境,损害人类的根本利益。其结果是造成贫富分化,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2](P548)。
再次,为己取向表现为个体以他人为手段。“由于市场行为的自由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限制,使得某些人有机可乘,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个人目的的实现。”[9](P15)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拥有者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而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人,只有在劳动力能够为自己带来利润时才会将其雇用,并将这种雇佣变成短期行为,随意解雇工人;抑制工人工资的增长,不改善工人劳动的条件;不合理地推升、哄抬物价;费尽心机诱导消费者消费;如安然、环球电讯公司那样进行公开的欺诈;甚至置他人的健康、生命于不顾。这必定会引发、恶化经济矛盾,影响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
三、主要结论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恶化状态,是经济系统内在矛盾的激化状态。它并非表明任何单一的技术性因素或者经济资源的异常增加,并非经济指标的恶化。单一经济因素的异常增加或者经济指标的恶化(如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负经济增长率),未必表明市场经济运行的恶化,未必引发经济危机。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具有整体性的危机,它是所有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由经济活动主体处理经济关系、解决经济矛盾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对经济危机的把握,应该将定性分析的视角与定量分析的视角、整体视角与个案视角、主体视角与客体视角结合起来。
经济危机虽然破坏了经济秩序,影响了社会发展,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灾难,但它并非全然消极。它虽然不能被理解为合理化的事件,但它却是寻求合理性的契机。它是人们认识和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的发现机制、反省机制和纠错机制。它所蕴含的正面价值并非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并非限于技术革新、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经济运行制度的健全乃至马克思所说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促使人们审视当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社会发展模式和流行的道德价值观念。问题只在于人们是否将经济危机视为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危机,进而也是道德价值观念的危机。否则,经济危机只是曾经且今后仍然会发生的一个经济事件,其全面的积极价值不会被真正发掘。
经济危机是在人们没有及时而又合理地解决经济矛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人为的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领域内所实际奉行的道德,因此,经济危机是道德危机的表征。这是对其进行伦理思考的逻辑前提。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在道德,并非只是市场经济运行中实际存在的如贪婪、失信、欺诈、巧取豪夺等这样的受到人们斥责的道德,更为主要的是由自由主义所提倡和经其论证而被合理化了的、且被经济活动主体普遍地奉行甚至被法律、经济政策等所制度化了的个体本位、自由至上和为己取向等道德观念。后者的合理化、制度化和普遍化,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本性所决定和所要求的,它掩盖并激化了经济矛盾,使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因为道德危机而陷于危机而浑然不知,也使较多的经济学家产生了将道德视为经济的“外生”变量的错觉。
既然经济危机是人为的危机,那么,它就是可以防控的。由于经济危机是所有经济资源、技术性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含着道德危机,因此,人们关于它的防控就可能既有技术性思路,又有伦理思路。这两种思路内含着三种取向,即放任自流、控制和优化。放任自流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防控思路,反对任何外在力量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干预,任凭经济活动主体自发作为,因而,它是消极的方式。控制是凯恩斯主义者或者政府干预论者的防控思路,强调政府积极作为。但由于它聚焦于经济资源的投入、技术性手段的采取,而不是着手对经济矛盾、利益矛盾的彻底解决,因而,它是一种“缺什么补什么”、治标不治本的思路,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尝试性、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会起负作用的思路,是延缓经济危机发生的思路。优化是着眼于理顺经济关系、化解经济矛盾的伦理思路,是对经济危机的道德防控,它要求摒弃市场经济固有其“自然秩序”的神话,对经济运行予以道德批判和道德审视,克服经济运行中的道德缺陷,反思并重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让不同国家、政府、经济组织和个人树立防控经济危机所应有的道德理念,共担治理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
[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向玉乔.财富伦理:关于财富的自在之理[J].伦理学研究,2010,(6):88-92.
[3][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M].上海:三联书店,2002.
[5][加拿大]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A].汪 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三联书店,1998.
[6][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郭进隆译)[M].上海:三联书店,1998.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彭定光.论政治伦理中的自由理念[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1):131-135.
[9][加拿大]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 莘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10][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李 布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12][美]罗伯特·布伦纳.正在显现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新自由主义到经济萧条?[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19-23.
[13][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M].北京:三联书店,1989.
[16][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7]陈岱孙.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8]刘湘溶.消费的伦理与伦理的消费[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2):22-25.
The Moral Crisis behind the Economic Crisis
PENG Ding-guang
(Center for Studying Moral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The economic crisis shows a deterior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caused by its internal conflicts resulting from a co-function of all economic factors and economic behavior,and long economic frictions.It 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sharpening of capitalist basic contradictions,but also reflects the evil consequence prompted by the notion of liberalism morality.The moral values,such as greed,dishonesty,and cheat,are considered as the roots of the present financial crisis.Among other things,individualism,liberalism and egoism,pursued in capitalist morality,played most important roles in bringing about the crisis.Since the economic crisis is the exhibition of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and representation of moral crisis,people have to think about how to prevent and control it by appealing to ethics and morality.
economic crisis;artificiality;moral roots;liberalist morals;mor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82-053
A
1000-2529(2011)04-0031-06
2011-01-2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政府的道德责任及其限度研究”(10AZX005);教育部重大项目“经济危机防控的政府道德责任研究”(10JJD720001)
彭定光(1963-),男,湖南双峰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