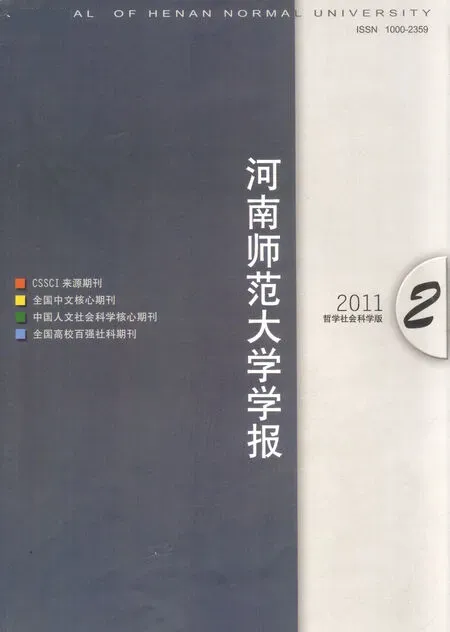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
2011-04-13段自成
段 自 成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57001)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
段 自 成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57001)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主要表现为乡约被赋予基层司法、稽查奸宄和催粮办差等职能。乡约基层司法权威的增加,是老人制度衰落的结果。乡约被赋予稽查职能,则是保甲稽查效果不佳造成的。而清代乡约催科的普遍化,则是以里甲制的衰落为背景的。因此,清代乡约的官役化,不仅是国家权力逐步下移的过程,也是其他基层社会组织职能向乡约转移的结果。
清代;乡约官役化;基层社会组织
清代乡约的基层行政管理职能日益强化,教化和自治功能日益削弱。清代乡约职能的变化,不仅关系清代乡约的性质,而且会引起基层社会组织之间职能的互动。因此,研究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对于研究清代乡约的变迁以及基层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与其他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说明基层社会组织职能互动背景下的乡约官役化模式。
一
清朝乡约和明朝乡约一样,都具有调解民间纠纷的职能,但两者又有差别。明代乡约调解民间纠纷强调公正和公平,一般有宣誓仪式。清代乡约调解民间纠纷时,则出现了显示乡约长权力的威严场面。比如,陕西省安康县的《唐氏祠堂地产纠纷调处碑》记载:知县令乡约调解纠纷,乡约遂将原被双方“传唤隍堂坐前理论”[1]。在东北宾州,乡约于会房受理词讼,“会房门亦悬虎头牌,立军棍”[2](丙编.风土调查)59,俨然公堂。在东北的梨树县,还流传着“些小事村三家,乡约老爷威坐衙”[3]的民谣。另外,清代乡约对民间纠纷的调解也带有强制性。比如,同治年间陕西洋县立的《洋县正堂为民除弊碑》记载:“近来年岁饥馑,田间小窃,不肯经官。乡约私自惩罚,原不欲坏其名节,冀其人自改也。乃近来乡约视为利薮,遇有形迹可疑之事,使人具售状。伊借庙会、船会为名,动辄罚钱数串或数十串文。无钱者折给地亩,乡约自行收租。”[4]303《牧令书》记载:“四川僻邑山中乡约,民间称为官府。词讼必先经其判断,然后闻于官。”[5]44道光年间,江西吉安府的乡约擅自处理盗案,“有指为偷窃者,辄于公所用刑审讯,且将蔑篓包裹,沉入深潭,更难保无诬枉无辜及挟嫌致毙情事。受其害者,多不敢经官控告。即有时控告,该乡约众口一词,州县亦无从申理。”[6]光绪年间,甘肃丹噶尔厅同知王恩海禀称,被当地民众称为“红牌”的乡约,“擅干民词,擅干民讼,甚至……胆敢私立公堂,擅作威福,私设刑具,欺嚇乡民,具有太爷之称。……民间词讼,先经红牌严问一番。如准,之后百姓方敢来厅投呈候讯也”[7](顺序号:17518)。这些例子说明,与明代相比,清代乡约调解民间纠纷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明中后期州县官已将诉诸官府的细小词讼批于乡约理处,而清代官府将细小词讼批于乡约理处的制度逐渐完善。清代官府一般将有疑点的案子交给乡约调查。比如,乾隆《合水县志》记载:“偶有口角是非,批令该处乡约会同公正绅耆查覆。”[8]215青海档案记载:“地方乡约有约束乡民、排难解纷之责,责任非轻,自应认真办公,毋负委任。……如有本府调查事件,务各亲身投案,照例具禀,不准借事推诿,亦不得仍以白禀代呈塞责,致干严提不贷。”[7](顺序号:4574)云南武定州彝族那氏土司档案记载,遇到词讼,知州派差役“协同乡约,查照控词,勘明具禀,以凭校断”[9]。清代官府还可要求乡约调查后提出处理意见,供州县官定夺。比如,《樊山判牍》记载:刘毓林争占堂兄刘毓时遗产一案,樊增祥批令“该村乡约会同族长、户首人等,妥议定规,开列应嗣之人,共同禀案候夺”[10](卷二·14-15)。州县官也可将诉诸官府的细小词讼“交乡约处息”[11]17,但乡约奉命理处的案子的处理结果要禀报官府。比如,《樊山判牍》记载:馆师崔树椿状告李隆不该将其辞退一案,樊增祥“饬差协约查明理处具复”[10](卷二·2);薛德荣与其嫂因经济纠纷而互控一案,樊增祥“饬差协约暨该亲族人等,查明秉公处息复夺”[10](卷三·13)。这种事后禀报,实际是官府对乡约理处细小词讼的一种监督。清代乡约民事纠纷诉诸官府后,原告和被告仍可私下和解。比如,陕西洋县人陈正秀殴打堰长,并恶人先告状,被知县识破,只好“仰托亲友,请同乡约,再四与堰长、田户赔罪,跪求饶免”[4]293。所有这些说明,清代官府司法权力下放的制度更加规范化。
与明代乡约的另一不同是,清代乡约在协助官府执法中还承担其他一些任务。比如,《樊山政书》记载,孟生春与马兴成争夺赎房权一案,樊增祥批示:“其皮箱家具,由西安府饬差会同坊约,查照原单,逐一点验封锁,开单存案。”[12]在直隶朝阳县,“凡地方发生命盗、打伤各案,由事主报知牌头,牌头报之乡约,乡约具报,县署核办”[13]21。在陕南洋县,“凡居乡在山乡约,遇差役持票叫人,必协同传唤。……如案内人或有事故不在家,则责成该管乡约,禀明因何故出外,先使差役回衙,限几日乡约将人送案”[4]302-303。乾隆年间,山东巡抚杨景素奏称:“东省旧例,每村庄数处设立地方一名,或乡约、总保一名。虽名色各有不同,皆以供催征钱粮及拘拿人犯等事之用。”[14]清末,东北临江县的乡约,“掌办关于词讼之和解、拘捕、押送及传达命令等事”[15]1122。总之,乡约在基层司法中承担一些本应由官役承担的职能,在清代已是普遍现象。
清代乡约基层司法权威的增加,乡约协助官府理处词讼的制度化,以及乡约在协助官府执法中承担的其他任务,不仅是州县司法权力下移的表现,也是里老职能向乡约转移的结果。明初,每里设一老人,负责一乡之词讼,一切民事、刑事案件,均应先经当地老人审理,否则即为越诉。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犯罪案件,经里老调处后,即可了结。事涉重者,才诉诸官府。宣德以后,里老制度开始衰落。明中后期,里老普遍勾结官府,肆虐乡里,导致老人制度进一步衰落[16]。及至清代,各地老人普遍淡出历史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乡约被赋予更多的基层司法职能。乾隆《镇江府志》记载,明“律与教民榜文之意,其待里老重矣。奈何初意渐失,人不选充,于是有司视为贱役。其充此役者,亦不复知自爱。乃别有乡约之设”[17]15。顾炎武曾说:“唯老人则名存而实亡矣。今州县或谓之耆民,或谓之公正,或谓之约长。”[18]这些史料说明,清代乡约是由明代老人演变而来,清代乡约基层司法职能的扩大与里老制度的衰落关系密切,是明初老人司法职能向乡约转移的结果。
二
宋代乡约有纠过之责。明代乡约时有纠恶的职能,但其纠恶主要是为了约内教化。及至清代,经常性的稽查已成为乡约的基本职能,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稽查责任的明确化。比如,乾隆《同官县志》记载:“乡约、保正为查察地方之人。”[19]13在山西蒲县,“稽逃亡,察奸宄,又责之各村乡约”[20]。在甘肃合水县,“乡约有稽察保甲”[8]219之责。在江苏盐城,各乡镇“例设乡约一人,奉行官府文告,讥查奸宄,清查户籍”[21]1。顺天府档案记载:“设立乡约、地保人等,原为稽查盗贼奸匪而设。”[22](卷89.号060)在四川什邡县,“城内外及各场市镇设立街约、街保……管理各处公务,巡查匪类,禀报事故等事”[23]4。稽查责任明确后,乡约必须承担失察之责。顺治初年,清廷颁布命令:“隐匿满洲逃人,不行举首,或被旁人讦告,或察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隐匿之人及邻右、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的确。……其邻右、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24]在四川郫县,“凡甲内有一切不法之事,外来面生可疑之人,许牌邻举首,甲约查禀,由县拏究。如敢狥隐,一经发觉……牌、约、甲长,则按罪犯之重轻,分别惩治”[25]2。在陕西朝邑县,王杨氏与奸夫合谋将其夫杀死,“乡约王锡法失于查察,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26]。乡约稽查责任的明确化,说明稽查成为清代乡约的重要职能。
二是乡约要定期向官府汇报约内治安情况。清代乡约要定期赴州县点卯,并向州县官具无事廿结。汤斌在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时,就要求乡约“每月朔望,仍各赴该管官投递有无左道廿结”[27]。山东临淄县为加强对信教之人的控制,“每季取乡约、甲长廿结,报县存查”[28]57-58。山东堂邑县乡约,“每月一报里中有无事故”[29]9。山东金乡县乡约,“每月具结有无讳隐,填记于簿,事发对勘”[30]27。嘉庆皇帝在谕旨中也说:“至乡约、保正,稽查匪类,随时结报,本系编查保甲内应办之事。并著实力奉行,毋得视为具文。”[31]乡约定期向官府汇报约内治安情况,说明乡约稽查在清代已经制度化。
三是乡约的稽查范围扩大。清代乡约除了造烟户册、立门牌外,还有其他一些稽查职能。比如,乾隆年间,兵部左侍郎舒赫德奏称,乡约要将外来流民登记入档,并将不愿入档者逐回原籍,“乡约若隐匿不首,严究治罪”[32]。在东北塔子沟厅,“凡地方发生命盗、打伤各案,由事主报知牌头,牌头报之乡约。乡约具报,县署核办”[13]21。清朝官员杨明时说,唆讼者获“释后,每逢乡约,另查其后行”[33]。清朝法律规定,疯子杀人,“责成亲属、邻佑、乡约、地方、族长人等,报明地方官看守”[15]5871。清代遣犯到新疆后,“由地方官酌量多少,随处安插,交乡约领保”[34]。乾隆年间,山海关外往来解送人犯住居歇店,须“通知屯领催、乡约按户派夫,帮同押解兵丁看守支更”[35]。总之,清代乡约的职能不再局限于社会动乱时期的乡村自卫和常年以教化为目的的纠恶活动,同时还承担了本应由保甲、捕役和营兵承担的任务,说明清代的乡约稽查制度十分完备。
稽查成为乡约的基本职能,固然是因为稽查须与教化结合,方能收到实效,但也与清代保甲制度的效果不佳有关。清朝虽一再强调编查保甲,但保甲稽查多无实效,造成官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弱化。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地方官转而寄希望于乡约稽查。嘉庆年间,河南巡抚马慧裕曾在奏折中说:“保甲一法,本系各省奉行成例,条款章程极为周备。然每有未能尽收实效者,缘保正一役,民间视为在官贱隶,稍知自爱者相戒不肯充当。其承充者均非诚实可靠之人,既不见重于乡党,亦不取信于有司。其始溺于便安,其弊流于徇隐,有名无实。职此之由,应责令地方官出示晓谕城乡村堡,每村堡各举公正信服之士民一二人充为约正,总司保甲事务,……督同保正、甲长,将所管村堡之内烟户男女丁口实数,并有无田产,作何生业,逐一查核确实,汇为总册,呈送地方官。……保甲内如有藏奸为匪,仍责成保正、甲长随时觉举。倘有徇隐,约正即查明具禀,照例严惩。”[36]湖南巡抚富勒浑在述及保正之外宜添设约正、约副的原因时说:“保正所辖,虽户口有畸零不等,总在千家上下。人居稠密之地,在数里内者,尚易查察。其山陬僻径、路险途遥之区,一人之耳目究恐难周。且保正统率牌甲,纵有弊端,他人不敢稽报,或致任所欲为。应请于保正之外,遴选老成持重、众所钦服之贡监生员一人以充约正,粮多大户内选择一人以充约副,听其稽查保正之公私以及保内民人之良莠。至于外来人户所有保结,亦听该约正、副查核明确,方准保正入册。如有奸匪潜藏,该保狥玩,许其据实密禀地方官。……其余地方事务,仍令保正照常办理。……庶保正知所警畏,而地方更有裨益。”[37]由此可见,清代乡约被赋予稽查职能,确与保甲制度的衰落有关。
三
明中后期就有乡约劝民交纳钱粮的记载,但乡约负责征派赋役直到明末仍是个别现象。清代乡约官役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各地乡约普遍具有催科的职能,但不同地区乡约负责催科的情况不尽相同。清代许多地方的乡约具有催征赋税的职能。比如,雍正年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称:“凡切近河洮、岷州内地番人与百姓杂处者……但就其原管番目,委充乡约、里长,令催收赋科。”[38]26前已有述,乾隆年间的山东巡抚杨景素曾说,山东省的乡约,皆供催征钱粮及拘拿人犯等事之用。在东北宾州,“催收学警垧捐、大小租赋、田房契税等事,向归乡约经理”[2](乙编.公牍辑要·7)。清代一些地方的乡约不仅负责征派赋税,而且负责办差。比如,顺天府档案记载,宝坻县的乡约有“承催租粮,办理差务”[22](卷90.号108)之责。在新疆地区,不仅征收赋税,“非用乡约,则呼应不灵”[39],而且“有大兴作徭役,乡约分檄各长,皆咄嗟立办”[40]。在云南姚州,“凡钱粮、夫马、杂派,乡约、巡捕责之保长,保长责之烟户”[41]18。左宗棠记载:“北五省及关内外各州县征收钱粮之外,均有差徭……丁役取其一,而承差头人、乡约、里正又倍之。”[42]清代一些地方的乡约只负责办差。比如,民国《重修汝南县志》记载:“同光之际,城乡各店有首事、保正、乡约等名目,职在分布政令,调息讼事,侦察奸宄,办理差徭。”[43]4在云南马龙县,“乡年轮乡约六人,堡年轮乡约三人,专供力役而已”[44]10。同治皇帝也说:“各直省州、县向有保长、乡约等名目,原为稽查保甲、承办差徭而设。”[45]尽管清代各地乡约催粮办差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乡约负责催科在当时是普遍现象。
清代乡约催科的普遍化,与里甲制的衰落有关。明初设里甲,用以征派赋役。清初沿用明代的里甲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流动加快,土地产权变化频繁,而原有的里甲编制并没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造成赋役不均,进而威胁到国家税源的稳定。比如,山东新城县“庄村杂乱……每一里人户又散居各约。其共约者,多不共里,里差不能画一。共里者多不共约,催粮奔走艰难”,且有“里甲不均之弊”“强弱不平之弊”“比较不公之弊”“花费民财之弊”“侵欺国课之弊”,致使“每至奏期,钱粮拖欠,在官不免有赔垫之艰,在民不免有敲扑之苦”[46]1-4。山东新城县里甲编制混乱导致赋役不均、税源不稳的例子,是清代全国各地真实情况的一个缩影,它表明里甲传统的僵化编制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变迁,难以有效控制花户,无法确保国家税源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传统的赋役征派制度,由按地域编制的乡约承办催科,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比如,乾隆《光山县志》记载:“编审一役,稽土田而籍生齿。……顾其制数载而一举,其法繁重而难行。比里而次之,里不一里也;计甲而按之,甲不一甲也;人人而呼之,人不一人也。道途跋涉,时日羁延。……今邑侯杨公又恻然念之,取籍于保约而民不出闾阎。”[47]22咸丰《清河县志》记载,该县连年水冲地毁,人少差繁,人丁逃亡严重,以致“地丁交困,逋之益多……总累现户。每正编一两,加补额银一两三钱,至有一丁而输额鞭数两不等。……虽屡至编审之期,止令里长、甲头填写册籍。故者仍生,逃者仍在,老者虽至七八十岁不除,幼者或始三四五岁亦列。富者反轻,贫者益重。偏枯偏累,弊窦丛生。邑侯管公檄到之日,聚一邑之耆庶,与之更始……举里甲乡镇之素有德望者,设为里评、甲评、约评、寓评,秉公编审,逐户细勘”[48]3-4,从而克服了里甲制度的弊端,保证了税收的完成。道光重修《宝应县志》记载,“康熙年间,民户多所迁徙,非复土著。而其册籍未能随时更易,遂有居在邑而籍在野,户在南而田在北者。于是乡图之名徒存虚册,寝久且失其故处。而凡公事之所管辖,赋税之所催科,在城改为九铺,在野更为三十三庄”[49]3,各铺、各村均设置乡约。可见,乡约被赋予催粮办差职能,确实是里甲制度衰落造成的。而清代各地乡约催粮办差情况的差异,其实是各地里甲职能向乡约转移的进程或程度的不同造成的。
由以上可知,在老人制度消亡、里甲制度没落和保甲制度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清朝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基层行政组织,以强化州县行政,巩固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而清代乡约的官役化,恰好适应了这一需要。清代乡约的官役化是老人、保甲和里甲的职能向乡约转移的结果。因此,清代乡约的官役化,不仅是国家权力逐步下移的过程,而且是其他基层社会组织职能向乡约转移的结果。
[1]张沛.安康碑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147.
[2]李澍恩.吉林行省宾州府政书[M].宣统二年铅印本.
[3]奉化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426.
[4]陈显远.汉中碑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5]徐栋.牧令书:卷八·屏恶[M].道光戊申年兴国李炜校刊本.
[6]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60.
[7]青海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青海档案[Z].
[8]合水县志:下卷[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9]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Z].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263.
[10]樊增祥.樊山判牍[M].民国年间法政讲习所印行.
[11]怀远县志:卷二·风俗[M].民国17年横山县志局石印本.
[12]樊增祥.樊山政书: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7:68.
[13]阜新县志:卷一·地理志[M].民国24年铅印本.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328-060[Z].
[15]徐世昌.东三省政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16]王日根.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J].厦门大学学报,2003(2).
[17]镇江府志:卷五·户口[M].乾隆十五年增刻本.
[18]顾炎武.日知录:卷八[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70.
[19]同官县志:卷四·风土志[M].民国21年铅印本.
[20]蒲县志:卷四·学校[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248-249.
[21]续修盐城县志:卷九·警卫志[M].民国25年铅印本.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顺天府档案[Z].
[23]什邡县志:卷七·户口[M].嘉庆十八年刻本.
[24]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444.
[25]郫县志:卷四十四·保甲[M].同治九年刻本.
[26]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4册·奏折[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54.
[27]汤斌.汤子遗书:卷二·陕西公牍[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481.
[28]淄川县志:卷七·艺文志[M].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29]堂邑县志:卷三·公署[M].光绪十八年刻本.
[30]金乡县志:卷四·兵防[M].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31]仁宗睿皇帝实录: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892.
[32]高宗纯皇帝实录: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689.
[33]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二·吏政八·守令中[M].北京:中华书局,1992:562.
[34]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九[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1123.
[3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六一·盛京刑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51.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朱批奏折:档号04-01-02-0024-001[Z].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朱批奏折:档号04-01-02-0017-003[Z].
[38]循化志:卷一·建置沿革[M].道光年间刻本.
[39]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153-154.
[40]袁大化,王树枬.新疆图志:第3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1728.
[41]姚州志:卷三·食货志·力役[M].光绪十一年刻本.
[42]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16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6:14337-14338.
[43]重修汝南县志:卷七·民政[M].民国27年石印本.
[44]续修马龙县志:卷三·地理志·乡屯[M].民国年间抄本.
[45]穆宗毅皇帝实录:第3册[M].台北:中华书局,1987:523.
[46]新城县续志:卷下·顺约编里条约[M].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47]光山县志:卷二一·艺文五·记下[M].光绪十五年补刻本.
[48]清河县志:卷七·民赋上·户口[M].同治元年补刻本.
[49]重修宝应县志:卷七·铺庄[M].道光二十年汤氏沐华堂刻本.
[责任编辑孙景峰]
OntheEnhanceoftheAdministrativeFunctionofXiangyueinQingDynasty
DUAN Zi-cheng
(Henna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The Enha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of Xiangyue mainly marked its function to levy tax, maintain law and order, and refer some settlements because of the decline of the system of Lijia, Old man and Baojia.Therefore,som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transferred from the office and the other local organization to Xiangyue.
Qing dynasty;administrative function of Xiangyue;the local organization
K249
A
1000-2359(2011)02-0213-05
段自成(1963-),男,河南唐河人,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770012)
2010-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