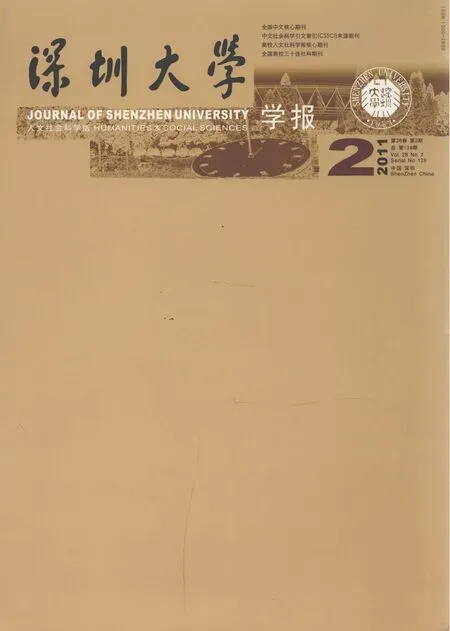论康德的“第三种自由”
2011-04-12苏娅
苏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论康德的“第三种自由”
苏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因为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以及法权的自由。其中,康德的“第三种自由”,即法权自由作为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弥补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不足之处,而且构成了人们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基础。
康德;自由;法权;幸福
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两部著作中所涉及到的自由概念至少包含了先验的自由与实践的自由两层含义。随着学者们对于康德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以及“自由即自律”等思想的深入研究,康德自由概念的这两层含义已经普遍为人所了解。但事实上,康德的自由概念还包含另一个重要含义,即法权的自由。这一意义上的自由不仅是一把打开康德政治哲学与法哲学思想之门的钥匙,更是深入理解和阐释康德道德哲学的必由之路。亨利·阿里森指出,外在的自由或行动的自由概念是康德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中心概念[1]。而国内的康德研究者也曾撰文指出,康德的自由概念包含3个层次,分别是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以及自由感。在康德自由概念的第三个层次,即自由感中又包含了审美鉴赏的自由感和社会历史中的“自由权”(言论自由、立法自由、财产权等)[2]。可见,法权的自由作为不同于先验的自由与实践的自由的概念,可以被看作是康德的“第三种自由”。
一
康德的“第三种自由”,即法权的自由是建立在法权概念的基础上。事实上,德文中的法权(Recht)一词包含了两层含义,分别是权利(Right)与正义(Justice)。在不同的语境中,Recht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含义。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Recht一词主要指权利,即法权,而recht作为形容词则可以理解为“正当的”,也就是“具有法权的”。在康德看来,“法权就是自由法则之下的任性这样一个纯粹实践理性概念。”[3](P256)具体而言,“法权是一个人的任性能够在其下按照一个普遍的自由法则与另一方的任性保持一致的那些条件的总和。”[3](P238)可见,康德的法权概念与其任性概念息息相关,所以,要理解康德的法权概念必须先弄清康德如何理解人的任性(Willkür)概念。
康德是这样理解任性概念的,“人的任性是这样的任性:它虽然受到冲动的刺激,但不受规定,因此本身(没有已经获得的理性技能)不是纯粹的,但却能够被规定从纯粹意志出发去行动。任性的自由是它不受感性冲动规定的那种独立性。这是它的自由的消极概念。积极的概念是:纯粹理性有能力自身就是实践的。”[3](P220)所以,在康德那里,任性可以被看作是介乎于自由意志与自然偏好的中间概念。因为人的任性是一种感性的任性,它必然会受到自然偏好的影响,但却不是一种动物性的任性,它并不必然受自然偏好的决定,“因为任性就它以生理变异的方式(由于感性的动因)受到刺激而言,是感性的;如果它能够以生理变异的方式被必然化,它就叫做动物性的(arbitrium brutum[动物性的任性])。人的任性虽然是一种arbitrium sensitivum[感性的任性],但却不是brutum[动物性的],而是liberrum[自由的],因为感性并不使其行为成为必然的,相反,人固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决定自己的能力。”[5]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任性概念一端连接着实践的自由,而另一端却连接着自然的偏好。
所以,在康德看来,人的任性既可能遵循道德法则,也可能屈从自然偏好。因此,不同个体的任性之间需要法权来协调,进而起到保障每个人的外在自由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康德指出自由是惟一的、源始的法权,“自由(对另一个人的强制任性的独立性),就它能够与另一个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并存而言,就是这种惟一的、源始的、每个人凭借自己的人性应当具有的法权。”[3](P246)这种法权的自由就是康德的“第三种自由”。这种自由不再意味着绝对的意志自律,而是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自由。
康德的“第三种自由”,即法权自由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它解决了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两大难题。第一,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只有当道德法则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时才能构成德性。但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很难直接判定自身或他人意志的规定根据。康德也承认“因为对于人来说,如此看穿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以至于他往往只是在一个行动中就能完全确知,其道德意图的纯粹性和意向的纯洁性是不可能的,即便他毫不怀疑这个行为的合法性。……就每一次行为而言,究竟有多少纯粹道德的内容处于意向中,对他们自己来说依然是隐秘的。”[3](P405)可见,在实际生活中,道德义务的约束力有限,所以,对于人的外在行为的合法性规范就具有重要意义,而康德对于自由法权的探讨就为人的外在行为的合法性划定了界限。所以,康德的这一思想有效弥补了仅以道德义务协调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所产生的缺陷与不足。
第二,康德长久以来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个持有严格的形式主义与普遍主义伦理学观点的哲学家[6],因为在康德的大多数研究者看来,幸福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占有的地位并不高,但幸福自古希腊以来就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幸福问题也是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在探讨伦理问题时最难绕过的问题之一。佩顿(H.J.Paton)曾指出,康德将追求幸福看作是低于道德的实践理性的功能[7]。康德确实认为,“幸福只是有条件的目的,因而人惟有作为道德存在者才能是创造的终极目的”[8](P454),但康德也同时认为,“幸福原则与道德原则的这一区分并不因此就马上是两者的对立,而且纯粹实践理性并不要求人们放弃对幸福的要求,而是仅仅要求只要探讨义务,就根本不考虑幸福。”[8](P99)所以,正如维多利亚·威克(Victoria S.Wike)所指出的那样,认为康德的义务伦理学是对幸福的拒绝的看法并非完全错误,只不过并不完全。康德确实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及《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中否定了幸福能够作为道德规范的根据、动机或原则,但这并不表示幸福没有其他积极意义[9]。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笔者将证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等著作中对于自由法权的阐释就说明康德肯定了人具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康德的这一思想不仅澄清了他对于人追求自身幸福的认同态度,而且有效反驳了康德研究者们对其思想的质疑和批评。
二
正如艾伦·伍德(Allen Wood)所认为的那样,康德将法权与道德相分离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当依靠人们的德性不足以确保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来保障我们的外部自由[10](P323)。在这个意义上,法权自由作为康德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可以被看作是对其道德哲学的一个必要补充。因为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既可以看作是对道德性的规定,也可以看作是对合法性的规定,“与自然法则不同,这些自由法则叫做道德的。就这些法则仅仅涉及纯然外在的行动及其合法则性而言,它们叫做法学的;但是,如果它们也要求,它们(法则)本身应当是行为的规定根据,那么,它们就是伦理的。这样一来人们就说:与前者的一致叫做行动的合法性,与后者的一致叫做行动的道德性。与前一些法则相关的自由只能是任性的外在应用的自由,而与后一些法则相关的自由不仅是任性的外在应用的自由,而且也是其内在应用的自由,只要它是由理性法则规定的。”[3](P221)
所以,法权的普遍原则并不是对人的准则作出要求,而是对人的行为作出要求。“一种严格的(狭义的)法权,人们只能称之为完全外在的法权。现在,这种法权虽然基于每个人根据法则的责任意识,但据此来规定任性,如果它应当是纯粹的。它就不可以也不能够根据这种作为动机的意识,而是因此就立足于一种外在的、与每个人根据普遍法则的自由都能够共存的强制之可能性的原则之上。”[3](P240)由此可见,在康德那里,法权概念并非用于判定一个人的行为的目的是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而是用于判定这个人的行为本身是否合乎法则。正如艾伦·伍德(Allen Wood)所认为的那样,法权并不直接命令我们去做什么或不去做什么,而是仅仅告诉我们什么是正当的(recht)[10](P322)。
虽然在康德看来,法权自由来源于先验自由,“我们惟有通过道德命令式才知道我们自己的自由(一切道德法则,进而甚至一切权利和义务都是由这种自由出发的),道德命令式是一个要求义务的命题,随后从这个命题中可以展开使他人承担义务的能力,亦即法权的概念。”[3](P249)但是,作为法权的自由本身具有不同于先验自由的全新涵义。在康德那里,先验自由从消极的角度看是不受偏好影响的独立性,即自由的任性;从积极的角度看是理性为自身颁布道德法则的可能性,即自由的意志。但法权的自由,从消极的角度看是对另一个人的强制任性的独立性。从积极的角度看是在行为的合法性的前提下,追求自我目的的自由。
针对这一点,有研究者指出,康德在法权论中使基于欲望的权利通过外在的自由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但是,康德在法权论中所提出的外在自由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所阐述的内在的先验自由似乎并不一致[11](P84)。该研究者试图弥合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之间的裂隙,他指出康德提出外在自由并非取消人的自律,因为虽然康德明确区分了法权义务与伦理义务,但无论是法权义务还是伦理义务都必须服从道德法则而不是明智原则。所以,该研究者认为,虽然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康德的法权论中具有重要的合法的地位,但这并不表示康德的法权论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之上[11](P85-112)。
确实,正如该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康德强调,“一种一般而言的外在法权的概念完全出自人们的相互外在关系中的自由概念,并且与所有人自然怀有的目的(对幸福的企望)以及达到幸福的手段的规范根本无关。”[12](P292-293)但事实上,康德的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一致性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一点上。因为外在自由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取消了人在道德上的自律。首先,从形式上看,外在法权是人的共同意志的产物,作为个体的人虽然处于强制性的法权之下,但是就全体的人而言,则仍是自我立法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康德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最终会导向道德上的完善,人类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从外在自由的实现转向内在自由的实现。
虽然康德认为法权的根据不是幸福,但康德并不因此认为人无权追求幸福,恰恰相反,人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正是法权自由的重要内容。康德指出,“对于一个共同体的制度来说,我以如下程式来表述这种自由的原则:没有人能够强迫我按照他的方式(他设想其他人的福祉的方式)去得到幸福,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沿着他自己觉得恰当的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不损害他人追求一个类似目的的自由(亦即他人的这项法权),这种自由是能够按照一种可能的普遍法律与每个人的自由共存的。”[12](P293-294)“要首先考虑的公共福祉恰恰是通过法律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那种有法律的宪政,在这里,只要他不损害那种普遍的合法的自由,从而不损害其他同为臣民的人的法权,他就可以随意地沿着他认为最好的任何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12](P302)
可见,在康德看来,追求幸福的权利包含在自由的法权之中。其中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决定对于自身而言什么是幸福的权利;“因为人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至少能够防免自己的不利,其规范并不是诫命。它们绝对不约束任何人;而且在一个人受到警告之后,如果他乐意忍受自己的遭遇,他可以选择他觉得恰当的事情。”[12](P291)第二,决定用什么手段去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因为“两个相对立的行动就可能都是有条件地善的,只不过一个比另一个更善而已(后者因此就会叫做相对恶的);因为它们不是在种类上,而是仅仅在程度上彼此有别。一切不是以无条件的理性法则(义务),而是以我们任意地奠定为基础的目的为动机的行动,其情况都是如此。因为这个目的属于一切目的的总和,这个总和的达成被称为幸福;而对于我的幸福,可能一个行动贡献更多,另一个行动贡献更少。因而一个行动比另一个行动更好或者更坏。”[12](P285)
不仅如此,康德还深刻阐释了政府职能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政府应当尊重和保护公民追求自身认定的幸福的权利,而不是由政府或国家元首来为公民决定什么是应当追求的幸福或者应当如何追求幸福,因为这样一来,公民的个人权利就被剥夺和侵犯,而这就意味着政府是最大的专制主义。康德指出,“若一个政府,建立在就像一个父亲对于子女那样对于人民的仁爱的原则之上,也就是说,是一个父亲的政府(imperium paternale),因此,臣民们在这里像不能分辨什么对自己真正有利或者有害的子女,被迫仅仅采取被动的态度,以便对于他们应当如何得到幸福,仅仅期待国家元首的判断,而对于国家元首也愿意这样做,则仅仅期待他的善意;这样一个政府,就是能想得出的最大的专制主义(这种宪政取消臣民的一切自由,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任何法权)。”[12](P294)
正如保罗·盖耶尔(Paul Guyer)在《康德论自由、法律以及幸福》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康德的真正观点在于如果政府干涉公民对于幸福的不同概念,继而干涉他们的信仰和个人目的,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专制的,政府唯一能够干涉的是幸福的来源,即他们追求幸福的手段。因为他们追求幸福的手段必须是平等的,这只有在一个公民社会中才能实现[6](P267-268)。当然,保罗·盖耶尔(Paul Guyer)这里所指的政府唯一能够干涉的是幸福的来源,即他们追求幸福的手段并非是指政府规定公民追求幸福的手段,而是限制公民追求幸福的手段,这种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就在于公民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具有自身的限制,即不能干涉他人同样的权利,即他人追求自身幸福的自由。
四
在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中不止一次指出幸福的来源或条件必须是道德,但在这里,康德对人的行为动机避而不谈,仅仅着眼于人的外在行为,从而得出人具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法权的结论,这两种观点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事实上,这种差异与其说是康德思想发生了转变,倒不如理解为康德的视角发生了转换。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康德运用了一种全视的视角或上帝的视角,因为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才能谈论人的真实动机。在这个基础之上,康德的道德哲学才能成立。而康德在政治哲学以及历史哲学中对追求自身幸福的肯定则出于一种发展的视角,这种视角体现在康德对于人类普遍历史理念的构想中。
康德与启蒙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认为人类的历史呈现一种进步与发展的趋势,他指出,“无论人们在形而上学观点上关于意志自由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意志的显象,即人的行动,毕竟与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都是按照普遍的自然法则被规定的。无论这些显象的原因隐藏有多深,以叙述这些显象为己任的历史仍然可以使人希望:当它宏观地考察人的意志之自由的活动时,它能够揭示这种自由的一种合规则的进程;而且以这种方式,在个别的主体那里杂乱地、没有规则地落入眼底的东西,在整个类那里毕竟将能够被认做其原始禀赋的一种虽然缓慢,但却不断前进的发展。”[12](P24)与康德惯常的审慎态度有所不同,康德对人类的历史发展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他指出“我可以假定:既然人类在作为其自然目的的文化方面不断向前推进,则这种推进也包含在它的存在的道德目的方面向着更善的进步中,而且这种进步虽然时而被打断,但绝不会被断绝。”[12](P313)
所以,在康德看来,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虽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与对抗,但在历史的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最终会导向道德上的完善,并使整个人类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康德指出,“正是这种对抗,唤醒人的一切力量,促使他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在求名欲、统治欲和占有欲的推动下,在他的那些他无法忍受,但也不能离开的同伙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这时,就迈出了从野蛮到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真正说来就在于人的社会价值;于是,一切才能都逐渐得到发展,鉴赏得以形成,甚至通过不断的启蒙而开始建立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能够使道德鉴别的粗糙的自然秉赋逐渐转变成确定的实践原则,并且就这样使形成一个社会的那种病理学上被迫的协调最终转变成一个道德的整体。”[12](P28)
综上所述,康德从先验的自由与实践的自由出发,提出了他的“第三种自由”,即法权的自由。这一概念旨在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它不仅弥补了道德义务在约束人的行为上的不足之处,而且为个体的人提供了追求自身目的的可能性,在这其中就包含了人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在这种权利的保障下,人不仅能决定将什么作为自己的幸福,而且可以决定将何种途径作为追求自身幸福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第三种自由”,即法权的自由不仅使康德的自由概念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而且增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完善性,建立了康德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得康德的哲学思想具有更深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但无可否认的是,康德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构想仍然是通过人类的道德完善来达成至善的最终实现,而绝不是仅仅停留在人的外在行为的协调上。因为在康德看来,如果人类没有结合成为道德的共同体,那么人类也永远无法实现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永久和平。这样一来,个人的法权自由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康德的“第三种自由”虽然是人类走向道德完善的必由之路,但如果人类仅仅停留在这种外在自由之上,那么人类就永远无法进入到一个至善的世界。
[1][美]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M].陈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
[2]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8-405.
[4][德]康德.康德书信百封[C].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1.
[5][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31-432.
[6]Paul Guyer.Kant on Freedom,Law,and Happines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i,267-268.
[7]H.J.P aton.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A Study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85.
[8][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Victoria S Wike.Kant on Happiness in Ethics[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27-28.
[10]Allen W.Wood.Kant’s Ethical Thought[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1]Katrin Flikschuh.Kant and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2][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湜得】
On Kant’s“Third Freedom”
SU Ya
(School of Philosophy,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Kant’s concept of freedom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concepts of Kantian philosophy,becaus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meanings,namely,transcendental freedom,practical freedom and liberty of right,which is Kant’s“third freedom”.As the core of Kant’s legal philosophy,it not only makes up for the inadequacies of Kant’s moral philosophy,but also form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right to pursue their own happiness.
Kant;liberty;right;happiness
B 516.31
A
1000-260X(2011)02-0029-05
2010-10-20
苏娅(1983—),女,浙江诸暨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