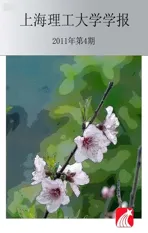英汉法律翻译教学面面观
2011-04-12傅敬民
傅敬民
英汉法律翻译教学面面观
傅敬民
(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上海 201400)
英汉法律翻译作为特殊用途翻译(Translation for Specific Purpose,TSP)目前日益受到关注。文章结合教学实践经验,对法律翻译的特殊性、教学目标、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探讨。同时指出,法律翻译教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围绕教学的方方面面予以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特殊用途英语;法律翻译;教学;
一、法律翻译教学现状
作为特殊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简称ESP)中一项重要的分支,法律英语已经成为目前许多高校中的专业英语,与此相匹配的是越来越受重视的英汉法律翻译教学。当下翻译研究对翻译类型的认识,较之于上个世纪已经更为深刻和广泛。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或者说翻译理论的形成,源自于对宗教经典翻译的实践,这一点中外皆然。只不过西方翻译理论的源头在于对《圣经》的翻译,不同文字针对《圣经》原文进行逐字逐行的对照翻译,构成了一切翻译的原型或理想;而中国翻译理论的源头来自于佛经的翻译,之后又经历了明末清初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以严复为代表的社会政治翻译。“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确切地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起,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摆脱了殖民者的统治并宣告独立,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经济、科技、商业等实用性文献成为翻译的主要对象,而在传统翻译历史上长期居于翻译中心地位的文学翻译则逐步退出翻译的中心。”而随着“实用性文献成为翻译的主要对象”,实用翻译教学也越来越受到翻译教学的关注。
但是,对于“实用翻译”这个概念本身,目前我国翻译界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许多冠以“实用翻译教程”之名的翻译教材并非关注于实用类文献的翻译教学探讨,而只是着重提示读者该教材对翻译学习或者教学具有实用性。方梦之教授在其编著的《实用文本汉译英》中,借用了法国翻译理论家Jean Delisle的定义:以传达信息为根本目的,运用语用学的原则来翻译实用性文本。这类文本几乎包括文学以及纯理论文本以外的人们日常接触和实际应用的各类文字,涉及对外宣传、社会生活、生产领域等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了科技、报刊与外宣、经贸、法律文化翻译等。而林克难教授则采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Mary Snell-Hornby教授的分类法,将实用翻译划分在文学翻译与特殊用途翻译之外,大致包括新闻翻译、广告翻译、电影(字幕、片名、配音)翻译、公示语翻译等,而将科技翻译、商贸翻译、法律翻译划在专门用途翻译范畴内。从翻译的文本类型而言,除了文艺作品(artistic works)翻译以外,其他各类凡以客观信息沟通为实用目的的翻译,如科技翻译、新闻翻译、广告翻译、公示语翻译、旅游翻译、公文翻译、政论文翻译、商贸翻译、法律翻译等,都属于实用翻译之范畴。这里所谓的实用翻译,指的是翻译的目的或者目标乃实用性的、特殊领域的,而非翻译实践过程的可操作性。所有的实用翻译都是源自某个特殊的领域、为了某个特殊的目的而进行的。它与文艺翻译的最大区别,在于实用翻译往往与某个专项知识领域紧密相联,有其专门的术语和语篇结构,需要译者对某个专项知识有所了解。诚然,任何翻译都不可能与其他种类的翻译之间存在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差异。各类翻译之间在翻译原则、翻译技巧方面的通用性、互涵性是翻译之所以可以独立为一门专门学科的主要原因。
但是,就法律翻译而言,它与文学翻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不仅体现在法律语言不同于文学语言,有其独特的词汇结构、句法结构、文体特征以及翻译要求,而且在法律文化、法律体系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不同属性。这就促使人们将法律翻译与其他翻译区别开来,并进行独立的研究。同时,它也要求在翻译教学中予以相对独立的对待,开辟相对独立的法律翻译教学体系。事实上,继科技翻译教学、商务翻译教学之后,我国的法律翻译教学在近几年异军突起,显然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实用翻译教学的又一重要领域。可是,与科技翻译、商务翻译等实用性翻译教学的研究相比,法律翻译教学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研究成果上,都显得比较薄弱,存在较大的差距,有许多的课题亟待解决。依作者多年从事翻译教学和法律语言教学的经验来看,其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律翻译这一活动的特殊性以及不同法系所引起的词语差异认识不足、教学目标不明确、师资队伍建设不完备、教材比较混乱、缺乏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等。本文拟对上述几个方面予以浅显的分析探讨,以求教于大方。
二、法律翻译的特殊性
法律翻译实践属于特殊用途翻译(Translation for Special Purpose,TSP),是针对特殊用途文本进行的翻译实践领域。法律翻译的特殊性,如果微观地分析起来,当然有许多具体的表现,但如果从宏观的视角予以审视,则不妨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独特的法律语言。顾名思义,法律语言由法律与语言交叉而成。语言是法律得以产生的媒介,是形成法律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尽管“道德或习俗也许根植在人类的行为中,但是法律——实际上根据其定义——却只是通过语言形成的”。法律语言的特殊性,首先源自于法律本身。法律之所以特殊,在于“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用于规范和约束全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具有无上的权威性和规定性”。也就是说,运用于法律的语言,它的功能并不满足于表达意义,传递信息,同时还要对人的行为给予规范,从而引导、影响或者调整人的行为。
如前所述,法律文本不同于文学文本,不像文学作品那样需要烘托气氛,调动读者的感情,让读者产生阅读的快感。因此,法律文本中每一个词语都是有目的地被赋予相对确定的含义,尽量减少模糊的解释空间。另外,法律从一开始就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而是“自上而下”的产物。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以伸张正义为宗旨,但法律最初产生时却是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其统治而制定的,法律语言从一开始就源自于统治阶级或者说上流社会。英语发展史告诉人们,法律英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语和拉丁语。1066年诺曼底征服英格兰之后的300年间,法语一直都是英国的官方语言,完全运用英语来制定法律,最早也不过是公元1489年以后的事。在此之前,英国的法律语言基本上是以拉丁文、法语为主的。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法律语言,起初自然不为普通百姓所理解。而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为了显示法律的庄重,还是为了保持该行业的特权,法律的从业人员普遍继承了“法言法语”的传统。对此彼得·古德里奇指出:“法律话语是通过级别、地位、权力和财富这些高度可视的组织性和社会语言标记由社会和机构授权的——证实的、合法化的和认可的。……法律是对授权的和组织的公共暴力进行垄断和编篡。”尽管近代也进行过法律语言平民化运动,但收效甚微。当下的法律英语继续保留着诸多有别于日常英语的区别性特征。这些区别性特征,有人将之归纳为规范性(normative)、述行性(performative)和技术性(technical)。也有专家更为具体地指出:“传统的法律文本大多不使用标点和现代版式;大量使用被动语态;使用长而复杂的句子结构;使用名词化等语法隐喻;使用专业术语、古语和其他语言的词汇和表达法;使用复杂的语法结构,等等。”就目前国内出版的法律英语文献中,陶博、龚柏华编著的《法律英语》就法律语言的主要特征,尤其是法律词语的特征予以了相对全面的论述:1)经常使用常用词汇的不常用的含义;2)经常使用曾经常用但现在已很少使用的古代英语和中世纪英语的词汇;3)经常使用拉丁语单词和短语;4)使用一般词汇表中不会有的古法语及法律法语中的词汇;5)专门术语的使用;6)行话的使用;7)经常使用官样文章用语;8)刻意使用具有可变通含义的词汇和短语;9)力求表述精确;10)冗长性、保守性和精确性。因此,“学习法律的第一要务是学习法律的语言,以及与之相符的、使得该语言知识能够在法律实践中得到应用的语言技能”。
第二,中国法律与英美法律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律虽然融合了中国法律传统以及马克思理论中的共产主义法律理念,但其根本却是基于大陆法系发展而来的。大陆法系又称为民法法系,法典法系、罗马法系、罗马—日耳曼法系,它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首先产生在欧洲大陆,后扩大到拉丁族和日耳曼族各国。历史上的罗马法以民法为主要内容。法国和德国是该法系的两个典型代表。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首先产生于英国,后扩大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以及附属国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到18世纪至19世纪时,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英国法被传入这些国家和地区,英美法系终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法系之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历史传统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法律中某些概念的认识不尽相同。“深谙法律文化的译者都知道,不同法律传统孕育的法律概念鲜有完全对等的。”“如果我们以基于大陆法系的固有思想模式和理念去理解和参悟普通法系的法律文化,且用我们的法律汉语术语去硬套英、美的法律术语,难免会在法律语言文化交际以及翻译过程中产生错位或谬误。”比如,中国法律中运用“正当防卫”一词,突出法律的正当性,而在英语中,则称为“self-defense”,强调个体的自我防御性。又如,法律汉语中“陪审员”不能简单地翻译为“juror”,因为,中国民诉中陪审员虽然是一审案件中可与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并与审判员有同等权利义务的人,但实际上对于最后决定“有罪”或“无罪”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而英美法中的“juror”在很多场合下则直接进行决定“有罪”还是“无罪”。况且,即使在英语国家中,英国法律英语和美国法律英语也不尽雷同,比如在英国,“table a motion”意为“提出动议以供当下讨论”,而该词语在美国却意指“将动议搁置,留日后讨论”。又如,“劳动法”在英国法律中常用“employment law”,但在美国则用“labor law”。凡此种种,都对法律翻译造成障碍,也必须成为法律翻译教学的重点内容。
第三,复杂的法律翻译范畴。法律翻译不像文学翻译那样,可以较为清晰地根据文学种类划分出诗歌、戏剧、小说等不同的文本类型。总体而言,法律文本包括了法律本身、谈论法律的文本以及其他场合下进行的法律交流文本。对此,有专家将其分为四大类:国内成文法以及国际条约;法律工作中的私人文件;法律学术文献;法律案例。但黛博拉·曹认为,这样的分类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译入语因素,对于法律译文的功能以及作用缺乏充分的考量,因而她提出了另外四种分类法:立法文本(legislative texts),司法文本(judicial texts),法律学术文本(legal scholarly texts)以及私人法律文件(private legal texts)。但这样的分类显然对于翻译来说也是不够的,因为,即使在立法文本中,合同法与刑法在遣词造句以及语篇结构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对于翻译的要求也不相同。比如,英语“capital”一词在经济法或者合同法中,只是表示“资本”,但在刑法中,“capital punishment”则是“判处死刑”。而刑法中所谓的“civil prisoner”是指刑事案件中“普通犯人”,而不是“民事犯”。
正如傅雷先生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所指出的,不会做诗歌的最好不要去翻译诗歌。在法律翻译中,擅长刑法翻译的未必能够胜任商法的翻译,精通公司法的未必对其他的民法都能驾轻就熟。因此,在英美法律界,作为律师,其执业范围往往仅限于自己受过训练并持有资格的领域,认为贸然涉足自己不了解的司法领域,不仅对自己、对客户都有害无益,而且也有违职业道德。在翻译法律文本之前,对法律翻译范畴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避免人们对法律翻译过于轻率的认识。
三、法律翻译教学中若干问题探析
厘清上述问题是极为必要的。只有在厘清法律翻译与其他翻译之异同,只有在认识到法律翻译 特殊性的基础上,才能对法律翻译教学予以有效的探析。
而在继续探讨法律翻译教学之前,首先需要纠正目前在翻译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误解,即学习英汉翻译可以提高英语。也就是说,要区别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的不同。如果从语言教学出发,翻译教学的确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两种语言的异同,提高两种语言的转换能力。但是,当翻译本身作为教学目的时,提高翻译能力,掌握翻译技巧就成为首当其冲的目的。在此视角下,翻译是双语的运用性实践活动,其目的不是为了提高语言水平,而是在具备了一定的双语能力后才能够从事的一项实践活动。就此而言,翻译可以作为检验语言水平的手段,但不能把提高语言能力当作翻译教学的主要目的。现在流行的翻译教学往往突出词语以及句子结构的讲解,把翻译教学当作语言教学的附庸,这无疑是对翻译教学的误读。翻译教学有其本身的要求。就法律翻译教学而言,应该首先突出法律翻译与其他翻译的不同,并且针对法律翻译的特点,找出法律翻译与其他翻译在翻译目的、翻译标准、翻译原则上的差异,从而对症下药,对法律不同种类的文本予以实践,让学生在对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有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运用翻译技巧,掌握法律翻译特有的规律,从而提高法律翻译的能力。例如:
No failure or delay on the part of any of the parties to this 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exercise of any right, power, privilege or remedy provided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operate as a waiver of such right, power, privilege or remedy or as a waiver of any preceding or succeeding breach by the other party to this agreement.
例句可以直译为:本协议所涉及的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未能或者延误执行本协议有关的权利、权力、特权或本协议提供的补救方法都不得视为放弃该等权利、权力、特权或补救方法,也不得视为放弃追究本协议另一方此前或此后的任何违约。
但也可以译为:本协议所涉及的当事人中,任何一方未行使本协议相关的任何权利、权力、特权或本协议提供的补救方法,其行为不得视为放弃该等权利、权力、特权或补救方法,也不得视为放弃追究本协议另一方此前或此后的任何违约。
在教学中,应该通过两种译文的比较,让学生对英语“No failure or delay”这一名词化词语特点有感性的认识,并且让学生掌握将英语无灵性名词化主语转化为有灵性主语的翻译技巧。
再比如,英语常用的副词“where”,在法律文本中就表现出较为让中国学生头疼的问题。请看以下例句:
Where a foreign, enterprise applies for trademark registration in China, the matter shall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any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the country to which the applicant belong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any international treaty to which both countries are parties, or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中国学生一看到where,往往就想当然地以为它引导地点状语,殊不知它在法律英语中往往引导一种状况,相当于条件状语从句。因此上例应该翻译为:如果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应当按其所属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按对等原则办理。
一旦明确了法律翻译教学的任务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法律翻译的教材建设。虽然目前以法律翻译为题的教材不少,但真正可以充当法律翻译教学之用的教材并不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作者已经专门做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作者发表在《上海翻译》上的“英汉法律翻译教材研究”一文。
法律英语是特殊用途英语(ESP)下的一个分支。法律翻译属于特殊的翻译领域。它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法律与语言的交叉。因此,从事法律翻译教学的教师,不仅要熟练地掌握英汉双语,同时也必须具备法律的基本常识,否则就会闹出笑话,有时甚至是严重的误解。比如:
“A growing global problem,is the illegal use of anoth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credit card numbe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or driver’s license number, to commit fraud or other crime.”
该句中的“identity crime”,就不能简单地汉译为“身份犯罪”。中国《刑法》中所规定的“身份犯罪”,指的是以行为人具有法律规定的某种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而英语世界中运用“identity crime”则指的是窃取他人身份信息用于欺诈、盗窃等犯罪行为,应该翻译为“身份信息犯罪”才比较贴切。再比如在英语合同中,往往不用“serious breach”来表示“严重违约”,而习惯上要用“material breach”来表达。
问题是,既精通法律又擅长双语的人才,实在是太缺乏。精通法律的人,或者说精通英美法以及大陆法的法律专家,往往不屑于从事法律翻译,更谈不上从事法律翻译教学。人们往往想当然地将翻译实践以及翻译教学的任务交给从事外语的人身上。可是,学外语出身的人所接受的传统翻译教学,基本上是以文学翻译为基础的,即使是接受过一些实用翻译教学理论知识并且具备一定的翻译实践经验,也不过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根本无力胜任法律翻译教学。黛博拉·曹曾对合格的法律翻译工作者提出过三方面的要求:翻译语言能力(translational language competence),翻译知识结构(translat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和翻译策略选择能力(translational strategic competence)。显而易见,对于法律翻译教学中的教师而言,黛博拉·曹所提出的三方面要求也同样适用。但在实际现实中,符合这三方面要求而且愿意从事法律翻译教学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翻译不被社会重视!如果从事文学翻译,出版的小说或者其他作品封面上好歹能够署上译者的姓名。而翻译法律文本,译者是完全可以被忽略掉的。在目前评职称、拿项目都要以科研成果为基础的氛围中,从事法律翻译的确不易。因此,如何培养一支既精通法律又具有相当的英汉双语功力,同时又熟悉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团队,是当前建设法律翻译教学这门课程的当务之急,需要有关部门花大力气去解决。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可以请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法学专家来担任法律翻译教学,因为从目前法律翻译的现状来看,翻译质量较高的法律译著往往都是由懂外语的法学家担纲翻译出来的;另外一方面是选派有志于这方面工作的外语教师(最好是已经从事过翻译教学的教师)去进修法律知识,或者选派有志于这方面工作的法学人士去进修外语知识,而后再从事一段时间的法律翻译实践后再来从事法律翻译教学。这里的法律知识和外语知识,不仅指法律和法律外语本身,同时还包括法律以及外语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
由此可见,法律翻译教学应该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能流于形式,应该予以循序渐进地推进。目前我国高校简单盲目地将法律英语或者法律翻译一股脑地对所有学生展开,显然属于不符合教学规律又不负责任的“大跃进”行为。依教学法律翻译的经验来看,在目前的情况下,法律翻译教学应尝试开展分层教学,建议在翻译专业硕士(MTI)阶段开展,在本科阶段,最好是针对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进行,不宜针对本科阶段的英语专业来进行,否则就会有些操之过急。如果教师和学生都缺乏法律知识基础,不仅使教师和学生都有些无所适从,而且还会弄巧成拙,起到拔苗助长的效果。理想的做法当然是招收法律翻译专业或者方向的学生,在教学计划上既安排法律知识的教育,又融入法律语言的教学,二者结合起来培养,才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法律翻译人才。同时,在教学方法上也要予以独立的研究。因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都比较强烈,也比较受到鼓励,但在法律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则受到一定的压制。那么,译者具体该如何处理好原作与译文的关系、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在提高英语和汉语水平的同时又熟悉法律教学?这都将成为法律翻译教学系统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1] 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2] 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13-14.
[3] 方梦之.实用文本汉译英[M].山东: 青岛出版社, 2003: 前言.
[4] 林克难.从信达雅、看易写到模仿—借用—创新[J].上海翻译, 2007, (3): 5-8.
[5] 傅敬民.英汉法律翻译教材研究[J].上海翻译, 2011, (4): 47-51.
[6] TiersmaP M. Legal Language[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7] 李克兴, 张新红.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8] 彼得·古德里奇.法律话语[M].程朝阳, 毛凤凡,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165-167.
[9] Deborah C. Translating Law[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13-19.
[10] 陶博, 龚柏华.法律语言[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1] 约翰·古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M].程朝阳, 毛凤凡, 秦明, 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23-25.
[12] 杜金榜.法律语言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88.
[13] AlcarazE, Hughes B. Legal Translation Explained[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导读.
[14] 庄智象.我国翻译专业建设: 问题与对策[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15] 卢思源.新编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218.
[16] 王相国.鏖战英文合同[M].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3.
Aspects of Legal Translation Teaching
Fu Jingmin
(,,,)
Legal translation as translation for specific purpose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entatively explores some aspects of legal translation, including its specialty, its teaching faculty, its teaching orientation, textbooks concerned and relevant teaching approache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legal transl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requires overall research, and we should come up with strategies accordingly.
;;
H315.9
A
1009-895X(2011)04-0249-06
2011-09-20
傅敬民(1965-),男,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语言教学,法律英语及英汉法律翻译等。 E-mail: kookworm@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