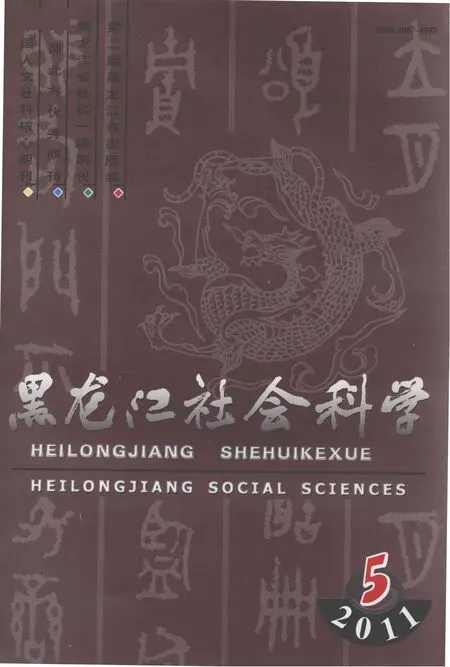超越与颠覆:近十年国外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研究述评
2011-04-11王晓丹
王晓丹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25)
超越与颠覆:近十年国外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研究述评
王晓丹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25)
近十年国外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研究脱离了新批评影响下对反讽和悖论叙述风格的片面描述,麦卡勒斯小说中的身份、种族、性别等话语体系进入了研究视野。同时,批评家们大胆尝试后现代框架下的文学批评在麦卡勒斯小说中的实践,使得文本的超越性和颠覆性成为研究的关键词。
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研究;超越与颠覆
一、麦卡勒斯小说中的身份意识与种族问题
近十年麦卡勒斯作品中的身份问题,不再局限于黑人问题或少数族裔研究。有的批评家尝试用精神分析等理论探讨普遍意义上的身份的形成,还有一些分析脱离黑白的传统二元对立,从美国南方白人和欧洲白人的对立讨论身份问题,十分具有启发性。
仙朵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戈博最先运用精神分析理论阐释麦卡勒斯的小说。她们利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分析马文和爱米莉亚决斗的时刻是两者“欲望的对抗”,并且把爱米莉亚小姐的失败解释为“惩罚她对阳具的渴望”[1]269。虽然二人的分析不够系统和深入,但是其运用精神分析的阐释颇具启发性。
2002年,多瑞恩·福勒借用拉康的“原始场景”概念分析《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爱米莉亚小姐、雷蒙表哥和马文·马西三个人物的关系。麦卡勒斯小说“戏剧化地表现了人类的疏离感,而拉康认为疏离感是人类主体性产生的必要先决条件”[1]260,因此福勒用拉康的身份理论观照麦卡勒斯小说的叙事风格。首先借用拉康对人类心理发展的三个阶段(前俄狄浦斯/想象阶段、镜像阶段、象征秩序阶段)的划分,分析主体和身份意识的变化和发展;其次是分析三个人物在三个阶段中形成的关系;最后说明“原始场景”与人物身份和自我的关系。原始场景是指父母交配的场景在孩子记忆深处存留的意象。福勒的文章最精彩之处是将爱米莉亚、马文和雷蒙三人的关系界定为母亲、父亲和孩子,并且指出小说中两个“原始场景”(马文和爱米莉亚的新婚之夜以及马文和爱米莉亚小姐的决斗)。福勒的文章摆脱了身份研究对混血或少数族裔人物的纠缠,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开辟了麦卡勒斯小说中人物身份构建的新范式。同样,后学语境下的批评家们眼中的种族问题研究,也不再拘泥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他们试图超越传统的黑白对立,寻找其他的参照物分析种族问题,以及在新的语境下白人的身份意识。辛希娅·吴认为种族差异、白人的优越感,身份协商是《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主题,而且“黑人”和“白人”的概念是相互建构的关系。辛希娅·吴提出疑问:白人性能否在没有黑人性的情况下被重新赋予含义?她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麦卡勒斯将欧洲移民的角色引入南方文学,这种姿态是在考察南方白人的身份问题,但没有通过黑人和白人对比的方式。“非裔美国人的缺席不是因为表现种族差异的新形式的疏忽,而是功能性的”[2]44。辛希娅·吴认为麦卡勒斯是在新的框架下探索新南方的种族问题,避免了黑白二元对立的陈词滥调。
辛希娅·吴列举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从北欧、东欧和南欧来到美国的移民的情况,说明麦氏作品中欧洲移民角色的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辛希娅·吴所说的“其他白人”在她文章中主要指犹太人。她借用犹太文化中“36个公正的人”的寓言,①“36个公正的人”的故事源自犹太神话。传说在大屠杀之前,这36个人作为选民,每人承担全体犹太人的苦难的1/36。当一个人死去时,另一个人就会被召唤继续苦难的使命。所以被召唤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既是荣耀也是危险。比喻犹太人作为白人的矛盾之处:“负担与荣誉并重”,因为在美国乔治亚州的犹太人“既为漫无边际的白人性感到不堪重负,又倍感荣耀”,并且“他们的似是而非和模糊性从内部挑战了白人性,在黑白对立之外重构了种族性”[2]47。辛希娅·吴的这种分析值得商榷:“白人”在种族的话语体系里仅仅是肤色的意思么?答案显然不是,“白人”的所指应该是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优越感和占据统治权威地位群体,而不仅是白色人种。所以,犹太人被放在这里考察白人和种族问题,其实起到的作用和黑人是一样的。和辛希娅·吴对麦卡勒斯小说里的犹太人的热衷一样,拉瑞·赫尔森也从种族问题的角度分析了麦氏《心是孤独的猎手》里的犹太人辛格和有1/8犹太血统布瑞农。他认为麦卡勒斯将“犹太身份看做智慧与受压迫的象征,精神超越常常在犹太人身上得以体现”[3]52。犹太艺术家们的创作“超越了小镇的物质主义”[3]68,代表了永恒的持续性。
二、麦卡勒斯小说的文本历史性和政治话语体系的建立
近十年麦卡勒斯研究脱离了新批评的影响,研究的着眼点不再仅仅是文体特征和模式,麦卡勒斯小说的孤独和精神隔绝主题也不再“被片面地理解为对文本衍生的反讽和悖论的陈述”[4],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政治话语体系成为研究的对象。
20世纪末,玛格丽特·怀特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结尾,把“苦役队之歌”的情节作为分析对象,探讨其隐含的历史语境意义和文本的历史性特征。怀特点明奴役之歌并非代表满足和幸福,而是“泪水疗伤的方式”[5]121。痛苦和悲伤的根源是不公正的社会体制,体制下的生存导致了美国南方人的孤独和精神隔绝。怀特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文本历史性引发疑问:是否只有共同的悲惨遭遇才能将人类团结在一起?怀特的结论充满不肯定的答复,“苦役队之歌是小说的框架,而不是神秘的结尾。麦卡勒斯用嘲讽的口吻成功地把人与人之爱升华到上帝之爱……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只有在上帝之爱能够被理解的世界中才能实现”[5]121。怀特的论断是要说明,黑人和白人共唱的和谐之音是麦卡勒斯想象力超越的方式,虽然现实是不和谐的孤独之音,十二个苦役队员如果没有了脚镣的联系,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平等和谐亦非一日之功。
达瑞恩·米勒的文章侧重对麦卡勒斯小说的政治话语的分析,并且指出以往批评家们对麦卡勒斯小说的精神层面的人类不幸百提不厌,但对作品的政治和历史维度鲜有提及,直到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莲·金斯伯格等人将麦氏作品的性别问题置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审视,认为怪诞和畸形人物是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模型,才出现麦卡勒斯作品准政治性的分析。萨拉·格林森·怀特评价麦卡勒斯的小说具有“威胁性的、最终颠覆传统的想象力,不受约束,具有强大的潜力”[6]87,而米勒分析“潜力”的主要表现,是指人物虽然过着暗淡无光的生活,但他们常常是梦想家,能够将自我情感投射到想象中的人际之间的淳朴的亲密关系。梦想的状态虽然将他们置于孤立离群的境地,但“如此多的梦想家出现在同一片天空下,象征着未受干扰的乌托邦的潜力,而每个人物的挫败仅仅强化了这种潜力”[6]88。米勒指出识别麦氏作品的乌托邦特质的关键是要考虑困扰人物生活和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性的条件。
2003年,格林森·怀特在麦卡勒斯作品中的“怪诞”女性时指出,怪诞女性的形象“挑战了理想化的、受压迫的白人女性形象”[7]46,理想化的、“正常”的女性形象在内战前占主导地位,但内战后的南方作家描写了许多扭曲的、碎片的身体,写作风格和人物形象的转变要归因于人物所处的不同的历史环境。怀特的出发点在于“女性身体对南方文化的重要性”[7]47,女性身体的贞洁能保持南方血统的纯净。女性的正常与非正常的划分便于男权社会对她们的控制,而白人女性的弱不禁风让她们远离凡尘俗世,使男性有机会在保护她们的同时建构自己的男性气概。因此,怪诞女性的出现绝不仅仅是灵魂孤独的意象,她们更是一种反政治话语。爱米莉亚以无性的形象反抗南方淑女的理想形象,她的男性气质正是麦卡勒斯逾越理念的具体表现[7]51。
三、麦卡勒斯小说的身体与性别研究
继“怪诞”女性的反政治话语之后,格林森·怀特又撰文系统地分析了“怪诞”研究存在的问题:“没有批评家将怪诞理论化,仅仅将怪诞等同于哥特或奇怪。”[7]109这种局限性的视角被斯皮波尔打破,他认为南方小说的怪诞不是故事的特定性质,也不是语气或表达的体裁,而是人物类型,是身体残疾或心理扭曲的人物类型。他们是异形人物,是局外人,他们的与众不同体现在身体上。由此,南方小说的怪诞对象是身体,因此格林森·怀特运用巴赫金的身体理论解读麦卡勒斯的作品中的怪诞女性。
格林森·怀特引入了麦卡勒斯的小说中的一组对立:怪诞身体与传统身体的对抗。怪诞身体具有开放性的阐释空间,是差异的潜能表现,代表另一种的秩序和另一种生活方式,传统身体意味着“封闭、连贯、僵化和停滞”[7]110。传统的身体研究认为女性被异形为亚当的肋骨,不仅忽视了麦卡勒斯的怪诞人物对“规范的身体政治的创造性的挑战”[3]111,她们拒绝屈服于女性理想的模式,变得怪异。她们不再是干净小巧、优雅贤淑或作为收藏品的洋娃娃形象,她们的异形挑战了对女性的限制,这些青春期少女代表了无限变化的可能性,她们“流动的、不固定的身份感,动摇了我们理解人类的方式的边界”[7]112。米克和弗兰淇等“假小子”们打破社会规范,竭力突破社会标准和传统身份的局限。
格林森·怀特的文章格外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她借用霍米·巴巴的“间质”的概念解读“巨人症”现象和“飞翔”的意象。“间质”简言之就是差异的并存,是一个充满变化的状态。女孩子们身材高大影响她们融入社会,身高使她们成了“局外人和他者,而且高大的身材是男性世界的一部分,半男半女代表了主体未完成的形式”[3]118。而飞翔是介于土地和天空之间,也具有间质性。飞翔和女孩子的梦想相关联,也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拒绝僵化和停滞的状态。
麦卡勒斯小说的性别研究也随着酷儿理论的发展有了新变化。莫丽莎·弗瑞的观点代表了近十年酷儿理论对麦卡勒斯小说研究的新方向。弗瑞首先明确了“酷儿”的含义:“酷儿不代表同性恋,而是被驱逐、排斥或沉默造成的心理扭曲”[8]426,并且她强调了酷儿理论的语境化特征,即酷儿不再是异性恋语境下的羞耻的称呼,“不再是异性恋的对立面,而是对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规范的挑战”[8]427。“当前的酷儿理论将酷儿性与性身份和性错位剥离,构建非标准化非规范化的酷儿概念,威胁并摧毁酷儿性和差异”[8]427,弗瑞进一步用新闻界的报道和媒体不再把男同性恋称为酷儿的事实,说明当前酷儿理论隐藏在用词变化下的观念的转变。弗瑞的文章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她用《金色眼睛的映像》举例说明文章题目中的酷儿、怪诞和沉默的关系时,有些有趣的发现。比如小说中“孔雀”和“鸟”的称呼都是20世纪30年代男同性恋的暗语。“沉默”是用来解释长官潘德顿暗恋二等兵威廉姆却从未表白,他的无言是一种压抑的表现,“具有破坏性……并导致潘德顿内心的冲突并引发怪诞的行为,他殴打妻子的马是排解他对威廉姆的性欲”[8]432。
弗瑞把新酷儿理论参照下的研究归结为麦卡勒斯如何“将非常正常化变得正常化”[8]443的过程,麦卡勒斯的小说世界里同性恋不再意味着堕落,她抛弃了性别与性偏差的固定隐喻,而是“以转喻的方式,反对偏差的可视性”[8]429,离经叛道的性取向与性无关,而是具有颠覆性的对抗行为的表现形式。
弗瑞用麦卡勒斯无性的个人生活和兄妹般的夫妻关系深化酷儿理论对麦氏作品的阐释力度。她指出作者麦卡勒斯自己的同性恋情节与性交配无关,“没有证据表明她曾和任何女性发生过关系”[8]430。早期以海富洛克·艾里斯为代表的主流同性恋理论,把同性恋看做“变性”。女同性恋的一方具有男性特质,这种同性恋本质上仍是异性恋。这种理论的背景是对“离经叛道的迫害的现实的恐惧,内化了的同性恋恐惧”[8]430,艾里斯借用弗洛伊德的模型,把同性恋看做心理发展的失败。
弗瑞虽然借用酷儿理论的新发展对麦卡勒斯小说中的性别问题得出别样阐释,找到了格林森·怀特所说的“颠覆”和“超越”的具体表现,但她同时也指出,在麦卡勒斯创作的年代保守的南方拒绝承认同性恋的存在,社会语境的含糊其辞和闭口不谈也影响到了麦卡勒斯,她“从未超越自己内化的同性恋恐惧症”[8]432,恐惧症导致麦卡勒斯作品的颠覆性和超越性显得不那么彻底。但是,这种缺陷似乎丝毫没有影响麦卡勒斯作品的活力,近十年国外对麦卡勒斯小说研究的热度充分说明了麦卡勒斯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而当下批评家们广阔的理论视角和严谨的论证分析无疑扩展了麦卡勒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多样性的阐释使麦卡勒斯的作品继续散发无穷的魅力。
[1]多瑞恩·福勒.麦卡勒斯的原始场景:《伤心咖啡馆之歌》[J].当代小说批评,2002,(3).
[2]辛希娅·吴.南方白人性的扩展:麦卡勒斯种族差异的重构[J].南方文学评论,2001,(1).
[3]拉瑞·赫尔森.张力与超验:麦卡勒斯小说中的犹太人[J].南方文学评论,2008,(1).
[4]林斌.卡森·麦卡勒斯20世纪40年代小说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2).
[5]玛格丽特·怀特.从兄弟之爱到上帝之爱:《伤心咖啡馆之歌》的苦役队之歌重读[J].短篇小说研究,1996,(33).
[6]达瑞恩·米勒.《婚礼的成员》和《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情感的乌托邦功能[J].南方文学评论,2009,(2).
[7]萨拉·格林森·怀特.丑陋的特别形式:韦尔蒂、麦卡勒斯、奥康纳;重解南方哥特:巴赫金与麦卡勒斯[J].南方文学评论,2003,(1).
[8]弗瑞.流放与反抗:麦卡勒斯作品中的酷儿、怪诞和沉默形象[J].小说研究,2008,(4).
J4
A
1007-4937(2011)05-0108-03
2011-08-05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卡森·麦卡勒斯小说赋格曲式结构研究”(11552119)
王晓丹(197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从事当代美国小说研究。
〔责任编辑:王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