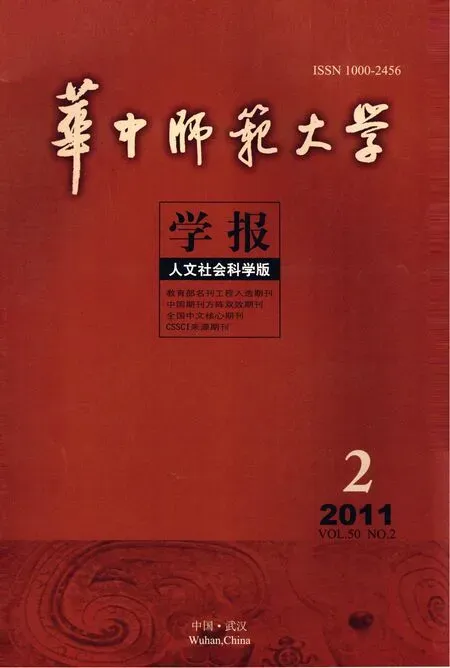革命纪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辛亥记忆
2011-04-10潘大礼
刘 伟 潘大礼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革命纪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辛亥记忆
刘 伟 潘大礼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纪念活动是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辛亥纪念中,“革命”一直是一个核心话语。“革命”话语来源于孙中山对革命进步性与正当性的阐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要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完成重建民国的任务,就必须把自己塑造成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者,借纪念来强化人们的辛亥记忆和现实认同。因而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确立了一整套党国体制下的“革命纪念”制度,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推向高峰。在“革命纪念”的名义下,国民党从凸显自身的革命斗争与革命功绩的原则出发,对辛亥史事进行裁剪并简化,并任意拔高与国民党密切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从而建构了一个“本党”革命奋斗史的辛亥记忆。在“革命纪念”的名义下,国民党进一步把自己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都泛化成“革命”,将“革命”打造成一种精神与信仰、一种价值标准,“革命”的宗旨和对象一步步发生异化,从而在内涵和形式上都偏离了孙中山的“革命”观,成为一种强劲的意识形态话语与说教。
革命纪念;国民党;辛亥革命;记忆
有学者精辟地指出:“近代中国以‘革命’频发而著称。”①实际上,不仅1920年代,就是整个民国时期,“革命”都是国民党党政要人政治论说中的核心话语。一种话语的形成与流行,常常需要借助一定的机制,而纪念活动,就是其中的重要机制之一。以往学界考察话语较多地关注报刊等媒介的作用而忽略纪念活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后者的作用要大于前者。尤其是官方主导的纪念活动,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把过去、现在、将来有机联系在一起,塑造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纪念又能以一定的仪式和场景,呼唤人们的历史记忆,激发人们的情感,动员民众。所以,纪念是打造和形成某种话语的空间场域,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和影响力;纪念活动年复一年的操演,又可以使话语保持时间上的延续性。正因为纪念具有如此大的功能,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建构了一整套“革命纪念”制度,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推向高峰,并在“革命纪念”的名义下,建构起以“本党”革命历史为主线的辛亥记忆,使“革命”成为一种强劲的意识形态话语。关于辛亥革命纪念和记忆的研究,正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研究还较薄弱,本文在此从其特征的角度作一探讨。
一、“革命”话语之源
国民党在辛亥纪念中常说,自己是“继续总理未竟的革命事业”,所以,要了解国民党的“革命”话语,就有必要先了解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孙中山何时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称为“革命”?学界引用较多的,是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记:1895年11月,孙中山赴日本,舟过神户之际,先生等“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类似的记载也见于陈少白的回忆。但《孙中山年谱长编》注明:“此事不见于先生本人记述,据安井三吉、陈德仁考查,当时日本报纸亦未见此种报道。”②亦有学者进一步从词语之语境的角度进行考察,指出孙中山1895至1897年之间的一系列谈话或书面陈述,口口声声强调的都是“改革”而不是“革命”。直到1903年之际,伴随着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邹容《革命军》的出版,伴随着“变革”、“进化”、“共和”、“民主”等现代意识的滋长,“革命”的正面意义达到阐扬,才被中国社会广为接受③。
正是在上述语境下,孙中山使用的词语也有了很大的变化。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对华侨的演说中说:“革命为惟一之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甚望华侨赞助革命党。”④这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演说,在这里,孙中山明确使用了“革命党”这一概念;在对“革命”的解说中,他将“汤武革命”与“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结合,说明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此后孙中山以“革命”自居。1903年12月《敬告同乡书》中说:“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⑤同盟会成立后,这一思想又发展成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在1906年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又将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名之为“国民革命”,革命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⑥。革命不仅是与保皇对立的颠覆清王朝之举,时间长度也延伸到了建立民国以后。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孙中山一度只谈“社会革命”。然而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再次举起“革命”大旗,发动“二次革命”,并于1914年7月成立中华革命党。章程宣布该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⑦,并准备进行意在达此目的的“三次革命”。此时孙中山的“革命”,在手段上是对反清革命的沿用,但进一步明确强调“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⑧。这样,既把现时的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的“革命”说成反清革命的继续,又进一步明确把革命方略的三个阶段纳入革命范畴。
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初,孙中山在领导护法和建立广东革命政权的斗争中,继续高举“革命”大旗。他多次谈到,救国之急务,当“重行革命”;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只有革命”。并一再宣称:“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画,然后再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⑨革命的宗旨是“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⑩他明确指出,“革命”既包含推翻旧政权,也包含建设新国家;“革命“的对象既包括打倒封建军阀,也包括打倒帝国主义。
孙中山之所以一再提出“革命”与“重行革命”的问题,蕴含着他对辛亥革命的一个基本认识,即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革命的任务。他说:“革命事业,在十年以前虽已推倒满清,成立中华民国,然以言成功则犹未也。武昌革命而后,所谓中华民国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切政权仍在腐败官僚、专横武人之手,益以兵灾、水、旱,迄无宁岁,人民痛苦且如甚焉!此即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难收良果也。”他还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忽视革命方略而不行,又有部分党人误以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革命意志消退,致使革命半途而废。所以还需要以革命“辅足前此未完之事业,继续为之”(11)。
正是在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中,孙中山借鉴苏俄革命经验,得出革命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和主义建设的认识。他说:“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做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三民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革命主义(12)。在孙中山一次次对革命必要性、正当性的阐释中,树立起了革命进步和惟有革命的核心价值,这一切也成为日后国民党革命纪念的理论资源。
二、“革命纪念”的制度设计
从孙中山确立“革命”时起,这一话语就成为正当性、正义性的化身,谁掌握了这一话语权,谁就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又因为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革命”本身就与辛亥革命紧密相连,所以,要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完成重建民国的任务,就必须把自己塑造成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者,借纪念来强化人们的辛亥记忆和现实认同。于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从民国元年起就开始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民国元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上海、南京、广东等地举行盛大纪念会,纪念黄花岗起义中死难的烈士。武昌起义周年之时,孙中山、张继等发起“革命纪念会”,以“愿中华民国继自今万岁千秋”(13)。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后,更是形成了一系列“革命”纪念日,除1月1日为革命政府开国纪念日、10月10日为国庆纪念日外,1925年3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通过决议,以阳历3月29日为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14)。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病逝,9月,国民党中央议决每年3月12日为总理逝世纪念日(15),以纪念他“手创民国”之贡献,并表达继承总理未完革命遗志之愿望。次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定11月12日为总理诞辰纪念日(16)。“革命”纪念渐成规模。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党国体制的确立,也使国民党有了将一党意志转化为全国意志的条件与可能。在这种局面下,国民党很快确立了革命纪念政策。1929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0次常务会通过并颁布“革命纪念日纪念式”,规定了28项革命纪念日(17)。这些纪念日的设定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围绕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历史这条主线而展开,突出了国民党的革命奋斗史;二是设立多个“国耻纪念日”,彰显了民族主义这个主题。革命纪念式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决议的形式通过并予以颁布,要求执行纪念仪式的则不仅包括国民党党部和政、军、警界,而且包括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商店,实际上是把党的决议作为了国家的法规而要求各界一律实行,体现了“党国”的精神。在中执会关于革命纪念式文件的“附则”中强调:“纪念仪式于必要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更之”、“纪念宣传要点于时局需要时,由中央宣传部酌量增加之”(18),即纪念日和纪念式的修订权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权在中央宣传部。不仅如此,在确定统一的纪念日的同时,还确定具体的纪念仪式、颁布了纪念日史略和宣传大纲及要点。这就把纪念日活动统一纳入到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之中,不仅形成了统一的革命纪念制度,而且造就了统一的革命纪念文化。
然而,28项革命纪念日活动不仅日子太多,而且“有的日子没有永久普遍独立的性质”,所以1930年7月10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对上述革命纪念日进行了修正,目的在“求其明显,在使民众能够诚意热心郑重的来作纪念,以统一国民的意志”。这次修订的原则是突出“民国建国历史”和“对本党具特别重要意义者”,分别定为“国定纪念日”和“本党纪念日”。其中“国定纪念日”包括: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国庆纪念日、革命政府纪念日、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日、总理诞辰纪念日、总理逝世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国耻纪念日。“本党纪念日”包括:北平民众革命纪念日、清党纪念日、先烈陈英士先生纪念日、总理广州蒙难纪念日、先烈廖仲恺先生纪念日、总理第一次起义纪念日、先烈朱执信先生纪念日、总理伦敦蒙难纪念日、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云南起义纪念日(19)。经过这次修订,纪念日被合并成18项,更加集中于纪念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斗争历史。
以后,革命纪念日又多次修订。如1934年本党纪念日新增10月30日为先烈黄克强先生纪念日(20)。1935年四届中执会第188常会通过增补3月18日为先烈邓仲元(铿)先生殉国纪念日(21)。1942年革命纪念日制度又有重大修改。3月国民党中执会第192次常会定国定纪念日为5天,分别是:中华民国开国纪念、革命先烈纪念、孔子诞辰纪念、国庆纪念、国父诞辰纪念。中执会第204次常会将“本党纪念日”改为“革命纪念日”,定总理第一次起义纪念、肇和舰举义纪念、清党纪念、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革命政府纪念、总理广州蒙难纪念6天为革命纪念日。值得注意的是,在纪念办法中特别提到要“讲述党史”,并规定了讲述党史的要求:(一)九月九日讲乙酉中法一役后总理立志革命至武昌起义之兴中会同盟会革命史;(二)十二月五日讲民国四年肇和起义及云南起义,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及中华革命党史,民国元年至二年十一月之国民党史附之;(三)四月十二日讲民国八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共产党之产生,十二年本党容共至十六年本党清党史;(四)七月九日讲十三年本党改组创办黄埔至北伐完成之本党军事党务史;(五)五月五日讲民元总理辞临时大总统至十年五月总理就非常大总统之本党护法运动史;(六)六月十六日讲自十年五月五日总理就非常大总统后陈炯明叛变至十四年广东统一之本党平定反侧史(22)。
相比以前的纪念制度,不只是数量的减少,更重要的是革命纪念的内容发生变化,不再直接提讲述国父革命史略,而是讲述本党之“党史”。把上述党史联系起来,可以明显看到一条基本线索:兴中会同盟会革命史—中华革命党史—护法运动史—中国国民党改组及军事党务史—清党史—平定侧反史。在这一大大简化和浓缩的历史中,进一步突出了国民党“革命”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这些党史的主角虽然仍是孙中山,但相应内容的附加,如“创办黄埔至北伐完成之本党军事党务史”、“清党史”、“本党平定反侧史”等,实际上都突出了蒋介石个人及地位,反映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地位迅速上升,已成为握有党政军大权的“总裁”的态势。
安德生在《想象的社群》中说,历史现象往往依赖于记忆与忘却(23)。而国民党革命纪念制度的确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关于“革命”的记忆,塑造了一个以国民党革命斗争史为基本线索的“辛亥革命”史。正是在这个“革命纪念”的观照下,辛亥记忆被重新建构。
三、革命纪念中的辛亥记忆
在“革命”话语之下,通过各项纪念活动,国民党完成了对自身“革命”历程的建构。
兴中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起点,许多研究者指出,孙中山早年也有改良思想,这从他的《上李鸿章书》等作品中就可看出。但在国民党的“革命”话语中,孙中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蒋介石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兴中会的成立,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年,国父宣布他的革命宗旨,是要‘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他的目的,在于复兴中华,使世世子孙免为外族的奴隶牛马。这五十年来,我们革命先烈和全国同胞,前仆后继,就为这一个革命建国雪耻强国的目的而奋斗。”(24)
1895年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后,孙中山领导了广州起义,国民党将此“第一次起义”作为本党纪念日。他们认为,这次起义是“本党革命之起源”,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之造反有本质的不同:“历来中国政治之更迭,不外朝姓之改换,五千年来,始终未尝脱离封建社会之窠臼”;而总理发动起义则是“以扫除专制遗毒,推翻异族蹂躏,解除民众痛苦,摧毁封建势力为鹄的”,所以此次起义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中华民族,实中国国民革命之起点,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25)。
在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中,有两次“蒙难”,一次是1896年10月11日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诱禁使馆,并准备秘密送回国内,孙中山通过英仆带信向老师康德黎求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老师),在康的营救下脱险。另一次是1922年孙中山主持护法,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率兵北伐。6月,军阀陈炯明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永丰舰率海军戡乱,在广州河面上相持月余,后于8月9日离粤赴沪。对于两次蒙难本身的意义,国民党通过纪念活动,也将其阐发到极致。在中央宣传部的关于总理伦敦蒙难纪念的宣传大纲中,称总理在伦敦是“为倾覆专制,创造共和而蒙难……总理博大慈祥的人格,光明伟大的事业,俱因此而愈加光大,获得国内外人士深切之同情与援助,革命的实力,因是而继长增高。”(26)
对于总理广州蒙难,蒋介石则称,要没有总理广州这一回蒙难,要没有总理在蒙难时所表现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我们的党我们的国或许早已亡掉,也未可知”。“从前外国人不但看我们不起,就对于我们中国的革命党都看不起,他们以为中国的革命党只会争领袖做,遇到事情,还是怕死。自有了六月十六这一天,才晓得中国的革命的领袖是不怕死的,是有牺牲精神的。”(27)
在辛亥革命的历程中,革命党人发动过十数次武装起义,但国民党尤为看重黄花岗起义。从结局看,黄花岗起义是一次失败的起义,但国民党则认为其是“中华民族革命运动最大之关键”,“推及辛亥革命之成功,中华民国之成立,与夫十九年来本党能由军政而训政,并能肃清反动,统一全国,巩固建设基础,发展党治精神,能逐渐解除民众痛苦,实在是总理之惨澹经营与民国纪元前一年的今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悲壮激昂的勇气,杀身成仁的毅力,以及他们那种笃信主义服从命令的革命精神所感召而得来的”(28)。他们甚至认为,黄花岗起义之地位超过武昌起义,“黄花岗诸烈士之殉国,间接上是奠定民国成立的基础,同时激起了革命的高潮,形成武昌革命的效果。”(29)也就是强调其在革命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绝对地位,强调其深远影响。
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历史意义之所以会提到如此高的地位,实际是国民党政治统治的需要。因为这次起义是孙中山亲自策划领导的最大的一次反清武装斗争。突出这次起义,更有利于突出国民党的革命斗争史,也更有助于提升国民党的威望。正如于右任在一次纪念报告中所说:“总理领导的十次革命当中,以此次为奋斗最烈、牺牲最大、影响最深。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本党精神最高度的表现。有了这次表现,本党的主义与力量方引起了世界的敬重。”(30)在许多党政要人的报告中,经常提到的是“中华民国是我们总理和诸先烈牺牲奋斗得来的,我们今天要保存中华民国,也要继续牺牲奋斗的精神”,“正是党人以坚忍不拔之精神的努力奋斗,才有革命事业之成功”等诸如此类的话。(31)通过这样一些叙述,建构起国民党为革命牺牲奋斗的历程,打造了国民党为中华民国建立而立下的丰功伟绩,也树立起国民党实为“民国之父”的形象。
然而,毕竟是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及此后的全国响应,才促成了清王朝的覆灭。对于此,1928年国民党中央为统一后国庆纪念告民众书中说:“十月十日为辛亥武昌起义造成中华民国之伟大国庆纪念,实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以四十年之心力,领导无数志士尽瘁革命,精诚无间,百折不回,造成时势,得全国人心之倾向所告成。”(32)这里明白无误的宣告,武昌起义的胜利是孙中山领导的结果。在他们的叙述中,“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目睹当时国家民族的厄运,自乙酉中法战役之后,以致辛亥的二十余年间,自身不断的奔走于日本南洋欧美各地,积极从事鼓吹革命”,从兴中会起,先后经历了十次失败,才能“唤起海内外同胞的民族革命思想,进而发为百折不回的国民革命运动,以摧毁盘踞国内之腐旧势力,而促进我中华民族之中兴。所以辛亥武昌首义,是总理二十余年奋斗与努力的结果。”(33)很显然,在这一高度精炼的表述中,除兴中会、同盟会及其发动的各次起义外,其他革命团体及其斗争、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都被遮蔽了。突出孙中山的作用,也就是要突出辛亥革命是“本党”领导和奋斗的结果。
对于辛亥革命的结局,1928年中央宣传部编制的《国庆纪念宣传大纲》将辛亥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四个方面:促进国内民族之平等、创立民主共和的政体、救中国于垂亡的危境、解放思想促进文化;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是三个方面:“忽视革命主义及方略”、“忽视民众的革命力量”、“党的本身之不健全”(34)。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或不彻底,为的是突出辛亥后孙中山为维护共和而进行的奋斗历程以及国民党完成北伐的功绩,说明国民党一贯坚持革命的正当性,并由此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及工作任务,即加紧巩固党的基础,厉行建设事业。1928年1月,在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在迅速完成北伐之际同时颁发宣言,说明中国革命“今方由理论宣传与武力征服时期,逐渐进于此两种工作与政治的建设经济的建设并行之时期”(35)。1929年中执会的国庆告同志同胞书则进一步强调:“我们知道革命有两个阶段,现在国民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破坏工作业已过去,所努力的应该是第二个阶段建设的事业了。”(36)这样,就有效地把国民党当下的现实任务与辛亥革命对接,将其说成是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从而为证明国民党的一切工作就是“重兴中华民国之工作”(37)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受非常国会之推戴,在广州就任大总统。这一日也称“革命政府纪念日”、“双五纪念日”。关于这个纪念日的意义,中央宣传部大纲将其作为孙中山“重整革命队伍,与一切反革命势力决斗”的开始,由此“使中华民国在重重黑暗势力包围中得到一线光明奋斗之路,三民主义因之而播及全国民众的脑海,革命势力因之而日趋扩张,给帝国主义军阀以极大的打击,使民众得从水深火热的痛苦中解放出来”,所以“这实实在在是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节日”,是“一个再生的纪念日”(38);因为总理“是中华民族的创造者”,所以“双五节的意义比双十节还要大”(39)。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两次就总统职,又两次去职,对此,在一些政要的演说中作了比较和解释。胡汉民的一篇五五纪念文章认为,总理第一次从总统位上去职是党内的原因,因当时许多同志对总理三民主义的建设工作不明了,就此懈怠,“总理鉴于党义的不明如此,革命便难以完成,自己对于国家,徒拥一个首领的虚名,所以慨然退职”。目的是便于“重新训练党员,重新巩固革命的基础,重新确定革命的策略和工作”。而总理在广州就总统职,完全是出于“对国民革命的责任心”(40)。可见在国民党政要们的解说中,总理就任广州非常大总统职,是革命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是孙中山承担起重新“造党建国”责任的开始,是革命一个新的起点。
总之,在国民党的“革命”纪念中,对已经远去的那场革命的记忆体现出有所裁剪并趋向简化的倾向,即表现为“建构”史事而不是“重建”史事的特征。建构的原则,是凸显国民党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功绩,采用的方法是拔高与国民党密切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以此塑造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四、辛亥记忆中的“革命”话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通过一系列纪念活动所建构的辛亥记忆,都是以“革命”为核心价值而展开的,在他们的表述中,不仅把孙中山领导的反对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斗争历史视为“革命”,还进一步把自己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都以“革命”冠之,并将“革命”打造成一种精神与信仰、一种意识形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入各项建设时期,他们将此称为“革命建国”。所谓“革命建国”,蒋介石在1938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国民书中解释道:“我们总理毕生倡导革命,他的目的,就是要‘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三民主义革命建国的理想,具体的说来,就是如此。”(41)革命建国即用三民主义建国,以达世界“大同之治”,这是孙中山所宣示的最高境界。蒋介石把它接过来,进一步阐述为在国民党领导下完成建国大业的目标,目的在鼓动国民树立对于国家的责任。
1943年3月29日《中央日报》发表纪念革命先烈的社论说:“今日的中国,正当国家民族存亡绝续之效,我们青年需要为国家来革命,为民族来革命……我们的抗战是革命,我们的建国也是革命。”(42)不仅抗战建国是“革命”,他们还将抗战后的“戡乱建国”也称为“革命”。1948年,何应钦在国庆纪念文章中呼吁发扬“革命先烈和全国军民同胞的奋勇精神”进行“戡乱建国”。并说:“争取戡乱作战的胜利,实在是我们革命建国过程中最后的考验”(43)。“革命”在这里被泛化成说明国民党统治正当性和惟一性的工具。
“革命”还成为国民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精神武器。1930年3月30日蒋介石以“纪念革命先烈的感想”为名作演讲,称“三月二十九日一役,可谓革命正气伸张的一个大纪念。这种革命精神,表示完全为主义为民族而奋斗,绝对不夹杂一丝一毫的私心私见,乃至私人利益的打算在内”。他以参与黄花岗起义的陈炯明后来背叛革命为例,说明不能为私利而置主义于不顾,并希望党内同志“应完全效法黄花岗诸先烈公而忘私的精神,在全局的利害和严正的是非上着想”(44)。这样,蒋介石就把继承革命先烈精神转变成了对党员的道德说教。
1944年,国民党定3月29日为青年节。蒋介石在“昭告全国青年”中说:“我们之所以特别选定这一天为青年节,就是因为当年为革命而成仁的黄花岗诸烈士,大半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他们纯洁热烈的爱国精神,成仁取义的革命精神,正是今日青年所当效法的。先烈之血,国族之光,这光辉是万古的,是引导着我们青年向革命建国成功之道路而前进的。”(45)此后蒋介石每年在这一时间发布告全国青年书,内容都是在“革命”名义下号召和动员青年。1944年的主题是“立志继承革命的历史”,“负起革命的责任”;1946年的主题是继承先烈精神,“建设现代国家”(46)。在这里,革命成了先烈的精神象征,革命成了动员青年投身党国事业的招牌。
在孙中山的各项纪念活动中,国民党都反复阐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并把其打造成革命的偶像。蒋介石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曾说:“总理是什么人?简单说一句,总理是个革命者。总理是革命的,除了革命以外,总理不晓得再有别的事情……革命者不是寻常的称号,不是一般人都可以称的,革命是实实在在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现三民主义的,这样才算是一个革命者。”(47)孙科也说:总理毕生的志愿就在“革命”。“革命”的目标就在“建设”;“革命”的破坏不过是“建设”的初步(48)。
他们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释为“救国救民救世的革命主义”(49)。1934年蒋介石在纪念孙中山逝世纪念会上借用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的理论,做了一番“总理之根本思想”的演讲。在他的演讲中,总理一生的努力,就是以革命的手段来救国家救民族。蒋氏特别指出,所谓“革命的手段”,“就是要打倒一切个人主义的迷梦,即一切自私自利的企图”。三民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唤起民众;而实行的方法,则是国民革命。“完成国民革命”本是孙中山的遗志,但蒋氏在演讲中又进一步发挥为要“集中全国民众与革命党的力量,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目标”,来奠定国家万年不拔的基础。他还比较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说虽然二者最后目的相同,但民生主义是出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精神,并污蔑共产主义提倡阶级斗争是“要自相残杀”。最后又将总理的革命人格和全部思想归结到“仁爱”两字,归结到“仁、智、勇”和“诚”。并说,“诚”就是“选定一个好的主义,诚心诚意来坚信笃行”,而这个好的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不许对三民主义有一点怀疑,有一点批评”(50)。这里,蒋介石既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又借助“革命主义”装进了自己的理论。
国民党虽然统一了中国,但政权并不稳固,内部反对势力不断。因此,“革命”还被树立成正统的标杆,成为一种判断事物的价值与标准。如强化黄花岗起义烈士纪念,就是为了说明只有国民党才是一贯革命的。他们所建构的逻辑关系是:因为七十二烈士是三民主义的笃信者,三二九殉国烈士是翼赞总理创造民国的元勋,中国国民党是秉承总理遗训的,所以是革命的真正继承者。那么,在此前提之下,一切与本党有不同政见者都成了“反革命”、“反动分子”。借纪念先烈谴责“反革命”,号召统一于本党之党义,就成了辛亥纪念中的重要主题。如1930年中央宣传部制订的七十二烈士纪念宣传大纲提出的要求中包括两条:一是“纪念先烈要踏着先烈血迹,彻底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它所指责的“反动势力”,是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改组派、“及阳唱和平阴忌统一之一切残余封建势力”。二是要“拥护中央、巩固统一”。提出和平统一是诸先烈不惜牺牲的奋斗目标,“然要和平统一之永久保持,即不能无强固之中央”,所以纪念先烈,就是要一致拥护中央,巩固统一(51)。
在孙中山的“革命”话语中,革命是一种运动与实践,也是一种理论。作为实践与运动,辛亥前与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国相连;民国建立后则与反对封建军阀及帝国主义、建设新国家相连。作为理论,它以三民主义为呈现方式,其中不乏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国民党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话语,但通过革命纪念和辛亥记忆的建构,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改变了“革命”的内涵。在实践层面,“革命”被塑造成了不断延续的过程和自身事业的化身,“革命”成了“我党”的革命奋斗史,“革命”的宗旨和对象一步步发生异化。在理论层面,“革命”的外包装中不断装入了蒋介石等人的私货,“革命”被打造成了国民党封闭的意识形态和说教。
注释
①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见《“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②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2页。
③(23)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3、134页,第61页。
④《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见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⑤《敬告同乡书》,见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1-232页。
⑥《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见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298页。
⑦《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中华革命党总章》,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6页、430页。
⑧《中华革命党总章》,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430页。
⑨《救国之急务》、《改造中国之第一步》,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646、637页。
⑩(11)《军人精神教育》,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92页。
(12)《修改党章的说明》,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693页。
(13)《革命纪念会消息》,《民立报》1912年9月29日第7页。
(14)《议决黄花岗纪念日》,《民国日报》1925年3月26日第2版。
(15)《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广州:《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5年9月7日,第312页。
(16)《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国民政府公报》第39号,第18页。
(17)(18)《革命纪念日纪念式》,《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9年7月13日,第541~552页,第552页。
(19)《一周大事述评·中央修正革命纪念日》,《中央周报》第111期,1930年7月21日第42页。
(20)《革命纪念日简明表》,《中央周报》第338期,1934年11月26日第2页。
(21)《国民政府训令第860号》,《国民政府公报》第1889号第5页。
(22)《国民政府训令渝文字第711号》,《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481号,第22~23页。
(24)《蒋主席昭告全国军民》,《中央日报》1944年1月1日第2版。
(25)《总理第一次起义第三十九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325期,1934年8月27日第2~3页。
(26)《总理伦敦蒙难第卅四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121期,1930年9月29日第17页。
(27)蒋介石:《总理蒙难五周年纪念演说词》,见谢振铎编:《革命史上的重要纪念日》,广州: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1927年,第48~49页。
(28)《七十二烈士殉国十九周年纪念告民众书》,《中央周报》第93期,1930年3月17日第47页。
(29)邹鲁:《民族的创造和生存端赖民族本身的觉悟和奋斗》,《革命纪念日史略》,(出版地不详)国民出版社,1940年,第32页。
(30)《中枢纪念革命先烈》,《中央日报》1943年3月30日第3版。
(31)《中央举行革命先烈纪念会》,《中央周报》第304期,1934年4月2日第3页。
(32)《中央为统一后国庆纪念告民众书》,《申报》1928年10月10日第3张。
(33)《国庆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121期,1930年9月29日第10页。
(34)《国庆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18期,1928年10月8日第11页。
(35)(3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统一后之国庆纪念告民众书》,《关于国庆纪念的认识》(出版地和时间不详),第37页,第39页。
(36)《民国十八年国庆纪念日告同志同胞书》,《国庆纪念册》(出版地和时间不详),第5页。
(38)《总理就任非常大总统职第九周年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8期,1930年4月21日第51页。
(39)(40)胡汉民:《双五节纪念》,《中央周报》第47期,1929年4月29日第19页,第20页。
(41)蒋介石:《告全国国民书》,见中央宣传部编:《革命纪念日史略》,第128页。
(42)《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中央日报》1943年3月29日第2版。
(43)何应钦:《当前革命建国之中心工作》,《中央日报》1948年10月10日第2版。
(44)蒋介石:《纪念革命先烈的感想》,《中央周报》第148期,1931年4月6日第1~2页。
(45)《第一届青年节蒋主席昭告全国青年》,《中央日报》1944年3月29日第2版。
(46)《蒋主席发表告全国青年书》,《中央日报》1946年3月29日第2版。
(47)蒋介石:《世界革命领导者总理的精神——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九江总理诞辰纪念大会》,第142页。
(48)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中央日报》1929年3月12日第3版。
(49)(50)蒋介石:《总理生平之根本思想与革命人格——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在江西省党部举行总理逝世九周年纪念讲演》,《中央周报》第303期,1934年3月26日,第4页,第1页。
(51)《七十二烈士殉国十九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3期,1930年3月17日第45页。
责任编辑梅莉
2011-01-1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与诠释”(09JZDW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