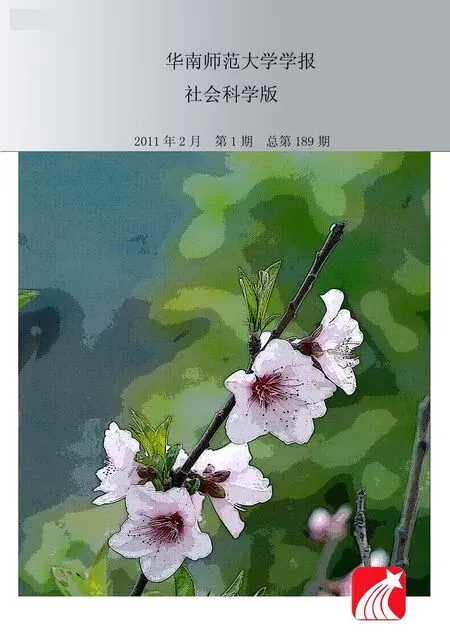汉语方言与地方民俗文化的多样性
2011-04-10吴璇
吴 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留学生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上说,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均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汉字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更远非其他文字可以比拟。汉字不仅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超稳定的内在凝聚力,而且由于人们共同使用的悠久历史又使其文化内涵愈加丰富。几千年来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使用着共同的文字——汉字进行交际,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既是汉字语言文字特有的历史,又是整个华夏文化的历史。“中国语言文字是中国通用的唯一交际工具,唯其如此,它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如果中国人有一天失掉了表意体系的汉字,那“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1]。因此,充分认识汉语言文字特有的文化意义,对于正确使用汉语言文字,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促进国际汉语推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从汉语方言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上,来分析汉语言文字对地方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和民俗文化的形成所具有的巨大影响。
一
汉语不仅因其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了古今的差异,而且因为使用地区的不同形成了方言的分歧。汉语的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言的地域分支,也是汉民族各类型的文学艺术和民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语言学家认为,汉语大致有七大方言,它们之间的差异在语音上表现得最为显著。一个方言区的人们往往听不懂另一个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所谓“吴侬软语、绮丽缠绵”,“朔漠高音、苍凉劲直”,讲的就是方言上的语音特点。帕默尔在谈到汉语的方言时说:“虽然中国的不同地方说着互相听不懂的方言,可是不管哪个省的人,只要是有文化的,都能马上看懂用古代文字写的一个布告。但是据说,一个广州人要是把它读出来,那声音对一个说北京话的人根本不能传达任何意思”[1]。汉语的方言分歧,给人们的生活交往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方言是以语音特点为基础形成了地方性特征,而语言文字又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汉语的地方性特征也就构成了汉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语言的差异性不仅反映了文化的地方色彩,而且促进了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首先,汉语方言促进了地方文学艺术的多样化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的地方戏。地方戏的生命力就在于使用方言,或者说戏曲先是地方的,而后才是全国的,有如艺术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是国际的。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戏剧文化,尤其在戏剧音乐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方面,更是独具特色,异常丰富。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繁富的方言土语,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及独特的地方音乐如民歌小调等,都给千姿百态的地方戏曲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丰富的地方戏曲声腔的产生和变化来源于复杂的方言,中国各种戏曲曲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演唱腔调的不同上,声腔的不同来自于方言和地方音乐的不同。方言不同,字音调值不同,必然造成旋律、行腔的变异。京剧的昂扬激越离不开北京话的抑扬顿挫,粤剧的南国风味离不开广东方音的特殊音系。单就声调来说,北京话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音与音之间音值差别较大,故音调变化明显,戏曲唱腔就有发音宏亮、抑扬顿挫之感;而粤方言的声调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等九个声调,音与音之间音值差别较小,故音调变化不如北京话明显,戏曲唱腔就有“靡靡之音”之感。即使北方方言内部一致性很大,但北曲仍然因“五方言语不一”而有中州调、冀州调之分(见魏良辅《南词引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认为北派声腔有金陵、汴梁、云中的不同,这些不同或区别都是由于方言语音的歧异而产生的。广东四大剧种中,粤剧自清末以来用粤语演唱,故流行于两广的粤语区(包括香港);潮剧因用属于闽南语的潮州方言演唱,故流行于潮州方言地区,即潮安、汕头、揭阳、普宁、陆丰、海丰、南澳、丰顺及福建的东山等地;琼剧本是潮汕地区高腔剧种的分支,全改用闽语的海南方言演唱,故流行于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海南方言区;广东汉剧则是客家方言区的主要地方剧种。而粤剧、潮剧、汉剧还广泛流行于聚集着众多广东华侨的东南亚国家地区。可以说,方言语音的差异是造成中国戏曲、曲艺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语方言的读音,也影响到地方民俗文化的形成。同是在广东省,讲潮州话的人因潮州音“橘”、“吉”同音,故旧俗春节时都要带四个橘子(主要是潮州柑,潮州人认为柑橘同类,潮汕地区又盛产潮州柑),到亲友家拜年,互祝“年年大吉”,“世世大吉(四与世同音)”、“二家(你我)大吉”,而亲友也以四个柑子回赠。广州话虽然也讲“大吉利市”,就没有拜年送橘子的风俗,广州人还把“橘”带进骂人的词及贬义的话中,如“混橘”(相当于普通话的“混蛋”,以橘子的外形类比蛋的外形),如表现一种做事不顺心或不能遂心愿的沮丧心情的话“只系得个橘”(一切都等于零的意思)。广州话“干”、“肝”同音,所以猪肝称为“猪润(干的反义词)”而讳“干”;潮州话“干”、“官”同音,所以小孩子生日要吃豆腐干、葱(与聪同音)加糖做成的菜——“甜豆腐干”,预祝小孩甜蜜可人、聪明,长大当大官。以上这些例子,反映了由于方言方音的不同而造成的有趣的民俗文化现象。
对于数字的应用,也反映了不同的民俗文化心理。同在广东省,讲广州话的人以“八”、“九”为吉祥数字,送礼常以八、九为数,而忌讳“四”。因在广州话中“八”与“发”谐音,取其“发达”、“发财”之意;“九”与“久”音同,取“长久”之意;“四”与“死”音近,讳死不吉祥而不用四为数。而讲潮州话的人则以“四”为吉祥数字,送礼常以“四”为数(现在送礼以“八”为数是受了粤方言区的影响,在潮州话中“八”与“发”音韵皆不同),忌讳“九”。因在潮州话中“四”与“世”音同,取“世世交好”(即世代交好)之意;“九”与“狗”音同,讳其骂人而不用九为数。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广州籍的准女婿给潮汕籍的未来岳父送聘礼,奉上三百九十八元,结果被未来岳父用扁担打出门来,理由是“你小子太过分,把未来岳父当‘狗’来嘲弄。”北方民间旧时婚俗,在新婚夫妇进洞房前,由一年长的女性亲属向寝帐撒枣栗,并唱《撒帐歌》:“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这是利用“枣”谐“早”,“栗子”谐“立子”,而取“早立子”的吉意向新婚夫妇祝贺。而在闽南方言中“枣”、“早”不同音,所以撒帐时并不用枣子,而用花生,撒帐人边撒边叫道“花生生不生”,闹洞房的人应“生”,谐“生子”之意。过年时广州人要吃鱼,以此象征“年年有余”(因广州话中“鱼”、“余”谐音);而潮汕人要吃萝卜,因为在潮州话中萝卜称为“菜头”,跟“彩头”相谐音,以此预兆新的一年有好彩头、好运气。这些例证都充分揭示了汉语方言方音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方言词汇的差异有时能体现文化发展在时代上的差异。比如,北京人炒菜用“锅”,广州人用“镬”,潮州人用“鼎”,其实三者异名而同物。三者异名正体现了炊具形制的古今变化。同是供睡觉用的床铺,北京话、广州话都叫“床”,而潮州话叫“眠床”,潮州人床桌不分,都叫“床”,具体使用“大床”(指大桌子,供放东西或吃饭用)、“床仔”(即小桌子,供吃饭或喝茶用)和“眠床”(即床,供睡觉用)等词,分别指称用途不同的物品,这印证了古代汉人的习俗和生活。一般来说操同一种方言的人,他们的生活、风俗习惯都有其一致之处。
方言词汇的差异往往能反映出不同地方的民俗文化特征。如“用小麦磨成的粉”北方叫“面”,南方叫“面粉”。用“小麦”粉制成的条状食品,北方叫“面条”,南方只叫“面”。“稻米”北方叫“大米”,南方只叫“米”。“粟”北方叫“米”,南方叫“小米”。用稻米煮成的干饭,北方叫“米饭”,南方只叫“饭”。这些名称反映了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的不同饮食文化特色。北方人吃饭主要是吃以面粉制成的食物,所以吃用稻米煮成的饭时要说“米饭”,以示与日常的“饭”相区别。南方人吃饭向来就是吃米饭,所以不必用别的词,但是偶尔吃面当饭(或点心)时,都要说“面”,以示与日常的饭相区别。南方以产大米为主,所以说“米”即指大米没有误会,指小米时要冠以“小”,以示区别。反之,北方产小米的地方,说“米”即指“小米”,说“大米”时,要冠以“大”。
二
汉语方言区的语言禁忌,也反映了不同方言区人民的不同文化传统及地方民俗文化。如北京旧时口语忌用“蛋”字,在以下几个词中都避用“蛋”字:鸡子儿(鸡蛋)、炒黄花(炒蛋)、松花(皮蛋)、木樨汤(打蛋汤))。“蛋”只作贬用:浑蛋、坏蛋、捣蛋、滚蛋、狗蛋、王八蛋。但上海口语却不忌用“蛋”而忌用“卵”字。因为它专指人的私处,所以“卵”字只用于罡语:老卵、小吋卵、阿胡卵。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述:“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圆果,伞为聚笠;讳狼藉,以榔槌为兴哥;讳恼躁,以谢灶为谢欢喜。”这是因词义产生的语言禁忌。
由语言禁忌还发展为民俗中行为的回避。例如沿海居民吃鱼时,吃完一边不能将鱼翻过来吃另一边,而要小心地把整条鱼脊骨挑起放在一边,再吃另一边鱼肉,这是忌讳翻船的“翻”字,谓“顺过来”。旧时杭州吃梨要吃整个,不能切开,因为“梨”、“离”同音,被认为暗示离散,到今天男女情侣吃梨时仍忌这一点。
这些各具特色的民情风俗,实际上是中国人语言禁忌在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本来语言是与劳动同时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但是,在汉民族的初民时期,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低下与征服自然能力的不足,人们往往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很不理解甚至感到困惑、恐惧,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往往被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或者同某些自然力给人类带来的祸福联系起来。这样,语言就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难,竟以为语言是祸福的根源。谁要是得罪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谁要是讨好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庇护和保佑。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语言的禁忌和灵物崇拜”[2]。语言的禁忌,其实是一种迷信语言的力量的表现,是一种原始心理的反映。这种迷信和原始心理并不仅仅存在于人类的初始阶段与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的少数民族的人们身上,而是由于语言的媒介作用和承续功能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虽然汉民族有着悠久辉煌的文明史,但是中国人却由于相对保守稳定的文化传统与心理作用,对于语言的禁忌的原始心理相对于其他民族更明显、更普遍。语言的禁忌成了长久根植于中国人心灵中的文化传统,也形成了不同方言区多姿多彩、风趣各异的民俗文化。
综上所述,汉语方言对地方文学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和民俗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充分认识汉语言特有的文化意义,对于正确使用汉语言文字,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促进汉语国际推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 陈原. 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