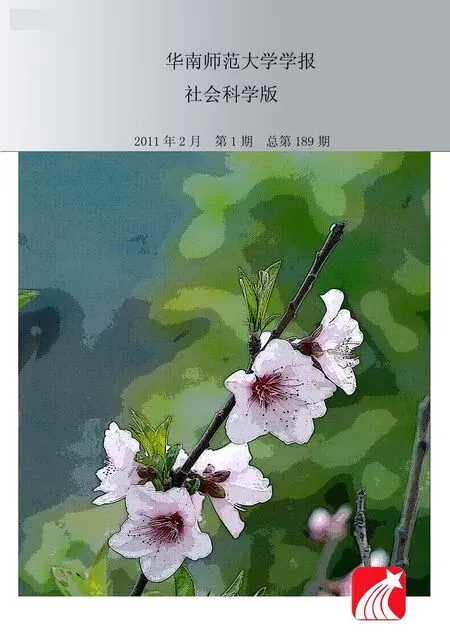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学说的改造及其内在问题
2011-04-10卢兴,吴倩
卢 兴, 吴 倩
(1.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2.天津外国语大学 涉外法政学院,天津 300204)
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重要代表,牟宗三力图会通中西哲学传统以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在牟氏思想的西学资源中,康德哲学无疑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所建构的“两层存有论”直接源自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身”的划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牟宗三对康德的“物自身”学说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实际上是借用康德的术语重建了儒家的价值本体。然而学界以往的研究或是依据于牟氏的观点进行述介,或是站在康德哲学的立场上批评牟氏的误读,而对于牟氏的这种改造工作的思想理路分析得不够细致,对于其中所存在的理论问题揭示得不够深入。本文试从康德和牟宗三的文本着手,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以期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
一、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学说的改造
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在于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批判,提出了“现象”与“物自身”的划界,在此基础上将知识的来源转到主体自身,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康德的“革命”中,传统形而上学所探讨的对象都被归入“物自身”的范围而置于“只可思而不可知”的彼岸世界,而“物自身”却成为康德哲学的“黑箱”,历来为后学所争讼不已。严格地说,康德所言之“物自身”不是一个“概念”(“概念”属于知性),而是一个超验的领域(知性所不及),其中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只不过基于一个共同特征而被归在一起,这个共同特征就在于“不可知”。康德有时用单数Ding an sich(英文thing in itself),有时用复数Dinge an sich(英文things in themselves)。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既然“物自身”不可知,那么何以会有复数(因为关于“量”的范畴属于知性而不能有超验的运用)?这就涉及“物自身”这一术语的具体所指。简言之,其在理性的理论运用中基本是消极的含义,是“感性的来源”、“认识的界限”和“理性的理念”[注]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第239-24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而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具有积极的含义,主要指实践理性的三个“悬设”。因此,尽管“物自身”是一个“黑箱”,但其对认识和实践所产生作用是明确的,其自身也透露给我们一些信息,至少我们思维到有三个不同的理念归属于其中,故而可以将“物自身”的所指符号化为“3+X”:其中的“3”指“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三个纯粹理性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的“物自身”属于“本体”(Noumenon);其中的“X”指刺激感性直观产生经验却不为直观所及、同时作为知性之统觉所对之“物”而作用于经验,这个意义上的“物自身”是“先验客体”(das transzendentale Objekt)。以上所言之“本体”与“先验客体”在消极意义上(不可知)可以等同,而在积极意义上有细微的差别。这样,在康德看来,所谓“物”(Ding)或“对象”(Gegenstand)被区分为两重身份:“现象之物”(“感性直观”的对象)和“自在之物”(“智性直观”的对象)。康德进一步在“物”(“对象”)的两重身份的意义上,以拉丁文“Phaenomena”与“Noumena”表示两个世界的划分,这两个世界分别是经验的“感知世界”和超验的“理知世界”。实际上康德所谓的“Noumena”是一个表征范围的概念(代表了整个“理知世界”),而不是表征实体的概念(因为不存在这样一个“实体”),因而“本体”可以是复数。
牟宗三不赞同将康德所说的“Noumena”直译为“本体”,而译之为“智思物”。因为这一概念与中国哲学中所讲的“形而上的实体”意义上的“本体”很不相同:后者是唯一的、绝对而无限的;而康德所讲的“Noumena”却是一个复数的概念,代表了一种“散列的态度”,其既包括“自由”、“灵魂”和“上帝”三个理念,也包括“物之在其自己”即作为“Noumena”身份的“物”。[注]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44、3、7页,(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在牟宗三本人的使用中,“本体”指“本心仁体”或“知体明觉”;“物自身”既指狭义上的“智思之物”(与三个理念并列),也指广义上的“本体界”(“睿智界”):当牟氏依据康德的二元划分而建立“两层存有论”时,“无执的存有论”对应于广义的“物自身”;当牟氏讲“心物一起朗现”时,这里的“物”是狭义的“物自身”。
尽管牟宗三大量借鉴了康德的术语,但两者根本不同在于牟氏完全摒除了康德赋予“物自身”的“不可知性”,由于承认人具有“智的直觉”(一般译为“智性直观”)的能力,可以直觉到甚至创造出狭义的“物自身”,因而后者成为一个确定性的表征实体的概念,这样的“Noumena”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之本来面目”,并且我们的“心”对其有完全的把握。这样进一步引起了牟氏的追问:“问题底关键似乎是在:这‘物自身’之概念是一个事实问题底概念呢,抑还是一个价值意味底概念?这点,康德并未点明,是以读者惑焉。”[注]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44、3、7页,(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康德的问题,而是牟氏自身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分辨清楚“物自身”是“事实的”还是“价值的”,那么其无疑就是可知的,这显然不是康德的思路。牟氏之所以有此问题,在于其肯定了“智的直觉”能够完全把握“物自身”,因而必须把“物自身”的内容说明白,而后者是康德说不明白抑或没必要说明白的问题。牟氏进一步指出,“物自身”不是一个认知对象意义上的“事实上的原样”,而是一个“高度价值意味的原样”,如禅宗所说的“本来面目”。“如果‘物自身’之概念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事实概念,则现象与物自身之分是超越的,乃始稳定得住,而吾人之认知心(知性)之不能认识它乃始真为一超越问题,而不是一程度问题。”[注]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44、3、7页,(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这样,在康德那里消极意义上的“物自身”(狭义)被转化为积极意义上的“价值本体”,进而将整个“本体界”(广义的“物自身”)转化为一个“价值世界”,这里既显示出牟氏将本体世界价值化的儒家立场,也可以看到其对康德哲学的一种创造性的“误读”。牟氏认定“物自身”是一个高度价值意味的概念,其实质在于:首先将“先验客体”意义上的“物自身”收摄于“Noumena”意义上的“物自身”之中,大大弱化了“物自身”在认识过程中作为经验统一性之基础的意义;其次将“Noumena”意义上的“物自身”实体化为“智的直觉”所对之“内生自在相”(Eject),成为宇宙本源意义上的“实体”,类似于神学中上帝所造之“物”;再次将这个“物”纳入儒家“道德的形上学”体系而价值化为道德意义上的“实理实事实物”,成为价值意义上的“物”。经过这一实体化、价值化的过程,“物自身”就成为了王阳明所讲的“明觉之感应”意义上的“物”;与此同时,三个超验理念“自由”、“灵魂”和“上帝”转化为一个呈现即“自由无限心”,故而在明觉之感应中“心”与“物”呈现为一种“体用互即”、“如如朗现”的关系。这样,康德那里广义的“物自身”概念所蕴含的“3+X”的结构就被牟宗三改造为“心体物用”的结构,整个“本体界”就等同于“价值世界”;而康德关于“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分就被改造为“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之间的划界。
二、牟宗三“物自身”学说的内在问题
如前所论,牟宗三对康德的“物自身”概念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肯断“物自身”是一个高度价值意味的概念,将这个概念进行了“实体化”和“价值化”,这显然并不符合康德的原意。同时在这种改造中包含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康德那里作为认识来源的“物自身”的意义被牟氏极大地弱化了。因此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本体界仅仅是道德的世界,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都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本体地位,整个认知活动以及事实世界都缺少形上根据。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尽管牟氏在“现象界的存有论”层面进行了知识论的建构,但这种知识论仅仅成为一种无根的附属物(用牟氏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虚执”和“权用”),难以真正为经验知识以及科学民主奠定基础。
以下具体分析牟宗三对“物自身”概念的“实体化”和“价值化”过程,进一步揭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先看第一步“物自身的实体化”。前文已述,康德所谓“物自身”的内涵是“3+X”,其中的“X”是“先验客体”。“先验客体意味着一个等于X的某物,我们对它一无所知,而且一般说来(按照我们知性现有的构造)也不可能有所知,相反,它只能作为统觉的统一性的相关物而充当感性直观中杂多的统一,知性借助于这种统一而把杂多结合成一个对象的概念。”[注][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28-229、331页,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先验客体”既为外部现象奠定基础,也为内部直观奠定基础[注][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28-229、331页,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康德对“先验客体”的描述表明这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术语。一方面刺激感官产生直观中的杂多,另一方面作为统觉的相对之物确保表象的统一性,这些对认识过程都有积极的作用。牟宗三通过研读康德的著作,指出其所使用的“先验客体”与“本体”两术语容易引起混淆,认为“‘超越的对象’(本文译为‘先验客体’——引者注)一词实是不幸之名,亦即是措辞之不谛”[注]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76、9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因而可以把康德“先验客体”之名取消。在牟氏看来,“物自体(本文译为‘本体’——引者注),假定预设一智的直觉时,它可以为一‘真正的对象’。”[注]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76、9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牟宗三之所以取消了康德这个认识论上具有积极作用的概念,实质上是将虚指的“先验客体”收摄于实指的“本体”(Noumena)之中,这样就完成了“物自身”实体化的转变。这个实体性的“物自身”就是“智的直觉”所呈现的“物”,亦即“自由无限心”之“经用”。
再看第二步“物自身的价值化”,牟宗三进而证明这个实体性的“物自身”必然是价值意义上的实体而不能是事实意义上的实体。在解析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身”之间先验的区分时,他曾多次引用康德《遗著》中的话:“物自身之概念与现象之概念间的区别不是客观的,但只是主观的。物自身不是另一个对象,但只是关于同一对象的表象之另一面相。”[注]Kant: Opus postumum,科学院版《康德全集》, Bd.ⅩⅫ, S.26. 这里引用是牟宗三的译文,见氏著《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37页。康德在这里所谓“主观的”(subjektiv)意思是说以上区分是对人的认识能力而言的,而其对人之外的存在者是否依然有效是我们不得而知的。这更不意味着确定有一个“上帝”在人之外实存着。而牟宗三则将这里的“主观的”理解为对于两种不同的“直觉”而言,认为对于同一个“物”,以“智的直觉”观之为“物自身”,以“感触直觉”观之为“现象”;而康德只承认人具有“感触直觉”,将“智的直觉”交托给上帝,故此康德不能充分证成“现象”与“物自身”的先验区分。由于牟氏将“物自身”实体化了。因此必然实存着一个“智的直觉”去创造它,这样“上帝”就作为一个实体性概念被牟氏引入了康德的哲学框架中:“如果我们把上帝类比于本体,则依康德,上帝所面对的不是现象,乃是物自身。如是,这乃成上帝、物自身、现象之三分。这是客观的、笼统的说法。如果详细言之,同一物也,对上帝而言,为物自身,对人类而言,则为现象。”[注]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14-15、10、111页。在牟氏看来,康德为了保证两层的区分,必须请出一个实存的“上帝”来创造“物自身”,这就将“上帝造物”的神学问题引入康德的论述:“吾人根据神学知道上帝以智的直觉去觉一物即是创造地去实现一物。”[注]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14-15、10、111页。就“上帝造物”而言,就出现了“无限”(“上帝”)如何创造“有限”(“被造物”)的问题,这里牟氏又将康德关于时空的观念性引入这个神学问题的解释中,指出上帝所造之物(“物自身”)不在时空之中(因为时空是人的先天直观形式)。“如果真要肯定它无时空性,它之为有限物而在其自己决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只有在此一转上,它始可不是一决定的有限物,因此,始可于有限物上而说无限性或无限性之意义。”[注]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14-15、10、111页。这里,“有限物具有无限的意义”就是说物自身“无而能有、有而能无”,这就是牟氏所谓的“价值”的含义,因而他得出了“物自身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的结论。接下来牟氏就比较顺利地将“智的直觉”归属于人之“自由无限心”,以此价值性之“心”呈现价值性之“物”,成就“本体界的存有论”。
牟氏的基本理路如上所述,但论证过程颇为繁琐,在本文看来至少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混淆不清。第一,牟宗三混淆了康德哲学的语境和神学的语境。在康德那里,上帝只是一个实践理性的“悬设”,尽管有“上帝创造自在之物本身”的类似提法*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40页,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但相关文本旨在说明:说上帝在“感知世界”中(遵从自然因果律)创造“物”(现象)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而只有在“理知世界”中“上帝造物”才能够避免矛盾,但究竟这个上帝是否实存、如何造物等都是我们人类所不可能知道的;在基督教正统神学看来,“上帝造物”是创造物的个体之实存,不仅创造物的形式,也创造物的质料,并且是使其形式与质料结合的动力因,甚至于人心中关于“物”的观念也是上帝所赋予的,这也就是说康德意义上的“现象”也是上帝的创造物,这里由“无限”到“有限”的转变是上帝之“全能”的表现,不同于牟氏所谓“觉之即生之”的创造方式。因此可以说,“上帝造物”的问题不是康德哲学中的问题,而是一个神学中的问题;而牟宗三将这一神学问题改造为“上帝以智的直觉去觉一物即是创造地去实现一物”,实际上是儒家道德的形上学“本体之创生性(活动性)”的投影。第二,牟宗三混淆了“时空中之物”的有限性和“上帝所造之物”的有限性。在康德哲学中,前者是现象身份的物,其有限性来自人的感性直观形式;后者物自身身份的物,其是否为“有限”或“无限”是我们人类所不得而知的。因为“限制性”(Limitation)是康德所谓十二个知性“范畴”之一,其只能用之于感性直观所得的经验,而不能用于物自身。在康德那里,不仅不存在“上帝造物”的问题,而且不存在“无限”创造“有限”的问题,因此牟氏就“创造”问题上讲价值性的说法就难以成立。因为康德所说的“物自身”不存在“有限”或“无限”的问题,也不能确定是“事实概念”还是“价值概念”,说其“空洞”也可,说其“并无实义”也行,这正是康德“经验实在论”的本义。总之,牟宗三并未能成功地证明康德的“物自身”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尽管他处处依托康德的术语,但在根本精神上与康德背道而驰,甚至有回归于神学的取向,因此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做法是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去批判化”*参见邓晓芒:《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三)——关于“物自身”》,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抛开康德哲学而不论,牟氏通过繁琐的论证而将“物自身”价值化的过程包含了许多混淆和臆断,不能真正使人信服。
由此我们可以确知,牟宗三所坚持的“价值优位”的立场无疑来自于儒家传统,而不是康德哲学。牟氏将康德所讲的“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在“先验人类学”意义上的优先性转变为在“存有论”意义上的优先性,力图证明康德也是一个“价值优位者”,这是对康德哲学的一种误读。牟宗三所处的“后工业时代”与康德所处的“启蒙时代”已然有相当大的差别。18世纪的思想家力图达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并重双显与和谐统一,而“现代性”演进到20世纪却出现了“科学”意识形态化、“工具合理性”一方独大之势,“事实”与“价值”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立。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具有为西方现代性补偏救弊的针对性,力图通过重建“价值之体”而为事实世界和科学知识奠基,其作为“科学一层论”、“事实一元论”的反话语出现,却以同样极端的方式予以表达。正如傅伟勋所指出的,这种“泛道德主义”与“唯科学主义”一样,同样具有“化约主义”的弊病*参见傅伟勋:《中国哲学往何处去——宏观的哲学反思与建议》,见氏著《“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同时也应该看到,牟宗三“泛道德主义”(或者说“泛价值主义”)的思想倾向根源于儒家传统本身,而这种“价值的泛化”只是在“现代性”之两个世界分化对立的语境中才成为问题的。易言之,就以关怀人之德性生命为根本特质的儒家系统自身而言,无所谓价值之“泛化”,只是一个“生生大化”之价值宇宙;只有对以“工具合理性”为基本动力的“现代性”而言,“道德”或“价值”的独尊性才对知识的独立性产生阻碍。综上所论,牟宗三哲学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必然要走出“泛道德主义”的思想窠臼,必须将“本体/现象”的划界与“价值/事实”的划界区别开来,以便在“本体”的层面为“事实世界”奠定基础,成就独立的、有根基的知识论,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物自身”学说包含着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