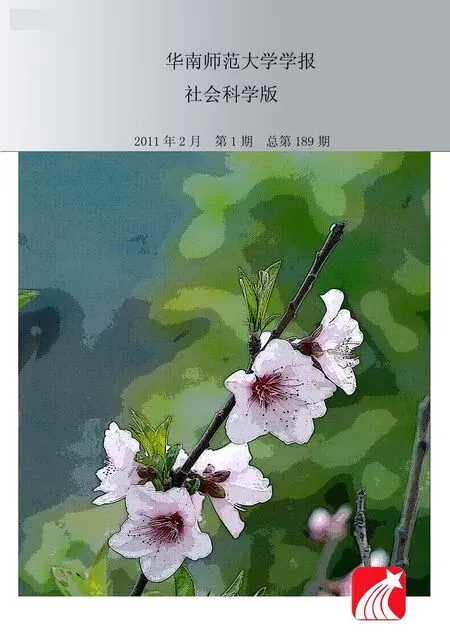以西释中与以中评西:从牟宗三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2011-04-10周炽成
周 炽 成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牟宗三之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传回大陆,至90年代而影响日著,到新世纪则更广为人知。不过,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牟学研究,大体上述得多而评得少,顺取者多而逆思者少,泛泛而论者多而有真知灼见者少。本文试图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讨论牟宗三之学,以冀为牟学研究和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献一孔之见。
一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以西释中是最正宗、最有影响的方法。在牟宗三之前,已有很多论者如胡适、冯友兰等运用这种方法。虽然牟宗三与胡适不和,并对冯友兰多有微词,但他们在以西释中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有很强的西方哲学背景。胡适和冯友兰都留学美国学哲学,上同一个学校(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同一个导师(杜威)。虽然牟宗三没有留学西方,但他的西方哲学素养比起胡、冯有过之而无不及。胡、冯都没有出版过专门关于西方哲学的著作,而牟则有多种这方面的书(《现象与物自身》、《认识心之批评》、《理则学》、《逻辑典范》等)。牟宗三对西方哲学之深度和广度的把握确实超过了胡适和冯友兰。
牟宗三很强的西方哲学背景为他以西释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他跟胡适、冯友兰一样都很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逻辑方法来讲中国哲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以注重逻辑方法而有名,冯友兰的新理学也非常讲究逻辑,讲究表达的严密性和系统性。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从朱熹的旧理学发展出来的。冯友兰之新,关键就新在吸收西方哲学的优点,尤其是其注重逻辑的优点。朱熹的理学,散见于他的语录、经典解释、书信等地方,而不是系统地阐述于一部或数部专著之中;但冯友兰的新理学却在一部专著中得到系统而严密的论说。新理学中的理,确实在逻辑上要比旧理学中的理更纯、更粹、更精。充分认识到逻辑分析方法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的冯友兰,[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见《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27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中娴熟地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典范。事实上,牟宗三也是这样做的典范。在20世纪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中,他对西方逻辑所下的功夫最深,成就最高。他走上哲学之路是从逻辑开始的。在读大学期间,他受张申府、金岳霖、张东荪三位教授的影响最大。张申府是中国数理逻辑的奠基者之一,而金岳霖在逻辑学上的贡献早已得到公认。牟宗三于大学期间就完成了《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及道德哲学》。在这部著作中,他已用逻辑方法研究《周易》。他说:“卦可以是一个逻辑命题,爻亦可以是一个逻辑命题。卦是复合命题,爻是简单命题。命题之合仍为命题。从这方面看,是谓‘数理逻辑’,或‘记号逻辑’。”[注]牟宗三:《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及道德哲学》,第3-4页,天津大公报社1935年版。颜炳罡指出:“他对《周易》的研究是其思辨和逻辑兴趣的结果,而通过对《周易》的系统研究,又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思辨逻辑兴趣。”[注]颜炳罡:《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第1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西方逻辑的视野使牟宗三对《周易》有了全新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批评中国人缺乏逻辑头脑:“中国人头脑简单,理智薄弱,每好将事实归化简单,说到自己所想到的因,必斩钉截铁以为是惟一的因、充足的因,旁的都不是,旁人说的都不对。”[注]牟宗三:《中国人的具体感与抽象感》,见《寂寞的独体》,第129-130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牟宗还对中国文化因逻辑等的不发达而未开出学统有清醒的认识:“一个文化的生命里,如果转不出知性形态,则逻辑数学无由出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无由出现,而除德性之学之道统外,各种学问之独立的多头的发展无由可能,而学统亦无由成。此中国之所以有道统而无学统也。”[注]牟宗三:《历史哲学》,第1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30年代开始,牟宗三对逻辑的兴趣保持终生,以逻辑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兴趣也保持终生。确实,在他的晚年,他关注道德甚于关注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逻辑。在他的哲学中,逻辑与道德并不冲突,而是融在一起的。牟宗三要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不是违反逻辑的,而是合乎逻辑的,甚至可以说是逻辑地推出的。从胡适到冯友兰,再到牟宗三,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逻辑方法越来越深入地运用于中国哲学研究中。
牟宗三在以西释中的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的西方哲学概念:本体、本体论、现象、物自体、知性等等,从而对很多中国哲学的内容作了新的解释。他最引人注目之处而且也可能是最有争议之处是以康德哲学来阐释儒学。牟宗三对康德哲学所下的功夫之深广为人所周知。他是华人中第一个独自全部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学者。他借用了康德哲学的很多东西来解释儒学。其中,他以康德对自律道德和他律道德的看法来分判王阳明与朱熹最有意思。在康德看来,自律道德建立在意志自律的基础上,而他律道德则建立在意志他律的基础上。道德法则(1)从经验确立,(2)从“范例”引申,(3)从人性的特殊属性、人类之特殊的自然特征、脾性、性好、自然的性向推演,(4)从上帝的意志来建立,这些情况都意味着意志他律和道德他律。牟宗三说:“康德将属于他律性的道德原则,或是属于经验的,由幸福原则而引出者,或是属于理性的,由圆满原则而引出者,尽管剔除,而唯自‘意志之自律’以观道德法则。……凡是涉及任何对象,由对象之特性以决定意志,所成之道德原则,这原则便是歧出不真的原则,就意志言,便是意志之他律。意志而他律,则意志之决意要做某事便是有条件的,是为的要得到什么别的事而作的,此时意志便不直不纯,这是曲的意志,因而亦是被外来的东西所决定所支配的意志,被动的意志,便不是自主自律而直立得起的意志,因而亦不是道德地、绝对地善的意志,而它的法则亦不能成为普遍的与必然的。不要说那属于经验的私人幸福的原则建立不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道德法则,直立不起我们的道德意志,就是那属于理性的圆满原则,不管是本体论的圆满概念(这是指柏拉图传统说),或是神学的圆满概念,即一个属于上帝意志的那独立的圆满概念,亦皆不能使吾人由之而建立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因而亦皆不能直立起我们的道德意志:一个是使我们的意志潜伏于客观而外在的本质底秩序中,一个是使我们的意志蜷伏模糊于那‘可怕的权威与报复’中或‘荣耀与统治’中。”[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112-113、1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另一方面,如果意志给自身立法,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东西,那就是意志自律。牟宗三在解释康德的有关说法时指出:“最纯净而能保持道德自性的道德法则必须是‘意志底自律’(autonomy of will),即意志自身给它自己立法,这既不涉于感觉经验,亦不涉于任何外在的对象,即意志之遵依法则而行纯是无条件的,必然的。”[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112-113、1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在阐发康德对自律道德与他律道德的看法的基础上,牟宗三认为,王阳明主张自律道德而朱熹主张他律道德。王阳明高扬良知,挺立意志,由内而外,与符自律道德合拍,这是很显然的。但是,为什么说朱熹主张道德他律呢?牟宗三解释说:“朱子系统中之实践规律并不是基于利益;但是他的格物穷理之路却使他的实践规律大类乎西方理性主义者之基于存有论的圆满上。依康德,基于存有论的圆满与基于上帝底意志俱是意志底他律之原则。快乐主义基于利益,基于幸福,亦是意志底他律之原则。基于利益之他律其所需要有的世界底知识是经验的;基于存有论的圆满其所需要有的世界底知识是理性的;基于上帝底意志最初是诉诸恐怖与权威,最终亦必落于需要有世界底知识,这知识或是经验的或是理性的。这些原则俱是他律,盖因为其所含的实践规律皆取决于作为目的的一个对象,对于这对象必须先有知识。朱子既取格物穷理之路,道问学,重知识。虽其通过‘道问学’所需要知的是太极之理(豁然贯通之理),存有论的最高实有之理,不是零碎的经验知识所识取的事象以及事象之曲折之相,然亦必须通过这些事象以及曲折之相始能进而认取那太极之理,此即所谓‘即物而穷其理’,即就着‘实然’而穷究其‘超越的所以然’。是则决定我们的行为者是那外在之理;心与理为认知的对立者,此即所谓心理为二。理是存有论的实有,是形而上者,是最圆满而净洁空旷的;而心是经验的认知的心,是气之灵,是行而下者。因此,决定我们的意志(心意)以成为吾人之实践规律者乃是那存有论的实有之理(圆满之理),而不是心意之自律。”[注]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阳明指责朱熹析心与理为二。在牟宗三看来,这种指责就是朱熹主张道德他律的证据。外在的理是主宰,它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而内心的意志不起决定作用。心意不自律,也就是道德不自律。牟宗三认为,朱熹之理相当于西方理性主义存有论之圆满。在西方,道理基于圆满是他律;在中国,道德基于理也是他律。牟宗三还进一步认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道德是他律道德。依牟宗三之见,如果主张自律道德,便不应该主张尊德性以道问学为基础,而应该为尊德性而尊德性;朱熹如此注重道问学,反复倡导“即物而穷其理”,这也是他主张他律道德的一个证据。
引入康德之自律道德理念的牟宗三坚持,从孔孟开始的正宗儒家无疑是主张自律道德的。既然朱熹主张他律道德,他就不属于正宗的儒家。牟宗三以朱熹为“歧出”,这是他研究宋明儒学的一个惊人结论。得出这个结论,与牟宗三的以西释中密切相关。假如他没有一个强烈的康德哲学背景,估计是很难得出这一结论的。当然,这一结论很有争议,正如以西释中很有争议一样。对此,本文最后一部分会进一步讨论。
牟宗三以西释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因篇幅所限,难以一一述说。
二
在牟宗三之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如胡适、冯友兰等只以西释中而不以中评西。这就是说,他们用西方哲学的理念来评论中国哲学,但没有以中国国哲学的理念来评论西方哲学。与他们不同,牟宗三除了以西释中之外,还以中评西。
上一部分已经指出,牟宗三以西释中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以康德哲学来阐释儒学。而他以中评西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以中国哲学来批评康德哲学。兹举其要者于后。
其一,以人可无限批评人只有限。在牟宗三看来,康德哲学有两个预设: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分、人是有限的。他可以接受第一个预设,但不接受第二个预设。牟宗三承认,就其感性生命来说,人是有限的,但人也具有无限心,因而可通往无限性。他将无限心视为本体,即为“无限心体”。牟宗三立足于中国的儒、佛、道三家来讨论这一点。儒家的良知、佛家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道家的玄智(分别相对于习心、烦恼心、成心),都是自由无限心。道德践履以致良知,明心见性而证如来,守静致笃炼神还虚,都是达成自由无限心的途径。在牟宗三看来,儒家的良知最能彰显无限心之无限性。他的结论是: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牟宗三以这个结论来批评康德的第二个预设。
其二,以人有智的直觉批评人无此直觉。在康德哲学中,人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物自体;认识物自体需要智的直觉,而只有上帝才有智的直觉,人无此直觉。人无智的直觉,这也是康德主张人有限的根据。但是,牟宗三认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要肯定人有智的直觉。牟宗三指出:“智的直觉不过是本心仁体底诚明之自照照他(自觉觉他)之活动。自觉觉他之觉是直觉之觉。自觉是自知自证其自己,即如本心仁体之为一自体而觉之。觉他是觉之即生之,即如其系于自己实德或自在物而觉之。”[注]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20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智的直觉’即是那唯一的本体无限心之自诚起明。此‘明’既朗照并朗现物之在其自己,亦反照其自身而朗现其自身。”“智的直觉就是一种无限心底作用。自由的意志就是无限心,否则不可说‘自由’。智的直觉就是无限心底明觉作用。吾人说智的直觉朗现自由就等于说无限心底明觉作用反照其自己如如朗现。因此,智的直觉之主观活动与其所照的其自己之为朗现之客观性是一。这里无真正的能所之对偶,只是一超然的大主之朗现。”[注]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第45、61页,(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康德把智的直觉归于上帝,而牟宗三则把它归于人。在牟宗三看来,它不过是人心的活动而已。这种活动朗现心物,既自觉而又觉他,显示了主观和客观的一体。牟宗三肯定智的直觉是与他肯定人可无限一致的。
其三,以良知的呈现批评意志自由仅仅是一个假定。意志自由与灵魂不灭、上帝存在一起构成了康德哲学的三大假设。它们是康德哲学体系所必需的,但其真实与否的问题是人凭自己的理性能力所不能回答的。牟宗三站在儒家的立场对康德之以意志自由仅仅为假定提出批评。在牟宗三看来,意志自由完全是真实的呈现,正如良知是真实的呈现一样。牟宗三经常谈到一个细节:他在北大读书时,听熊十力与冯友兰交谈。冯友兰说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而熊十力则大为惊讶地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熊十力的话给牟宗三很大震动,让他终身难忘。在牟宗三的话语体系中,自由意志就是良知、性体、心体等。既然良知是呈现,自由意志也是呈现。牟宗三批评康德道:“如果自由只是一假设,不是一呈现……则道德律、定然命令等必全部落了空”;“康德这个不恰当不相应的思考方式,不相干的无意义的赘词,实只表示其对于道德生命、道德真理之未能透澈,未能正视道德真理与道德主体之实践地真实地呈现之义。把一个道德实践上的真实问题弄成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宋、明儒所讲的性体心体,乃至康德所讲的自由自律的意志,依宋、明儒看来,其真实性(不只是一个理念)自始就是要在践仁尽性的真实实践的工夫中步步呈现的。步步呈现其真实性,即是步步呈现其绝对的必然性,亦就是步步与之觌面相当而澈进其内蕴,此就是实践意义的理解,因而亦就是实践的德性之知。”[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133、138、145页。
在批评康德的过程上,牟宗三试图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学(moral philosophy)。在牟宗三看来,康德只建立了道德底形而上学( philosophy of metapyhsics),但未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学。构建道德的形而上学,是牟宗三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它以三个命题为前提:德行优于知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人有智的直觉。[注]颜炳罡:《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第221页。后两个命题前面已经讨论过,而第一个命题也已广为人知。在这三个命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牟式道德形而上学,其最重要的内容可能就是无执的存有论。作为佛教用语,执意味着执着、僵执、停滞。在牟宗三那里,执心是有限心,对应于现象;而无执心是无限心,对应于物自体。佛家的识心、道家的成心、儒家的气灵之心,都是有限心;而佛家的智心、道家的道心、儒家的良知明觉等,都是无限心。牟宗三无执的存有论既是对这几类无限心的现代弘扬,也是对康德哲学的超越。它试图以中国哲学的智慧解决康德遗留的问题,克服康德哲学的不足。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他以西释中和以中评西两方面相结合而得出的理论成果。
以中国哲学来批评康德哲学可以说是牟宗三以中评西的点上的工作,而他对此还有面上的工作。例如,他以中国哲学之内容的真理(强度的真理)而批评西方哲学只注重外延的真理(广度的真理)就属于后者。在牟宗三看来,外延的真理是有数学量、物理量的,而内容的真理就既没有数学量,也没有物理量。内容的真理是道德、宗教方面的真理,它属于生命,系属于主体。西方人用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些科学来研究人,把人纯粹当做对象,就好像研究原子、电子那些对象一样。由这种研究而得的关于人的真理,是外延的真理,而不是内容的真理。而在道德、宗教的意义上研究人,把人作为主体而不是作为客体,由此而得的真理才是内容真理。牟宗三又把外延的真理称之为抽象真理,而把内容真理称之为具体真理。比如说二加二等于四,这是普天下的人都要承认的,这里面没有主观性、没有主体性、没有弹性,这就是抽象的真理。但是,具体的真理则不同。比如说孔子的仁是个普遍的原则,但是你不能说仁是个抽象可以在我们眼前真实的生命里头具体呈现。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也同样如此。仁和恻隐之心都是具体的,但又具有普遍性。孝也是仁的表现,也具有普遍性,只不过孝在对父母亲的特殊关系中表现出来。这情形本身虽然是特殊的,但是表现出来的是理,是普遍的真理。而且孝的表现是无穷无尽的,它在一个具体的强度里随时呈现,并且有不同程度的呈现。仁、孝、良知这些具体真理都既具有普遍性而又具有主观性、主体性和弹性。牟宗三指出:“西方文化现在是当令领导世界,它本身不觉得它的文化究竟有没有毛病,即使有感觉也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当它一旦感觉到光讲外延真理是不够的时候,那它就可以正视东方文化中这种内容真理也有它的价值。”[注]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三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以西释中是主流,而以中评西是支流。此主流和此支流都汇集到牟宗三身上,他实现了以西释中和以中评西的统一。
在牟宗三之前,胡适、冯友兰等都在运用以西释中法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都是以西释中的典范。对胡、冯多有不满的牟宗三事实上继承了二人的以西释中法。略有差异的是,他们所用的西有所不同:胡适用实用主义、冯友兰用新实在论、牟宗三用康德哲学。不过,他们都注重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在这点上又是一致的。对此,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讨论过。
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不久,梁漱溟就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针锋相对地运用以中评西法。他对胡适的以西释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照胡先生所讲的中国古代哲学,在今日世界哲学可有什么价值呢?恐怕仅只做古董看着好玩而已!”[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1、131、130、16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他以中国的直觉批评西方的理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关注呆板的静体,而关注变化,要把握变化,就不能用理智,而只能用直觉。梁漱溟把直觉与孔子的仁和孟子的良知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1、131、130、16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我们今日谓之直觉。”[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1、131、130、16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与中国哲学重直觉不同,西方哲学重理智。梁漱溟对西方理智之过分发达提出批评:“西洋人近世理智活动太盛太强:对自然是从我这里划开,而且加以剖析,把它分得很碎很碎,而计算操纵之……人对人也是划界限而持算帐的态度,成了机械的关系。”[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1、131、130、16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在梁漱溟看来,西方之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人的不和谐,都是理智活动太盛的结果。
梁漱溟和胡适岁数差不多,并同在北京大学教书,但胡适的名气要比梁漱溟大得多。胡适从美国名牌大学回来后即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而梁漱溟是没有出过国门、没有念过大学的土包子。不过,默默无闻的梁漱溟敢于挑战大名鼎鼎的胡适。这位土包子对那位留洋学者的挑战,当然包含了以中评西法对以西评中法的挑战。梁漱溟还在很多细节上批评胡适:批评胡以知识论的方法解释孔子的形而上学和人生论,批评胡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仁,批评胡以为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道德习惯,批评胡不懂得孔子不计较利害的态度而偏袒墨子的重利态度,如此等等。这些批评,事实上也都是对胡适以西评中的批评。因为胡适的知识论、道德习惯论、实验主义(实用主义)等都来自西方。梁漱溟运用以中评西法而得出的具体结论难以让每一个人都接受,但是,他对中国哲学主体地位的追求不应被人忘记,他敢于与西方哲学对话并批评西方哲学的勇气值得充分肯定。读梁漱溟的著作,就不会得出这样的印象:面对西方哲学的大老师,中国哲学的小学生毕恭毕敬,只老老实实听话而没有己见。敢不敢以中评西,是一个问题;评得对不对,是另一个问题。某人是否敢以中评西?这一眼就能看得出。他评得对不对?这个问题就复杂得多,对此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牟宗三的老师熊十力也是以中评西的代表。与梁漱溟以中国的直觉批评西方的理智相似,熊十力以中国的修养批评西方的知识。熊指出:“中人学问起初只是因注重修养,知识看得稍轻,结果便似屏除知识而没有科学了。西人学问起初只因注重知识,所以一直去探求外界的事物之理,他也非是绝不知道本身的修养,只因对于外物的实测工夫特别着重,遂不知不觉的以此种态度与方法用之于哲学,他遂不能证得实相而陷于盲人摸象的戏论。因此,他底修养只是在日常生活间,即人与人相与之际有其妥当的法则,此正孟子所讥为外铄,告子义外之旨即此。后儒所谓“行不著,习不察”,亦谓此等。……站在东方哲学底立场可以说,西人底修养工夫还够不上说修养,只是用科学的知识来支配他底生活,以由外铄故。”[注]熊十力:《答张东荪》,见《十力语要》,第67-68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知识和修养都是人的活动,但这两种活动的方向不同:知识向外而修养返己。熊十力认为,西方人自古希腊时代始即猛力向外追求,而中国人则有注重向里用功的悠久传统。他充分肯定西方人外求知识的意义,尤其是它对于成就科学意义。不过,熊十力对西方科学输入中国之后中国人转向过分地外求感到不满:“自西洋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皆倾向科学,一切信赖客观的方法,只知向外求理而不知吾生与天地万物所本具之理元来无外。中国哲学究极的意思,今日之中国人已完全忽视而不求了解。”*熊十力:《答马格里尼》,见《十力语要》,第145页。熊十力在当时没想到:中国人后来在外求的路上越走越远,以致于内求和返己被作为“唯心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东西遭到猛烈地批判。
这些批判让我们联想起中国大陆几十年以西释中的伤心史。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以西释中总体上还不算太糟糕;但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它的死板单调、横蛮无理就很突出。以西方的一个学派来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以之衡量所有中国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闹了太多的笑话。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阶级斗争等来自西方的话语来讲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所造成的伤害,至今在一些论著还可以看到。“五朵金花”的盛开与“五阶段论”的滥用,都与以西释中密切相关。此“二五”把以西释中推到了荒谬绝伦的顶峰。回顾这段离我们太近的历史,我们就会对以西释中的局限性有更深的认识。
不过,很多论者对牟宗三以西释中的局限性缺乏认识。虽然他以西释中并不比50-80年代的大量大陆学者糟糕,但他也同样有主观武断的地方。例如,他跟大陆学者一样滥用本体论来说中国哲学。其实,在中国哲学中,甚少类似西方本体论的内容。牟宗三三大册《心体与性体》为宋明儒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西方本体论的有色眼镜妨碍了他对那时儒学真相的把握。不错,宋明儒者很热烈地谈“心”论“性”,但是,他们几乎没有用“心体” 与“性体”二词。着迷于西方本体论的牟宗三把一个“体”字加上去之后,宋明儒者的很多说法就可能会被扭曲地解释。心与心体、性与性体的差异是不可以被忽视的。再如,中国哲学家甚少有人讲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但对康德哲学有强烈兴趣的牟宗三却经常以此区分来讲中国哲学。又如,自律道德与他律道德的话语是康德的话语,牟宗三以此话语来讲宋明理学,早已引起了不少非议。笔者同意很多论者的看法:朱熹并不排斥自律道德。在笔者看来,牟宗三以朱子之学为“歧出”,似乎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动机:跟冯友兰“抬杠”。冯友兰讲新理学,发展了朱子之正统。不满冯友兰的牟宗三别出心裁地以朱为“歧出”,从而抗衡新理学。在历史上,阳明学与朱子学之辩不乏意气成份。在现代,牟宗三与冯友兰之辩也同样如此。
在以中评西方面,牟宗三对梁漱溟和熊十力都有所继承。当然,作为熊十力的学生,他对熊的继承更多。不过,他确实超越了他们。牟宗三以中国哲学批评康德哲学,有胆识,有智慧。虽然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曲解了康德,但是,这总比曲解中国哲学更少受非议。作为不是生活在德国的中国人,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把握不够客观,这是情有可原的。而如果他误解了中国哲学,那就不那么容易得到原谅了。
在过去一百多年,西方一直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追赶的目标。“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这一模式无处不在。哲学上的以西释中,也体现了这一模式。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以西释中的局限性就更为明显。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位伟人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过去20年,中国的工业品源源不绝地涌向世界,这确实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但是,我们应该还有其他的贡献。例如,我们还应该把学术产品(包括哲学产品)贡献给世界。而再走以西释中之路不容易达到这个目标;相反,走以中评西之路更合适。在以中评西的视野下,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就可得以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的吸引力就可得以加强。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哲学家沿着牟宗三等人所走的以中评西之路往前走,更广泛、更深入地批评西方哲学,从而为中国哲学对世界的贡献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