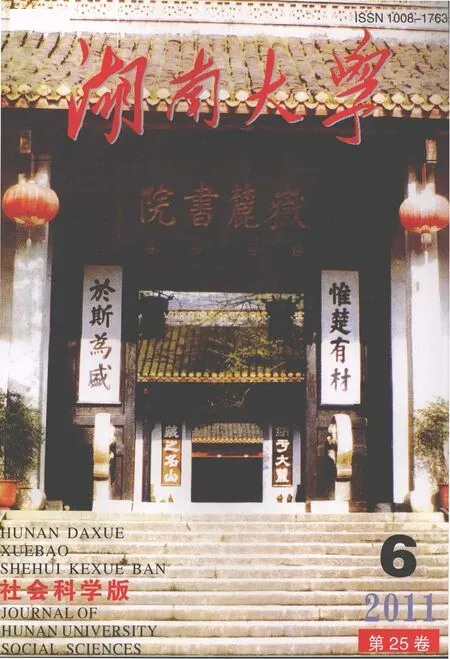国内公共行政基本研究范式的缺失与认同危机*
2011-04-08李学
李 学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厦门 361005)
国内公共行政基本研究范式的缺失与认同危机*
李 学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厦门 361005)
自公共行政学科恢复设立以来,公共行政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其它的社会科学分支相比,已有的理论研究尚未形成应有的学术影响与广泛的社会效应,难以在学术共同体内获得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本土化研究不足、研究问题的空疏性,以及研究方法的不规范,致使公共行政的研究难以产出具有较高学术品质的作品。公共行政的学术共同体必须充分认识既有研究范式的负面影响,提高研究作品的质量,力争使公共行政研究步出初始化的困境。
本土化;研究问题;研究方法;认同危机
公共行政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已经有二十几个年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公共行政相关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该研究领域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影响亦有所提高。然而,公共行政的研究成果,并未在实践部门与学术共同体内部获得足够广泛的认同,普通公众仍然将其理解为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理,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难以满足相关领域实际工作的需要,社会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学术社区中,公共行政研究仍被判定为处于学科发展的初始化阶段。尽管二者对公共行政研究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其共性是一致的,即公共行政已有研究所生产的知识,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这种研究现状,当然有历史的原因,该学科在国内的发展还比较短暂。但是,本着一种学术自觉的追求,公共行政的学术共同体必须惊醒,毕竟公共行政研究既有的学术地位与其研究质量息息相关。因此,很有必要反思已有公共行政的研究,发现其间存在的问题,努力进行改善,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和社会影响力。本文的目的不是贬低以往研究的质量,而是尝试将纳入分析视野里的研究文献,进行一个中观层面的评估,希望通过阐释已有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剖析公共行政研究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来改善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
一 非本土化研究的误导与迷失
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研究的非本土化,也就是说公共行政学者关注的对象并非国内公共行政的实践与问题,非本土化研究主导着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格局。中山大学的马骏教授将其称为研究中心的“非中国化”,指出“相当多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家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和实践,而不是中国公共行政本身”[1],本土化的研究非常不足,尽管个别公共行政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尝试进行了一些本土化研究的努力,但是并未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主流方向。公共行政研究形成这一基本范式是可以理解,公共行政在国内的发展毕竟只有二十几年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个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时期,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引进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努力的一个基本方向。但是,正是这一研究导向与前置性的学术发展环境,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成为公共行政学科产生认同危机的起源。问题决非只是马骏教授言称的“非中国化”那样简单,他对于这一问题危害的认知过于简略,对“非中国化”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缺乏认真的分析与说明。鉴于学科知识引入的必要性与学术研究进行国际知识对话的必然性,仍然有必要深入剖析国内非本土化研究的文献。一方面,可以探析其对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负面影响,引导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关注点由国外向国内转移;另一方面,指出学科知识体系引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提高国内公共行政知识引进的质量。公共行政研究之所以产生认同危机,在以下三个方面与非本土化研究密切相关,值得引起广大学人的重视。
首先,非本土化研究的研究路径,一方面,不能为理解国内的行政管理提供系统的知识,在对公共事务的辩论与社会讨论中难以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坐视其它学科分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对自身研究领域的侵入,使得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难以获得良好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误导了国内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甚至是个人经历,因而社会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社会属性。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公共行政和其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行政作为中立性的“科学”特征,“我们没有理由作出这样一种设想,公共行政学的原则在任何民族国家中会同样有效,或者在某个国家中取得成功的公共行政措施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环境中必然也会取得成功。”[2]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汪丁丁与林毅夫教授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依据经济学学科的特点,阐发了盲目尊奉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局限性以及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但是,反观学科知识更加直接受政治环境制约的公共行政研究,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并未受到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应有的重视,由于缺乏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国内公共行政学者所提供的大部分知识,充满了美国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体系,耳熟能详的一些学术用语如“铁三角”、“互投赞成票”等,实质上只是国外的公共行政学者,根据特定国家的公共行政的现实,直面行政管理的各种社会现象,所构建的理论概念与解释框架。由于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根植于特定国家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与心理的具体场域,这些基本理论与国内公共行政的现实相去甚远,很难对国内公共行政的各种现象进行有效的解释,无助于理解国内公共行政的现实,也难以为政府的实际工作提供符合社会现实的理论指导,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缺乏社会认同的根本原因。
在非本土化研究格局的主导下,公共行政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强烈的倾向:以充分掌握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或者获取国外最新的研究方向,作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评判的重要标准,而轻视或冷落本土化的研究努力;在此非正式学术规则的负面激励下,进行本土化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风险,二者互为推动,形成棘轮效应,抑制了国内公共行政本土化的研究;尤其是早期学者进行非本土化研究所获得的成功,客观上误导了国内的公共行政研究方向,后进的青年学术群体多承袭此研究路向,致使非本土化研究不断持续,误导了学术发展的方向。
其次,由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地位与其学术作品的质量高度关联,非本土化学术研究自身的迷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行政的学科地位,成为公共行政学术研究缺乏社会认同的一个基本原因,这种迷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公共行政知识的选择性引入,获取的知识比较片面;二是盲目接受国外理论研究结论,缺乏批判汲取的学术精神。首先,非本土化理论研究先天的不足,造成对异域公共行政知识的片面理解。学术是在一个相对有效竞争的学术规则下进行的,相关知识的增进与累计需要学术人共同的努力产生,因而只有在一个本土化研究的框架下,才能获取较为全面的公共行政知识,这先天性地决定了非本土化研究的不足。由于公共行政知识的推进,过分依托非本土化的研究,许多学者将获取国外公共行政知识作为学术追求目标,由于时空与价值观念的限制,加上许多学者并未在国外获得过正规的学术教育与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国外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缺乏充分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误解,加上在学术观点引入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性,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致使获取的许多公共行政知识具有很强的片面性,加重了知识引入过程所产生的适应性问题,以其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国内学者在介绍国外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时,常常忽视了国外学术共同体对其的批判,在未对国外公共行政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的前提下,片面强调此类改革的正面效应,将该思潮作为严谨的理论进行传播,误导了国内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兰志勇教授指出国内“新公共管理的学习,属‘紧跟潮流,生吞活剥’”。[3]事实上,根据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迪格对美国100个大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研究,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其实名不副实:一方面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规模极其有限,局限在一些资产专用性不强的公共服务项目上,如垃圾回收与街道维护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改革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并不必然能够起到降低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效果,“城市官员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行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随着城市的差异和时间的流失而变化,诸如城市中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签约者的数量、城市的政治气候、城市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城市政府的监管与评估体系。”[4]许多城市在实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契约到期时将其收回,重新由政府机构提供。诸如此类的问题还表现为:当国外将拉斯韦尔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日渐冷落之时,许多学者仍然将其作为国外公共行政研究的主导范式,甚至将其作为替代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图式。在引入绩效评估时,忽视绩效评估的社会技术特征以及其与法治和民主价值相得益彰的交互作用,将其过分地理想化与科学化。这些片面的研究或者选择性的引入,使非本土化公共行政的研究呈现一种病态的特质,而且或多或少地误导了国内的公共行政的实践。由于许多研究仍将一些新概念的引入,作为自身学术推进的有效路径,我们所获取和提供的知识,只是一些缺乏有效统一的知识线索或公共行政知识的断切面,研究作品的质量与信度比较低劣,进而影响了公共行政学科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
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国内公共行政非本土化研究的另一诟病,是对国外研究成果与学术观点的盲从,存在着不敢逾越的强烈倾向,难以产生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由于公共行政学科诞生的历史相对比较短暂,即使在公共行政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的美国,在研究质量与研究规范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换句话说,尽管国外的理论研究,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美国学者对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进行认真评估后,指出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仍然限于描述问题,并将其概念化的阶段,从学科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国内的非本土化研究只是简单地将其进行编译,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使国内关于公共行政问题的研究屈从于国外学术权威的观点,没有超越国外学术研究水平的内省追求,研究的质量与层次必然难以提高,所获得的知识必然不符合本国的国情,如何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中指出“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5]可见,质疑已有的理论研究对于理论向精深方向的推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国外公共行政研究成果,乃至研究方法的盲从,无疑制约了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质量与学术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与前面两种不利影响相比,弊端更为深重,将别国未经充分验证的学术观点与学科标准奉为圭臬,湮灭了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超越的冲动;尤其是它误导了公共行政研究的青年群体,使其屈从于已有学术权威观点的压力,难以创造出符合国内现实的理论学说,持续地影响公共行政研究水平的提高。在此问题上,同属社会科学系列的社会学、人类学与经济学等学术共同体的努力,有许多值得公共行政研究学人认真借鉴的地方,他们在学习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同时,努力进行学术超越和开展学术对话,而不是盲目的顺从与驯服,极大地提高了其学科分支体系的质量,获得较高的学术声誉和良好的社会认同。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群体,必须勇于突破既有的学术羁绊,以开放的心态锐意进行革新,使理论研究在植根于国内公共行政现实土壤的同时,积极开展学术对话,致力于解决国内公共行政的现实问题,才能生产出能够符合国内公共行政现实的精深理论。
二 研究问题泛化和空疏
如果非本土化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国内公共行政研究认同危机的起因,研究问题的空疏与泛化,则是公共行政缺乏学术影响的另一重要原因。公共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这门学科发轫之时,即带有强烈的实践导向,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是其基本的学术使命之一,实现这一使命则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基本条件。“(社会)科学研究是以个体思维方式从事的社会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领域,他的著作和文章是整个社会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是写给别人看的,是用这种方式影响社会。”[6]而许多公共行政领域理论研究者在学术行政化的影响之下,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官方评价体制下的学术成就,忽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缺乏剖析实际问题的勇气,致使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显得泛化与空疏,作品缺乏现实性与针对性,不但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降低了学术的品格,二者交互作用,加剧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认同危机。
所谓研究的泛化与空疏,主要是指许多研究缺乏明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研究成果的贡献局限在学术观点的引进与评析上,而对于这些学术观点的内在的逻辑结构与前提假设缺乏认真的思考与论证,缺少理论的验证与辨析。研究的空疏与泛化,一方面表现在对国外公共行政的研究上,许多公共行政的研究停留于概念的辨析,盲目追求国外的“学术时尚”,满足于学术思想的整理与归纳,这种学术努力对于完善学科的基本知识当然重要,但也是理论研究泛化与空疏的原因之一。国内知名行政学者周志忍指出“我国学术界对国外政府改革的研究相当重视,西方政府治理新理想可谓耳熟能详。但除了少数例外,多数研究停留于总结和概括新的提法和新的理念上。”[7]对其他民族国家改革的具体原因与存在的问题,则缺乏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国外行政改革实现的前提条件与实施机制的探讨也比较少见。许多研究作品只是在国外学术思想与观点的导引之下,辛苦地进行概念的辨析与争论,许多学术成果只是已有学术下带有强烈臆想色彩的填词游戏,难以进行有效的学术创造与思想发明。此外,部分学者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术理念,在对国外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及其经验研究之后,往往简单地推断出相关的借鉴经验,盲目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学说的普适性和科学性,而忽视了国情的基本限制。事实上,西方的这些理论学说只能是一些“地方性”的知识,或者是“地域性”的经验,并不必然能够适用于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许多研究者将问题的研究停留在逻辑的演绎,甚至是主观的想象之上,鲜有学者能够结合我国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体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提出符合现实行政环境的政策主张;而且,由于国内的公共行政的研究者,缺乏国外公共行政现实的经验感受,对国外公共行政的现实难以形成准确的判断,很难客观地把握国外公共行政的真实的发展趋势,基本判断往往只能停留在已掌握文献的分析与整理上,因而,以之为基础得出的政策建议,其空洞与肤浅就在所难免。
尽管对国外公共行政研究的泛化与空疏,影响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质量,但这只是问题相对不太重要的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已有公共行政的研究,对国内的公共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比较稀少。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明确研究问题所导致的空洞性。客观而言,公共行政学人对于国内问题的研究虽未成为主流,但也不乏对一些问题的探讨。然而,在这些有限的研究中也存在着泛化与空疏的问题,这些研究泛化与空疏与国外问题的研究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问题过于宏大,对于研究问题的界定缺乏明确的界限,致使研究缺乏有效的约束范围,导致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大而无当,追求宏大叙事的系统化,形成了一些看似是理论精品的观点堆积,而缺乏有力度的分析。许多研究只是将不同学者围绕某一问题的观点进行分析综合,而忽视了不同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与局限性,对于同一问题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学术创见。更有甚者,是部分学术作品根本没有研究问题,只是围绕某一研究主体,进行漫无边际的“浅谈”,研究的空泛性便不可避免。二是许多研究问题属于学术意义上的“假问题”或“伪问题”。“假问题”与研究问题的过于宏大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突出表现为研究问题缺乏真实性,即许多研究设定的“问题”是假设性的,不是现实社会的真实问题。由于研究围绕一个大而且空的“假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得出的只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言论。由于公共行政带有很强的实践导向性,从服务于社会的角度而论,解决和解释现实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不可回避的学术责任;公共行政研究的“真问题”应该根植于中国社会发展与公共行政实践的社会问题,它不应该是学术研究者的臆想与推测,而是忠实反映公共行政领域现实问题的学术追问;公共行政的研究应该强调社会变迁过程中经验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深入揭示出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前置条件、行动意义与社会后果。
总之,正是由于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缺乏对“真问题”的探索,因此难以生产符合国情的“地方性”知识,更难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应有的理论指导,社会公众不得不从其它学术共同体那里获取相关的基本知识,这即是其它学术共同体频频侵入该研究领域的外部力量与社会需要,也是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的努力,难以获得社会认同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与症结所在。因此,公共行政的研究群体,必须认识到自身学术研究的社会性,谨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决非简单地追求个体思维活动的愉悦,必须根植于公共行政的现实领域,在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发明与创造。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公共行政的研究不仅可能继续成为学术研究的二等公民,而且可能因为丧失在自身学术领域的发言权而继续沉沦。
三 缺乏规范的学术规则与研究方法
缺乏规范的学术规则与研究方法,是国内公共行政研究范式中,存在的另一突出的问题。如果说研究问题的空疏与泛化,是该领域研究作品质量不高的初始原因,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则,则是制约研究水平提升的重要瓶颈,它使学科进步缺乏必要的基础条件。首先,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缺乏规范的学术规则,制约了学科的知识增长。“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规则)指的是知识的辨伪存真、有序积累和继承,以及学术交流、对话和批判性反思所应遵循的一整套规则和标准。”[8]西方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与其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学术研究规范是分不开的,各个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正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学科的传承和扬弃,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进行学科的对话和批判,才得以持续的繁荣。整体而论,我国的社会科学尚未形成具有“学术宪章”性质的研究规范,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是公共行政研究方面的问题,则尤其突出。因为其它社会科学分支学界同仁,基本上已经形成一个大概的判断,或者说是一个心理契约,能够对学术作品的研究质量,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则对此缺乏必要的内省与反思。
由于国内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对研究规范缺乏足够的内省与重视,公共行政的研究一直缺乏学科内部的学术质量评价标准,对理论研究的可验证性与效度缺乏学术关怀,因而难以对学术作品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直接导致许多研究作品缺乏明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潜在地激化了研究的空疏与泛化,许多公共行政研究总是在综合、归纳已有学术观点上徘徊,缺乏明确的文献综述,既不标明别人的理论贡献,也不明确地说明自己的理论创新之处。文献综述是理论对话的起点,既然缺乏理论对话的基础,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推进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而且,由于缺乏基本的研究规则,其它研究者难以按照作者的理论观点,遵守大致的资料收集原则,进行类似前置条件下的研究,影响了学术研究作品的可验证性,使后续的研究无法获得比较稳固的研究基础,难以进行必要的学术批评。研究作品往往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稍加综合,便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得出一些大同小异的结论与对策意见,根本谈不上学术的创见,难以将研究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正因为如此,许多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倾向,即将理论引述作为理论研究水平的标志,研究论文中存在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引述。事实上,理论引述并非研究水平高低的可信性标志,只是在进行专题性的文献评估或理论论战时,它才具有一定的意义,即使从这个层次而言,研究者也必须具体说明这些文献如何能够联系在一起,并能够进行理论的构建或检验。“(文献)引用只能表明作者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资格,而不能用来论证理论的建构。”[9]
其次,国内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对规范研究方法的认识比较模糊,甚至存在错误的认识,在研究方法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充分的共识。与其它社会科学分支相比,这是制约公共行政研究水平提高的关键原因,是公共行政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工具问题。因为,虽然社会科学整体上尚未建立其规范的学术规则,但大部分的学科分支,已经就研究方法问题,形成了共识,促进了学科内部的交流与研究水平的提高。公共行政学科,则缺乏这样的共识,无论在研究方法的认可,还是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都非常混乱。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为:一是部分学者对研究方法存在错误认识,主要表现为将文字描述理解为定性研究,而把数据分析理解为定量研究,误解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内在本质。二是对具体的研究方法存在模糊认识,比如对扎根理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认识不清,否定其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作用,拒绝将其接纳为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将案例事实的列举与堆砌视为案例研究,对如何开展规范性的案例研究,缺乏必备的理解和训练。此外,一些研究还将方法与研究视角相互混同,影响了学术研究质量的提高,颇受许多其它社会学科分支的学术共同体轻视,影响了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事实上,关于研究规则与研究方法问题,早已引起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内有识之士的注意,除上文提及的马骏教授和徐湘林教授外,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胡伟教授都曾对此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陈振明教授非常注重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指出“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在方法上的突出特征是强调用跨学科研究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提倡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法。”[10]胡伟教授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底子薄、基础弱的现实,提出“公共管理在其发展之初,就要注意提高学术门槛,重视学术规范、术语和方法,培育自身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尽可能提升公共管理的专业化水平。”[11]认为只有在方法和术语上严谨,才能防止学科门槛过低的倾向。然而,整体而论,公共行政学科在方法论上,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或是简单的理解为借鉴其它学科的思想观点,摘要性地选择适用别人的观点,而置别人的研究方法与得出结论的途径于不顾,难以用开放的心态,采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提高学术作品的质量。或是囿于自身学术训练的局限性,纠缠于其间的难以言明的学术利益,对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种抵制的态度,不利于学科内部规范研究规则与研究方法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行政研究停留在初始化的阶段。[12]由于缺乏学科内部的研究规则与规范的研究方法,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意思”,造成该学术领域门槛过低,研究质量难以提升。
大概而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量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数据的分析,揭示社会复杂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达到理论分析与预测的目的;质化研究方法则是通过田野调查质量的收集、遵守特定的研究程序,分析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定性与定量研究质量的争论,但质化研究方法的扎根理论、民族志、现象学等具体的研究方法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同,在探讨社会个体、社会团体以及组织行为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许多学者不为学科分支的桎梏束缚,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研究各自学科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质化方法也适用于揭露并解释一些在表面之下鲜为人知的现象,对于一些人尽皆知的事也能采取新鲜而又具有创意的切入点,而且,对于量化方法所无法铺陈的一些细致复杂的情况倒也颇为得心应手。”[13]加强方法论素养的训练,真正积极、正确地加以适用,深入探测公共行政的诸类现象,不仅能够提升公共行政的研究质量,使公共行政研究步出初始化阶段的困境,促使学术研究根植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提高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水平。而且,可以以之为基础,进一步积极地进行学科的国际对话,提高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国际影响,有效地解决该研究领域的认同危机。
结束语
公共行政学科的认同危机与其理论研究的质量紧密相关,认同危机的存在,一方面表明了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显示出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其潜在的或已浮现出的危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信心,因为任何一门学科,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其它社会学科分支,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种问题,各个学科也都是在持续不断的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其研究质量与社会影响的,只要我们能够切实的解决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公共行政研究的质量必然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学术影响。本文针对国内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粗略的分析,并对其如何影响公共行政的研究质量以及学科认同,做了相应的分析说明,希望对此有所助益。
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恢复与重建,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无论是学科发展还是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败利钝,已成昔日旧事。然而,与其它社会学科分支相比,公共行政的研究还非常不成熟。对后来者而言,关键在于发现其间存在的问题,并认真对待,及时纠正过往研究中存在的缺失,惟此才能继承已有的成就,不断提升该学科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地位。针对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的上述三个问题,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必须本着学术自觉的态度,积极寻求建立学科内部契约性的研究规则,大力倡导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取向,注重规范研究方法的应用,关注公共行政领域的“真问题”,不断提高学术研究的品质,改变研究水平初始化阶段的困境,获取国内的学术认同。并在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以一种文化自信的态度,积极进行公共行政研究的国际对话,力争使研究成果在世界学术共同体内获得一定的认同。
[1] 马骏.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反思[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3):73-76.
[2] [美]罗伯特·达尔.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A]彭和平,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 [美]兰志勇.它山之石 如何攻玉-从公共管理视角看中国精英学习外国经验的心路历程[J].公共管理学报,2006(4):22-30.
[4] Robert Jay Dilger;Randolph R.Moffett;Linda Struyk:Privatization of Municipal Services in America’s Largest Citie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7,(57):21-26.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6] 陈先达.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和学者的责任[J].中国社会科学,2004,(4):4-12.
[7] [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 徐湘林.中国政策科学的理论困境及其本土化出路 [J].公共管理学报,2004,(1):22-27.
[9] Robert I.Sutton;Barry M.Staw.What Theory is Not[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995,40(3):372-373.
[10]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1]胡伟.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若干战略思考 [J].公共管理学报,2006,(3):97-99.
[12]龙献忠,胡斌,张鑫.论市民社会发展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J].大学教育科学,2010,(2):42-46.
[13][美]安赛姆·斯特斯,琼立特·考滨.质性研究概论[M].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1997.
The Limitation of Domestic Public Administration Basic Research Paradigm and Identification Crisis
LI Xu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Since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ience has restored,It has been made great achievements,However,compared with other social science branches,the literatur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ldom accomplish effective academic and social influence,Academic production fi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ain identification by large community;Because of lack of indigenous research and normal research methods,Besides the inanition of research problem,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production seldom provide academic production with high quality,which make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ace identification crisis.In order to walk out of this initialization stage,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munity must be fully aware of its underlying influence,try to solve the central problem in the main paradig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research production.
indigenous;research problem;methods;identification crisis
D630
A
1008—1763(2011)06—0066—06
2011-02-16
李 学(1975—),男,河南西平人,厦门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行政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政务公开,公共组织与地方政府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