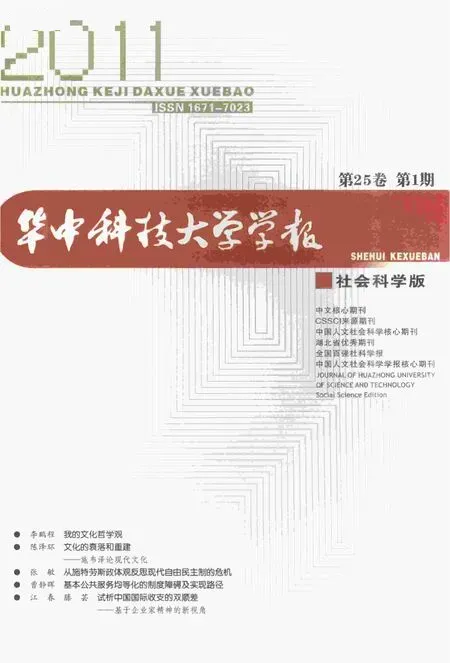从施特劳斯政体观反思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危机
2011-04-08张敏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张敏,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从施特劳斯政体观反思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危机
张敏,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很多当代的左翼或右翼政治理论家们都对以美国为范本的现代自由民主制进行了反思,然而,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他们的反思仍停留在以现代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政治哲学的内部。因此,施特劳斯强调,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一定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而这个视野在他看来就是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施特劳斯认为,古典的“最佳政体”观建基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以人的目的性、完满性、优异性与德性为指导,因此它能够对抗现代自由民主制在人性观和道德观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从而为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别样的、可能性的思路。
施特劳斯;自由民主制;自由主义;最佳政体
一、引言: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
我们知道,以美国为范本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是近现代政治智慧与政治实践的结晶,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现代自由民主制亦在其具体实践与理论前提上暴露出许多的局限和困境。很多当代的政治理论家们都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由民主制进行了反思,甚至将这种反思直接指向自由民主制在最深层的道德基础上的危机,他们主要对自由民主的原则、根据及其道德后果持怀疑态度。
然而,不论自由民主制在多大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疑虑和反思,整个近现代政治哲学作为一种“自由”(或现代“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其始终保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最接近正义的社会安排应首先确保个体公平合法地追逐其利益的基本权利。这一基本观点更建立在现代政治哲学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之上。也就是说,现代自由民主制主要力求在公共领域内为公民提供均等的机会以及各种规则框架,而将公民的目的性需求完全交给个体存在的私人领域。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就是权利必须优先于善。可见,现代自由主义想在一个道德上多元 (甚至破碎)的社会里成功实现政治和平。也正因为如此,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好处在于它将现代自由主义从关乎公民整体利益的复杂政治争论中“解放”了出来;相应地,其弊端也就在于它使得现代政府变得越来越“道德中立”,越来越不关心那些对公民来讲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价值争论与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在有关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上,自由民主制完全站在了“旁观者”的立场之上。它对所有的生活方式都一视同仁,只是当某种生活方式试图打破所谓“多元”的局面而统领其他生活方式时,它才出面干涉。
认为“道德中立”是现代自由国家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因为现代自由主义为其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一,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在人类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不存在理性的基础,人们无法在“善”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所有有关“善”的观念都是极其个人的和主观的,因此,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可以发现或建立一套“权利”系统,这套权利系统可以不以任何一家的善观念出发,却能平等对待所有相冲突的善观念,而“道德中立”的民主国家自然就是人类公共生活中唯一能实现这种权利系统的非武断、非任意的组织机构。第二,现代自由主义者们普遍认为个人自由是最高的价值所在,因此“自由地”选择犯错要好过“被迫地”追求行善。所以,在现代自由主义看来,排除了道德纷争的“中立国家”被证明是保护个人自由优先性的最佳公共护卫者。许多著名的当代政治理论家都曾表明过自己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上的“道德中立”立场。例如,罗尔斯就说过:“目的序列并不归类于价值之中。”[1]19德沃金也认为,自由国家“必须在良善生活的问题上保持中立;政治决策也必须独立于任何有关良善生活的特定观念之外,或者必须独立于给予生活以价值的东西之外”[2]127。
无可否认,上述理论原则使得现代自由民主制在政治自由、有限政府以及法律程序正义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很多弊端也由之繁衍。伴随个人自由的是个体的原子化、失范化与异化,尤其是将个人自由看作整个价值系统中的“绝对律令”会损害大众的“公共精神”。同时,政治腐败与企业贪污亦变得司空见惯,由社会失范引起的暴力冲突以及精神治疗方法的“日新月异”也见证了人们理智秩序的阙失。在政治上,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危机更表现为特殊利益集团对公共议程以及政策制定的操纵,并且这种操纵与控制已成为公共生活习以为常的模式。因此,柏克和托克维尔所谓公民和政治家(即罗马式的积极公民和具有审慎智慧的政治家)的消失,可谓在现代自由民主制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上述道德中立的观点揭示了自由民主制在价值信念与道德基础上的危机,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自由民主制所谓的“道德中立”不正是认可了个体权利优于其他所有个人或社会之善吗?如果对现代自由主义来说,个体权利的基础在于“自由”的话,那么,这种中立于任何善或者说不以任何善为基础的“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其本身的基础何在?值得注意的是,将道德问题完全归依于个人的偏好或选择是一种亟需审视的公共道德判断,它直指了一个我们无法再回避的问题,即现代民族国家有无绝对可靠的根基?或者说,现存的所谓“不偏不倚”(im partial)的自由民主制度能否为其自身提供一个普遍性的合法基础?
许多当代的政治理论家都从道德根基上对自由民主制进行了反思,同时,反观现代自由主义在国家观念上的“道德中立”原则,我们的确可以将现代自由民主制的主要危机归因于某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义务的消减甚至丧失。最吊诡的是,这种道德义务本是人们步入“自由社会”的动力和基础,因为它是个人对自我的立法,是社会对其成员的立法,这才是“自由”的真切含义;然而,在人们跨入“自由社会”之后,“自由”却反噬了“善”与“道德”本身,最高的“善”就是把所有的善都放到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领域,最高的“道德”就是不必裁判哪一种道德是最好的,摆脱一切道德纷争。因此,所谓的道德义务至多只是一种“作茧自缚”。然而,依托于个人领域的自由道德观虽然对划定政府权力界限的政治原则贡献显著,但它却终究无法充分勾连宪政国家中个体自由与公共美德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现代自由民主制虽一方面努力将自己从道德义务的作茧自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却又过多地将自己限制在对政治领域的消极理解之上,从而无力确立一个“公共的善”来保存并导引其自身。在缺乏“公共之善”的目的性导引之下,现代民主国家到底该何去何从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自由民主制的困境时曾问到:“你想使人的头脑达到一定的高度,让它以宽宏大量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吗?你想让人们对物质财富产生一种鄙视感吗?你想养成和保持坚强的信念吗?你想使风尚高雅、举止文明和艺术大放异彩吗?你向往诗歌、音乐和荣誉吗?你试图组织一个民族对其他一切民族采取强力行动吗?你打算创办伟大的事业,而且不管成败,使其名留青史吗?假如你认为人生在世的主要目的就是如此,你就别要民主政府,民主政府肯定不会把你带到这个目的。假如你认为把人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活动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和创造福利是有益的;假如你觉得理性的判断比天才更对人们有利;假如你的目的不是创造英雄的美德,而是建立温良的习惯;假如你喜欢看到弊端少造成一些罪孽,而且只要没有重大犯罪,你宁愿少见到一些高尚行为;假如你以在一个繁荣的社会里生活而满足,而不以在一个富丽堂皇的社会里活动为得意;最后,假如在你看来政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使整个国家拥有尽量大的力量或尽量高的荣誉,而在于使国内的每一个人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涂炭;那末,你就得使人们的身份平等和建立民主政府。”[3]280-281
托克维尔的忧虑也应是我们的忧虑。正是在这种危机的背景下,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施特劳斯是一位较为特立独行的政治哲人,他一直认为尽管许多当代政治理论家都对自由民主制进行了反思,而且这种反思也一度深入了自由民主制的道德基础和理论前提,但是,在他看来,当下对自由民主制的批判仍然停留在自由主义的视野之内,这种“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做法无法超越性地揭示现代自由民主制的真正症结所在。所以,施特劳斯强调,对自由民主制和自由主义的批判必须首先获得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a horizon beyond liberalism),这一视野在本文中即具体化为施特劳斯所恢复并重建的古典政体观念。因此,笔者将具体分析施特劳斯独特的政体观念,以及他在这种政体观念之下对自由民主制进行的批判,希望通过施特劳斯的视角,我们可以从更广阔、更独到的视野来观察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及其可能的解决之道。们是内在统一的。重新探讨政体问题可以说是施特劳斯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内容,亦是施特劳斯在这一问题上批判现代自由民主制的一个“超自由主义的视野”。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施特劳斯本人是如何理解“政体”这一概念的。
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中,施特劳斯解释到,“政体是一种秩序,一种形式,它能赋予社会以其特征。因此政体就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a specificmanner of life),一种群居生活的形式,一个社会的存在方式,同样也是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方式。”[5]34将政体视作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古典视角,它意味着将一社会的统治形式与该社会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一社会或一政治共同体之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性地依赖于这个社会或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占支配地位的某种人类类群;亦即一社会或一政治共同体中的统治者决定着这个社会或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政治秩序、形式和生活方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的政体观念其实具有一种“整全”②关于对施特劳斯“整全”概念的解释,可参见拙作《现代性危机的救治——施特劳斯“自然正当”观念的内涵与理论地位》,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 9期。(the w ho le)的意义,它同时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生活风格、道德品味、政府形式、法律精神等。所以,施特劳斯进一步解释说:生活是一种直接导向某个目的的活动;从而社会生活就是一种直接导向某种社会目的的活动;既然社会生活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政体又是该社会的特定生活方式,因此,政体或政治生活就应该从属于这个目的,也就是说,该政治共同体必须以一种与此种目的相一致的方式组织、建立并规制起来;因此,这也意味着在这个社会中具有权力的那部分人必须与这个社会的目的保持一致。这就是施特劳斯政体观的“整全”意涵,它意味着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是有目的导向的,它们不能脱离由这个“目的”所规定的基本道德义务与约束力。
以事物或存在之目的来理解事物或存在,是古典目的论的要旨,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曾对此有过清晰地表述:“一切自然存在者,至少是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者,都指向一个终极目的、一个它们渴望的完善状态;对于每一特殊的自然本性 (nature),都有一个特殊
二、施特劳斯的古典政体观
施特劳斯分析自由民主制的背景主要来自他对所谓“现代性的危机”①有关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拙作《施特劳斯论现代性的危机》,载《财经界》,2008年第 11期。的认识。我们知道,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危机”主要源自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和背离,因此,他一生都致力于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重建。施特劳斯在《论古典政治哲学》一文中曾开宗明义地说到:“古典政治哲学与当今政治哲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后者完全不再关注于前者的主导性问题:最好的政治秩序的问题。与此相反,现代政治哲学则异常专注于一种其重要性对古典政治哲学来说要少得多的问题类型:方法论的问题。”[5]79施特劳斯所谓的“政治秩序”狭义来讲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体,而“最好的政治秩序”即是“最佳政体”(亦有译“最佳制度”)。施特劳斯曾多次表明,“政治(Po liteia)”的首要涵义就是人类有关政治权力的实际安排(即政体形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施特劳斯的话语中,“政治”、“政体”以及与这两者密切相关的“国家”(或“城邦”),这三个概念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达,它的完善状态归属之。”[6]90因此,施特劳斯对政体所做的上述解释,实际上是以一种古典的视角阐明了政治共同体之社会目的、生活方式和统治者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社会之统治者和基于这些统治者的统治形式 (即政体),决定了该社会的生活风貌和生活方式,而该社会的统治者和生活方式又在其自然本性上被定向于该社会的自然目的。所以,特定的政体导向特定的自然目的,特定的政体有其特定的完善状态。
在了解了施特劳斯关于政体的一般观念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施特劳斯所谓古典政治哲学中“最好的政治秩序”或最佳政体呢?根据施特劳斯的理解,一社会之政体以及由这种政体所决定的生活方式主要取决于该社会的统治阶层所归属的人类类群,那么,最佳政体的问题实质上变成了什么类群的人应该进行统治的问题。为了能使社会或政治共同体导向其良善的自然目的,施特劳斯眼中的古典派们认为建立在人类的良善品质、优异性及德性基础之上的人类类群最能符合统治的要求,而由这种人类类群进行的统治就是所谓的“贵族制”。在现实的城邦中,贵族制实际上就是贵族、精英或最优秀的人们根据良善的法典而对政治共同体进行的统治,施特劳斯称这样的“贵族”为“高尚之士”(gentleman),他们是过着城邦生活方式并从农业中获取收益的城邦贵族,他们最能够以立法者的精神公正不阿地施行法律,或者,他们能够根据立法者所无法预见的情势的要求来“完成”法律。[7]143-144所以,施特劳斯得出结论说,现实的“最佳的制度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共和国,在其中,教养良好而又深具为公精神的土地贵族(他们同时又是城邦贵族),服从法律而又完成法律,进行统治而又反过来接受统治,他们雄踞于社会而又赋予社会以特性”[7]144。同时,施特劳斯又继续解释说,以贵族制为核心,古典政治哲学家们谋划和举荐了各种有利于上述优异人类类群进行统治的体制,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混合政制,它是王权、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在混合政制中,贵族制的因素——贵族院的庄严肃穆——居间的也即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位置。因此,混合政制实际上(而且它也旨在于)成为一种由于加入了君主制和民主制的体制而得到了加强和保护的贵族制。[7]144所以,施特劳斯认为,现实城邦中的最佳政体乃是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统治或者混合政制。
笔者在上段讨论最佳政体时一再强调“现实城邦中”这一层面,也就是说,在施特劳斯看来,贵族制(或上文所谓“高尚之士的统治”)或混合政制只是古典政治哲学家在最佳政体问题上达成的一个实际可行的现实方案,它还不是一种能超越所有现实政体并能成为所有现实政体之最终标准的绝对理想的最佳政体。施特劳斯认为,这种理想的最佳政体只能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家的统治,或称哲学王政制。因为,在古典理论中,智慧 (或哲学、知识)在整个自然秩序中居于最高的地位,只有它才具有统治的资格。因此,最合于自然的同时也是最好的统治形式当然就是拥有真正智慧或掌握真正知识的哲学家的统治。因此,施特劳斯最后得出结论说:“在有关最佳制度的问题上最终达到一个双重的答案,乃是古典自然权利论的一个特点。那答案就是:单纯的最佳制度就是明智者的绝对统治 (即哲学王政制——笔者按);实际可行的最佳制度乃是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统治或者混合政制。”[7]144在此,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在有关理想最佳政体的问题上,施特劳斯可能容易遭到当代自由派学者的误解和指责,他们认为这是在自由民主成为人类共识的进步时代宣扬非民主的极权主义言论。然而,施特劳斯本人其实已经多次指明:“最佳的制度在其是可能的同时,其实现又绝非必然。它的实现极其困难,因此未必能实现,甚至难以实现。因为人们不能控制它赖以成为现实的那些条件。它的实现取决于机遇 (语出亚里士多德——笔者按)。合于自然的最佳制度,或许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它存在于言而非行中,这是它的本质所在。简而言之,最佳制度就其本身而言——用柏拉图《理想国》中一个思想深邃的学生所杜撰的术语来说——是一个‘乌托邦’。”[7]141
然而,对施特劳斯来说,无论是理想的最佳政体还是实际可行的最佳政体,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以“人应当怎样生活”为目的和使命,为人类优异性的发展、为人类灵魂的完满、为人类自然目的的实现提供一个良善的制度安排。施特劳斯认为,古典政体理论其实传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幸福或幸福的核心部分在于人类的优异性、完满性与德性,它是一种发现并发展人类潜在可能性的善的生活,因此,政治活动,尤其是以政体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活动,如果是朝向人类的完善或德性前进的,那么它就导向了正确的目的。所以,政治、政体和国家最终以个体为目的,公民社会或国家的道德与个人的道德并无二致,公共的善与个人的善是同构的。对施特劳斯来说,建立一个真正健全的政体意味着发掘并培育一种高贵的、与宇宙秩序相关联的人类生活方式,只有这样的政体才能真正获得其内部成员的尊敬与拥护。这是一种“宏大”理解的政体观念,它关注的是个人与政治共同体的潜在完满以及政治实践的目标导向,而不仅仅是退守于技术层面的国家之良好组织的手段问题。
现在让我们回到对自由民主制的讨论上来。笔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论述过,现代自由民主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由以“自由”为己任的现代自由主义所提供的,而在施特劳斯看来,发展至今天的现代自由主义其实有其更为悠久的理论渊源,它可以说是整个现代政治哲学背离古典政治哲学的结果 (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对此问题无法一一展开,但我们可以在现代政治思想的传承与流变中举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来做简要的说明)。施特劳斯认为,自霍布斯提出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强烈、最根本的欲求并以之取代人的目的性与完满性之时,国家的职能和政体的目的就不再是创造或促进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而是要保护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于“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所以,施特劳斯才说,“自由主义的创立者乃是霍布斯”。[7]185发展至洛克,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的“自我保全”升级为一种“舒适的自我保全”,因为在洛克看来,人们不仅具有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也有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这种对幸福的追求依赖的不是“自然的赐予”,而是人自身的劳作和自由创造,因此,通向幸福之路就是脱离“自然”的过程,同时,个人、自我(而非人的目的性与完满性)成为了道德世界的中心和源泉。无独有偶,施特劳斯在解读斯宾诺莎时发现,《神学政治论》正是为了给上述脱离“自然”、追求幸福的个人扫清障碍,它试图将“人”解放为摆脱了所有道德偏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真人”。后来的康德道德哲学首先设定一个只有“自由意志”而绝对不依赖经验世界的先验道德主体,亦是为了保证这样一个“自由真人”的出发点。当然,由此我们更能理解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设立“原初立场”和“无知之幕”的初衷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极类似于其理论先驱的现代翻版。
由此不难看出,在施特劳斯眼中,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将人从他的自然本性与自然目的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它试图使人脱离古典时期的宇宙秩序和中世纪的神性秩序,以人类中心论代替宇宙中心论和神学中心论。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尤其是一种绝对的、自主自足的甚至是将人连根翻起的“自由”,代替了“善”(人的目的性、优异性、完满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当然,伴随这种“自由”之发展的,是西方道德政治理论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再到“人的权利”(即“人权”)的蜕变过程,施特劳斯认为这个蜕变过程就是西方走向虚无主义①施特劳斯认为“虚无主义”是其所谓“现代性的危机”的实质。参见拙作《施特劳斯论现代性的危机》,载《财经界》,2008年第11期。的过程,因为在他看来主张“权利优先于善”,就是否认有真正的善,就是否认“自然正当”②关于对施特劳斯“自然正当”观念的解释及其与自然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可参见拙作《现代性危机的救治——施特劳斯“自然正当”观念的内涵与理论地位》,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 9期。。所以,施特劳斯认为,以“自由”或直接以“权利”来定义人,是一种“唯法律主义”或“准司法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它的实际结果是将所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善好观念等都打入“非法律”的私人领域,使其失去了意义,尤其是失去了“公共的”意义。可以说,现代自由主义所追求的“自由”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即人们最后“自由”得什么都不是了,包括“自由”在内的所有价值最终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却并不是整个世界。
因此,施特劳斯提请我们重新关注古典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最好的政治秩序”,就是试图让我们在“政体”这个政治生活最核心的层面上重新思考、审视我们身居其中的自由民主制。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每种政体都是一种灵魂的洞穴监狱,施特劳斯本人亦非常清楚每一种政体对在其中成长起来的人们的灵魂所施加的可怕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民主制的限度亦是在这种自由民主制中生活的人类灵魂的限度。所以,回归古典意义上的宏大政体观,回归以人的目的性、完满性、优异性以及德性为导向的政体观,当然地成为了施特劳斯批判现代自由民主制的“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亦为我们超越自由民主制的限度与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选择。
三、一种“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批判
我们知道,施特劳斯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亡美国的犹太学者之一,他虽然在不幸的魏玛共和国中长大成人,而后却有幸在美国得到庇护,逃脱了法西斯的迫害,所以他是自由民主制的坚定支持者和朋友——但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并不恭维现代自由民主制。
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讨论马基雅维里时曾说到:“他 (指马基雅维里——笔者按)将古典政治哲学、从而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传统视作徒劳无益的而加以据斥:古典政治哲学以探讨人应该怎样生活为己任;而回答何为社会正当秩序的问题的正确方式,是要探讨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马基雅维里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反叛,导致了以爱国主义或纯粹的政治品行取代人类的优异性,或者更具体地说,取代道德品行和玄思的生活。它有意地将最终目标降低。目标之被降低,是为了增加实现它的可能性。”[8]182
在施特劳斯看来,马基雅维里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反叛并非他个人的理论特征,而是整个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性格,马基雅维里只是其首创者。这种由“应然”转向“实然”、由“潜在性”转向“现实性”的“现实主义”反叛,是一种以对人的现实性理解取代目的性理解的过程,它表现在现代自由民主制中,就是实际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取代了个人的善和公共的善而成为现代政体的核心。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将政体的视野仅限于有关居民利益的实际问题之上,这是掉进了“第二层的历史洞穴”①对施特劳斯“第二洞穴”理论的相关解释,可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 70页。之中,而环绕在洞穴之外的人的完善性这一维度则被忽略甚至放弃了。同时,施特劳斯认为,以实质性的个人利益或个人权利取代理想性的个人之善,使得昔日的“封闭”社会变成了今天的“开放”社会:向着激进的个人主义开放,向着完全的自我主义开放。再者,由于将人抽离其自然目的,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缺乏对人类自然本性的真正知识,它无法深刻认识到人类本性的完满与卓越所能带来的个体生活的幸福,更无法将这种个体幸福同公共的善、公共精神以及治国安邦联系起来。因此,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根基几乎完全偏安于追求幸福的条件、手段与力量之上,而这在他看来无疑是一种搁置目的而强化手段的异化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所谓的技术统治和方法论研究大行其道的原因。施特劳斯还进一步指出,现代自由民主制的这种技术化倾向更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裂中得到加强,在这种分裂中个人之善不再统一于公共之善,特殊且分散的幸福取代了美德与虔敬。所以,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成功之处亦是其弊端所在,因为它越是普及对私人幸福的追求,就越是掩盖了其公共危机的蔓延。因此,施特劳斯认为,自由民主制真正需要的是对公民美德、宏大的爱国主义以及宗教虔敬的培养。
当然,施特劳斯更看到了现代自由民主制在上述现实化意图背后所潜藏的道德水准的局限和退化。上文已经说过,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政治哲学不再以人“能是”和“应是”的视野来把握人,而是以人的“所是”来接受人,这表现在道德领域中,就是古典道德的规范性要求被现代道德的实用性意图所取代,道德水准被“有意地”降低了。在施特劳斯看来,正是由于现代自由民主制将自己局限于“历史洞穴”的技术性问题之上,德性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应该以其为基础的超历史的标准,反而是社会的标准成为了道德的尺度。所谓公正的,就是社会认可的、对社会有用的。施特劳斯认为,德性的道德维度,消失在现代自由民主制对市民德性的偏爱之中。与此相关,狭隘的爱国主义,或者说对集体性自私的迷恋,成为了自由民主制道德教诲的核心。同时,施特劳斯也看到,德性的衰微意味着私欲和激情的解放。相对于道德性的告诫或戒律而言,私欲和激情更容易成为实现个人或社会利益的工具,因此,它们自我膨胀,大行其道,不再接受德性的限制和调节,并在现代自由民主制中代替德性履行着自己的各种“义务”。既然私欲和激情在现代社会中“鸠占鹊巢”,施特劳斯进一步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背后的伦理态度必然是他律主义的,这同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唯法律主义”或“准司法主义”的伦理道德观不谋而合。当然,古典时期也存在他律主义,但是,施特劳斯认为,在古典目的论的导引下,人的生活以德性为基础,政体和以政体为核心的政治活动也旨在促进这种人的德性,所以,在施特劳斯看来,古代的他律主义是以自律主义为前提的一种边缘化的、反政治本性的、纯个体性的伦理形式。然而,施特劳斯认为,现代的他律主义却成为了政治观念的基础,它使得自由民主制内部的各种关系都更加革命化了。
再者,施特劳斯认为,在上述对政治与道德的重新定向之下,现代自由民主制与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矛盾。在施特劳斯看来,容忍与尊重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标志,施特劳斯本人亦十分钦佩现代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容忍与尊重,因为它不仅为遭受迫害的哲学提供了避难所,还允许(尽管并不鼓励)令人鼓舞的政治争论的出现。然而,施特劳斯认为,也正是这种过度的容忍造就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 (liberal relativism)”。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经提到,现代自由主义认为,人们无法在“善”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所有有关“善”的观念都是极其个人的和主观的,因此,这就使得我们“被迫容忍”各种有关“善”的意见,把一切的偏好和一切的“文明”都视作旗鼓相当。所以,施特劳斯认为,对现代自由主义来说,唯一符合“理性”的做法就是漫无限制的“宽容”,只有当每一种偏好、每一种价值、每一种“善”的观念、每一种“文明”都能容忍别的偏好、别的价值、别的“善”的观念、别的“文明”之时,我们才能谴责或拒绝所有不宽容的或“绝对主义”的立场。因此,施特劳斯说到:“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植根于宽容的自然权利论传统之中,或者说植根于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按照他对于幸福的理解而去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之中;但是就其本身而论,它乃是不宽容的一个源泉。”[7]6
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自由主义的这种只讲宽容的传统,表现在现代自由民主制中,就是首先容忍自由民主堕落为一种随遇而安的信念,即认为所有的观点都是相同的,因而没有任何一个值得进行热情地辩论和深刻地分析;其次容忍自由民主堕落为一种刺耳的鼓噪,即认为为某种特殊的道德见解、生活方式或人类类群的优越性而辩护的任何人,都是“精英”统治论者或是反自由民主的——因而也就是“不道德”的。因此,施特劳斯认为,与其说现代自由主义为现代自由民主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倒不如说现代自由主义使得现代自由民主制“去意识形态化”了。也就是说,在现代自由主义的宽容传统之下,人们觉得意识形态的存在已不再必要,因为只有在一个非意识形态的社会里所有的价值才都是均等的、宽容的、不受偏袒的。毫无疑问,在现代自由民主制的“理性法庭”面前,所有的价值偏好或价值选择的确都获得了平等的地位。然而,最吊诡的是,这样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或非意识形态的社会却恰恰十分“理性地”证明了有利于自由民主制的偏好——现代自由主义在其宽容姿态的背后其实与自由民主的偏好携手共进,并心照不宣地缔结着导向自由民主制的私下盟约,从而否定了它自己所标榜的意识形态自由与价值多元的可能性。
四、结语
施特劳斯虽然赞赏古典政治哲学家,但他也同样钦佩为人类世界创建自由民主制度范本的美国开国元勋,他曾这样写到:“(美国的)自由民主制或宪政民主制是我们的时代中最接近于古典派要求的现实可行政体。”[8]113在施特劳斯看来,尽管自由民主制或大民主制在其理论和实践上同古代的公民共和政体相距较远,但它仍然是共和政体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公民自治的一种形式。所以,施特劳斯坚持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仍然要求希腊和罗马理想公民的再现 (当然是一种弱化形式的再现),这种理想公民是活跃的、积极的、自豪的,并且对杰出的政治家充满富有见地的尊敬。当然,施特劳斯同意美国开国元勋关于国家政体并不能完全呈现人类所有善德的这个说法,但是,若想将自由民主制从一种僵化的自我忠诚中解救出来,重新赋予其崇高的志向,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是自由民主制的出发点和归宿。
当然,施特劳斯清楚地知道古典城邦肯定无法再现了,他对古典政体理论的重建也绝不是真的想开历史的倒车。施特劳斯要告诉我们的是,要想建立一个以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为基础的政体,要想建立一个以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政体,现代自由民主制亟需重新审视以庸俗的人类平等和个人权利为前提的理论基础,亟需超越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以及异质的个体幸福为归宿的政体目的,亟需提升以“人实际上如何生活”为基础的人性视角,亟需改变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更亟需丰富以搁置人的个性发展而单靠制度建设来推进政治成功的政体理念。所以,施特劳斯提请我们注意,要超越自由民主制的困境,其解决之道需建立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真正知识之上,建立在对人的目的性理解之上,建立在对以政体为核心的政治活动的宏大理解之上。
施特劳斯借助古典政体理论来批判现代自由民主制可能仍有较大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这也许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哲人所担当的基本责任。本文以施特劳斯在《古今自由主义》中说过的一段话结尾,以作为本文主旨的再现与总结:“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 (perverted liberalism),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教育,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尚、出类拔萃、德性完美。”[9]64
[1]John Raw 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Ronald Dworkin.Liberalism,in Stuart Hamsphire ed. Public and Priuate Morality,Cam b ridge:Cam b 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3](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4]Strauss,Leo.On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in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5]Strauss,Leo.W 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in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6](美)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版。
[8]Leo Strauss.W 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And Other Studies.New York:Free Press.
[9]Leo Strauss.Liberalism,Ancient and Modern.New York:Basic Books,1968.
责任编辑 蔡虹
A Reflection on the Crisis of Modern Liberal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o Strauss′Concept of Regime
ZHANGM 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Man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ists ( left-wing or right-wing) have reflected on modern liberal democracy which is mode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n Leo Strauss thinks their reflections still stay inside the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is based on modern liberalism. Therefore, Strauss emphasizes that the critique on liberal democracy must be established on“a horizon beyond liberalism”,which in his op inion,is the concept of the“best regime”in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Strauss believes that the classical concept of the“best regime”was connected to a noble way of human life and guided by the end, the perfection, the excellence and the virtue of human being, so it can cope with the“realistic”attitude of modern liberal democracy and provide a unique possible thinking of the solution to the dilemma and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fall of public spirit and the subversion of moral basis.
strauss;liberal democracy;liberalism;best regim e
张敏 (1983-),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欧美政治。
2010-10-23
D033
A
1671-7023(2011)01-00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