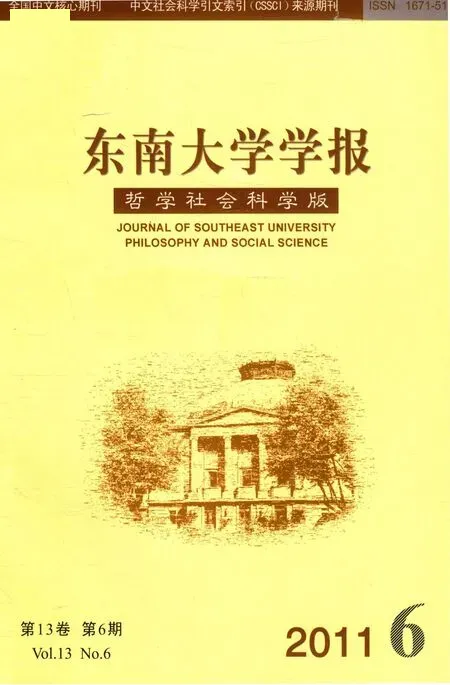论欧阳修诗歌的气格
2011-04-04吴大顺
吴大顺
(怀化学院中文系,湖南怀化418008)
论欧阳修诗歌的气格
吴大顺
(怀化学院中文系,湖南怀化418008)
气格是指诗人品格、诗歌内容、形式等因素综合融会后所体现的诗歌品格。欧阳修诗歌气格主要表现为:诗歌中蕴涵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力量、诗歌内容中的国运民生意识和穷究物理的理性精神、诗歌语言上下字运意的笔力。欧阳修对诗歌气格的追求,导引了宋诗的发展方向,为宋调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阳修;气格;笔力;宋调
对于欧阳修诗歌的总体风格,世人多以“平易”视之。如王安石称“欧诗如玉烛”[1]291;叶梦得称欧诗“平易疏畅”[2]365;魏庆之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3];今人也指出欧阳修诗歌“虽有摹拟韩的痕迹,却一般是平易流畅、闲淡容与,风格究竟不同于韩愈”[4]。宋人说的“平易”主要指诗歌遣词用字的避难趋易,是从诗歌的语言特点着眼的。如《漫斋语录》云:“用意要艰深,下语要平易”[3]209;《遁斋闲览》称苏轼《咏梅》中“竹外一枝斜更好”是“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5]189。尽管诗歌的语言特点也是构成其诗歌风格的要素之一,但不能成为一个诗人创作风格的全部。就欧阳修诗歌言,“平易疏畅”的语言仅是其诗歌风格的外在表征,因其诗歌所彰显的人格意志、现实内容和诗歌构思立意的理性精神、下字运意的创新意识,使其诗歌呈现出格力劲拔、气韵疏淡、语言流走的特点,即所谓“气格”,才是欧阳修诗歌风格的主要内涵。
一、关于“气格”
格,本指木之长枝条,后引申为规范和法式。《说文》曰:“格,木长儿,从木,各声。”[6]251《礼记·缁衣》云: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孔颖达等疏曰:“物谓事之征验,格谓旧有法式。”[7]1650“气格”既用于指诗文的气韵和格调,也用于指人的气度品格。如《旧唐书·韩愈传》:“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对偶,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8]4203-4204范仲淹《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曰:“公少而倜傥,负气格。”就诗歌风格言,“气”主要指诗歌情感的力量和气势,“格”指诗歌的规范和法式。诗歌对格力的追求,其实是对于流俗的超越和对于更高规范的追求。亦即说,有规范就被视为有骨格力度。规范又主要得之于后天的涵养而不是先天的气质,因此,一方面格力得求诸作者的胸襟气骨,另一方面格力又通过用笔的技法力度具体体现。这样,“气格”的内涵既指诗人人格与诗歌风格的统一,也指诗歌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的统一。宋代诗文品评十分崇尚气格,所以多以“气格”或“格力”的高下衡量诗文的得失。诗文气格的高下又通常与作者的道德品格相联系,因此宋代文人所崇尚的诗歌气格,其实是诗人主体道德品格与诗歌艺术风格两者融合与统一后所体现的诗歌品格。
二、欧阳修诗歌的气格
欧阳修非常注重“气格”,他常用“格”来品评诗歌作品。如《六一诗话》以“格不甚高”批评唐末诗人郑谷,以“诗格奇峭”称道友人石曼卿。在创作实践中他十分重视诗歌的气格,总是将有无气格作为诗歌高下的重要标准。因此,他的诗歌创作被叶梦得视为“专以气格为主”: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然公诗好处岂专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诗》:“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此自是两段大议论,而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会,要当如是,乃为至到。[2]407
在叶梦得看来,欧阳修诗歌一方面以矫正西昆体浮艳为己任,诗歌讲究气格,所以语言平易疏畅,另一方面还有巧发议论、对仗工稳、文思抑扬曲折的特点,尤其对欧诗在七字之中巧发议论的高妙之处,赞叹备致。方回《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中也认为“诗以格高为第一”,并在列举诗歌史上格高的诗人时曰:“宋惟欧、梅、黄、陈、苏长翁、张文潜”[9]。具体而言,欧阳修诗歌的气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在诗歌作品中渗透着作者的人格力量。
欧阳修十分强调道德品格修养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并身体力行,一身砥砺名节,注重人格修养,成为后世道德文章的典范。他在《新五代史》中指责冯道浮沉浊世、安富尊荣是“可谓无廉耻者矣”[10]56,将其与节烈寡妇李氏作比较,揭露他连村姑野妇都不如,以此警告那些“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的士人。却专为忠义之士和隐逸之士立《死节传》和《一行传》。他评价文人往往从道德品质着眼,强调其人格修养。如其《石曼卿墓表》称石曼卿“以气自豪,……独慕古人奇节伟行,非常之功”[11]168;《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称谢绛“为人肃然自修,平居温温,不妄喜怒。及其临事敢言,何其壮也”[11]183;《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称苏舜钦“位虽卑,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11]221。此外,还在与当时文士的书信交往中反复阐明他的文道观。如《答吴充秀才书》曰:“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1]222;《答祖择之书》曰:“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11]499;《与乐秀才第一书》曰:“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11]506。由是可见,欧阳修对道德品格修养与文学创作关系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识。
他还身体力行,一生始终坚持道德操守和人格修养。王安石《欧阳修祭文》称赞他说:“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11]1332吴充在《欧阳修行状》中说:“公为人刚正,质直闳廓,未尝屑屑于事。见义敢为,患害在前,直往不顾,用是数至困逐。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真豪杰之士哉!居三朝数十年间,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11]1336可见,欧阳修的道德人格修养已经成为当世公论,其道德文章成为一世楷模。
其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人生情怀的感遇述怀诗,比较鲜明地体现出其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在其仕宦生涯的三次贬谪外放中,所到之处,能随遇而安,表现出很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这种心理调适能力的养成,反映了诗人对儒家人生观念中进退荣辱的深刻理解和参悟,也反映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君子人格。如《戏答元珍》写于夷陵贬所,虽然身居贬所,却吟诵出“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诗句,尽管全诗情绪不免有些低沉,但能从诗句看出作者对自己流落天涯的自我安慰,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孤芳自赏的人格自信。又《黄溪夜泊》:“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这句诗更能显出作者对个人进退穷通之理的洒脱精神,其实质是诗人以忧国恤民的政治使命化解个人进退荣辱的精神解脱。它直接影响了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人生态度和创作风格,形成宋代文学普遍的自适心理与乐观情调[12]。
其二,在诗歌创作中十分讲究构思立意。
在宋人看来,诗歌格力的高卑强弱与诗歌的立意有很大关系。在欧阳修创作理念中,好的诗歌应该是“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的。《蔡宽夫诗话》也说:“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1]385可见,立意是诗歌格力高下的关键。而诗歌的立意主要体现为作者精心构思的结果。欧阳修诗歌在构思上出奇制胜者,如《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该诗由一块三国时期的古砚台联想到铜雀台及其相关的汉魏历史,描绘了“当其盛时争意气,叱诧雷雹生风飙”的气象,想象奇特,用词遒劲,气势飞动。《栗城遇风效韩孟联句体》、《菱溪大石》、《初食车鳌》、《鬼车》等诗均以构思奇特而著称。
欧诗的立意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立足国运民生。他认为“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13]。所以,欧阳修的诗歌内容充实,题材多样,他的诗歌既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又有深刻的人生思考。在《镇阳读书》中宣称:“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在《赠杜默》中能看到他对“京东聚群盗,河北点新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等社会现实的忧虑。在《食糟民》中能看到他对农民“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的社会不公现象的揭露。他还善于从平常而通俗的题材中提炼出有关国事民生的大道理。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庆历元年的《晏太尉西园贺雪歌》。下雪本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古代文人墨客常以此作为诗歌、绘画的题材,或者以雪的洁白的质地象征文人高洁的人格,或者从雪的自然作用,即所谓“瑞雪兆丰年”的角度立意。而欧阳修这首雪诗在描写了一场大雪情景之后,比较巧妙地以“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结尾,点明诗歌题旨。他能从瑞雪兆丰年的传统构思中更进一层,委婉地规劝晏殊作为朝廷最高军事长官,应当更多地关心西夏的战事和将士的寒温。由此可见欧阳修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关注,也能看出诗人刚直的秉性。他不顾老师晏殊的面子,以诗表达自己的意见,以致因此而与自己的老师晏殊不睦[14]126。
又如嘉祐四年对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的和诗也以立意高绝著称,表现出诗人在叙述中巧发议论的智慧。王安石原诗在对王昭君远嫁故事的叙述中发表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的议论,此议论妙就妙在诗人能把王昭君的悲剧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相绾合,既是对王昭君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又是对人生普遍意义体认的升华。这种情感的泛化与升华使昭君的悲剧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欧阳修的和诗则翻出新意,把笔触转向汉皇对佳人“一失难再得”的遗憾,“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据此,由昭君故事升华到对整个社会的反思与批判:“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这一议论立意以小见大,突出了“汉计诚已拙”的主旨,表达了诗人对汉元帝昏愦无知的指责。其用意则在影射北宋朝廷的对外政策。
二是重视表现诗歌题材的“物理”。所谓“物理”,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些普遍而共同的认识,尊重“物理”就是不要过分违背人们习所共见的事实、忽略人们普遍留意的特点,使诗人的个性认识和人们的共同感受相融合[15]。明道元年,他称赞梅尧臣“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书梅圣俞稿后》),晚年称韩愈诗歌“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可见,他对“叙人情,状物态”等表现生活“物理”的自觉意识和不懈追求。《巩县初见黄河》刻画了黄河的惊险壮阔,《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描绘幕府文士的神情笑貌,都深得“叙人情、状物态”之妙。韩诗重抒情,叙事要求蕴含比兴寄托,因此选择叙事对象时喜欢挑选奇闻异事,或者对习见习闻的事喜欢写得千奇百怪,如《南山》诗,表面上是刻画山石情态,实际上是勾画一幅栩栩如生的众生相,行文之中透露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欧诗主理,叙事是为了更好地阐明道理,因此,欧诗在表现论据时尽量客观公允,从常人习见习闻的角度对事物做出描绘。这样,使欧阳修的诗歌既在题材上突破了韩诗偏好奇闻异事的局限,使叙事对象涉及到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又使其诗在内容上形成了平常易懂、明白晓畅的风格。欧诗的题材有描写自然风光,如《忆山示圣俞》、《游琅琊山》;有揭露社会问题,如《食糟民》;有颂美道德文章,如《镇阳读书》;有品评诗风文风,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有写奇花异石,如《紫石屏歌》、《菱溪石》;也有题画论琴,如《盘车图》、《于刘功曹家见杨直讲女奴弹琵琶戏作呈圣俞》);等等。此外,还有将生活中琐碎之物入诗的,如《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橄榄》等。
其三,在诗歌语言使用上讲究下字运意,突出语言的表现力。
白石道人姜夔说:“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立格,成于句字。”[16]683可见诗歌语言使用是诗歌获得气格的重要手段。
为了诗歌气格,欧阳修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同时,也很重视诗歌的语言表达技巧。他曾说:“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第534页《论尹师鲁墓志》)[11]在这种作诗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了其平易疏畅的语言风格。平易是指诗歌语言平白易懂,疏畅是指诗歌行文舒缓,文气畅达。欧阳修诗歌语言的平易疏畅,并非白居易诗歌语言的浅显通俗,自有其独特的个性,尤其显著者有三。
第一,语言的选择服从内容的需要。欧阳修是一位兼政治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诗人,他总是把诗歌的内容放在最重要位置,语言的表达艺术总是服务于诗歌内容的,所以他重视“叙人情、状物态”等语言驾驭能力的训练。他往往根据诗歌表现对象和情感表达的需要合理选择最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根据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对象采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时而雄快奔放,时而舒缓平白,时而清新自然。正如诗人所言的“变态百出”、“曲尽其妙”。如《晋祠》诗,诗人以流畅舒缓的句式抒写承平时代宽松和乐的心情:“晋水今人并州里,稻花漠漠浇平田。废兴仿佛无旧老,气象寂寞遗山川”。《沧浪亭》则以清放的句式表现和苏舜钦之间的相交莫逆的情谊:“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总体上说,他不像韩愈那样在语言上刻意造作,求奇求怪。正如朱熹所云:“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的字。”[17]3309
第二,合理吸收融化各种文体语言于一炉,语势流畅而变化自如。欧阳修在诗、文、赋等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均取得了辉煌成就,成就最巨者为散文,他被尊奉为宋代文坛的领袖。庆历初,他的散文就进入成熟阶段,在文坛已经享有很高的声名。在诗歌创作中则追求着以文为诗的尝试,将散文的句法和铺叙技巧引入诗歌,强化诗歌的叙述功能,也使得其诗歌行文流走酣畅。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景祐元年)等。关于这一特点,论者尤多,此不赘述。他还常常将赋的笔法引入诗歌创作。如《答梅圣俞寺承见寄》(宝元二年)是一首代书体诗歌,首先叙述初到京洛时“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的盛况,接着写五六年来彼此相离的情形,再写欢聚谢绛处的景况,最后表达天热政烦、渴望秋来的愿望。全诗纯用赋体,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欧梅二人的真情厚谊,行文委曲详尽,语言晓畅。对各体诗歌语言的改造和创新,在欧阳修诗歌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在律诗中有意识地加入散句,或在古诗中穿插律联等是其常用的语言手法,他曾说:“古诗中时作一两联属对,尤见工夫。”[18]6
第三,大量采用杂言,句式长短参差,自由灵活,文气畅达。欧阳修在诗歌语言上自觉学习李白。他在庆历末作的《紫石屏歌》,皇祐以后作的《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和刘原父澄心堂纸》、《盘车图》、《赠沈博士歌》、《明妃曲和王介甫》等都用了杂言句式。诗人自己对这些诗歌也十分自得。他曾说:“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吾能之。”[2]424从他自己的话语中可以看到诗人对这种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这些诗歌也能充分代表欧诗语言风格的特点。梅尧臣称赞说:“一诵《庐山高》,万景不得藏。”[19]756这些诗显然受到李白诗歌语言的沾溉。
当然,欧阳修不少作品因追慕韩愈诗歌创作方法,往往用难词押险韵,在语言上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态。如明道二年(1033)《巩县初见黄河》全诗七十句,纯为单行,无一对偶。诗中诸如“巩洛之山夹而峙”、“其势不得不然尔”等散文句式的使用,古史传说的铺叙,增强了全篇的气势与笔力。清人施补华说:“少陵七古多用对偶,退之七古多用单行。退之笔力雄劲,单行亦不嫌弱。”[20]988此诗用单行、重气势,正是学习韩愈七古所致。说明欧阳修诗歌除平易疏畅外,也有部分构思奇特、笔力雄劲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作者早期学习韩愈诗歌以矫除西昆体浮艳诗风的产物。其夷陵时期的诗歌语言就开始逐渐向平易方向转变,到滁州时期,其诗歌平易疏畅的语言风格得以确立。如《游琅琊山》、《题滁州醉翁亭》等诗皆明白如话,贯通流畅。欧阳修成就最高的诗歌是七古。与其夷陵时期七古比较,此期少了清丽藻饰,而多了舒缓流畅。标志着欧阳修此期诗歌借鉴前人而能自成面目了。如《沧浪亭》开端数句:“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诗歌意脉流贯,语言平易畅达。最为诗人称道的当属《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这首诗典型地体现了欧阳修作诗博采众长而自成一体的创作方法。该诗在构思立意上学习韩愈,诗写庐山高耸于长江之滨,以飞动的气势描写庐山千岩万壑、晨钟暮鼓之趣,从而表现对同年刘中允归隐其间的羡慕之情。以散文章法为诗,生新拗折。在韵律上追步韩愈《病中赠张十八》,使用江韵,江韵属险韵,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而在语言上,又直接学习李白《庐山谣》、《蜀道难》,句式参差,语言疏畅,气韵流走,有一气呵成之感。欧阳修《居士集》中的诗歌,在语言上大多具有“平易疏畅”之特点,而作者学习韩愈诗歌技巧所写的那些气势雄胜,语言遒劲的诗歌较多地保留在《居士外集》中。《居士集》为欧阳修本人晚年亲自编定,《欧集》周必大跋云:“惟《居士集》经公决择,篇目素定。”[11]说明他在编集时,对自己的诗歌进行过认真的删减和斟酌取舍,这也反映了欧阳修对“平易美”的自觉追求。
欧阳修诗歌语言的最大特点有二:一是无施不可的表现力。他称赞梅诗“变态百出”,韩诗“曲尽其妙”,肯定西昆诗人“笔力有余,故无施不可”(《六一诗话》),其实质都在于强调诗歌语言丰富自由的叙事、抒情、体物能力。他对古典诗歌传统风格的继承、融合,其目的也是使诗歌的叙事说理能深入浅出、易知可感。这是构成欧阳修平易疏畅诗风的关键所在。二是舒缓畅达的文气。“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的语言技巧在其诗歌中的表现是很突出的。他总是通过“逆卷顺布”的方式叙事说理,使其诗歌“意、法、情俱曲折”,从而达到“情韵幽折,往反咏唱,令人低回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21]276的艺术效果。
三、欧诗气格与宋调
欧阳修作诗注重气格,是因为当时诗坛、文坛普遍存在着格调卑弱的毛病。如韩琦在欧阳修《祭文》中说:“自唐之衰,文弱无气。降及五代,愈极颓敝。唯公振之。”[11]1331不仅散文如此,宋初诗歌也是如此。当时风靡诗坛的西昆体虽然标榜自己学习李商隐,但是,只是在辞藻、对偶、音节等形式上下功夫,缺乏李商隐诗歌的气格而失之浮艳;以晏殊等人为代表的后期西昆派诗人虽然以平淡作为诗歌的审美追求,努力摆脱诗歌的“富贵气”,在艺术表达上较杨亿等前期西昆诗人有了一些改进和提高,但仍然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终究缺乏现实精神,格调卑弱[22]。《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曰:“《豫章先生传》载在《豫章外集》后,不知何人所作,初无姓名,其传赞叙诗之源流,颇有条理。《赞》云:‘自李、杜殁而诗律衰,唐末以及五季,虽有兴比自名者,然格下气弱,无以议为也。宋兴,杨文公始以文章莅盟。然至于诗,专以李义山为宗,以渔猎掇拾为博,以俪花斗叶为工,号称西昆体。嫣然华靡,而气骨不存。嘉祐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高风之所扇,作者间出,班班可述矣。’”[5]58
欧阳修在诗歌中标出“气格”,突出诗歌的现实精神,并不仅仅以太白为范,在诗歌表现技巧上还自觉学习韩愈诗歌,其目的均在于改进西昆体格调卑弱的弊病。当然,欧阳修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强调诗歌对“物理”的表现,突出诗歌表现国运和普通百姓生活的能力,这样又避免了西昆诗歌的浮艳和韩愈诗歌的怪巧。因此,不管何种题材,诗人均能根据描写对象的特点,变态百出,曲尽其妙,使人能知易懂,表现出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艺术风格。
欧阳修高举“气格”的主要意图是反拨五代以来诗风的卑靡和西昆体的浮艳。而五代至宋初诗风之弊,又是整个唐诗主情传统流宕所致。因此,可以说,欧阳修诗歌标举“气格”的本质意义在于对唐诗主情传统的反拨与超越[23]。他导引诗歌由主情而转向求意,倡导“意新语工”的创作理念和平淡的审美理想,在诗歌语言上大胆创新求变,追求平易疏畅之美。这些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关键。因此欧阳修对诗歌“气格”的创作追求,为“主气骨、尚理趣”的宋调形成导引了正确的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诗歌史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陈辅之.陈辅之诗话[M]//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叶梦得.石林诗话[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胡守仁.论欧阳修诗[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1).
[5]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6] 许慎 撰,段玉裁 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 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 刘昫.旧唐书·韩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方回.桐江续集[M].卷三三,四库全书本.
[10] 欧阳修.五代史记·杂传序[M]//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三一)[M].北京:中国书店,1986.
[12] 莫砺锋.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J].中国文学研究,1997(4).
[13] 欧阳修.诗本义·本末论(卷十四)[M].四部丛刊本.
[14] 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 刘宁.论欧阳修诗歌的平易特色[J].文学遗产,1996(1).
[16]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 朱熹 著,黎靖德 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陈善.扪虱新语[M].丛书集成初编本.
[19]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0] 施补华.岘佣说诗[M]//王夫之.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1]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2] 祝尚书.论后期“西昆派”[J].社会科学研究,2002(2).
[23] 秦寰明.宋诗的复雅崇格倾向[J].中国社会科学,1993(4).
I207.22
A
1671-511X(2011)06-0064-05
2010-12-10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唐宋文人唱和与唱和诗研究”(05B058)成果之一。
吴大顺(1968-),湖南保靖人,文学博士,怀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