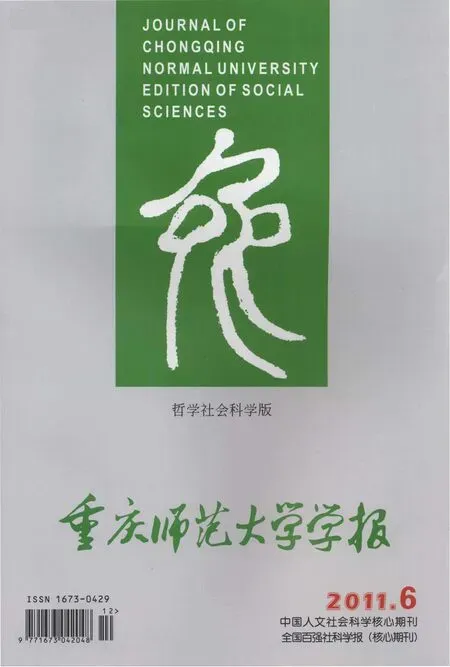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解读师陀的《果园城记》
2011-04-02常慧明
常慧明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 400031)
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
——解读师陀的《果园城记》
常慧明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 400031)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孤独代代传承,抒写孤独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1940年代的师陀更是将孤独主题在其小说集《果园城记》中发挥到了极致。在《果园城记》中,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二者有机融合,建构和彰显了文本强烈的“孤独”主题。
师陀;《果园城记》;叙述者;孤独者
“五四”文学以来,叙述孤独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写作主题,以鲁迅《野草》的自我叙述与郁达夫的“零余者”叙述最具代表性。由于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动荡不安,传统文化的浸濡和西方文化的侵入造成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自我背负理想和与现实生存困境之间的强烈反差,造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难以释怀的孤独感、寂寞感,孤独成为他们生命中独特的审美体验。叙述孤独成为作家一种体验人生、体验社会、体味自我的话语方式和叙述策略。到了1940年代,这种叙述的传承性仍然存在,师陀的《果园城记》更是把它推向了极致。不同的是鲁迅叙述的孤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劣根性改造的艰辛与他“荷戟独彷徨”的自我苦闷的孤独,郁达夫叙述的孤独则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性苦闷”与“生苦闷”的孤独,而师陀的孤独则是一种“物是人非”、“人在江湖”、“乡土礼俗与现代文明”、“游子与故乡”、“自我生命体验与现实生存困境”的孤独。在《果园城记》中,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二者有机融合,建构和彰显了文本强烈的“孤独”主题。
一
果园城是一个“有很多规矩的单调而又沉闷的城市,令人绝望的城市”,“永远繁荣不起来,不管世界怎么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自己的平静,猪可以蹒跚途上,女人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可以在街岸上打酣”(《果园城》)。同整个世界相比,果园城是孤独的,因为它不与外界发生任何接触,无论时间如何变幻,空间演绎多少事件,它永远不发生太多变化,依旧是一个孤独的、没有生息的、一潭死水的果园城,它始终处于一种时空双重意义上的孤独状态中。
果园城是孤独的,果园城中的每个人也是孤独的。《灯》中的“他”为了生存,走街串巷挑担卖煤油,直到“最后只剩下空洞没有行人的小胡同”。“所有的灯他都认识,只要摸摸他就知道是谁家的,甚至是谁用的。”可是,自家的灯却还没亮。“他”的孤独是下层小人物一种源于生存意识、生存本能的孤独,只有自己的孤独,才能换来生存。《葛天民》中的葛天民曾经对农场非常热心,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力去有所收获。但却不得不接受农场被毁的现实,靠着祖传的一点医术去求得自己的生存意义。这个“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会应对任何风浪。将来很可能活到八十五岁,然后安静的死去的人”,由于自己的抱负得不到实现,生活的平淡对他而言就意味着一种孤独,一种生命价值得不到实现的孤独。《贺文龙的文稿》中的渴望像鹰般屹立于小丘之顶,像“生成的野物”一样“毅然遥望天陲”的贺文龙终逃不过“四周是无际的平沙,没有生命的火海”,开始养养蟋蟀,弄弄花草,在琐碎庸俗的生活中消磨着意志,消磨着生命,忍受着生命的孤独。《桃红》中的素姑曾是“一个像春天般温柔,长长的像根杨枝,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的”的少女。她为自己缝绣了十七年的嫁衣,绣满了两只大箱,而谢光了的花红终于让她意识到了青春的逝去和爱情的无望、生命的褪色。她的情感无所寄托,大雁飞过,晚风萧瑟,孤独的她只能以泪珠相伴,一颗接着一颗,“惆怅的望着永远是说不尽的高和蓝而且清彻的果园城的天空”。《颜料盒》中的油三妹曾经是一个“两颊是红润的,一双大的闪光的眼睛”喜欢笑的女孩,由于追求自主的新生活而受辱吞颜料自杀。她生前是欢乐的,死时却是孤独的。《期待》中的徐父徐母,儿子早已死去,而他们还蒙在鼓里。他们还日夜思念自己的儿子,一年一年地等待着。他们的情感期待注定是孤独的,而又只能在孤独中慢慢变浓且又慢慢消解。《狩猎》中的孟安卿是一个有气度、有雄心的青年,带着很多希望回到果园城,本想寻找过去的故乡梦、情感梦,但在果园城,他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故乡人的陌生,梦中人的情感转移,迫使他最终在极度孤独的心境中踏上离乡的火车。《一吻》中的虎头鱼在“时间的飞逝下”为了老婆和一群孩子拉起了洋车,在辛苦的奔波中早已忘记了他青春的“一吻”。而倔强活泼的大刘姐已是一个“满身肥肉”的太太。当他们再相遇时,由于情感错位,他们身上都已失去了青春和生命力,他们彼此在情感上都是孤独的,他们在生活中消磨着生命,安乐却没有欢乐的生命激情,最后大刘姐孤独地离去了。一切早已忘却了,“一吻”也成了孤独的“一吻”。《邮差先生》中的老邮差是善良的,人们没有钱也可以把信寄走,老邮差还替贴邮票,即使不认识,他也相信人家会把钱送来。老邮差的生活是和谐而美丽的,每天忙着自己乐于做的事。“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天气多好”的背后仿佛也隐含了另类的孤独,因为果园城中的人除了老邮差,没有一个人说这里的天气很好。这种孤独,是一种只属于老邮差自己的孤独,一种人性恶中善良的孤独,一种呼唤人性美的孤独。《阿嚏》中的阿嚏可以算是《果园城记》里最可爱、最有趣的一个小人物了。可是就是这个可爱充满生气的阿嚏身上却发出“老呆在这个鬼地方还是要气闷的”的愤懑,他和我们一样在空闲中总爱寻找少年时期的旧梦,这梦虽然有些破碎、冷落和酸苦,但“十分无谓”而且“朦胧”。可见,阿嚏的孤独是一种童年的孤独,一种儿时的孤独。《鬼爷》中的朱魁爷曾经是“暗中统治果园城的巨绅”而今却被已被人淡忘了,曾经热闹的门庭而今冷淡了,曾经“高大丰满”的他苍老了,家产也分了,仆人也遣散了,现实的遭遇注定了他晚年必定在物质和情感的双重孤独中喘息。《说书人》中的说书人,曾经在自己的三尺说书场创造了热闹和喧嚣,可如今却慢慢地变“荒凉”了,他在荒凉中孤独地死去,葬礼上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也没有像样的灵柩,有的只是一根绳子,最后他只能孤独地守侯在小城的城外。《三个小人物》中的胡凤梧、胡凤英也在家族衰败中走向没落,走向孤独。胡凤梧荡尽财产后为了生存讹诈人被土匪打死,在“无边的荒野和无边的黑暗”中孤独地死去。胡凤英也在遭受情感欺骗后,趋向自我的孤独,“那双不久前还充满热望的眼,现在是又大又空又干”。在家族衰败后,她为了母亲和自己的生存,迫不得已地去做妓女,强颜欢笑的背后是强烈的生活的孤独、情感的孤独。
二
《果园城记》中从果园城到城中的人,都在叙述孤独。他们不想孤独,不甘心于孤独,然而他们在叙述者的叙述下却不得不别无选择地承载孤独。他们的孤独叙述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叙述者的叙述孤独的强烈欲望。而这种欲望的根却来自于叙述者的孤独。
《果园城记》不仅叙述了不同类型的孤独者来展示孤独主题,而且文本的叙述者本身就是孤独的。文本中存在三个不同的叙述者:人物叙述者马叔敖;内隐的叙述者果园城;还有可靠的叙述者师陀。马叔敖是整个《果园城记》的人物叙述者,所有人的遭遇和孤独都是通过他的所见所闻叙述出来的;而所有的人和事都是在果园城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发生的,果园城见证了发生的一切,果园城是它们的叙述者;马叔敖和果园城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和地点,它们遮蔽了我们读者的眼睛,真正的可靠的叙述者应该是师陀。这三个不同的叙述者彼此交叉,共同构造了《果园城记》别具一格的孤独主题。他们也成为《果园城记》中叙述孤独而自身也处于孤独的叙述者。
离乡的马叔敖在“无目的向窗外望着”的百无聊赖的心态中踏上了故乡的土地。然而处身在“有许多规矩的单调而又沉闷的城市,令人绝望的城市”才发现“并没有人注意我”,“连一条走着的狗也没有看见”,他怅然了,他懊悔了他没有悄悄离开这个城市。分明归乡不久,他便发现是个美丽的错误。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寂寞。然而他没有离开,而是继续在孤独之中寻找童年的记忆,接着他看到的是小城一如既往的平静:“猪照常安闲的横过街道,狗照常在路边晒暖,妇女们照常在门口闲谈,每天下午它的主要的大街仍旧静静的躺在阳光下面,到了秋天,果园里的花红仍旧红得像搽过胭脂。”听见的是“以前就在小胡同里听惯了的叫卖声,也许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它没有改变,原来小城市的生活也没有改变”。时间仿佛在小城驻足,历史在这里歇脚。不管经历怎样的变化,这些现象都难以挤入小城。
马叔敖,对果园城来说是一位匆匆过客,又是一位归来的游子。他曾从这里走出,而现在回乡的他已被涂上了一个异乡人的色彩,所谓的家乡不过是一个“异乡人”眼中的家乡。可是,他和家乡的人们有着情感上的牵连,共同拥有这片他所“怀念的原野”和过去的时光。因此马叔敖多了一份对生命和时光流逝的哀伤和更为抽象化的思索。在某种程度上,师陀的“回乡”小说与鲁迅的“回乡”小说有着相近的气息,一种哀伤、温暖的情感的潜流和冰冷的寒意同时袭击着主人公。他们叙述的视角既是“他者化”,同时又属于自我经验的,具有双重性。所有的批判和不满都是建立在那无法表达的爱和痛之上,无论是马叔敖还是《故乡》中的“我”,他们都是在“回乡”中失望的一群。他们并没有在“故乡”中找到精神上的归属感,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叙事模式中,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群现代知识分子无处可依的境地。他们面临的是“异乡”和“故乡”的双重失落,这决定了他们在生命的途中只能永远地行走,没有归属,这造成了他们心境中一种难以言谈也永远说不尽的寂寞感、无归属感和强烈的孤独感。
最后,马叔敖正如师陀先生所讲的“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要到何处去”[1](94),他又继续去寻找,去流浪。因为孤独的他只是“在这里小做勾留”,同《狩猎》中的孟安卿一样注定要孤独地离去。
马叔敖孤独地离开了果园城,见证了他孤独的果园城也是孤独的。表面上看《果园城记》这个文本的主人公是人物叙述者马叔敖,但真正的主人公却应该是内隐的叙述者果园城。作者在《果园城记》序中写道:“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小城,不是那位马叔敖。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生命,像一个活的人。”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小城,每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形象都被扼杀:葛天民的改革无疾而终;贺文龙的文稿最终还是那几行字;桃红在一年年地绣着嫁妆,但却只能装在箱子里让它发霉;快乐的油三妹自杀;徐立刚被杀等等。在这些叙述中,“只有时间的流程是恒定的,生命在它那里是虚无可笑的存在,死亡也只是一个偶然的变数”[2]。“果园城”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凝固物,以它的对抗消融着社会的“变”的因子。正是果园城人传统的思维模式造就他们思想的休眠,不争的温吞状的生活态度,使得小城因此“永远繁荣不起来,不管世界怎样变动”,“人生活在小城里,一种散漫的单调生活使人们慢慢地变成懒散,人们也习惯于不用思索”,“我们从此感到要改变一个小城市有多么困难”。处于这种时空中的果园城不能不孤独,而对乡土风俗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它却能通过自身的封闭、自身的孤独去避免,因此它将更加封闭,更加孤独。
人物叙述者马叔敖是孤独的,内隐的叙述者果园城也是孤独的。然而这两者的孤独则是文本中真实可靠的叙述者师陀孤独的外化,文本通过他们的孤独来凸现和彰显师陀内心的独特孤独。在沦陷的上海“孤岛”,师陀身居棺材样狭小的阴暗的“饿夫墓”,“心怀亡国之牢愁”,孤独地创作了《果园城记》,他把自己别样的孤独都融入了文本之中。果园城“小国寡民”式的安宁固然美丽,但对在民族存亡危机面前一直有强烈的现代性诉求的知识分子师陀来说,这样的安宁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在永恒的轮回中不思进取、坐以待毙的盲目的生存状态。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着种种纠结于历史、道德和同审美之间的乡土情结的悖论。师陀出生在一个破败的地主家庭,童年时代的他,已经不得不在田里劳作。另外,青年时代父亲的死、小侄的死和分家等等都给他以打击。这使本来就颇为荒凉的故乡在他眼中更涂上了一层忧郁、冷酷、孤独的色彩。即使在果园城里,那像“云和湖一样的展开,装饰了小城”的果园也只是残酷、无情的人生的背景,果园被寂寞地遗忘,人们在这文化的废墟中毫无希望的生活着。“从停滞不前的‘惰性’文化中,师陀天才的发现了‘凝视’,渴念的生存方式,发现了无流动、无呻吟、无煎熬、无挥霍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发现了于默默下滑中熄灭着生命的‘无生命’意识。”[3]我们总能感受到师陀那“异乡人”的灵魂始终在旷野中游荡,总在寻找、思索,但目之所及只是一片沼泽满地、无所去从的“荒原”以及无望地挣扎在其中的生命,所发现的始终是生的悲哀和生命的逝去的无可挽回的忧伤,所感受到的是广大无边的空虚和寂寞、无归属感和孤独感。
“师陀是乡土中国的后裔,又是现代的知识者。双重的身份使他在营建果园城世界时情感与理性相互纠缠:情感上他向往着对乡土的归依,无法摆脱思乡的蛊惑;理性上又清晰地认识到果园城世界的本质。”[4]“作者的心,历经着乡与城,爱与恨,恋与返,希望与绝望,时间的止与动……等等矛盾的网状撕扯,毫无归属,心灵悬空。”[5]情感与理性的纠缠,游子与故乡的割舍,“物是人非”、“人在江湖”的困境,形成了师陀的孤独。
三
人物叙述者马叔敖,内隐的叙述者果园城,可靠的叙述者师陀,文本从点到线,再从线到面,构筑出了一个孤独的世界。叙述者把自身的叙述孤独转变为一种孤独叙述,用孤独叙述的话语方式和叙事视角把叙述孤独的内容叙述得淋漓尽致。马叔敖、果园城、师陀都是孤独者,文本正是叙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孤独。然而他们同时又担当文本的叙述者,正是在他们不同的孤独叙述下,才充分展示了他们作为孤独者的孤独。果园城是孤独的,果园城中的人也是孤独的,就连营造果园城世界的师陀也是孤独的。正是在这种递进的层次下,叙述孤独和孤独叙述才统一在一起,共同建构了文本中的孤独主题。
师陀首先把自己的孤独投射到马叔敖和果园城身上,从而间接地折射出孤独的影子。不同的是,马叔敖是从时间的叙述视角去叙述果园城中的孤独者,马叔敖作为一个“异乡人”回到果园城这一封闭的空间,他是一个自由穿行于文本内外的结构者,是一个以过去的“印象”来对照小城现在的意象,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可怕变化才更显现出他的意义和形象,为文本提供了反省的可能。马叔敖是观望“故乡”的一双“眼睛”,他把故乡从回忆的空间拉回到现实空间和历史过程之中,使“故乡”具有阐释的可能性。这双眼睛里面蕴涵的还是无法抹去的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生命、时代以及文化的感受。而果园城则是从空间的维度去叙述的,显而易见,果园城成了师陀笔下的一个动荡的大世界中的封闭而日渐衰落的小世界,而这一封闭停滞的世界正是作者通过时间凝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为“人作为叙述者的知识、视野、情感和哲学的投入,成了左右叙事时间速度的原动力”[6](141),他可将时间“凝止于一非时间性的人生哲理思辩之中”[6](137)。在对时间的处理中,充满了对历史、人生的透视感与预言感。“作者就是这样,从叙事时间这一角度出发,通过讲述时间对个体生命的撞击和对果园城的历史遗忘来书写小城的过去,现在甚至预示未来。”[7]在《果园城记》中,作者利用时间的凝止状态磨制出一面安静如止水,淡薄世事的人生镜子,用来映照出果园城人“宁静恬适、封闭自足、顺乎自然地生生死死”[8](439)的生存状态。这里用时间的凝止方式正是为了突出空间的力量,以此来加强时空的凝聚力,从而引起在叙述上的张力。无论是时间叙述还是空间叙述,它们最终都停留在对果园城中众多孤独者的关注上。
从文本中我们感受到了“故乡”与“异乡”的双重失落。“故乡”丑,人性、人情和生命丑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和残酷。但是失落并不意味着绝望,残酷也并不意味着憎恨。师陀曾说过“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我怀念那广大的原野”[9](81)。“在这里我们发现家乡与原野间出现情感的断裂:家乡,其实是超验的传统的诗意化,是一段文明的载体;原野,是一个民族和文明生存繁衍的永恒的空间。”[10]永恒不变的“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识使师陀对生命、对社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表达,它使作家不自觉地把对社会的批判、对历史的审视以及对生命的体验都沉入到自己的生命体味之中,从而一切所观之物皆为自我生命的关照。
作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种理性使师陀清醒地认识到“故乡”的真实:“除了甜甜的带着苦味的回忆而外,在那里,在那单调的平原中间的村庄里,丝毫没有值得怀恋的地方。我们已经不再是那里的人……”[9](146)“故园归去已无家”,他是“城里的乡下人,乡下的城里人,或者说,既非乡下人,又非城里人,城市与乡村都遗弃了他。他承受着双重的失落,成了精神上无可依傍的弃儿,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个在流浪中苦苦追寻的跋涉者”[11]。寻找与流浪的永恒性无疑给师陀和他的主人公们以深刻的痛苦,造就了他们的孤独感、寂寞感、无归属感。
真实的叙述者师陀把自己的孤独投射在人物叙述者马叔敖身上,而马叔敖又把自己的孤独化为果园城中各形各色的孤独者,而这个孤独化的过程又是内隐的叙述者果园城见证和在其中发生的。叙述孤独和孤独叙述实则上是叙述者与孤独者二者之间心理冲突的二元对立体。正是在这种冲突与碰撞中,文本把叙述者和孤独者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师陀——马叔敖——果园城这个叙述者的转换,完成了从孤独到叙述孤独,从叙述孤独到孤独叙述这个三线一体的叙述。正是在叙述孤独和孤独叙述的过程中,文本形成了叙述和审美上的张力。
师陀在《果园城记》中以一个始终流淌着乡下人血液的都市知识者的双重眼光重新打量故乡,留恋着农业文明的“具有牧歌风味的幽闲”[12](233),同时又“憎恨”它“流播着封建式的罪孽”[12](233)。作为孤独的叙述者,叙述了孤独者的故事,演绎了小城的衰落和孤独,忧伤地浅吟出一曲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返乡却难以回归,又不得不寻找、流浪的孤独、寂寞、无归属感之歌。
[1] 师陀.果园城记序[A].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C].北京出版社,1984.
[2] 梁鸿.论师陀作品的诗性思维——兼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诗性品格[J].中州学刊,2002,(4).
[3] 杨晓塘,宋立民.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方式[J].洛阳大学学报,1996,(1).
[4] 马俊江.论师陀的“果园城世界”[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1).
[5] 李春红.“不希求了解……”——师陀(芦焚)漫谈[J].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9).
[6] 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7.
[7] 刘敏慧,周鸿.乡土中国的忧伤凝眸——师陀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读解[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2).
[8] 杨义.杨义文存(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8.
[9] 范培松.师陀散文选集[C].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10] 李抒音.直面历史:挽歌中的寓言之“城”[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1).
[11] 余党绪.跋涉与沉思——论师陀小说的文化品格[J].上海大学学报,1997,(4).
[12] 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C].北京出版社,1984.
Narrating Solitude and Solitary Narration——Interpretation of Shi Tuo’s Records of Orchard Town
Chang Huim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400031,China)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lonely spirit is inherited,and expressing loneliness compose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theme.Shi Tuo in the 1940s displayed the theme of loneliness extremely in his novel collection Records of Orchard Town.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art from the text of Records of Orchard Town,from two aspects:narrating solitude and solitary narration.
Shi Tuo;Records of Orchard Town;narrator;lonely people
I206.6
A
1673-0429(2011)06-0021-05
2011-08-30
常慧明(1978—),男,山西长治人,四川外语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