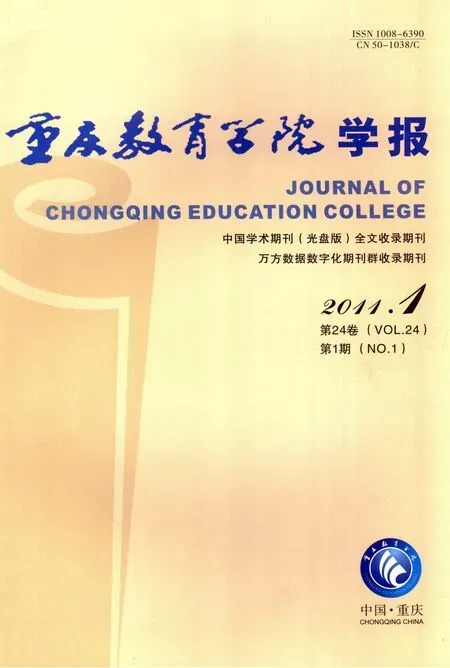柏拉图《理想国》女性教育思想评析及反思
2011-04-01康夏飞
林 木,康夏飞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柏拉图《理想国》女性教育思想评析及反思
林 木,康夏飞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柏拉图《理想国》第五卷阐述的女性教育思想有其积极性与局限性,解读柏拉图的女性教育思想,对促进当代中国女性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柏拉图;女性教育思想;《理想国》
一、柏拉图女性教育思想的理论溯源
追溯柏拉图所处的时代,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女性缺乏同男人一样的受教育机会和政治话语,她们最主要的任务是生育后代、掌管家务。面对扭曲的社会现实,柏拉图萌生了探求一个稳定、和谐、正义、完善的理想城邦的宏愿,女人作为城邦的一半力量,对她们实施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是柏拉图教育理想的重要环节。因此柏拉图的哲学观和政治观为其女性教育思想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观
柏拉图的哲学观受到毕达哥拉斯灵魂不灭思想的影响,相信轮回说和灵魂转世说,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灵魂只有脱离肉体,才能升华,达到灵魂的净化,[1]肉体在哲学中被贬损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只有灵魂才是至高无上的。一边是灵魂、精神、理性等,以男性为代表价值,另一边是肉体、物质、感性等,以女性为划归标记,后者总是处于劣势地位。[2]就当时整个古希腊哲学而言,二元系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带有明显的性别取向。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指出,“如果一个男人的灵魂是懦弱的,那么他的灵魂下辈子就会进入女性的身体”。[3]但《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女性除了在生理上弱于男性以外,男女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认为“肉体的不同不影响灵魂的区别”,理性同样地分布于男女两性,对于工作的选择依赖于该人的头脑和品格。这反映了柏拉图哲学思想上的矛盾性,也为其女性教育观的不彻底性埋下了隐患。
(二)政治观
柏拉图政治观的形成受到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影响。一是内因。柏拉图自身是一个社会本位论者,他认为个人只是作为分子而存在,国家的目的就是个人的目的。不论男女都应为国家服务,女子也应当为国家的强盛和发展承担责任。在柏拉图构想的理想国家取消了家庭和私有财产,要求孩子、妇女公有,使妇女从繁琐的家庭工作中解脱出来,接受教育,参加国家事务,选择职业。二是外力。一定程度上斯巴达体制给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参照,尤其在妇女问题上,更得到柏拉图积极的响应。斯巴达妇女的地位极高,不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妇女都受到尊重,她们接受同男子一样的教育,训练内容和方法方面与男子完全相同,且斯巴达的女人享有财产权、土地权、参与国家管理权等其他现实古典社会妇女所难以想象的权利。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也赋予女子同男子一样的教育权、公共事务权、财产权、社交权等多种权利。
二、柏拉图女性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教育目的
柏拉图女性教育的目的是基于他的政治观。作为一个社会本位论者,柏拉图认为个人只是教育加工的原料,它的发展必须服从社会需要。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符合准则的公民,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延续。培养具有勇敢美德的能治理国家统治者和能守卫国家的女护卫者,是柏拉图女子教育的目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男女在天赋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两性之间的唯一的不过是生理上的区别。“没有任何一项管理国家的工作,因为女人在干而专属于女性,或者因为男人在干而专属于男性。各种的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4]柏拉图正是在承认男女天赋相同的基础上,提出让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教育的权利,接受同样的教育,把女子培养成为和男子一样的统治者和护卫者。
(二)教育内容
柏拉图说:“为了同样地使用女子,一定要同教育男子一样用音乐和体操来教育女子,并且还要给他们以军事教育。”[5]他强调“以体育锻炼身体,以音乐培养美德,以故事掌握知识”。在理想国中,在学前阶段,男童和女童一样都应在国家设置的教养院中接受教育。教育内容主要有:唱歌、学习知识、讲故事等。然后经过2-3年体育训练,10岁时所有男女孩子都被送到乡下去受教育,除识字、阅读外,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20岁时,进行第一次筛选,被挑选出来的青年要能将学过的课程加以综合,以考察他们有无辩证法的天赋。30岁时,根据第一次挑选出来的人在学习、作战和工作中的表现,作第二次筛选并进行考试。被选出的人用五年时间学习辩证法,35岁放到实际工作中锻炼,50岁通过重重考验成为哲学王。[6]
(三)教育方法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儿童出生后由国家派专人抚养和教育,倡导儿童公养公育。柏拉图认为“为了培养护卫者,我们对女子和男子并不用两种不同的教育方法,因为不论男性,女性,他们的天然禀赋是一样的,出类拔萃的女人和男人都是教育的结果。”[7]他要求女子和男子一样在体育场上赤身接受军事训练。在他看来,美德就是女护卫的衣服,女性裸体并非不妥反而是正当且必须的,如果有男子对此加以嘲笑的话,只能证明自己不智、反笑人愚的可悲。这也符合他的灵肉二元论观点:灵魂高于肉体,灵魂只有脱离肉体,才能升华,达到灵魂的净化。另外,他非常重视早期教育。“在幼小柔软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他雕塑成什么形式,就能塑成什么形式。”[8]从小养成的习惯会成为第二天性,正如白色的羊毛一经染上颜色就不会褪掉。[9]他还重视实践教育,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卫者,少年时参加实习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女子和男子整队出征时要带上身强力壮的孩子,让他们将学习和实际锻炼紧密结合。
三、柏拉图女性教育思想评析
柏拉图的女性教育思想大体上融合了雅典和斯巴达教育模式中的基本要素。一方面吸纳了雅典的全面和谐教育思想,培养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吸纳斯巴达的女性与男性一起接受教育并一起出征的社会性教育。我们在肯定柏拉图为女子教育做出贡献的同时,需要透过现象看清他宣扬的男女平等教育本质。
(一)“平等”的意义
1.承认男女天赋相同
他指出男女之间的天然差别就像秃头的人和长头发的人一样,如果我们仅根据他们头发长短不同来安排他们的职业,就可能让秃头做鞋匠而禁止长头发的人做鞋匠,或者让长头发的人做鞋匠而禁止秃头做鞋匠,这显然是十分可笑的。[10]这就论证了男女的差别只是在生理方面的不同,从事工作依赖的是个人天赋,只要天赋相同,男女就可以从事同样的职业。柏拉图认为那些具有同样天赋的女性可以和男性一起成为统治者。“统治者也包括妇女在内。……我所说的关于男人的那些话一样适用于出身于他们中间的妇女们,只要她们具备必要的天赋。”[11]
2.赋予男女平等的教育权利
柏拉图强调教育对改造人性所起的作用,他说:我认为一种适当的教育,只要保持下去,便会使一国中的人性得到改造;而具有健全性格的人受到这种教育又变成更好的人,胜过他们的祖宗,也使他们的后裔更好。[12]柏拉图所设想的培养军人和哲学家的教育体系,是向具有公民资格的男女儿童和青年开放。他在总结斯巴达男女教育平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男女教育应该平等的主张。柏拉图认为既然女子和男子在本性上并无区别,那么教育方面应该男女平等。女性接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有利于消除男女间由于教育不平等而造成的差距,为女性参与政治社会提供了有力依据。
3.实施同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柏拉图认为男女既然赋予平等的教育权利,且彼此禀赋相同,教育内容和方法也应该是一致。这是斯巴达教育在他的思想上的反应,斯巴达女子要在国家监督之下接受体育和军事训练,以便在男子出征时担任后方的守卫工作。“假如我们要求女人做男人做的事,那么我们必须对她们进行同样的教育。”[13]尤其在军事教育上,他要求女子和男子一样在体育场上赤身接受军事训练。他主张女子应该同男子一样学习算术、几何、辩证法等科目,这种身心协调发展的教育模式在现在仍是可行的。
4.指出男女应承担相同的职务
在柏拉图所处的古希腊城邦社会里,女性通常过着幽居的生活,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等多方面的权利与女子无缘。针对这一状况,柏拉图主张男女都可以担任与其本性相符合的职务,在某些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柏拉图用狗的比喻来进行讨论,除非把母犬当成弱者,否则它们应当承担与公犬天性相同的工作。他认为只要男女天赋能力相同,不论性别都可以从事同样的职业。理想国中实行儿童公养公育,帮助女性从繁琐的家务工作中解脱出来,参与社会活动。这种不以性别指称来划分职业、不依生理差异来限制女性活动的观点,充分证明了柏拉图男女择业平等主张的先进性与超时代性。
(二)“平等”的局限
初看之下,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女性似乎被赋予了一种声音,一种主流的、智慧的声音,但是,当我们挖掘他思想深处,会发现其女性教育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
1.相同天赋的质疑
柏拉图虽然宣称男女具有相同的禀赋。但是他又认为灵魂是有性别的,如果一个男性的灵魂是懦弱的,那么他的灵魂下辈子就会进入女性的身体。既然只有懦弱的男性的灵魂才能进入女性的身体,那么勇敢的男性的灵魂是决不可能进入女性身体的。这就从反面论证了真正的男人是优秀的、正义的代表,女人是劣等的、不正义的代言人。依此类推,既然男女在灵魂上有区别,那又怎样让男女接受相同的教育和从事高级的职位呢?柏拉图一方面邀请女性加入护卫者阶层,声称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又认为女性在整体上弱于男性。如果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就有所区别的话,那么他们接受不同的教育似乎才是比较恰当的,但是柏拉图始终坚持男女护卫者应该接受相同的教育,此乃质疑之处。
2.教育平等的遗憾
首先,他的男女平等教育仅限于上层妇女,不包括奴隶和贫民在内,他的女性教育观是建立在精英教育基础上的,并非普通教育。其次,长期以来形成的男女不平等模式,人类在教育中积累的大量经验大多都是关于男性的经验,教育只会将男性的教育经验延伸到女性身上。正如普卢姆伍德所言:他所要求的平等教育实现是要求女性的男性化,柏拉图认为只有当女性的灵魂是男性的或者她们的身体属于男性模式时,女性才是完美的。[14]在教育过程中,女性逐渐失去自己的话语权,从属或者完全成为男性的发声筒。平等背后仍未摆脱贵族意识和哲学思想上父权制形而上学的框架,此乃遗憾之处。
3.教育内容的矛盾
在《理想国》有关音乐的讨论中,苏格拉底提出废弃挽歌式曲调的理由仅是 “因为它们对一般有上进心的妇女尚且无用,更不要说对男子汉了”[15],这流露出他对妇女的明显歧视,即使她们有上进心,也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肯定是弱于男性群体的。其次,从柏拉图培养哲学王的过程来看,女性在层层选拔过程中处于劣势,作战对于女性来说很不利。柏拉图也承认:“各种职务,不论男女都可以参加,只是总的说来,女的比男的弱一些罢了。”[16]女性由于自身生理特点的限制,在作战方面势必劣于男性,以女性的弱势同男性的强势相比,难免会使女性甘拜下风。按照这种方式筛选,选出来的哲学王只能是男性。其矛盾之处在于他拘泥于自身经验范围,认定“一种性别在一切事情上都远不如另一种性别”。[17]
4.社会职务的偏颇
柏拉图认为根据男女的天赋才能,男女可以从事同样的职业,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成为理想国的哲学家、护国者等。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希腊,职业种类的稀少,大多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虽然女性可以从事,但生理特点的限制,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柏拉图关注的是上层的精英女性,对大多数的雅典家庭妇女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理解,她们仍然被桎梏在繁琐的家庭生活中。
综上所述,他驳斥以生理差异为借口歧视女性的社会习俗,肯定女性和男性具有同样的天赋,为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有力依据,但女性在柏拉图心中仍是被轻视的弱者。他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建议只是基于革除现实弊病、完善国家机制的目的,并不是从女性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的。也就是说,柏拉图探讨女性问题是基于为他整个政治理念服务的,充分显示了柏拉图哲学思想强烈的父权性质。因此,以辩证的态度客观看待柏拉图女性主义思想是我们分析其女性思想时不能忽视的基调。
四、对当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反思
1840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学校教育和较高水平的文化科技教育几乎与女性无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教育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不论在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进,但总体来看女性教育仍处于劣势。解读柏拉图的女性教育思想,对促进当代中国女性教育理论的完善相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重视两性在生理与心理之间的差异
柏拉图认为男女两性在天赋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生理上存有差异,天赋一样的人可以从事相同的职业,因此男女可以接受完全相同的教育。就当时情况而说,柏拉图忽略女子的特殊性,反对教育区别对待,主张男女一视同仁,他的思想是革新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为男性和女性提供同样的教育,并不能为男女两性提供平等的教育。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男女平等”存有误解,很多时候都在以男性为基准进行“无性别区分”的教育,忽视两性生理差异,抹杀两性的不同,以形式上的同一掩盖两性事实差异的不平等。现代科学已经证实男女两性在生理结构方面确实存在差异,那么,在对两性进行教育时,必须考虑采取适合两性的教育方法和内容,因性施教,促使两性更好的发展。
(二)深化男女权利平等的教育改革
柏拉图的女性教育观是建立在精英教育基础上的,并非指大众教育而言。我国现阶段所提倡的教育权利平等,指的是一切人,面向所有公民。《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女性平等的教育权利;同时《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都对女性的教育与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8]但这并不意味着男女平等的教育权在事实上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实现。由于我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整个社会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女性教育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深化男女权利平等的教育改革,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国家要加大扶持力度,投入更多资金资助贫困女童教育;教育政策要促进男女两性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同时,特别要注重法律规定的女性平等教育权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还要从各个层面进行社会性别平等文化和制度的架构,以确保女性平等教育权利的真正实现。
(三)宣传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公平化理念
柏拉图男女天然禀赋一样,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目的也应该一致,这样才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女人和男人的观点,现在仍有可取之处。在我国,深受传统思维影响的父母往往把传统的社会性别差异的偏见和角色定型渗透给孩子,教育女孩要文静有礼,男孩要勇敢坚强。在学校教育中,教师们也在潜意识中认为女生不如男生聪明、男生学习更有潜力。女生在学校接受的信息大都以男性的话语来解释世界和自我,教科书、名著、古籍等书中的男性人物普遍多于女性人物,男性经常被描绘成勇敢、智慧的化身,女性则成为懦弱、无助的代名词;主流文化(男性文化)也不时暗示男性的优势地位,社会传播媒介的广告中女性往往是家庭主妇的形象,而男人则往往与成就、财富和能力联系在一起。宣传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公平化理念要一以贯之,要在教育实施过程中消除性别歧视,要从儿童社会化的起始点着手,家长要摒弃传统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学校教育要树立性别平等的新理念,开设性别公平化的多元文化课程,大众传媒应该利用自身舆论影响,提高公众的社会性别公平意识,逐步消除社会教育中的性别歧视。
(四)均衡社会分配过程中的性别比例
柏拉图认为各种的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女性可以做任何事情,男性也可以做任何事情。在他的理想国中,女人可以当农民、手工业者、护卫者、哲学王等一切男人干的事务。这种不以性别来划分职业限制女性活动的观点在当时是很大的进步,对现代女性就业择业具有借鉴作用。根据2007年调查资料显示,女大学生就业比例比男性少。男性毕业生的“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比例为52.14%,女性毕业生的比例为46.62%,两者相差不到6个百分点,相比去年14个百分点的差距有所缩小。[19]一般来说,女大学生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及其形成的挫败感,会使她们逐渐丧失其主体性的抗争,进而助长了社会上性别歧视的作为。在均衡社会分配过程中的性别比例上,虽然《就业促进法》、《反就业歧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已经开始生效,但由于内容比较抽象,实施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政府应增强政策的导向性,在消除就业歧视和实现平等就业方面,逐渐降低性别差异在女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影响,实现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综上所述,作为当时奴隶主阶级代表,柏拉图的女性教育思想不可能完全跳出时代、阶级的局限,他所谓的女性教育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在那个忽视女性价值、贬低女性地位的时代,柏拉图能提出男女平等教育的主张,赋予女性以平等的教育权利,让女性接受与男性同样的教育内容,他思想上的革新性是值得称赞的。当今的中国社会,男女平等仍未真正实现,重温教育经典著作对我们再阐释女性教育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人类另一半的智慧,女性的价值就会更好地凸现,也就能更好地发挥其才能为整个社会和谐、进步做出贡献。
[1]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63.
[2][3][16][17] 柏拉图著, 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 (卷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93.293-294.185.186.
[4][5][7][8][9][10][11]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87.181.188.71.140.185.310.
[6]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63.
[12]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518.
[13][15] 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1.365.
[14] 燕宏远,梁小燕.柏拉图:西方“女性主义”的先驱者[J].哲学动态,2005,(10).
[18]张莅颖,邵彩玲.柏拉图《理想国》的女性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4).
[19]周逸梅.大学生求职与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发布:研究生就业优势不明显[J/OL]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12/26 /content_7314141.Htm 京 华 时 报 [N].2007-12-26.
[责任编辑 蓝 天]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f the feminine education thought in The Republic
LIN Mu,KANG Xia-fei
(Education Colleg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Both initiative and limitations existed in the feminine education thought expounded in Volume Five of The Republic by Plato.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terpret Plato’s feminine education thought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eminine edu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Plato; feminine education thought; The Republic
G40
A
1008-6390(2011)01-0162-04
2010-07-10
林木(1986-),女,河南漯河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比较教育学硕士;康夏飞(1984-),女,甘肃嘉峪关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外国教育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