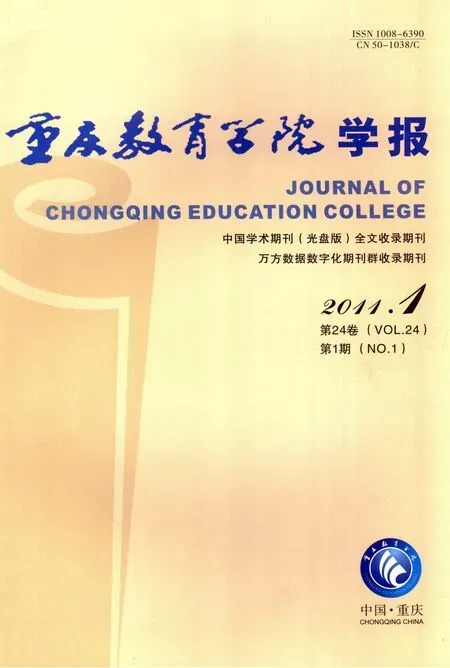察言观色:中国古代“家天下”文化的痼疾
——兼析古代社会个体价值实现的策略
2011-04-01冯雪燕
冯雪燕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基础教学部,重庆401331)
察言观色:中国古代“家天下”文化的痼疾
——兼析古代社会个体价值实现的策略
冯雪燕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基础教学部,重庆401331)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实行的是“家天下”统治,“家长”权力在自上而下传达的同时造成了权力的相对“范畴化”,从而使深受人伦关系束缚而 “身”“心”分离以及“心”支配“身”的社会个体,要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只有采取“察言观色”、谋取提携和推荐的机会的策略。某种意义上讲,“察言观色”策略是“家天下”文化固有的一种附带品,是其与生俱来的顽疾。
察言观色;“家天下”;权力“范畴化”;“身”与“心”;个体价值
梁启超1902年在其《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病时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1](P2-3)梁氏之语可谓一语中的,说出了中国古代统治特色就是采用的“家天下”之术。而且,“家天下”的统治方式应该还不只限于封建社会,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可以说是实行的“家天下”统治。据《史记·五帝本纪》,传说中具有丰功伟绩被奉为五帝的黄帝、颛顼、喾、尧、舜,就是血脉亲缘(颛顼为黄帝之孙,喾为黄帝曾孙,尧为黄帝玄孙,舜为黄帝九世孙)相承,“实际说来,中华古史五帝传说里所称‘天下为公’的官天下,却正是以血缘亲族关系为基础的远古部族社会,五帝之间所存在的亲缘世系明白昭彰,似乎已经足以表明,那种所谓的‘官天下’从一开始便已是家传”[2]。接下来的夏商周三代,就更是兄传弟、父传子的家传方式,并加以规范化、固定化、天经地义化,以后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在各种家姓中绵延发展。
在这样一个国家即是某姓的家产,国只不过是一个大家,社会个体不过是大家中的一个成员的环境下,个体所有的言行举止都必须遵循在自己还未出生之前“家长”就已设定好的框架内以及“家长”的时刻训斥下,不可越雷池半步。社会个体唯“家长”马首是瞻,为求得生存、实现价值,社会个体不得不时时刻刻关注着“家长”,闻其言、观其行、悟其心。久而久之,“察言观色”成为了社会个体实现谋生、晋升以及实现抱负的不二法门。
我们下文准备从“家长”权力的“范畴化”和社会个体“身”与“心”关系角度阐释“察言观色”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家长”权力的“范畴化”
在古代,无论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甚或五帝时期的部落联盟还是夏商两代,尽管实际执行的是血缘亲属继承制,但并没有加以法制化、规范化,而从行政上、宗法上完成此项任务的是周代。周取代商后,大肆分封子孙,从而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统治集团,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四个等级;各级次中的嫡长子分别继承父亲爵位,而相应的庶子则被分封到比嫡长子低一级别的统治阶层中去;即天子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而庶子被分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而庶子被分封为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卿大夫之位,而庶子成为靠技艺谋生的士[3](P45)。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并非等齐划一,而是上级是下一级的宗主,即天子是诸侯的宗主、诸侯是卿大夫的宗主、卿大夫是士的宗主,这样层层管制,最终将权力收归天子。而后,嬴秦、刘汉、杨隋、李唐、赵宋、朱明、爱新觉罗清等朝代尽管对血缘亲属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本质核心仍是遵循着周代设定的嫡长子制和“家长制”。
在统治者看来,天下是一姓之天下,是天子一人的家产;而天下所有百姓都是天子的家臣或奴仆。天子是理所当然的“家长”。《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取得天下后向父亲炫耀说:“始大人曾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之所就,孰与仲多?”将整个天下和以武力取得的国家当作自己私产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还向世人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为此,将家产怎样分配以及将家庭成员怎样安排布置的权力全集中于天子一人身上,意即所有权力皆由天子一人掌握、裁断。
天下大定,面对偌大的家业,“家长”难免有无从下手、力不从心之感,寻找自己权力的执行者和代言人是不可缺少的。于是,选拔官吏、任用贤能便提上议事日程。本着家业的稳固,有着血缘关系的人固然放心可靠,可终归治理国家非同儿戏。“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划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墨子·尚同》)这样,天子、三公、诸侯、正长构成权力的高级指挥机构,向下是层层控制,向上是层层负责。然而,天子、三公、诸侯、正长有时难免鞭长莫及,为使“家长”权力在全天下的任何角落生根发芽,再找具体的“家长”代言人是不可缺少的。于是,乡长、里长的称谓又产生了。在这时,“家长”从上自下的整个统治阶层成立了。依照权力等级依次为(“>”表“权限大于”):
天子(“家长”)>三公>诸侯国君>正长>乡长>里长
为使自身权力的畅通无阻以及增强代言人的权威性,“家长”通过正长向全天下发布命令:“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
“家长”或许只考虑到自身权力的不可动摇以及对自身选定的大小代言人的极度信任,在推行自身的“中央地方化”和“地方中央化”[4](P326)政策时忽略了一个当时的“基本国情”,那就是中国古代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存在的农业社会,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是架构农业社会的基础”[5],而百姓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道德经》80章)对于百姓而言,任何一级的官吏代表的都是皇权,都是“家长”的理念与规范,人们只有听命顺从别无选择。
从中国古代整个历史来看,正是由于“家长”的疏忽,执行者和代言人在执行“家长”命令时一方面严格遵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地对上唯唯诺诺,另一方面又为了扩充自身实力和增长一些现实的“养身”条件而对上层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下,又将“家长”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充分利用起来,将其进行了“地方性改造”,具体化为“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墨子·尚同》)。尽管从理论上讲国君最终“是之”“非之”的应是天子“是之”“非之”的内容,可治下百姓却只将跟自己接触最为直接的官吏当作“家长”的化身,当作自己密切相关的“家长”,奉为父母,所以史称“父母官”;从而使各级执行者和代言人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集军事、行政、财政和税收大权于一身。又加之下级官吏只对上一级官吏负责,而不可越级;这样层层管制,上下级官吏为了切身利益而相互勾结,对“家长”权力进行泛化,从而成为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一个个“小家长”;对上敷衍塞责,对下称承天子之命,对百姓任意苛责剥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个的“权力圈”。天子这个大“家长”处在“权力圈”的最外层,权限最大,又是权力的最终收归者;三公、诸侯国君和正长处在中间,权限依次缩减,而里长处在“权力圈”的最里层,权限最小。
尽管天子权力广垠无边、至高无上,可由于自身的权力是通过三公、诸侯国君、正长和里长等执行者和代言人去实施的,所以相对于三公、诸侯国君、正长和里长而言,天子这个“家长”的权力在百姓心中是抽象、模糊的,给人一种“山高皇帝远”的感觉,不及其执行者和代言人的权力来得具体、可操作。
于是,“家长”的各级执行者在自己管制范围内形成一个个“潜权力圈”,在这个“潜权力圈”里,他们美其名曰“为君请命”,而实际上在百姓面前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为自身捞取物质、金钱。各个“潜权力圈”的存在,使得“家长”的权力被分割、“家长”的权力被束之高阁,代之而起的是各执行者和代言人的任意发挥与断章取义。历史上曾因执行者实权过大、不愿服从既定的宗法束缚而弑君、造反的举不胜举: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大权旁落各诸侯国厉兵秣马自不待言,而西汉吴王刘濞谋反、唐代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叛乱,而历史上朝代更迭、天下换主也大多是前朝“家长”权力式微而臣子实权过大导致的。历史上已有有识之士看到了这种“权力圈”的存在,并力主“家长”对执行者权力进行限制,西汉晁错就向景帝提出了“削藩”政策,可终归因执行者的反咬一口而落得“替罪羔羊”“腰斩东市”的可悲下场。
由于“家长”的执行者和代言人在“权力圈”中作用的无意识扩张,“家长”权力在被抽象化和实际上的大大小小地“范畴化”,形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权力范畴和权力关系网络。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一个社会个体,要想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抱负,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行得通呢?
二、社会个体“身”“心”的分离与融合
在实施统治时,中国古代“家长”一方面将权力进行强硬的规定化,另一方面对治下百姓实行思想清洗和意识箝制。尽管战国时是“百家争鸣”,可最终统治者选取了儒家作为自己巩固天下、保持民心的“软件”。这个“软件”似乎可以只用《礼记·中庸》里的“仁者,人也”来概括。“人”只有在人与人的某种特定关系中才可成为人,单独一人是不能称其为人的。也就是说,作为个体,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人是没有独立性的,从出生之日起就被限制在人伦关系的群体意识中。自身作为“人”的认定、存在和价值,都是由处于某特定人伦关系中的群体、社团进行判断的。中国人生来就必须“做人”,而不是像“西方人则‘是’(to be)人,一个只‘是’他自己而不肯在别人面前去‘做’的人”[6](P108)。
作为个体存在的必要要素,“身”“心”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体身上最初是相分离的。“身”指纯粹的肉体,即人的物质外壳、臭皮囊;“心”指人的情感倾向、理智、意志、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等精神追求。个体的“心”尽管寄存在“身”上,但并不受其约束,而是驰骋在限定的家庭、家族或更大的社群关系中。而这些所谓的社群关系亦无非是作为天下的大“家长”早已命定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 宜。”(《韩非子·解老》)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光荣使命;而这些人伦关系、社群关系成为个体为人处事的鉴别标准:符合之,国家社会得以承认或旌扬;不符合之,国家社会将鄙视唾弃甚至还会连累自身的“身”以及亲属的“身”受苦遭罪乃至灰飞烟灭。这样,个体自己的“心”被完全控制在设定的架构中而不能“从心所欲、为所欲为”。在任何一个锁定的“权力圈”内,个体都应将“权力圈”的最高代表当作父亲来尊重、孝敬,对“父亲”的孝敬顺从就是对“家长”、对国家的忠诚与服从。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实施的都是“家长制”作风,中国古代统治者一般采取的是“怀柔”政策,将统治者的意志通过自身层层级别的代言人传达与潜移默化。
从表面看,个体唯一可以支配的就是自己的“身”,满足身体躯壳各个器官、各个部位的感知觉,而最直接、最通常的无非是衣食住行:用漂亮华丽的服饰包装“身”,用美味可口香醇舒软的食物填充“身”,用宽大豪华的住宅安放“身”,再用便捷快速且舒适的交通工具保养“身”。有吃有穿有住有坐和吃饱穿暖是社会个体追求的目标。在佛教传入前,中国古代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所以个体只有将所有希望寄托于现世今生,尤其是物质享受,使自己的“身”“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礼记·礼运》)。
可社会个体也并非完全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身”,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篇》)个体对父母的孝,首先要保护自己“身”的任何部位,其次是得道进取、光宗耀祖;而父母又是天子的“子民”,对父母的孝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对“家长”的忠。国家、天下就是天子的“家”,国家的法人代表天子“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家之长,合君王、家长于一身”。[7]作为个体,“中国人整个 ‘人’被组织的方式,就是让自己之‘身’由人伦与社群的‘心’去加以组织,而不是由自己去组织的;因此,就总会觉得能对自己加以肯定的力量是来自‘身’外——它就是别人、众人、集体、国家、民族等等”,[8](P132-133)个体的“心”已然不在自己的“身”,而“身”的何去何从又由“心”的取舍而决定;那么,个体的“安身”“安心”就必须服从于人伦与社群的“心”,即“家长”的规范。为此,个体实际上是连“身”之躯壳也不可随意支配。
为完成既定框架中的“孝”与“忠”,社会个体要努力一步步实现《礼记·大学》中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又实个体的“身”跟随“心”的所属而做出“献身”“舍身”的举动。可中国人并不是你有十八般武艺、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心就可以得以重用的,因为“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墨子·尚同》)意即个体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上级官吏不向上保举推荐也只空有叹怨了;相反,如果个体在合适的时机碰到适合官吏的推荐就可以青云直上、施展才能。历史上这种事情是举不胜数的。主父偃在得势前,在各地漂泊四十多载,非无才也,无人也。著名抗金英雄岳飞能青史留名,时任资政殿学士的刘仲偃对他的赏识与提拔是至关重要的[9];而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若非好朋友鲍叔牙的极力推荐也不会名满天下而是早就身首异处了。这也就是俗语说的“朝廷有人好做官”。保举人的重要性在古代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古代,“家长”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加之执行者和代言人在执行权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权力 “范畴化”,“每一位官员权力的取得、巩固和扩大都必须依靠上级的提携和照应”[10],“权力圈”中各地所谓的“父母官”在推荐保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完成“孝敬”的责任、实现生平抱负,寻找一个推荐人就在所难免,而这迫使人们要了解各级官吏的结构、各个“父母官”的脾气习性、兴趣爱好;然后投其所好,专攻其软肋;直至最后双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当然,由于古代中国人注重现世今生,强调物质享受,所以作为保举人的“父母官”一般也是追求金钱等实物;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与财产的交换就必不可免了。可“父母官”终究不可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向需保举人索要,而是采取一些迂回曲折的路径或含混的“言外之意”,让需保举人自己去心领神会。长期以往,保举人通过自己言行、眼神或面部表情传达自己的心声,而需保举人通过自己缜密的心思去揣摩保举人的真实意图。这样,“察言观色”这种行为动作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种人际交往中的家常便饭,也成为个体获得晋升与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个体受到“家长”的“怀柔”思想清洗和“大棒”权力高压的双重挤压,“身”“心”最终都将归属于所处的家庭、家族、社群、国家和民族;而又加之“家长”权力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形成了权力的 “范畴化”,扩大了各个“家长”执行者和代言人的实权;在这样的畸形环境中,为求得自身的“身安”与“心安”,社会个体不得不采取迎合上级的办法,极尽“察言观色”之能事。在这个意义上讲,“察言观色”只是社会个体为实现自身价值不得已采取的迂回之术,而迫使个体做出如此举动的又是“家长”权力的自上而下性以及个体的“身”“心”的既分离又胶着的复杂关系。久而久之,“察言观色”就成为广泛实施于下级对上级、贱者对尊者、年幼者对年长者、有求者对被求者的一种下意识动作和理所当然的举措;这也正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论语·颜渊》)的灵活运用了。应该说,“察言观色”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家天下”统治本身固有的顽疾,是与生俱来的毒瘤。
[1]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A].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王亚南.中国神话古史与“国家”传统[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6).
[3]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修订本)[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6][8] [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 高欣.浅论“家国同构”背景下的传统文化[J].文史杂志,2002,4).
[7] 高光晶.“国家”一词的源流新探[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5).
[9]王小珍.忠节与斯文并重之典范:宋代崇安五夫里刘氏家族文化探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7,(3).
[10] 李娟.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文化解析[J].求索,2004,(10).
[责任编辑 于 湘]
Words surmising and face observing:obstinate illness of the culture“patriarchal authority” of ancient China——Concurrent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individual values in the ancient society
FENG Xue-yan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Chongqing City Administration Colleg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The society of ancient China was governed by the “patriarchal authority”, the top-down implementation of which formed the relative “categorization” of the “patriarchal” power.Consequently, a social individual with the “body” separated for the“heart” and “heart” governing the “body” because of being fettered by human relations, could only resort to the strategies of “surmising words and observing face” waiting to get opportunities of being promoted and recommended, so as to realize his social values.In a sense, the strategy of “words surmising and face observing” was an inherent appendage of the culture “patriarchal authority”,the innate obstinate illness.
words surmising and face observing; “patriarchal authority”; power“categorization”; “body” and “heart”; individual value
G122
A
1008-6390(2011)01-0052-04
2010-09-28
冯雪燕(1975-),女,四川宣汉人,文学博士,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主攻大学语文教学研究和汉语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