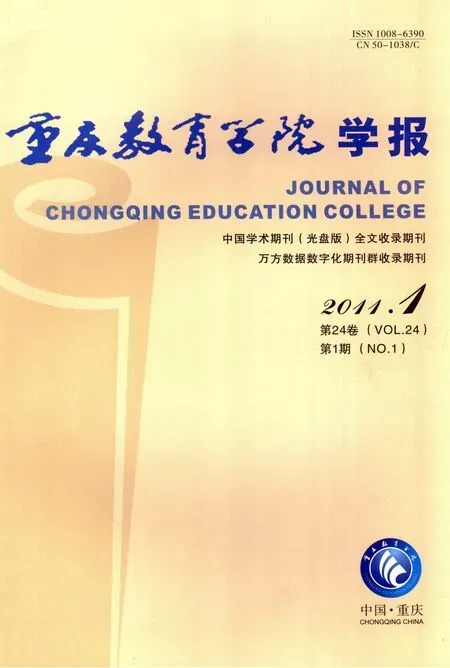试论公司章程的自治底线
2011-04-01方芳
方 芳
(重庆教育学院 通识教育部,重庆 400067)
试论公司章程的自治底线
方 芳
(重庆教育学院 通识教育部,重庆 400067)
公司的设立经自由主义到特许主义、核准主义和严格准则主义的变化,公司法的私法性日益彰显,公司章程被看作股东间的自治契约。然而,公司章程自治不能完全信赖于当事人的自由协商,亦应受公司法强制性规则的限制,本文从原因分析入手,并结合具体内容,探讨公司章程的自治底线。
公司章程;股票期权;私法自治; 公司法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法律由身份到契约的进化,公司的设立历经由自由主义到特许主义、核准主义、准则主义和严格准则主义的变化,历史上公司法包含的强制性规范为大量的授权性规范取代,公司法的私法性日益彰显,产生了公司合同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本身即是由各方当事人——股东、董事、经理、债权人、供应商、客户——达成的契约关系网,现实经济生活复杂多变,各项公司的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弹性,因而只有在合同拟制中才可能得到实现。一些公司制度安排由当事人面对面谈判逐一达成 (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协商制定章程条款);一些由一方制定,另一方只能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做出选择(如投资者在一级市场上买进股票或经理接受公司委托);一些公司的制度安排已经确定,有意加入者只有随行就市以当时的价格加以接受(如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买入证券),另一些公司的结构由立法或法院进行规定,而这些规定是总结以往成千上万次真实协商的结果中的共同性因素而来 (如股份有限公司中,“董事会”这一组织结构的设置),公司由此本质上是合同性的,[1]公司的产生、运营、解散都是当事人共同自由谈判的结果。
上述理论用于对公司章程性质的认识自然延伸出公司章程契约说,认为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公司的设立、运行、权利义务分配机制等达成的合意。公司法出于节约谈判成本、提供公共产品等效率问题的考虑,提供了一套示范合同文本,当事人亦可基于同样考虑自由选择退出公司法规范而不受其约束。公司章程自治是在私法自治的框架内提出的,其奠基于与后者同样的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前提,即“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定者”,每个人都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一经自由交易,有限资源即在最低成本下产生最大效益,整体的社会福祉也自然达成。[2]
二、公司章程契约说之反思
公司章程契约说引入经济学的方法,旨在通过市场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来克服政府机制低效高耗的弊端,通过充分尊重股东的个人意志来实现公司之治理成本的降低,该理论有其合理性,并在公司法的实务界及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但从把公司看作是政府强行法管制的对象过渡到其截然相反面,将其视为公司章程这一契约下的纯粹自治产物,其间恐有矫枉过正之嫌,而公司章程自治也不能完全与私法中传统一次性交易合同的自治等量齐观。
首先,公司章程的涉他性意味着公司章程不能仅凭股东意志安排,公司章程的效力不仅及于其制定者,而且扩展到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依法制定的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除上述内部关系人外,公司章程对与公司交易的外部关系人亦颇具影响,尤其是章程中关于经营范围和公司资本的记载,是决定交易安全与否的重要因素。因此,公司章程是一种典型的涉他性文件,这也是它不同于发起人协议、合伙合同之处。涉他性行为总是易于受到法律的管制,而且一般来说,行为的涉他性因素愈强,法律管制程度愈高,特别是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基本上是一个内部控制过程,受其效力影响的债权人等公司外部人无法参与发表意见,如果对此种关涉到第三人的契约的形成过程不进行任何监督,则该契约的拟定可能根本不会考虑到第三人的利益,从而极可能使其利益受到损害。[3]
其次,信息不对称和内部人控制问题使公司章程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股东意志自由令人怀疑。合同自由有利于合同当事人和社会的福利是以经济理性人为前提的,契约当事人必须具备足够的订约能力和订约自由才能保证私法自治的良性结果,但在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公司中,公司的规模巨大、股份分散,在公司的实际运营中,公司内部人员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而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所掌握的信息却十分有限。由于信息的成本高昂和持股量细小,小股东通常对市场表现出理性的淡漠,他们本可搭乘有足够激励收集信息的大股东的便车,但后者收集信息并把信息变为有用的行动的成本大于预期收益,其最终也采取一种被动的策略,而在公司实践中,谁掌握的信息准确和广泛,谁就能控制公司。故公司的控制权旁落于董事、经理之手,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变化的不可预测,所有人和发起人在公司初次发起时制定的公司章程不可能就将来的事情作充分的安排,即契约总具有不完备的特征,因此在公司存续期间,章程的修改在所难免,这时,管理层可能为了自身利益利用手中广泛的权力和运用各种议事策略,背离公司和股东的初衷,胁迫或诱使股东通过不利于自己的提案,所以股东对章程修改方案的投票权是在信息不对称和意志自由受限制的前提下行使的,需要强行法界定公司章程的自治范围,以修正公司实践中有名无实的契约自由,避免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再次,市场调节和激励机制不足,不一定能使反映在公司章程中的治理结构得到有效估价,由股东“按值论价”的订约公平性呈现瑕疵。公司收购市场虽然能从外部给管理层尽心尽力为股东和公司利益工作以巨大的压力,但其不是整合股东与管理层效用差异的灵丹妙药。实践中经营良好盈利可观的公司往往成为收购目标,而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管理层和公司的利益关系,但经理参股数量有限,一旦其独享的得利于自己行为的收益大于可与其他股东分享的股价损失,内部持股的约束功能便失灵了。股票价格受整个股市行情宏观风险影响,其上下波动易受不良居心的投资者违法操纵,并不一定真正反映公司的经营绩效。又如“公平定价理论”认为,假定市场是有效的,有关公司所有普通规则的信息都是自动反映在该公司股价中,如果公司采取了一种牺牲股东利益而明显偏向管理层的治理规则,那么该公司股价自然会下跌,所谓“一分钱一分货”,此时买进股票的投资者并没有受到剥削,此种理论对于面临公开发行,要在未来接受市场定价的公司及其股东尚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对于已买入股票的投资者来说,由于支付买价在先,修正规则在后,如果没有强行法作为保障,投资者只有或者不声不响地呑下苦果,或者在二级市场上忍痛把已经跌价的股票卖出——无论如何,损失只能由自己来承担,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4]
另外,如果把公司章程定性为纯粹契约,则股东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能提起违约之诉,而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权利未必合理,即使最初发起人订立了合理的章程契约,也难免以后公司经营过程中,内部控制人利用优势地位间接支配股东会通过谋求自利的章程修改案。允许公司法强行规则介入公司章程自治,则当股东权益无法通过契约之诉救济时,他们可以转而依靠违反强行法的侵权之诉。
最后,即使是私法自治传统领域的一次性交易合同的自由亦受诸如显失公平无效条款、格式合同条款规则等强行法干预,更何况公司章程这一牵涉利益主体众多、内容繁杂并持续运行的组织型契约,其更难逃“绝对的合同自由受限制”这一本世纪以来合同法发展的重要趋势。
因此,公司章程的制定与变更虽然是公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由于公司章程的涉他性、内部人控制、市场调节和激励机制不足等因素的介入,公司章程的自治只能是有限的自治,它势必受到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限制。公司自治不应该是公司自由、任意程度的管理自我,而应是在国家法律规范下的自我调节。公司章程应该既能够为公司当事人主张权益提供依据,又可以为国家权力的适当介入寻求契合点。[5]
三、公司章程的自治内容
随着近年来各个上市公司纷纷提出修改公司章程,章程内容由过去千篇一律、毫无个性走向多元化,其在公司法人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表明上市公司已开始自觉地规范自身行为,同时这样一个问题亟待解答:公司章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治?或者说,公司章程的哪些内容应该受到公司法的制约?
实际上,公司章程的自治与公司法的强制,是两个相互联系、此消彼长的问题。公司法到底是任意法为主还是强行法为主,这直接决定了公司章程制定过程中享有多大的自治空间。当公司法强调公司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享有意思自治和行为自由时,公司法的私法性或者任意性就比较突出;当公司法要求公司行为必须因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而受到干预和限制时,公司法的公法性或者强制性获得张扬。有学者把公司法规则分为三类:赋权型规则,即可以选择适用的规范;补充型或任意型规则,即可以排除适用的规范;强制型规则,即不能排除也不能更改的规范。其中,前两项属于作意法,后一项属于强制法。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也相应分为任意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前两项属于自决记载事项,后一项属于强制记载事项。可见,公司章程的自治只能是在法律框架内的自治,以不违反公司法的强制型规则为底线。然而,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并无明显形式上的标志,“应当”、“必须”、“不得”等用语也非绝对的判断标准,这使得公司章程的自治界限有待进一步明确。
从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看,无论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章程单一式表现,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章程由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组成的两分法表现,公司章程条款被用于强制规范的公司事务,基本上涉及的是公司的对外关系,涉及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主要有:1.公司名称条款:公司名称可以自由选择,但必须遵守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2.公司住址条款:将公司住址列入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因为公司是法律实体而非物质实体。3.公司目的条款:公司目的条款的确定,既限制了公司营业行为范围,不允许随意超范围经营,又有利于交易相对人评估交易风险。4.公司资本条款:如公司可发行的资本总额或者股本总额、股份数量、每股金额、股份种类等。还应包含发起人认购数量和出资额情况的记载。5.公司责任条款:即公司股东的责任、公司是否负有担保等。6.公司公告条款:包括公告方式、公告载体等。
相比而言,公司章程条款可以自由选择的公司事务,基本上涉及的是公司的内部关系和日常运作,与公众无关。如公司内部机关的权力配置、决策权的行使、责任的限制、利润分配等,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章程两分法形式中属于章程细则的内容。因此章程细则被视为公司与股东、董事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一种协议。通常章程细则无须登记,在制定程序和修改程序上要求并不严格,以自治约定为主。但是章程细则并非完全不受强行性法律规范的制约。比如,美国《示范公司法》规定:第一,公司修改章程细则不得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和理念,如免除董事过失责任或者在约定之外增进董事责任的条款无效;第二,章程细则的条款与章程大纲抵触,该条款无效;第三,章程细则的任何修改与法院的命令冲突无效;第四,如果章程细则的修改涉及对某一类成员权利的修改或者废除,都必须遵守公司法关于变更此类权利的规定,并通过特别决议之;第五,公司修改章程细则,还必须在总体上遵守真正为了公司利益的原则。[6]
例如,公司法规定的税后利润分配及其比例能否为公司章程所修改?目前,中国众多的上市公司中,年终不进行红利分配的公司越来越多,除去一些公司业绩下滑,确实没有分红能力外,大量的公司从业绩分析来看,明明具备分红能力却仍然采取了不分配方案。[7]但是,这种方案即使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确立,也应受到强行法的制约。因为公司法规定的资本收益权是股东权益之自益权的最基本内容,属于强行法规范,分配公司税后利润又是这一基本权利的最大体现,因此,在是否分配税后利润这一点上,公司章程并无自治余地。实践中,不分配股利的决议多半由控股股东为了一己之私操纵股东大会做出,其不愿将所有利润与中小股东共享,而是以年薪或奖金的方式发放给自己派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干脆通过关联交易使大量利润落入自身手中,如果允许这种章程修改内容有效,无疑会严重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动摇公司为其所有者得利这一终极价值理念。
另外,新近出现的公司承包现象,即由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发包给一个股东经营,并由公司与承包股东签订承包合同,不论公司盈亏,承包股东都要向公司缴纳规定承包金。公司经营利润归承包股东享有,经营期满后,承包人需保持公司股权价值不变或增值,若出现亏损则由承包股东弥补。[8]这改变了公司法关于税后利润分配比例之规定,而法定主义分配方式具有维系股份平等原则的价值,股份平等又是公司法中的帝王条款和基本原理,这一原则在公司法中属于强制性规范,约定的股份分配比例不得违背股份比例性平等这一维护股份公司资本团体性的本质性规则。同时,股东按出资比例在公司中享有权利,承担有限责任,也是维护公司形态法定主义的必然要求,所以除非公司法有例外规定,任何违背这一规则的公司章程条款均属无效。
四、小结
公司章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股东间的自治契约,但出于种种原因,公司章程的自治不能完全依赖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亦应受到公司法制约。制约的程度会因公司的规模大小、涉及公司事务的性质而异,但自治始终是公司章程的本质属性,仅当章程内容违背负载公司法乃至整个司法价值的强行法规则,即超过其自治底线时才被认定为无效,否则宜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给公司章程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留下广袤的空间。
[1][4] 汤欣.论公司法与合同自由[A].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16).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73.310.
[2][3]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89.285-286.
[5] 沈贵明.公司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朱慈蕴.公司章程两分法论——公司章程自治与他治理念的融合[J].当代法学,2006,(5).9-16.
[7]王保树、杨继.论股份公司控股股东的义务和责任[J].法学,2002,(2).
[8]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20.
[责任编辑 于 湘]
On the bottom line for the self-governing of a company’s regulations
FANG Fang
(General Knowledge Department, Chongqing Education College, Chongqing400067,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any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 from liberalism to special permission, authorization and strict standardization.The privacy of Company Law is becoming conspicuous and a company'regulations are regarded as the selfgoverning deeds between shareholders.However, the self-governing of a company’s regulations can not only rely on the free negotiation of parties completely, but also be restricted by the coercive regulations of Company Law.Start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combining the concrete cont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ottom line for the self-governing of a company’s regulations.
company’s regulation; stock option; self-governing of private law; Company Law
DF411.91
A
1008-6390(2011)01-0042-03
2010-03-17
方芳(1979-),女,重庆市人,硕士,重庆教育学院通识教育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