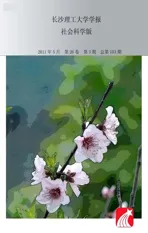举爬梳之全力 发潜德之幽光
——《易顺鼎研究》读后
2011-03-31彭富强
彭富强
(湖南人民出版社湖湘文化编辑部,湖南 长沙 410005)
著名史学家蔡尚思先生曾概略论及中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在众多的清代诗人中,从“异于前代”的角度出发,独推于今声名黯黯的两个人——清初的李柏和清末的易顺鼎,可见蔡先生去取标准的不同流俗。一个文学家的文学史定位,固不能以他的“异”于前代或者“同”于前代的若干因素来确定,也不能仅以其技术操作的“巧”或“拙”来定高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第二自然的“文学史”,毕竟是“人造”的历史,文学家声名的显隐、文学地位的高低,不完全取定于他本身的作品。好在易顺鼎去今未远,文献大抵可征,因而下述事实便无法视而不见:易氏在晚清诗坛,尽管毁誉不一,却声名藉藉,文评家与选家不曾冷落他。比如,吴闿生的《晚清四十家诗钞》,收录晚清诗人41家,诗作646首,其中选录易顺鼎诗25首,与只录公认的大文豪王闿运的诗1首相比,足可见从选家的桐城派的眼光与宋诗派的偏好来看,王、易二人是不可等量齐观的。1949年以后,在文学批评的庸俗政治化、社会化的喧嚣中,像易顺鼎这样的作家,尽管为民时极其爱国,为官时极其爱民,然而由于他既不像遗老那样死抱“上国天朝”的情结,也未对革命倾心赞誉,总之,不属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官方文学史所肯定的系属,所以在1949年之后近40年里,被人选择性遗忘,自在情理之中。假若长此以往,易顺鼎的诗名,大抵会湮没在浩瀚的近代文学文献中。当然,实际的情况,并没有完全令人失望。譬如,在对岸的台湾学术界,大约因为他两次赴台襄助抗日的义举,以及儿子易君左作为著名港台作家的不俗的影响力,因而时常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未曾被遗忘。相比而言,1949年后的大陆,在沉寂近40年后,自20世纪90年代,他才真正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其间,易顺鼎的《琴志楼诗集》(王飚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和《易顺鼎诗文集》(陈松青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的出版,使读者看到了易顺鼎诗文创作的大致全貌。尤其后者,收录易氏诗4300多首,词500多首,辞赋、骈散文100多篇,是迄今为止收录易氏作品最全、甄别最确的本子。而陈松青著的《易顺鼎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作者数易寒暑整理易氏诗文的又一成果,具体而言,是有条理的、成体系的校读札记。这样一种写作背景,决定了该著的基本思路与特色。
如前述,易顺鼎是一位长期被忽视的作家,他留给后人太多的疑点。对他思想的评价、文学史的定位等诸多问题,只有在对文献加以充分发掘、合理择取与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得出中肯的结论。换言之,如何复原易顺鼎的生平、创作、心态的历史风貌,是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易顺鼎的集子,举凡文学的,学术的,总计约60种,假如加上他父亲、兄弟、姐妹、子孙等的著作,总量约是前者的二三倍。而且易顺鼎未刊行的著作尚多,据其收藏者所言,易氏手稿即近30斤重。至于他的零章碎简、雪泥鸿爪,散见于报刊以及各种文集、日记、杂著中的,又不知凡几。该著以易顺鼎为中心,尽其所能,对相关文献做了深细的挖掘,因而文献的梳理、考辨,成为本书突出的特色。比如,易顺鼎别号禆牛山民、橘州醒人,为今人罕见。该著指出,这两个别号跟易顺鼎出生的地望有关:汉寿境内有禆牛山,故他自称“禆牛山民”;沅水流经汉寿,水中有汜洲,又名橘洲,故又自称“橘洲醒人”。再如,不少人说王闿运与易顺鼎是师生关系,但据《湘绮楼日记》等文献记载,易氏兄弟遵从父母的意愿,不曾拜王闿运为师。又有资料说,王闿运曾与易顺鼎、寄禅于天童山联吟唱和,而实则王闿运未曾参与。易顺鼎晚年在袁世凯政府做官,这是事实,但有人说他赞成袁氏称帝,恐非事实,因为项士元《慈园丛话》记载着他拒绝“筹安六君子”的邀约,应可信的。该著虽极力表彰易顺鼎的爱国思想,但同时指出这种爱国思想夹杂愚忠成分,他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也夹杂书生意气,因而放在其时已有的思想文化的高度来考察,其心志虽然可嘉,而理性未至。甚至被常人视为封建迷信的“乩笔诗”,该著也拿来揭示易氏一家特殊的文学气象,说明易顺鼎丧母之后“墨绖从戎”、意欲蹈死沙场的心态是复杂的,也是不坚定的。如此等等,无论巨细,该著都做了细致的爬梳剔抉。这对于全面认识易顺鼎思想性情的复杂多样,是有帮助的。
易顺鼎与军政、士林、僧道、艺苑各界都有广泛交往。为了突出他与时代及文人群体的互动关系,该著具体考察了他与王闿运、张之洞、樊增祥、陈三立、杨锐,以及艺人群体的交往,通过交游网络,构建起易顺鼎生活时代文人的生态图景。该著指出,易顺鼎与樊增祥虽号称“文字骨肉之交”,但是真正对易顺鼎充满“理解之同情”的,不是樊增祥,而是陈三立,这与易、陈二家为世交,顺鼎与三立有“总角之游”相关。易顺鼎风流自喜、流连声色,也好用“冶游”、“好色”等词语“自污其名”。年轻时,三立即对之加以劝戒,但随着时世的变迁和仕途的不顺,人性的弱点在易顺鼎身上日渐膨胀,以至于颠倒颓废,放浪形骸,纵情速死。对此,三立不像樊增祥那样语多调谑,而为之深深痛惜,其哀悼顺鼎的挽联、祭文,可谓字字泣血。该著分析易顺鼎对女性的情感体验,除引用大量诗文史料外,甚至还引用小说《孽海花》中的人物“叶笑庵”(以易顺鼎为原型)评说历史的怪论,说明易氏晚年对历史、现实与人生的幻灭,以此贯通,印证他对坤伶(女艺人)的倾心与伤悼,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强烈的幻灭感,不仅使诗人所言所行,一任一己之所为,同时也使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一意孤行”,不顾他人讥评,以追求诗歌风貌个性的“唯一”为最高目标。易顺鼎以才情自负,以才子自命,他的诗,“不唐不宋”,不依傍“家派”,是一种抒写真性情的文学,是一种不断求新求异的文学。该著通过详博的材料梳理,结论符合事实。
该著不仅在掌握大量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沉潜考镜,梳理辨析,订正讹误,补苴罅漏,同时也将学理性的思辨分析和对作品的审美把握融合起来,得出了一些较为通透的看法。如论易顺鼎与清末民初诗歌演变的关系,揭示其诗与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存在彼此呼应的关系,并将之上升到文学史的高度,认为以“诗界革命”的理念是无法对古典诗歌构成根本性触动的,继之而起的“南社”,由于文化保守主义、文学复古主义的立场,其可贵的爱国、革命的情怀都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因而到“五四”,文学革命才被“逼上梁山”(胡适语),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对于旧式文学却不能彻底抹杀,“几千年的古典诗歌,绵延不断地发展演变,自有它存在的正当性。它在内部改良也好,或者仍旧是魏晋、唐宋、元明风貌也好,在文艺的百花园里仍有它争春的权利”(第293页)。文学是可以、也应该多样性地存在,这样的认识是合理的。
易顺鼎除诗之外,又兼长词、赋、骈散文的写作,但这方面的成就,一向为其诗名所掩,学术界对其词、赋、骈散文多不究及。该著对此进行发掘,尤其考辨了其词学活动,将其词学师承、人生际遇与词的情感特征、艺术风貌,做了通贯的考察与分析。易顺鼎是晚清词的名家,当可无疑。
总之,该著对文献的发掘,十分用心,一些结论性的意见都建立在考辨、深思的基础之上,因而胜义颇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当然,由于近代文学文献过于浩瀚,哪怕是对一家一姓,要搜罗完备,殊非易事,因而诚如该著所提及的,某些细节仍有待确考与补充,而作者一直在从事这一工作,可以相信,该著及后续成果,对于近代文学的研究,对于湖湘文化资源的挖掘转换,都会起到积极的学术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