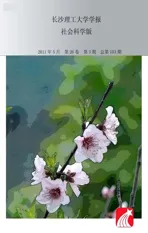试论孙光宪词的抒情方式
2011-03-31成松柳巢晶晶陆群
成松柳,巢晶晶,陆群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词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女性化的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首先,从词的生成和传播的过程来看,离不开女性所做的努力和女性化的创作环境。作为应歌而作的文学样式,词歌唱的“主体”便是最典型的女性形象之一——歌妓。其次,歌妓及其所处的女性化的生活环境,为词人带来了奇妙的灵感刺激和创作素材。正因为如此,词在初起时建立了这样的创作模式:其创作目的是为了城市生活中的欢场歌舞;主要人物是城市女性;审美趣味是女性世界;语言风格是用语的香艳精美和节奏的错综变化;境界小巧精美;抒情方式是描写对象的类型化和抒情方式的模式化。这和诗的创作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词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不同的探索和创作实践。孙光宪词虽然整体上没有脱离花间藩篱,但词人却将诗的题材、语言和意境引入词中,其词作抒情方式上也就与那些模式化、类型化的花间词有了区别,表现出他自己独特的个性。
一
正因为词的产生和发展是在这样一个女性化的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之下,所以,纵观唐五代词的文学舞台,基本上是由才子佳人和情男怨女们当纲主角。女性皆是轻摆柳腰,浅笑含颦,处处显露出楚楚可怜的形象。而男性也同样是细声慢语、柔情似水的多情才子的形象。这些词中的抒情人物,既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某一个特指的个体,甚至有时他们的身份和性别都模糊不清。词中的抒情人物与抒情主体的分离错位,使得这些词中的抒情人物成为非我化的,类型化的一群人。而孙光宪的笔下不仅有风流才子,绝色佳人,还有散淡渔翁、边关将士、失意文人等不同于花间词的抒情人物形象,其”女性的身份也丰富多彩,妓女、贵妇、渔姑、道士等,不似其它花间词中女性形象”(宋纯 《的别调:对“孙词近韦”现象的反思》)具有普泛化的色彩。
在他的《渔歌子》二首中,抒情主人公是一个超然物外的渔人形象,他泛舟于茫茫江上,虽孤寂一人,却心境豁达,自得其乐,不为世俗所羁绊;《定西番》(鸡禄山前游骑)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身姿矫健、射技高超的边关将士,他于塞外草原驰骋游骑,不畏边关艰苦,一心保家卫国,建功立业;《浣溪沙》(落絮飞花满帝城)、(十五年来锦岸游)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失意的文人,满腹才华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心中满是愁绪,哀叹韶华易逝,虚老平生……这些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类型化、所指不明的模糊朦胧的人物,而是一个个身份明确、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的人。
虽然孙词的抒情主人公大多也是女性,但部分词作中女性形象清新、活泼,展现了灵动的生活化图景,与花间词中那些千篇一律柔弱不堪、娇慵无力的美人也大不相同。如《菩萨蛮》(青岩碧洞经风雨)的抒情主人公就是几个天真浪漫的渔家女,她们相约游船,放歌湖上,清新脱俗,明丽可人;《八拍蛮》(越女沙头争拾翠,相呼归去背斜阳)的抒情主人公是一群形象清新的南方姑娘,她们呼朋引伴,滩头拾翠,一个个热情奔放,青春逼人。《女冠子》两首虽是缘题而作,抒情主人公仍为女道士,但这位女冠自诩清高,几乎不食人间烟火,与温庭筠、薛绍蕴等人的同调词大异其趣。
即使同样是闺阁题材,孙词与其他花间词人所描绘出的人物形象也不尽相同。《花间集》中的闺阁词,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上很下工夫,却不太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塑造。他们的词,无论展现了如何美丽幽雅的意境,却依然是当作观念的表象加以构筑的,是一种普泛化的形象。孙光宪笔下的女性,不同于《花间集》中其他的普泛化的女性形象,而是极为真实生动,一一可辨的。同样是描写幽怨的思妇,“孙词中的女子不再满怀思念地一味等待,而是以责问的口气直逼男子,从“思”到“责”,口吻的力度自然由软弱无力、缠绵悱恻转向决绝高亢。如“终是疏狂留不住,花暗柳浓何处”(《清平乐》、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谒金门》)等词都夹带着一股迫人的气势。还有部分闺阁词将爱情与边塞征战相连,用边塞粗犷浩渺之大气来中和思妇哀怨悱侧之弱气,也提升了词作整体的力度感。”(宋纯 《的别调:对“孙词近韦”现象的反思》)
二
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有这样一句话:“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1]苏轼在论张先词也曾说过:“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波耳。”[2]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认为诗为文之余,词为诗之余,虽然这样的观点有失公允,但是我们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到,散文、诗、词的文体功能确有宽窄之分。散文的文体功能最为宽泛,叙事、抒情、议论等等均可包括;诗的文体功能相对狭窄,虽然也有用诗来叙事和议论的,但主要的功能还是抒写情志;而词的文体功能则最为狭窄,它似乎只适合抒发人们儿女情长之类的私人情感。诗词在文体功能的不同,也注定了诗词在情感表现上的不同。诗中的情感,是个性化的,是诗人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表现对社会、人生、自然和历史独特的观察和见解、感受和反思。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抒情诗的内容是主体(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观照和感受的心灵。”“抒情诗采取主体自我表现作为它唯一的形式和终极目的。”[3]而词的情感,则是普泛化的,既不是词人独有的人生感受,也不是某一特定个体的人生感受,而是人类共通的或某一社会群体、阶层所共有的情感心态。词中的情感,是非政治化、非社会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超越时空的情感。(王兆鹏 《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在词兴起的早期,特别是温庭筠确立了词有别于诗歌个性化的类型化抒情模式后,词这一文体形式所表现的情感基本上都是以描写男女间的爱慕之情和离愁别恨为主的。然而孙光宪的词作在情感上的表达,突破了以往的抒情模式,开始用词抒写了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将词所表达的情感从普泛化又回归到个性化。
从孙光宪的生平中我们得知,孙光宪虽出生寒微,且生逢乱世,但是他从小勤奋好学,胸怀经国治世的伟大抱负。无奈唐末藩镇割据,战乱不断,先后经历了前蜀荒逸统治和荆南地小势薄,始终宏图难展,不得不在彷徨和等待中耗尽了几乎大半生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荆南归顺北宋,受到太祖激赏委以重任,却又垂垂老矣,天不假命。因此,虽然他一生学富五车、志存高远却始终英雄无用武之地,故常常有生不逢时遇的抑郁沉沦之叹。《十国春秋》载:光宪“每谓知交曰:‘宁知获麟之笔,反为倚马之用’”这样的情怀表现在词作中便成了一首首感叹悲剧人生,抒写难酬壮志的作品。试看《浣溪沙》中写到的: “看看春尽又伤情,岁华频度想堪惊”、“未甘虚老负平生”,一“恐”一“且”表达了他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和宏图难展的失望之情。伤春实际上就是感伤自己韶华的逝去而又始终抱负未伸,因此才“堪惊”,才“未甘”,据此不难想见作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沉郁之悲。因此高锋评价说:“在孙词中,第一次或直露或委屈地把一位有志于时却怀才不遇、放荡不羁又坚守节操、骚愁满腹而又旷达豪爽的失意士子形象呈现出来。”[4]这首词正面抒写了他内心的不平之情。有时他还用比兴寄托之法,间接抒发这种情感,如《生查子》(金井堕高梧),单从表面看是一首宫怨词,但华钟彦先生就曾猜度它“有寄托之意”[5],加之古代文人多有以失宠宫女隐喻自身怀才不遇境遇的传统,不难想见,此处词人的确很有可能表达的是内心深处对生世浮沉的感叹和壮志未酬的失意。
孙光宪历经三朝,政治眼光犀利。他作为政治家以历史的、社会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沉浮、世事沧桑和人生遭遇,积淀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厚度。于是他的词中经常出现感叹不合理社会现象,表现规劝讽谏的情感。如《河传》、《后庭花》二首等,就是借隋炀帝和陈后主两位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来说明君王的荒淫无度将导致亡国这一道理。《宋史》卷483《孙光宪传》载他在荆南曾向高从诲进谏:“徒奢侈僭汰,取快一时,危亡无日。”因此,陈廷焯评其《后庭花》(石城依旧空江国)说:“胸有所郁,触处伤怀”[6]可谓一语中的地道出孙光宪的创作情感来源,此处他确是表达为荆南的政治局势深切忧患之情,意图借古讽今,讽劝荆南统治者汲取前车之鉴。
孙光宪受到道家的影响较大,我们从《北梦琐言》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道家的条目,如谈相论命,讲风水阴阳报应,鬼神怪异等,还曾多处提及他与道士的交往,道家及玄学色彩在他身上表现明显。故而当孙光宪仕途上遭受挫折时,便转向另一方土地找寻精神解脱,即使在当时视为小道的词中,他也加入了“不食人间烟火”之感,大力抒发旷达情怀,歌咏闲情逸致。《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这首作品中,虽然无一字表露作者心情,但是只“鸡犬自南自北”一句,两个简单的“自”字,便马上使人联想到老子小国寡民式的和谐自适的乡村,并且似乎还能听到这乡村的茅舍中“轧轧鸣梭穿屋”的织机声。
《渔歌子》的词调与民歌有着渊源关系,同时和楚辞的《渔父辞》也有着内容上的联系,因此,这些词调本来就是以自适、闲适为主题的。[7]孙光宪的《渔歌子》(“草芊芊”和“泛流萤”两首)特地选取了这一词调,来表达旷达自适的情怀。两首词以“谁似侬家疏旷”、“尽属侬家日月”收结,充分肯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展示了作者闲适自在却又狂放不羁的心态,其洒脱豪迈之情真可与苏、辛媲美。
孙光宪有着经世治国、建功立业的抱负。同时,他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从他在《北梦琐言》卷五中所说的 “而以诗见志,乃宣父之遗训也”和卷七中所说的“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8]可见他认为词也具有言志抒情的功能,在词的创作中也应文质并重,所以在他
词中也抒写了理想壮志,流露出浓厚的用世之情。如《定西番》(鸡禄山前游其骑),描写的是一位身姿矫健、弯弓射雁的勇武之士,整首词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感情色彩,表现出强烈的意欲建功立业,经世治国的激越情怀。
五代十国是一个兵荒马乱、战事频繁的非常时期,战争带给人民的是深重的灾难和离散的哀伤。人民的不幸深深地触动着孙光宪的心,他在他的多首词中抒发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悲悯。如《上行怀》(草草离亭鞍马)是对良朋挚友因征戍而承受“分衿”苦痛的怜悯;《临江仙》(霜柏井梧干叶堕)是对因战争而生离死别的夫妇的同情;《酒泉子》(空碛无边)更是与边塞征人感同身受的思乡曲。
孙光宪一生辗转多地,经历丰富,不仅看到了天府之国的地大物博,也领略过荆楚之地的江南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各地的民俗风物引发作者对大自然的浓厚热爱之情,于是成就了词人笔下如“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菩萨蛮》、“越女沙洲拾翠羽,相呼归去背斜阳”(《八拍蛮》)、“商女夜幕过楚江,散抛残食饲神鸦”(《竹枝》)等明丽清朗的词作。词人在这些作品中用灵动的笔触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山川民俗图画,尽情地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
三
诗中的时空场景,是纪实性的,是此时此地特有的时空环境的真实描写。虽然或有变形和夸张,但都是以真时真地真景为基础进行艺术建构,有着明确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而以温词为代表的花间词的大多数作品的时空场景是虚拟的,因而是模糊的,没有时代性和地域性。词中的时空有意被消解,它虽然也有时间性和季节性,但没有时代性,它是超时代的,任何时代都会有此时此季。它虽然也有空间环境的描写,但没有地域性,是泛化虚拟的空间。[9]孙光宪词作的时空场景虽然仍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被架空的,没有明确界线的,但同时,词人致力于变化和创新,在他的词中我们仍能看到不少有明确所指的时空和场景。
首先,他的部分作品有着明确的地域性。不同于花间词中常用的“深院”、“空闺”、“玉楼”、“画堂”等虚拟的,没有特殊地域意义的场景,孙词中的很多场景我们都能找到真实的、具体的所指。由于孙光宪很长一段时间身处荆楚之地,所以他的词中荆楚地域色彩非常浓厚,经常出现 “蓼花”、“杜若”、“橘柚”、“楚天”、“潇湘”、“湘山”、“湘妃”“楚云”等荆楚特有的物象。如《酒泉子》(展屏空对潇湘水)、《浣溪沙》“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河渎神》“江上草芊芊,春晚湘妃庙前”等等。
孙词中的言情造景,也不再限制在人造建筑空间之内,而是像诗歌那样回归大自然,写真山真水真景物,还有很多专门描写吴越之地、江南水乡民情和风俗的作品。
如《八拍蛮》:
孔雀尾拖金线长,怕人飞起入丁香。越女沙头争拾翠,相呼归去背斜阳。
借用蛮人山歌,引入孔雀、丁香、越女等南国独一无二的物象,描绘出清丽、绚烂的南越风俗图景。《菩萨蛮》(木棉花映丛祠小)一词中,一丛丛火红的木棉花,一座座小小的神社,南国独特的鸟儿(越禽)在宛转歌唱,四周是一片铜鼓、大鼓的音响,亦是只有南国社祭才有的典型场景。《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中的茅舍、槿篱、溪流、织机、菰叶、水葓,梭鸣等物象,也一看便知描绘的是典型的水乡农舍图。
除了描绘南国景致的作品外,孙词中还有一些明显带有边塞地域色彩的作品。如《定西番》“何处戍楼寒笛”、《定西番》“鸡禄山前游骑”、《酒泉子》“空碛无边,万里阳关道路”,“戍楼”、“边草”、“空碛”、“阳关”、“胡霜”等都是只有塞外才特有的景致。
其次,孙词的部分作品时间上也很具有很强的指向性。不同于其他的花间词中没有明确的时间性和季节性,或即便是有时间和季节,也只是虚拟的“那年”、“去年”、“明日”、“昨夜”、“深夜”等普泛化、模式化的时间,孙光宪的一些词有很强的时间性,词中所描绘的事物和场景只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内。例如:《浣溪沙》(十五年来锦岸游)明确的记载了时间和地点,很有可能是孙光宪真实生活的写照,记录了词人游历锦官城的经历和狂放不羁的心路历程。另外《竹枝》:
门前春水竹枝白蘋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作品以春江迟暮为背景,描写商女饲鸦的偶然小事,很具有典型性。徐士俊评曰:“偶然小事,写得幽诞。”[10]《渔歌子》两首中“沿蓼岸,泊枫汀,天际月轮初上”和“夜凉水冷东湾阔”、“经霅水,过松江”等句子将秋夜太湖上特有的悠远、空阔之境写得极为传神,时空特色清晰可辨。
孙光宪能够冲破花间词的俗套,展现自己别具一格的抒情方式,还不得不归功于他的作品独特的情境选取。同是描写离别的场景:
韦庄《菩萨蛮》: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温庭筠《菩萨蛮》:
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
孙光宪的《上行杯》两首:
草草离亭鞍马,从远道、此地分襟。燕宋秦吴千万里。无辞一醉。野棠开,江草湿,伫立,沾泣,征骑駸駸。
离棹逡巡欲动,临极浦、故人相送。去住心情知不共。金船满捧。绮罗愁,丝管咽,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
都写离别,韦词选取绣楼为背景、温词选取闺房作为背景,都是模式化的女性生活环境,皆难脱闺阁中小儿女缠绵情态,但孙词第一首选取离亭作为背景,一反花间词香艳、秾丽之风,而有一种 “风萧萧兮易水寒”那般苍凉悲壮之情,别具一格的场景选择,使得整首词刚健遒劲而又不失温婉,曲致而有清俊之情。第二首词选取江边作为背景,以江水奔流不尽衬托词人心中无限离情,意境悠远,情思缥缈,耐人寻味,兼沉郁俊逸之美。
总之,在孙光宪的部分词作中我们惊喜地看到,其抒情人物由类型化转向了典型化;抒发情感由普泛化转向了个性化;时空场景由虚拟转向了真实。其描人绘物,不是完全套用模式,而是偶有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抒情写意不是完全因文造情,也偶尔坦露词人的自我情怀和精神气度;其言情造景,不完全像温词那样“假多真少”[11],而间有真景真物。孙光宪别异于花间的抒情方式,为词的进一步发展,为诗词抒情方式的贴近与融合提供了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M]《四库全书》集部十.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七十一)[C]北京:中华书局,2008.2254.
[3]黑格尔.(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99-100.
[4]高锋.花间词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91.
[5]华钟彦.花间集注[M]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227.
[6]张璋、黄畲.全唐五代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09.
[7](日)青山宏著 .唐宋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69.
[8](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M],北京: 中华书局,2006.135.
[9]王兆鹏.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10]王兆鹏.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2004.412.
[11]唐圭璋.词话丛编[C] .北京:中华书局,1986.1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