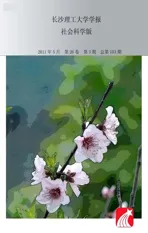浑圆与清浅
——废名与朱英诞新诗比较
2011-03-31陈茜
陈 茜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330022)
废名和朱英诞的诗歌倾向接近于卞之琳,他们的诗都是在日常生活黙想。但是,他们表现的方式并不一样。本文将侧重比较废名与朱英诞诗歌的差异,并思考朱英诞被文学史家忽视的原因,探讨诗歌研究者应有的研究态度。
一
废名认为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不同不在于是否用韵,“新诗要别于旧诗而能成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1](P7)“一首旧诗里情生文,文生情”,[1](P31)旧诗只是一株树上的一枝一叶,而靠枝枝叶叶合成空气。古代的诗歌常常只有一句是好的,其它句子是做出来的。而诗不是写出来的,是在写作之前已经完成。因此,在废名的诗歌中,他比较强调诗歌的气氛,不一定取用古代诗歌中的意象,也无完整的形式,他追求诗歌意境的浑圆和义理的藏蕴。
《冬夜》是废名早期的诗歌,“朋友们都出去了,/我独自坐着向窗外凝望。/雨点不时被冷风吹到脸上。/一角模糊的天空,/界划了这刹那的思想。/霎时仆人送灯来,/我对他格外亲切,/不是平时那般疏忽模样”。这首诗歌带有日常生活叙事风格,前四句通过环境勾画来描写自己存在人世与自然当中的一份孤独。“仆人送灯”代表双重的温暖,回到人间的温情和世界的明亮当中。诗歌采用对比的方式表达对温情的感念。这首诗看上去是描写一个场景,一次心理活动,正如废名自己所说,“我的诗是天然的,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还是诗的”。[2](P369)
朱英诞早期的诗歌,多有来自古代诗词中的意象:如《西沽春晨》:
鸟鸣于一片远风间,
风挂在她的红嘴上;
高树的花枝开向梦窗,
昨夜暝色入梦来。
最高的花枝如酒旗
也红得醉人呢;
望晴空的阳光如过江上,
对天空遂也有清浅之想。
鸟鸣来自王维的《鸟鸣涧》,高树来自曹操的“高树多悲风”,远风、梦窗、 暝色入梦、 花枝如酒旗等,偏正词组或用自然景物与人文景物结合,都是古典诗歌追求简洁凝练,营造氛围之法。
与废名不同的是,废名诗歌中的“我”可以是诗歌写作者,也可以指代普泛意义上的人类。朱英诞的这首诗是无“我”的,书写者视角物化,即通过“花枝”做梦,“花枝”望晴空,对着天空想心事来替代诗歌写作者,“花枝”成为诗人的移情对象。
在诗歌中,朱英诞喜欢通过加入语气词,使诗歌显出说话的调子,与古文文法结合,形成朱英诞三十年代独有的诗歌表达方式。
第一节不改变其意,可以改成纯粹的现代白话:
鸟在风中,远远地叫
她的红嘴上挂着风
高高树上开着花,花枝向着梦中的窗户打开
和昨天晚上的昏昏所想一齐入梦。
朱英诞的这首新诗并未脱去古诗模型,稍加删减就是一首五言古诗:
鸟鸣远风间,
风挂红嘴上。
花枝开梦窗,
暝色入梦来。
朱英诞的《西沽春晨》分两节,类似词的上下阕,第二节是第一节意境与形象的补充和解释,整首诗描绘出春天的自然风光。鸟、树、花构成春天的美景。诗歌有似一幅写意国画,画面感很强。
废名的诗经常是一气呵成,一节形式居多。在诗歌人物设计和景致描写上,追求瞬间感悟。如《海》一诗:
我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妙善,—
“我将永不爱海了。”
荷花微笑道:
“善男子,
花将长在你的海里。”
诗歌阐释的是人类与物质世界的一种关系。“我”是代表人类,“花”就是物质本体的代指,那么“海”有两重含义,第一次“我将永不爱海了”,是“我”面对池岸中亭亭玉立的荷花而言,第二次荷花对“我”说“善男子,花将长在你的海里”,这里的海非自然中的大海,指的是人类所看到的如海洋一样的内心世界。废名诗歌中的意象常是混沌的,两个“海”并非递进或并列关系,而指向不同的两个范畴。
朱英诞的《早秋》是一首叙事风格的诗,从梧桐叶飘落,捡起梧桐叶夹进书里写起。由并不完美的梧桐叶想起它所在的山水,“山水落于晴意的远处”,如是废名,诗歌到此即止,从自我世界引申到宇宙或人生就立刻结束,而朱英诞还要在比喻中强调诗中的“我”在,强化“我”对描绘现象的体悟:“一帆如蝶而非梦/我爱这一叶之影即是浓阴”。把梧桐叶比作是蝴蝶,用一种物体来印证另一种物体的存在,表达“我”对存在过往的情感。相对而言,朱英诞的诗注重情感的完整性。废名的诗更重说理,并不追求诗意表达的完整,而是类似禅的顿悟。
朱英诞早期的创作中常有由此及彼的联想。如《大觉寺外》,由杏花、罄声而联想到夜航船,“我”在诗中:“我将航到天边”,《想象—赠林庚》“以微语念迢遥迢遥的/与摇着的幸福的手指/招来一个熟悉的地方/为一个暗笑打断了”,从低声说话联想到遥远的地方。《静默中的弛想》从秋风瑟瑟,梧桐积叶而静默,“弛想着丹山”。废名的诗歌常有的是发散式想象,甚至带有非理性的幻觉。如他自己最喜欢的《十二月十九夜》,由“深夜一支灯”,想象为“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由地面想到天上,“星之空是鸟林,”由天上又到人间“是花,是鱼”。“海是夜的镜子”,此海非大海,是内心对世界的成像,因此,他说到“思想是一个美人”,可理解为:美人并非女人,而是使人感到美好的事物。废名的诗歌常常使用诗家爱用的歧义,串起一系列美好的事物,如诗中继续下去的是排比,思想还是“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这些并非具象的意象作为概念,衬出他内心海(世界)中所映出的思想(美好)。这是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因此十二月十九日也是一个充实的夜晚。
二
从朱英诞三十年代的诗歌写作看,他试图在古典和现代诗歌间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只是现在读者所能看到的:三十年代的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诗人用非常流畅的现代汉语写作表达古典诗韵,新月后期诗人用北京土话创作的现代诗在诗坛有过一席之地。在这种历史语境当中,朱英诞的诗歌并未表现出夺人耳目的新鲜感。因此笔者对于朱英诞在新世纪的浮现,可以肯定,在很多读者眼里,会认为他不过就是戴望舒或卞之琳的模仿者,被诗歌史和读者忽略是可能的。无独有偶,在二十年代末,草川未雨写的中国第一部新诗史专著《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中对同为海音社成员的谢采江的诗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弹簧上》是中国明日短歌的标准。而笔者阅读《弹簧上》时,发现作者不过用了冰心式的短句表达汪静之类似的情诗,在当时的诗坛和现在的诗坛都并未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这的确牵涉到诗人诗歌出场时间先后的问题。
我们暂且忽略这重要的时间魔术师,在时间和历史之外再次来探究朱英诞的诗意与废名的差异。
朱英诞的诗是宁静的,与他选择的意象有关。他的诗歌意象来自自然,来自古诗文。他选择的时间意象如“春晓”、“月夜”、“星夜”、“早秋”、“晚秋”,空间意象如“墓园”、“宇宙”、“邮亭”、“西窗”,物件意象如实在的为“草”,“枯树”、“槐花”、“渔火”、“玉簪”,还有虚幻的意象如“梦”、“浪花船”等。
废名的诗有动感,在动感中收获思想。他的意象并不太丰富,喜欢用“灯”、“星”、“炉火”、“日”一类照明性的词语,还喜欢“宇宙”、“上帝”、“人类”、“真理”、“人间”、“海”、 “花”(“莲花”、“荷花”)、“妆台”、“镜子”、“玩具”、“鱼”这类哲学或佛教中常用的特殊用语,“泪”、“尸体”、“垢尘”、“坟墓”一类指代生与死的存在意象。
在三十年代创作黙想类诗的作者有卞之琳、戴望舒、废名、林庚等诗人。在朱英诞的诗中,很多浅尝辄止的意境,就像一次没有完成的谈话。废名的诗在跳跃的思维中往往一次成型。朱英诞有一首《说梦》:
看看行云,出去吧
默诵一篇悼文
青松与白石相对无言
人啊是多么好事
蓝天里雨丝和斜阳舞蹈
一只蝴蝶如负重而飞来
花阴遂作为说梦的场合
夏至日绿叶是更绿一番了
诗中的意象在交织中诉说诗人情感,行云与悼文、青松与白石、雨丝和斜阳等意象充满着生命感悟:死与生,永恒与短暂。行云是指无法把捉的东西,人生似行云流水,然而与人的短暂生命相比,行云是永久的存在。悼文是对逝去人的追忆,它同时又是默诵者的永远的记忆。行云是暗示生命流动变化的意象,而悼文是提醒读者一个人的生命终结,却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的意象。青松白石,为墓地庄严的物象,象征着往生者的人格,也期待生命永存如青松,人格洁白似白石。这些都是人类文化拟定出的意象,“人啊是多么好事”,应该是指向文化延续,使很多物象都有特殊的含义。就因为这样,在“雨丝和斜阳舞蹈”的想象性景象中,“负重而飞来”的蝴蝶是否象征着生命的蜕变,或是文化的负载?一只蝴蝶又暗示着孤独?无疑,“蝴蝶”意象增添历史的厚重感和画面的灵动感,这是诗中唯一活跃的生命,它是蝴蝶,它也是文化,也可以看作是叙事者,或者诗人,一个生命来到一幅画面中,画面整个具有了新的生命力,花阴就成为说梦的场合,绿叶更绿,不仅说夏至日到来的生命的旺盛感,而是在阴与阳,暗与亮的画面中,强调时间的现实感。诗歌中的情感是一贯相同的。在文字上,朱英诞的诗歌没有阅读障碍。在意象设计上,有独到之处。废名的《梦中》只有四句:
梦中我梦见水,
好像我乘着月亮似的,
慢慢我的池里长了许多叶子,
慢慢我看见是一朵莲花。
这是一个浑然的梦幻意境:水、月亮、叶子、莲花,梦中意象的不断幻化,不过是在讲述佛教中的色即空的道理。废名的《渡》也是写梦,同样有更多的理性参入。如第一节:“梦中我梦见我的泪儿最好看,/是一个玩具,/上帝叫他做一只船,/渡于人生之海,/因为他是泪儿,/岸上之人,/你别唤他”。诗歌以泪为船泅渡人生来强化人生生存实为在灾难中度日,在梦中梦见泪好看是因为现实当中泪并不好看,它做虚幻的船,也只能泅渡虚幻的人生,最怕的是梦醒,所以你“别唤它”,不要让他从虚幻当中坠入现实。第二节的最后一句是“你别看他”,加深了诗歌的现实意义,“别看”,那么就是因为它经不起看,经不起人们的推敲,它是虚幻的,又是实在的东西。废名的诗歌更让读者感到诗意的混沌。
朱英诞和废名都喜欢在诗里写宇宙。朱英诞的宇宙是静物画的,从“青灯”和“瓶花”中来,“我爱这一盏雪后的青灯/赞颂它是宇宙的雏形”,“瓶花得之于九月的寒郊/献给你一束美梦/点缀你的宇宙/黄昏温柔的来临”从一个大宇宙到一个小宇宙。他的宇宙还是“我”的。而废名的宇宙构思来自声音:
街上的声音
不是风的声音—
小孩子说是打糖锣的。
风的声音
不是宇宙的声音—
小孩子说是打糖锣的。
小孩子,
风的声音给你做一个玩具吧,
街上的声音是宇宙的声音。
——《街上的声音》
在这首颇有童趣的诗歌中,声音屡次被小孩子说成是打糖锣的,在孩子的世界里只有糖锣,没有风的世界,没有宇宙的概念,而宇宙又是客观存在着的。废名这首诗是从小到大,不断地扩充一个世界,显出孩子可爱的。废名的宇宙是天下的。
三
朱英诞被诗歌研究界所忽略的原因颇多。一是与朱英诞的性格有关。朱英诞幼时朋友何炳棣曾说朱英诞七岁丧母,性格含蓄。[3](P36)最了解他的妻子陈翠芬说“英诞为人耿介,不喜交道,但对知交,诚恳相待”。[4]从朱英诞的诗歌讲解、[5]写作和风格可以看出,他是内心高远,为人低调,诗风内敛。不是一个特别爱与环境直接抗争的人。他的诗歌中一直在表现人与宇宙的和谐,并非冯至《十四行集》中那样描写人与宇宙的合二为一,也不像郭沫若笔下那条不羁的“天狗”,向世界发出“我的我要爆了”的大吼。二是时代强行改变个人命运。四十年代朱英诞在周作人负责北大的时候,由朋友沈启无推荐成为北大助教。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周沈破门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从此与周先生的关系断绝了”。[6](P401)朱英诞两万字左右的传记《梅花依旧》中写到周作人的人生悲剧。可见,朱英诞本来性格温和,目睹周作人遭际,也无意走入江湖,宁愿选择静默,远离喧嚣大众,为自己内心黙写。三是朱英诞离开北京大学之后,经历坎坷,先后在东北、华北工作,因身体有恙,1963年退休。退休后,他转向古典文学研究,这可能是他被新诗界遗忘最大的原因。即便朱英诞三十年代出版过诗集《无题之秋》,自己编订的诗集有《春草集》(1934-1935)、《小园集》(1936)、《深巷集》(1937-1944)、《花下集》(1940-1944)、《夜窗集》等多本,诗歌创作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他应该是现代诗歌创作生命力较长的一位诗人,比他的老师废名、林庚的作品都要多。但因为他远离诗坛,乃至他的子女对他的诗歌认识也来自于他去世之后,[7]可见他的沉默与淡泊有多深。四是朱英诞诗歌创作本身存在个人原因。据林庚所写“他似乎是一个沉默的冥想者,诗中的联想往往也很曲折,有时不易为人所理解”,[8]这也应是朱英诞不为人所知的重要原因。在一个大众狂欢共享的年代,或是只要求写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的时代,朱英诞诗歌中的自然灵性与知识分子隐藏起来的思考无人有耐心去解读,去体会。以上原因,造成了一位勤奋诗人无人理会的结局。
八十年代,批评家的眼光都在关注朦胧诗热潮,或是对归来诗人的赞美,朱英诞没有步入归来诗人的队伍,也非有地下诗人那样振聋发聩之作,他一直安然生活在读者视线之外,继续主流放逐的创作。正因为他只写给自己看,诗歌中没有大众化的情绪,只有内心的苍凉与沉郁:
入夜,当我钻进我的老屋
仿佛葬身空腹
这时候,你说,我是逃避呢
还是想找个地方痛苦?
你说,这中天月色,惨淡的
那两三颗星,岂非鲛人的泪珠?
我不一个感伤主义者,明朝
窗外石榴树盛开着谎话,并静静落下。
——《老屋》
“老屋”是个多义性意象:它既是逃避现实的私人空间,也是让痛苦得以发泄之处。在这里,月色和两三颗星,象征着生存气候,或者人世间寡淡的情感。在这个空腹般的的“老屋”里,也可以说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包括书、人、地点带来的熟悉环境中,怀着一种并非“感伤主义者的信念”等着“盛开着谎话”的石榴花,静静落下。虽然不像食指那样绝望,又那样充满信心“相信未来”,朱英诞诗中的 “我”只是等待“明朝”判断得到进一步证实,没有更多的渴望。
[参考文献]
[1]废名.新诗问答[A].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
[2]废名.妆台及其他[A].废名,朱英诞著.新诗讲稿[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69.
[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6.
[4]陈翠芬.朱英诞生平与创作1913-1983[J].诗评人,2008(9).
[5]笔者另有专论废名与朱英诞的诗歌讲义论文,《高高持着:废名与朱英诞的新诗讲稿比较》,待发.
[6]朱英诞.梅花依旧[A].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01.
[7]朱纹.《诗评人·卷首语》中说到:“父亲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诗评人。我是在他去世之后,阅读他的自传体《梅花依旧》,翻阅他的遗作,又到图书馆查找旧报刊之后,才逐渐认识和了解他的”。《诗评人》2008年总第九期
[8]林庚.冬夜冬花集·跋[A].朱英诞著,陈翠芬选编.冬夜冬花集[C].文津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