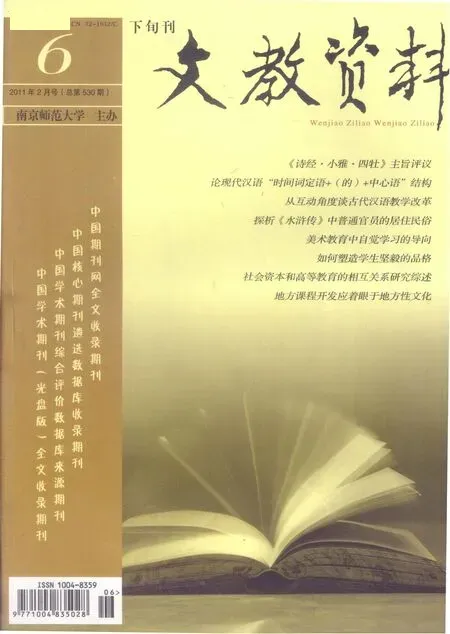以泰戈尔、宗白华为例浅析中西诗歌同源有异
2011-03-20王俭博
王俭博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2)
通过对世界的存在的探讨可知,万物的产生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人更是历史中慢慢演化的结果。人从产生后便开始与自然发生各种关系,有直接的、间接的。人类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实践劳动中开始有意识地积累,并形成固定化的思考模式,当然这个过程是极为漫长的。李泽厚先生在马克思文论的影响下提出“历史积淀说”,并强调人类在具体实践中积累经验,形成观念,加深主体人对客观自然的认识。马克思把人对自然改造和自我创造的过程叫做本质力量对象化。文学创作虽然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却是思想最自由飞翔的天空。作者通过诗歌创作表达其最初的冲动。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将诗歌的源头概括为情感。虽然这在中国和西方都不算是第一次对情感的重视,但却明确了对诗歌的心理上的思考。中国传统文论有“诗言志”、“诗缘情”等说法,西方也有模仿说等相关概念。总之,中西文论都比较认可诗歌是对情感的表达。诗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抒发着自己的情感。虽然中西诗歌在语言上有极大的不同,但我认为语言、文字、修辞技巧等方面的不同是比较潜在的表面的不同。在这方面的区分比较并不能从根本上区分出中西诗歌在情感根源基础上所体现出来的更深层次的差异。在对泰戈尔的《飞鸟集》和宗白华的《流云小诗》进行了反复的研读和联系比较后,我有了一些心得,对中西诗歌情感本原中的差异进行了思考。
中国人的思想深受儒道佛的影响,这些思想融合为中国文化中气、阴阳、五行等观念,使得中国诗歌产生了朦胧的神秘感。在不确定的言语中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任凭感情流淌而勾画意象蓝图。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比较明晰化,更为确定。无论是古希腊时期还是中世纪以后,西方学者都力图用数学模式证明一切现象,或用数学思维考虑一切问题。黑格尔说:“通过辩证逻辑,我们就可以获得有关变化着的现实的恰当观念。”[1]正是在深层中理念不同,中国诗歌显得更为浪漫,西方诗歌相对理性,但都属于哲思。我觉得泰戈尔的诗歌便是理性的诗化,宗白华的诗歌是诗化的理性。
诗人运用语言流淌自己的感情,体现虚实的差异偏好。泰戈尔希望“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虽然这优美的词句中含有翻译者的独具匠心,虽然这词句还不能尽善尽美地再现诗人的本意,但读者们的传诵已经证实了这诗句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事实上宗白华本人也写过一首诗赞扬泰戈尔的诗情画意:“森林中伟大的沉郁,凝成东方的寂静。海洋上无尽的波涛,激成西欧的高蹈。”细细品味会发现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外国诗人在创作时以具体实物的客观属性和特点直接类比人类的相似之处。而中国诗人更注重对意境或境界的追求。宗白华先生曾著《艺境》对意境做了精辟总结,他概括出五种境界,分别为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宗教境界。认为艺术境界介乎学术境界与宗教境界二者中间,是“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的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2]诗人对审美对象进行情感化的描述。西人注重的是形象。中国诗人认为形与象是有区别的。《周易》说:“在天成象,在滴成形。”形是实体,象是虚体。泰戈尔的“夏花”“秋叶”便是“形”;宗白华的“沉郁”、“寂静”、“波涛”、“高蹈”体现的都是虚境。泰戈尔的诗文有的是很简短的,但却表现了深深的哲思,如:“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夜秘密地把花开放了,却让那白日去领受谢词。”“杯中的水是光辉的;海中的水却是黑色的。小理可以用文字来说清楚;大理却只有沉默。”他的诗句中大多都是以鲜明形象为中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内容和情感的。中国早期的哲人早就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思考,也提出了诸如 “立象以尽意”、“得意忘象”、“得意忘言”等观点,事实上都说明了中国诗人对“虚”的偏好,对那种只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形而上的观念世界的眷恋。宗白华在诗中问道:“花儿,你了解我的心么?她低低垂着头,脉脉无语。流水,你识得我的心么?他回眸了几眼,潺潺而去。……”还问道:“恋爱是无声的音乐么?鸟在花间睡了,人在春间醉了,恋爱是无声的音乐么!”虽然同样都体现哲思,都流露情感,但是后者那种人与自然的对话,那种对内心的拷问,那种不存在的比拟,处处为读者营造空灵的虚境,处处建构一种朦胧虚幻的想象空间,在似有非无中体验。比起泰戈尔直接明白晓畅的哲思更多了些诗的味道。
席勒认为诗歌有“朴素”和“感伤”之分,实质上是诗人对诗歌观照方式上的差异。中国诗人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无不体现老庄的“游”的闲适;外国诗人则更多体现一种集中的对“真”的描述。都说诗画不分家,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无言的诗,可见诗画关系紧密,相互显现。宗白华先生说:“中国诗人、画家确是用‘俯仰自得’的精神来欣赏宇宙,而跃入大自然的节奏里去‘游心太玄’。”而且中国诗人陶渊明有诗:“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中国书法家王羲之云:“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其中都体现了中国人“游”的心态。不仅仅在亭、台、楼、阁间游走,更表现为心情的波澜起伏、状态的游离不定。“啊,诗从何处寻?从细雨下,点碎落花声,从微风里,飘来流水音,从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品读宗诗,我们的想象得到极大的跳跃和充分的展望,仿佛在无垠的田中驰骋,也仿佛在广阔的海洋中随波起伏:一会细雨,一会微风,一会落花,一会流水,一会蓝空,一会孤星。这自由的游走,怎能不使人愉悦,怎能不使人神往。而西方的诗画讲究的是真实。或许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模仿说影响过于深远,总之外国诗歌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直观的,可见的,相对真实的。康德曾评价中国绘画怪诞不经,认为画中形象不自然,在世界上什么地方都不会存在。或许中国诗歌在外国人眼中也是这样的吧。泰戈尔的诗文是比较具化的;“跳舞着的流水呀,在你途中的泥沙,要求你的歌声,你的流动呢。你肯挟跛足的泥沙而俱下么?”他的流水、泥沙,如在眼前一般,直接导出了道理,失去了那种于悠然中得真理的轻松。“采着花瓣时,得不到花的美丽。”“当我们以我们的充实为乐时,那么,我们便能很快乐地跟我们的果实分手了。”每一句都相似的深刻,但每一句又有那样不同的感觉体验。一个置身“游”的空间,一个展现“真”的世界。
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语符化,这是苏珊·朗格等人提出的著名的符号说,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诗·大序》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虽然大家都承认诗文语言中蕴含着诗人的情感,但这些丰富的情感是在何种状态下表现呢?泰戈尔的诗显示为意大利克罗齐的直觉,宗白华的诗表现为中国儒家的“诗可以兴”。直觉是不依赖于概念、逻辑和现实的,几乎是无迹可寻;兴是一种内在情感冲动,由外物引发而成。二者虽都是心理情况,但差别甚远。或许是天才观念的根植,或许是神学观念的深入,泰戈尔的诗仿佛是“神来之笔”,而且多次出现“神”的字样,如:“神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神的静默使人的思想成熟而为语言。”“神在他的爱里吻着‘有涯’,而人却吻着‘无涯’。”“神的右手是慈爱的,但是他的左右却可怕。”等诗句的切入点都很难扑捉,似乎在用一个不存在的上帝直接讲述的方式进行心灵对话和情感表达。宗白华的诗讲究境,但却不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他自己说:“诗中的境,仿佛似镜中的花,镜花被戴了玻璃的清影,诗镜涵映了诗人的灵心。”也就是说总要有些直观的参照物来引起诗人的冲动,将诗人的灵心映射出来。陆机说诗人创作时的情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但这情况出现于李白痛饮之后、杜甫感伤之际。杜甫强调“语不惊人死不休”,但贾岛感叹“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见唯有艰苦的积累训练和“触景生情”的外物才能激起诗人的创作欲望。有过文字功力积累的宗白华面对夜晚轻吟:“黑夜的影将去了,人心里的黑夜也将去了!我愿乘着晨光,呼集清醒的灵魂,起来颂扬初生的太阳。”偶然被夜雨惊醒又有如下思绪:“门外夜雨深了,繁华的大城,忽然如睡海底。我披起外衣,到黑夜深深处,看湖上雨点的微光。”可见宗诗的创作不是直觉的产物,是兴致使然。
[1]转引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4页.
[2]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