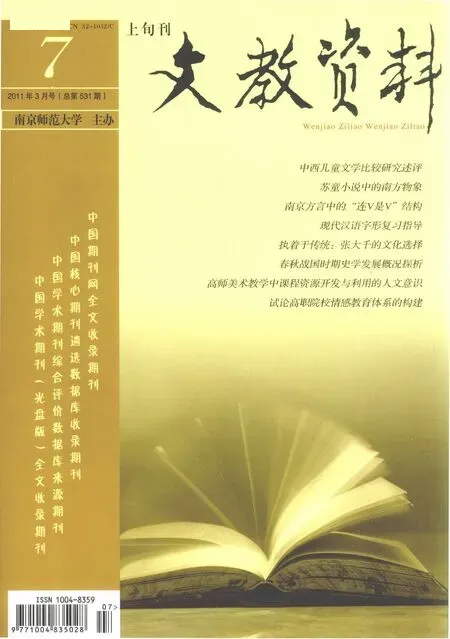革命浪漫主义在左联时期与延安时期的不同之处
2011-03-20李保国
李保国
(江苏省东台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东台 224200)
浪漫主义是基本的文艺创作方法之一,侧重于反映人的主观内心世界,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是“五四”新文学运动者怀着浪漫的情怀和热切的追求向西方借鉴的独抒情怀的创作方法。当“五四”运动的热潮慢慢退去,又耳濡目染了一系列的血腥的悲剧、惨案之后,浪漫主义自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生变异,在1928年由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的革命文学从酝酿开始兴起,因“革命”姿态的融入,浪漫主义焕发出新气质,出现了被称为“革命的罗曼蒂克”的浪漫主义创作潮流。“革命的浪漫蒂克”这一概念,最早在瞿秋白为《地泉》作序时即使用,题目为《革命的浪漫谛克》。此后,“革命的浪漫蒂克”作为专用词组,记录在文学史上。延安时期,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开始创作无产阶级文艺,现实主义位居主位,但从中还透露出一些中国化的革命的浪漫气息。两个时期的浪漫主义有明显差异,下面作简要论述。
一、内在型浪漫主义与外在型浪漫主义
左联时期的“革命的罗曼蒂克”思潮产生于社会政治急剧动荡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中国内忧外困、民生凋敝,懵懂的青年情感的落差极大,压抑与反抗、兴奋与失落、憧憬与幻灭并存。在复杂的情绪驱使下,他们不甘寂寞,文学就成为他们倾诉、宣泄的方式,蒋光慈及时地发出了“革命的罗曼蒂克”的呼声,这种文学还有着“五四”浪漫主义的精神,总是把革命与自我联系起来,抒发了自我内心的感受。“有的凭借文学来抒发革命中身陷战场与情场时个人兴衰际遇所引发的浪漫情思,如洪灵菲;有的藉文学来追摄人生飞扬与安逸两相妨碍、革命与爱情交相碰撞所造成的心灵两伤的‘时尚’图景,如丁玲;有的藉文学来排遣个人因革命而起的颓败意绪,在对革命的深沉感兴中试图救拔自我,如茅盾。当然也有人借文学来驰骋革命的‘乌托邦’想象和‘罗曼蒂克’式空想,如华汉”。可以说左联时期“革命的罗曼蒂克”仍向内在型寻求发展,与抒情小说一脉相连。与之不同的是延安文艺中的浪漫主义只占据很小的空间,在文艺政策的高压干预下,抒一己情怀已不再现实,只能把少有的浪漫情思寄托于外物之上,比如孙犁小说洋溢着从现实出发的具有浪漫主义品格的诗情画意,这种抒情是通过描绘“完美型的女性形象”和“浓淡相宜的优美画卷”而展现出来的,没有呼叫式的呐喊,没有立即投身革命的急切心情,没有夸张与想象,一切情怀都表现的平淡轻柔。
二、彻底的革命意识与被遮蔽的革命意识
二者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革命意识是否显现。左联作家们大都具有双重身份,是作家又是革命家,在创作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用笔为革命助威,表现出对革命极大的热情,所以他们在作品中表现了彻底强烈的革命意识。蒋光慈的革命小说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论为指导,以文学的方式体现了政治革命对思想文化启蒙的取代,这在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文化语境中,毫无疑问地具有一种先锋性、话语领导权。那些压迫与反抗、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正是迎合革命、宣传革命、鼓动革命的需要,因而政治斗争的言说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被重笔书写。蒋光慈不单单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拓荒者,他的一生都在实践他的文学理论,从《少年漂泊者》到《短裤党》、《野祭》、《冲出重围的月亮》,再到《咆哮了的土地》,一切都围绕着革命生发而出。在延安文艺中浪漫只是表现在对革命认识的简单化,对革命的超级乐观的态度,但明显带有革命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品很少,新歌剧、民歌叙事诗中的浪漫气息更为浓厚,其间的革命意识也没有如此浓厚。因为延安地域偏僻,相对比较安宁,并不是作战的主要战场,血与火的斗争很少面对,所以直接描绘敌我冲突、压迫反抗的作品不再是主题,只是一笔而过,而多描写改造农民、农村变革、农民青年爱情、妇女解放的故事,乡间生活气息浓郁。
三、开放式浪漫主义与封闭式浪漫主义
1.从视野上来看。左联时期革命浪漫主义小说的社会画面广阔,视野辽远,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革命宏大叙事的先河,比如华汉的《地泉》三部曲反映了大革命后从农村到城市社会变化,以及农民、知识分子、工人思想激烈的转变,作者的写作视野不断变化。蒋光慈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是对现代革命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初步探索,不可避免地存在有缺陷,但作为当时文学史无前例的文学叙述方式,其功不可没。蒋光慈最后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是其鼎盛之作,纯熟地把广阔革命背景与复杂的、多线索的叙事融为一体。延安文艺中的作品长篇小说很少,并以现实主义方法为指导。而短篇小说革命浪漫色彩浓厚但没有左翼时的大手笔,只把视野局限在农村当地、个别家庭,《芦花荡》《荷花淀》的优美只是发生在河北白洋淀,《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故事仅仅是发生在霞村。
2.从借鉴外国文学上来看。左联革命小说向外国文学借鉴得较多。漂泊主题的小说是吸收西方的 “寻找意义”的叙事方式,主人公总是在寻找一件物,这是西方民间叙事的基本结构,体现出寻找的意义,即寻找个体的存在与革命的契合点。此外,蒋光慈还曾公开宣布“莫斯科变成了我的亲爱的乳娘”,他向苏联文学及理论借鉴的力度最大,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研究了别林斯基的《现代批评之诸问题》,卢纳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基础》、《普列汉诺夫文集》,等等,他的创作深受其影响。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大多是从苏联借鉴而来,比如周扬的文艺主张多继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把文艺当作是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武器,使文艺为现实服务,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但根据文艺政策的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这四种人服务”,又主要强调“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了创造出民众喜爱的作品,只有采用他们熟悉的模式。于是掀起了向传统的、民间的文艺中寻找寄托的高潮,希望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革命的效果。比如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就是在吸收民间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适应表现解放区新的生产与斗争的需要,诗人认真学习民间小调、信天游,以及说唱艺术如鼓书、评弹等的形式、语言、表现手法,王贵和李香香的浪漫爱情故事便由这种民歌叙事诗来讲述。
3.从题材上来看。左联革命浪漫主义小说选材的角度要比延安时期宽广。以丁玲为例,因为在延安时期她是创作小说时浪漫色彩比较浓厚的少数作家中的一位,所以由她的这一时期的创作选材不同可以看到一些信息,《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围绕乡亲们保护小红军来写;《入伍》叙述徐清作为新闻记者,为收集战争材料、亲历一场小战斗的故事;《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我在霞村休养,与贞贞这位被村人误解的女子交往的故事。小事入手选取素材,人物、事件都离不开当时当地的环境。而左联作家创作题材则很宽泛,人物画廊丰富,地域跨度大。洪灵菲写了不同类型人的革命,《流亡》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型的革命者,《在洪流中》表现农民斗争,《气力出卖者》描写工人悲惨的境遇及其斗争,《大海》反映潮汕地区农民运动。再如《鸭绿江上》则把视角伸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下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可见那一时期的题材来源较广,并没有受制于时空的痕迹。
总之,革命浪漫主义是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政治、环境不断整合变异的产物,不同历史时期表现的特点也不一样。尽管在艺术价值、文学美感上各有千秋,但从中可见作家们结合环境在创作上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及他们强烈的、积极的入世意识,这种精神让人感动,并激励后人不断前进。
[1]范伟.革命文学浪漫主义创作潮流论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