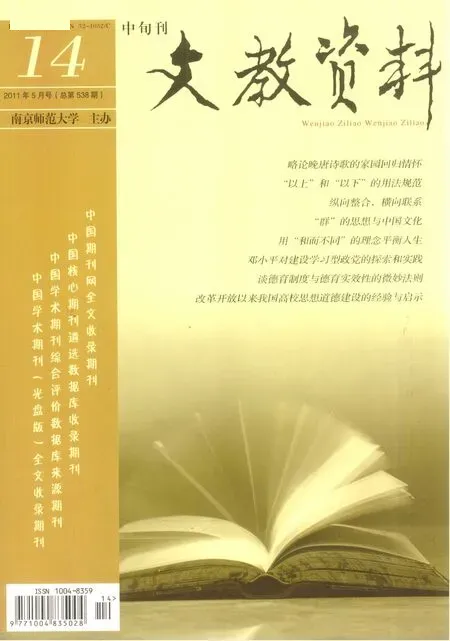吟味温情——论食指诗作中的女性意象
2011-03-20黄永茂
黄永茂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08)
历经人世磨难,饱尝岁月冷暖,深秋的夜晚,谁在凄凉大地上用孩子的笔体写下了“相信未来”?无论是时代的风云巨变,还是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食指对于诗歌和命运的热爱追求,都深深地感动过一代人。多多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说他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1],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也认为他是“文革新诗歌运动第一人”[2],林莽则在《并未被被埋葬的诗人——食指》中写道:“食指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 ”[3]
在食指诗歌里女性意象出现的频率很高,主要可以划分为四种,即一直萦绕在自己心头的母亲,朝夕相处的老伴,勤劳朴素的中国青年女性,以女性手法来描写的乡土。通过这些意象分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异性在诗人的生命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从这四类女性意象来探讨诗人的情感世界。
一、伟大的母亲
母亲的形象始终印记在诗人的心中,生命是母亲给的,生命的意义是母亲植入的。母亲的爱一步一步伴随着诗人的成长而老去,母亲的爱永远是推动诗人向前发展的动力。“妈妈,您的慈祥/是儿心上的太阳//儿时胆怯地迈出第一步/是因为有您在儿的身旁/现已知,道路坎坷漫长/人世间儿却敢阔步闯荡//您做的俭朴的家乡的饭菜/给了儿丰富的精神营养/几十块布缝成的尿布/而不敢造次定终身难忘//您经常吟唱的古文 ‘祭十一郎’//竟叫儿不自觉地合拍击掌/懂得了中国语言的律韵/儿这才步入了艺术的殿堂//妈妈,您的恩泽/是儿头顶的太阳”(《给妈妈》)①。 无论诗人身在何处,无论诗人遇到什么困难,漫漫人生路,诗人带着母亲的希望上下求索。
有人说食指是不幸的,其实诗人是幸运的,他的母亲是一位智慧的母亲,是她让孩子学会阔步闯荡社会的精神,她的《祭十一郎》让诗人知道了什么叫做艺术。食指的母亲原是小学校长,具有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当诗人四岁时,母亲调到平原省图书馆工作,于是便经常跟在母亲的身边,此时的他已经开始识字和背诵中国古典诗词,所以比一般人更早接触到文学艺术。也可以这么说,诗人有如此的诗歌艺术成就,与他的母亲有直接的关系。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这一首诗中,诗人并没有刻意去刻画母亲的形象,但母亲的形象依然跃于纸上。离别的时刻总是多情的,敏感的诗人生动地写出了离别时的悲伤。母亲是“缀扣子的针线”,身上的衣服是用母爱一针一线缝成的,把衣衫披在身上,母爱早已深深地植入诗人的心中。1968年12月20日诗人离开了母亲,到山西杏花村插队,这是诗人在列车上对母亲的依依思恋。此时的诗人就像古代的游子,开始漂泊异乡,诗人是那忽高忽低的“风筝”,而亲情就是妈妈手中的线,诗人把母亲对儿子的思念比喻成妈妈的风筝,用母亲对儿子的爱衬托出儿子对母亲的依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诗人与母亲心灵深处的共鸣。
1972 年,年仅24岁的食指“精神压郁,以烟为食”,在这一年里正在部队服役的他只写了《吹向母亲身边的海风》一诗。假如我们过滤掉诗人的革命情感,显而易见,这首诗也是表达诗人心中“恋母”的诗篇:“在海防战士的怀抱中/祖国的海洋/是多么安宁/母亲看到了/一定高兴”,“去吧,去吧/吹向母亲身边的海风/母亲已经为你/——推开了千山的门户/打开了万家的窗棂”(《吹向母亲身边的海风》)。一个战士,在离家万里的军营里守卫着国家海防,海水的晶莹是母亲的微笑,掠过的海风夹杂着诗人对母亲的款款思念,身在边关,心早已随风潜入到母亲的怀抱。诗人幻想着能够像童年时一样尽情地享受母爱的无尽恩泽,以此逃避当时那个充满了阶级暴力、散发着残酷血腥气的历史时代。
对母亲的牵挂,一直是诗人的痛。母亲的离去,使他一辈子无法忘却。诗人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即通过诗歌来纪念自己的母亲,来抒发自己不敢在母亲面前大声说出的情感。母爱无言,大爱无声,无论诗人是在遥远的他乡,还是身处艰难的境地,都能感受母爱的力量,都能把思念化作一曲赞歌。
二、贤惠的妻子
在食指的诗歌中,关于妻子形象塑造的不多,但是这并不妨碍诗人笔下妻子形象的鲜明性。
细读食指的诗歌,隐隐约约中有着一种忧伤的感觉,在悲剧性的场合下,诗人又带有一种英雄般乐观主义精神,在痛苦边沿又罗曼蒂克地歌唱,让人心醉神迷,诗人的《书简(一)》就是最好的范例。这首诗是为十二月党人被流放时,妻子前来送别而写的,在这一首诗中,妻子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心身痛苦的镇定剂,她支撑着流放的丈夫对未来的信任、对乐观的向往和对真理的追求。这种的妻子形象已经远远超越了生活伴儿和生儿育女的普通妻子的概念。她是诗人夺取敌人阵地的冲锋号,是坦白忠诚的友谊的象征。越是痛苦,妻子的模样越是清晰,她是丈夫活下去的勇气,她美丽的容颜中有着圣洁的心地,“忧郁之神征服了你/我亲爱的妻——/她同样折磨着我/使我不时痛苦的忆起你//为了感谢你/对我爱情的忠贞不渝/愿北去的春风代替我/热烈的吻你,我亲爱的妻”(《书简(一)》)。“在今天看来,它是浪漫、美的艺术诗品,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诗人若他真的写出反常识的诗,他首先就是一个异端,而不是聂鲁达那样的为女人写诗并被热爱的智者”。[4]
“入夜,老伴为我沏好了一杯茶/在床头灯下把纸笔靠枕放好/斜倚在床头上我随意点上一支烟/让思想天马行空般脱缰野跑”(《五十多岁了》)。这里的老伴形象由原来的抽象具体化了,她由原来的精神寄托转化为生活的相依相偎。诗人没有特意去写老伴的动作,也没有为了表达对老伴的感情而宏篇描写,而只是用了两个动词“沏”和“放”就把老伴的贤妻良母的形象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一览无余;在一旁的诗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深深地烙印在心里,此时的温馨场景无需语言互相表达,彼此心照不宣。看似平凡的动作,却包含着无限的爱意,就像舒婷的《致橡树》:“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5]
《家》是食指写给自己五十多岁才有的家的,也是写给夫人寒乐的,全诗25句,写到老伴的只有两句:“老伴忙着用用电热水壶烧开水”,“水开了,老伴为我沏好了茶”。与《五十多岁了》一样,对老伴的刻画言简意赅,而韵味无穷,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白。一杯茶驱走了雪夜的寒冷,有了老伴寒乐的家,不必再为冬天里的寒风瑟瑟发抖,家是港湾。这里的老伴是家的象征,“暖暖的家中品着茶/却分明在听/窗外一阵阵呼啸而过的寒风”,这是对眼前温馨生活的反衬,更是寓喻自己和老伴的人生一路坎坷,寒风已过,如今生活幸福安乐。“‘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品味着诗句,微微睁开双眼/才发觉暖暖淡淡的冬日的阳光/已经悄悄退出了朝南的门窗”(《冬日里阳光——给寒乐》)。
在食指的诗中,老伴是无言的,默默地无微不至地照看着家,时间沉淀下来的感情,也是无法用只言片语来形容的。诗人是明智的,他坚信家是生活的希望,而老伴是这希望的缔造者。清晨离朝霞喷薄很近,离未来的希望却是很远,人生路漫漫,诗人把老伴的“无言”带在身边上下求索,为自己的执着追求添上一抹色彩。
三、别样的女性
食指的诗歌里女性意象很庞大,除了未来与希望、母亲和老伴外,也包括正在建设新中国的杨家川女青年,水库里的铁姑娘,安徽女佣市场里卖母鸡的女佣,倔强调皮的女儿,等等。诗人敏感多情,这些女性意象包含着诗人的复杂的看法。
(一)朴实辛勤的创造者
在食指的诗歌中,有对革命者的讴歌,有对劳动创造者的赞许,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人对保卫和建设祖国的人民都有着由衷的赞美,其中也不乏对女性创造者称赞。在诗人的眼中,这些女性不是深在闺阁娇滴柔弱的形象,而是为建设革命新面貌的朴实辛勤的创造者。
这一类的女性身上焕发出女性的力量美。她们为建设家乡,鼓足干劲,用自己的双手撑起半边天,泪漪涟涟、弱不禁风的传统印象在他们身上找不到痕迹,她们“吹响号角干劲大/擂起战鼓手不酸/去冬苦战乱石岗/斗大的石块双手搬/一鼓作气斗春旱/扁担挑龙上高山”(《杨家川——写给为建设大寨县贡献力量的女青年》),“铁姑娘能/手捻碾碎万仞山/吓退四面/险峰峻岭/姑娘含笑梳妆来/万顷碧波当明镜//铁扇在手/斗酷暑,成竹在胸……”(《红旗渠组歌——铁姑娘(水库)》)。她们身上的这种劳动的自然美,胜过于梳妆打扮,她们身上焕发的力量正在书写青春宣言。“磨破了手掌压肿了肩/撂下轻松挑艰难/杨建川这姑娘腰板硬/日月在肩也敢挑”(《杨家川》),诗人毫不掩饰这种夸张的修饰,从她们身上显现出来的“敢叫日月换新天”“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正是诗人一直讴歌的主流精神。
(二)美丽哀伤的女孩
“饭后她一边收拾碗筷和板凳/一边把剩下的菜汤一口喝净/别笑,要知道这位从灾区/刚刚到北京的安徽女佣/在家连白薯干都吃不上/又怎见得这一点油星//你的宝贝舒适的依偎在她前胸/被她轻轻摇晃着哄入梦境/你可曾想到她亲生的孩子/一样同样可爱的小生命/竟在去年遭灾的情况下/楞这样饿死在她的怀中”(《北京的安徽女佣》),为了生存,她在富裕人家艰难地活着,为了消除饥饿,她吃着别人剩下的残羹剩饭,逃避灾难的命运让她不得不在人家的屋檐下做佣人。她不在乎睡在过道和厨房,只要有过夜的地方就心满意足,她也不会藏着私房钱而是全部寄回家里,家里还有她的丈夫,这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共有特征,朴实善良,容易满足,以夫为天。但是这样的女人同样也难以抚平胸口的创伤,失去孩子永远是她心中的痛,手捧着别人的孩子,心里一直割舍不下在灾难中死在自己怀中的亲生孩子。家是她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她眼中常含着泪水,这泪水中有过对社会的愤怒的控诉,也有过对灾难的恐慌,还有母爱的成分,更有质朴心灵的成分。她是美丽的,美丽中含着忧伤。
在 《在自由市场里》,“看那小姑娘的欢乐的眼神/像以往和大母鸡在做游戏”,“我”用纸币和冷酷转身换回了小姑娘心爱的东西,“我”忽略了她的眼神,也扼杀了她对母鸡的感情,从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大爱,因为“我”的冲动而不顾她眼中的泪水。因为“我”那是不懂得这种质朴的心灵美,所以到如今我始终无法忘记逃避她的目光。
不管是为了生计而外出做工的女佣,还是在市场中依依不舍自己的母鸡的小姑娘,在诗人笔下的这类女性形象,她们的眼中常含着忧伤的泪水,生活的困苦让他们艰辛地活着,为了生存她们付出了生命中最可贵的东西:自由,容颜和自己最喜欢的物品,从她们身上表面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伤痛,但从他们的品质而言,无不散发出质朴的心灵美。
(三)不谙世事的女性
“当你步履轻盈的向我走来/像一枝花蕾在清风中轻轻摇摆/神态得意,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含苞待放不由人暗暗喝彩”,“只有当青春逝去,方如梦清醒/人生的哲理你这才略知一二……”(《致年轻的女孩》)。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她们单纯可爱,青春年少又不谙世事,她们还不理解生命的衰败无常,不懂珍惜青春资本,等到人老珠黄的时候,悔时已晚。诗人从善意的劝诫年轻的女孩们学会爱惜青春、激荡青春,不要让身上质朴的灵魂和青春的魅力随时间的流逝而一起老去。
《晓渡讲》塑造了不谙世事又略带顽皮的女儿形象:“女儿做错事,但拒不认账/气得我对她一通大吵大嚷/可她毫不理会,还一脸倔犟。”女儿的顽皮与父亲对女儿的爱形成了强烈的反比,如对于父亲的谆谆教诲熟视无睹,把父爱当作是一种唠叨。其实这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倔强而又不讲理,当诗人小的时候一样,“这眼神这么熟悉,像哪里见过?/嗨,完全是我年轻时的模样!”同样,当我们还小错事的时候,我们又何尝乖乖地低着头在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教育,只是我们还小,不谙世事,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会明白一切,明白父母的用心良苦。
对于此类的女性塑造,诗人丝毫没有因她们不谙世事而责怪她们,只是用心良苦地奉劝年轻的女孩,不要把青春任意挥霍,要学会感恩。
四、厚德的大地
“她”不仅仅是女性的代表,“她”在食指的诗中更是祖国家乡的象征。
食指的诗歌,和孩子一样,隐藏不住包含在心中的乡土情怀、漂泊的命运,始终不忘自己扎在老北京的根,日思夜想、魂牵梦萦,“根”是诗人生命和精神的归属寄托。当诗人离开这片土到杏花村时,带走了母亲的泪水,同时也带走了对家乡的依依离愁,“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食指是离家的游子,是自然的赤子,为什么诗人的眼睛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地深沉”。乡土是食指的生命初始,祖国的这片广袤的土地哺养着诗人长大;乡土是诗人艺术勾勒的轮廓,万里河山为诗人的诗歌增添了色彩。“我已把身心全部/都交给了母亲大地”(《田间休息》),可以想象出诗人对这片大地执着的迷恋,深沉的热爱,要把身心与母亲大地融为一体。
诗人对这片热土的称颂,不是随意感性的,他在抒发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往往是经过理智的思考的。对于处于“文革”中的这片狂热的土地,诗人依旧寄予无限的希望,而不带有一点点怀疑的态度,“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的人们——/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相信未来》)。顾城在《一代人》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那风雨漂泊的年代里,食指同样把自己的诗魂化作燃烧的热血,激流的泪水,寻找着希望的印记,呼唤着爱的回音。
诗是诗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诗人个人命运的沉浮,依旧阻挡不了他对乡土的情感,“我爱难以驯服的江河/想我多年对命运的反抗/更爱欢快清澈的小溪/她使我回味童年的时光”(《我爱之一》)。在这片土地上,有着太多的美好回忆,童年的时光是诗人一辈子无法忘却的记忆,与其说是对孩童时代的追缅,不如说是对重温这片乡土的款款情怀。
在人们的眼中,食指对爱与希望的歌颂,对未来的向往,一直在悲凉的诗歌中闪耀着。我们从食指诗歌女性形象中,可以看出他对未来的追求没有松懈,对母亲的思念与日俱增,对无言的老伴的爱深深地藏在心中,对年轻的女性大声地歌颂,对乡土深沉的爱,都是带着真诚的眼光。
注 释:
①本文中所有选自食指的诗均选自:食指.食指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7.
[1]多多.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J].开拓,1988:(3).
[2]杨健.文革新诗歌运动第一人[M].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90.
[3]林莽.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J].诗探索,1994:(2).
[4]葛艳丽.催生爱与希望的不屈歌者[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4).
[5]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