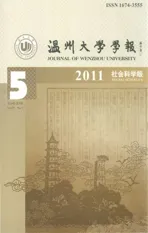清代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生态变迁
2011-03-19颜晓红
颜晓红
(浙江农林大学人文学院,浙江临安 311300)
清代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生态变迁
颜晓红
(浙江农林大学人文学院,浙江临安 311300)
清代浙江山区涌入大量外地人口,他们开山种地、做工经商,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等多种经营活动,成为山区资源开发的主力,为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和商品化的特征,但这种开发也导致了当地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清代;浙江山区;经济开发;生态变迁
清代是传统农业大规模扩张的最后阶段。在此阶段,由于各区域地理条件、农业发展的历史基础等社会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开发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变迁也呈现新的历史态势。浙江山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陈桥驿: 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J]. 中国社会科学, 1983, (4): 207-217.吕锡生. 明清时期畲族对浙南山区的开发[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2, (2): 90-91. 刘秀生. 清代闽浙赣的棚民经济[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8, (1): 53-60. 郭润涛. 钱塘江流域山区与平原产业结构的比较[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 (2): 31-42. 朱自振. 明清东南山区农业的商品化发展与特点[J]. 中国农史, 1993, (4): 27-37.张祥稳, 惠富平. 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其遏止措施[J]. 中国农史, 2006, (3): 13-21.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第六卷[M].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叶建华. 浙江通史: 第八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张建民. 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 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尤其是张建民先生提出的许多观点, 如流移人口的流移特性与山区开发、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的关系, 外地商人控制山内商品生产及其消极影响等等, 使笔者深受启发和教益.的基础上,对清代浙江山区资源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作一综合论述。
一、清代浙江山区经济开发的主要动因
浙江山区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即由仙霞岭山脉、洞宫山脉、雁荡山脉和括苍山脉组成的浙南山区;由白际山脉、昱岭山脉和千里岗山脉组成的浙西山区;以及位于宁绍平原以南、括苍山以北,包括会稽山脉、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的浙东山区。历史上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时常受到干扰,如清初“三藩之乱”期间,浙南山区“独衢之江、常、开三县,温之永、瑞等五县,处之云、龙等七县被陷三载,仳离困苦,备极颠连。……自闽回处,惟见百里无人,十里无烟”[1]157。而各亚区之间的开发程度也很不平衡。浙西山区,由于地理条件相对较好,梯田早在宋代就相当普遍,垦殖系数较高,人口密集。至清初,浙西山区只有山地陡坡尚未开垦。而浙南山区,晚至清末,尚未充分开发。“环治皆崇山峻岭旷土邃谷,可垦之土所在皆是,故患民不为农,不患农无可耕”[1]889。明代全省人口主要集中于浙江北部平原地区,诸如湖州、嘉兴、绍兴、杭州和宁波诸府,而严州、处州、金华、衢州和温州等山区诸府,人口就要稀少得多。至清前期浙江山区人口依然稀少,人口密度远低于平原地区[2]。而人口的多寡历来是中国古代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系数之一。
但是,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固以及一系列积极有效措施的推行,国内人口开始迅速增长。浙江周边之江西、福建、广东、安徽和两湖等地成为清代著名的人口输出地,尚有潜在可耕地资源的浙江山区开始吸引本省及周边地区的大量过剩人口。户部尚书张廷玉上折说,“查浙江之衢州等府、江西之广信等府,皆与福建连界,江西之赣州等府又与广东界”,“闽广无籍之徒、流移失业者”遂来此垦山种麻,搭棚居住[3]。
如浙西山区,“杭州府属之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昌化等县为嘉兴湖之上游;湖州府属之乌程、归安、德清、安吉、孝丰、武康、长兴等县为苏松之上游,皆系山县……三十年前从无开垦,嗣有江苏之徐(州)、淮(安)民,安徽之安庆民,浙江之温(州)、台(州)来杭湖两属之各县,棚居山中”①[清]王延熙, 王树敏.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M]. 清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 上海: 久敬斋.。而在浙南山区,各府州县亦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口。如处州府云和县,“工匠杂伎土著绝稀,业此者多外籍人,故流移转徙者比比而是”[1]898。青田县,“旧日土旷人稀,外民多聚于此。种麻者多江西人,栽菁者多福建人,砍柴者多广东人,烧炭者多仙居人,永嘉、平阳、龙泉、金华和东阳亦间有寄居者”②[清]雷铣, 王棻. 光绪青田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65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康熙、雍正年间,该县招抚开垦的人口中,外籍移民几占全县人口的一半。宣平县,“闽人居其七”③[清]陈加儒, 雷育仁. 乾隆宣平县志[M]. 乾隆十八年刊本.。龙泉县,“侨居者什之五六”[1]896。金华、衢州两府在明代即有福建人迁入。入清,闽籍棚民日众,经常闹事。至康熙、雍正年间,来自江西、福建和安徽等地的种麻棚民在龙游、常山和开化等县,人数甚至超过土著居民,以致当地居民十分担心移民“反客为主”[4]931。
太平天国战乱虽然使地处僻远的浙江山区也受到严重波及,但在地方官员的招抚政策下,浙江山区很快吸引了大量的省内外过剩人口流入。如杭州府於潜县,“寇平后,田亩荒芜,公私灰烬,荆棘满地,无异洪荒。……不得已有招垦之举。……於是渐有客民自江西、安徽、福建及浙东诸郡来者,……居民既多客户,土著不过十之二”[5]136。金华府兰溪县,“咸同之间历洪杨大劫,民人存者仅十之三四,田地多温台客民垦种”[6]。
人口的自然增长及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浙江山区人口激增,从而为山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裕的劳动力资源。
二、浙江山区经济开发的多样性和商品化的特征
前来浙江山区的外来人口,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雍正初年浙江官员曾报告说:“查棚民多系福建、江西之人,在各处山乡租地搭棚居住垦作者,皆以种麻、种菁、栽烟、烧炭、造纸张、作香菇等务为业”[7]。可见,浙江山区的经济开发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和商品化的特征。
一是租垦土地,广泛种植和经营杂粮、经济作物、经济林及特产。浙江早在明代中期已引种番薯、玉米等类杂粮作物,因杂粮作物高产耐旱,对土质要求不高,至清代中后期得到广泛种植,成为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如严州府各州县,“向无此种(玉米)”,“乾隆间,江、闽游民入境,租山刨种”①[清]陈常铧, 冯圻. 光绪分水县志[M]. 光绪三十二年刻本.,于是玉米迅速传播开来。处州府,“山居之民多种苞米,夏种冬收可作正粮”[8]129。温州府,“(番薯)五邑俱有,玉环更饶,凶年可为粮”②[清]李琬, 齐召南. 乾隆温州府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65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苎麻、蓝靛则是山区流民广泛种植和经营的商品性农作物,许多山民以此为业。如宣平县,“清光绪以前种靛为出产大宗,次则莲子、菸叶、苎麻”[8]135,“麻始于江右人,靛始于闽人。江闽人居宣者十之七,利尽归焉。今土著亦种靛”[8]129。丽水县,“苎麻,初鲜种者,乾隆间江右人来种之,今渐广”,“靛,……闽人始来种之,俱在山,今渐种于田矣”[9]。缙云县,山民种靛,“资以为利”[10]。在安吉、长兴、遂昌、景宁、青田、乐清、汤溪、泰顺和奉化等县,山民植麻种靛也很普遍。
烟草、乌桕、漆树、杉木、竹、笋、耳菌类和蜡类等农林产品的种植也是山民的重要经济活动。如烟草获利丰厚,杭州各县,“今土人多种此(烟草)为业”[11]2345。乌桕是制作白油、青油的原料,一次种植,可为子孙数世之利,且不占良田,故清代浙江杭、湖、严等地区的农民多以种植乌桕为业。如富阳县乌桕树种植为当地“土产之大宗”③[清]龚嘉俊, 李木客. 光绪杭州府志[M]. 民国十四年排印本.。在临安、分水和於潜等地,桕籽成为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林木种植费多利重,浙江山区“民间惟栽杉木为生”。如淳安县,“当杉利盛时,岁不下十万,以故户鲜逋赋”[11]2445。於潜县,松木培养成材后,“用舩装至省会,乡人籍以觅利者为多”[5]312。漆,“获利颇厚,乾嘉以后,栽种者渐多”[12]。开化、淳安、安吉、长兴、武康和昌化等地皆有种植。竹、笋亦是山区居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余杭县,“土瘠山多,养竹资生”[13]。武康县,“西南所产(竹)为盛,利过蚕桑,其息间岁一收”④[清]疏筤. 道光武康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29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於潜县,“嘉前嘉后二乡所出(竹笋)颇多,初夏时,贩鬻于嘉苏以千百计,谋生之资不为无助”[5]312。此外,松阳县的药材,庆元县、景宁县的蕈业,汤溪、松阳和龙泉等地之团腊类特产的种植培育,皆颇多赢利。
二是充分利用山区资源,从事筑窑烧炭、砍竹造纸、烧制砖瓦和开挖矿山等带有显著山区特色的手工业活动。浙江各山区县产竹地区均有纸厂,而尤以杭州府的富阳,衢州府的江山、常山、开化和龙游等地造纸业最为发达,成为当时造纸业的重要基地。如富阳县所产纸在浙江各郡邑中为最良,“邑人率造纸为业,老小勤作,昼夜不休”[11]2281。衢州府,民多“以造纸为业”,那里生产的纸张品种繁多,“大小、厚薄、名色甚众”[11]2450,河南、福建等地的生活用纸及官府用纸大多到衢州购买。龙游县溪口村则是纸类贸易中心,其村之繁盛倍于城市,而该县南乡居民全赖造纸为生,其所以培养竹山者,专为腌料做纸,故当地官府多次下令禁止外地人盗伐竹笋[14]612。此外,温州、湖州各山区县生产的纸也比较有名。
浙江山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故清代浙江山区矿业、冶炼业颇为发达。如上虞县产铁,其“南乡多铁厂,棚民之寄居者业此”⑤[清]储家藻.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42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松阳县的铁与硝磺“向来销流甚广”[15]。雍正《浙江通志·物产七》还对“五金之矿”的开采和冶炼作了详细的记载。浙江窑业则分为陶窑、灰窑和炭窑,杭州的钱塘、仁和、富阳和余杭都有造砖瓦的窑穴和烧石灰的灰窑,如富阳人除造纸外,“又有烧炭炼灰造砖等务,运土焙火,不辞辛苦”[16]。尤其是钱塘的瓶窑由于陶窑业的发展而由村发展成镇,陶穴和陶制品市场相望如栉比。湖州府各县也有陶业,但以安吉、武康和孝丰等县的炭窑业最出名,这些地方生产的陶制品除供应人们日常取暖、烧饭等所需外,还满足育蚕之需,质好价低,贩卖者络绎不绝[17]。
三是沟通有无,甚而直接介入山林特产资源开发,控制生产过程,促进了山区内外经济的流动与交换,加速了当地城乡商品经济和地方性小市场的发展。浙江山区土著从事手工业、商业者甚少,间或有之,亦多不及外乡人,故工商业“悉资外籍”、“率多异乡”之类的记载在地方志中比比皆是。如於潜县,“邑中造作,率多异乡工匠”[5]132。景宁县,“商贾之业,邑人鲜谙,……其负贩贸易,大率皆羁寄人也”[18]451。汤溪县,“工,土著亦有,然多劣作”,“缘习最重农,不喜牵牛服贾以走四方,故商业迄未发达”①丁燮, 戴鸿熙. 民国汤溪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52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因此,客商资本在浙省各山区资源开发和货物流通过程中更具重要性,“至商业一道,素操纵于外帮若闽、若赣、若徽、若绍,率占其大部分”[19]730。如龙游县,“其稍大之商业皆徽州、绍兴、宁波占之”[14]43。山林特产之利也多为客商攫取,如衢、严和处州等府,贩卖木材获利颇厚,但当地山民无力将杉木运出山发卖,只能卖给资本雄厚的客商开采[11]2445。其中徽商的木材采购点扩大到严州、衢州、处州等浙西和浙南山区。清中后期,浙北地区的木材市场几为徽商垄断。
外地商人还通过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介入、控制浙江山区的商品生产。那些迁往浙江山区的移民,多来自福建、广东和江西等地,皆有种植、经营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作物、经济林及特产的传统,而山区兴盛一时的木厂、炭厂和纸厂等,亦多有外地商人介入或直接开办。如建德城西有煤矿一处,即为光绪五年徽商叶仲俊开办②夏日璈, 王韧. 民国建德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9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衢县之石室埠煤矿,道光年间计有矿工千余人,日产煤数百吨,后因矿工肇祸而封闭。光绪年间又由“杭绍商人单某等合赀,禀请藩司立案,承开此矿”[19]776。这些活跃在浙江山区的徽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和宁绍商等地域商人,其经营范围广泛,涉及木材业、茶业、靛业、窑业、矿业、漆业、纸业、麻业和糖业等等,促进了山区内外人员、物产、资金和信息等的流动和交换,推动了山区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性贸易中心的形成。如景宁县的香蕈销售,“曩时皆于江右闽广,今更远在川陕楚襄间”[18]453。武康县的三桥埠是竹木集散地,而上柏镇则是浙西竹木山货的集散市场③[清]刘守成. 乾隆武康县志[M]. 乾隆十二年重修刊本.。
三、浙江山区经济开发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清代浙江山区资源开发主要以外来移民为主体,以养活诸多增长的人口为目的,兼受山区运输条件限制,土地资源开发无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特征和过度搜刮的倾向。此种开发模式必然导致浙江山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平衡越来越脆弱。
一是浙江山区玉米、番薯等作物的广泛种植所引起的生态环境的失衡。当时人已认识到“苞谷苗壮根长,沙土易于掀松”,会加剧雨期山土的流失,并直接影响到下游农田水利事业的维护。如嘉庆、道光时人潘瑗在其《南湖水利论》中明确指出:要根本解决南湖水利淤积问题,必须禁止乱垦山地。但是,外来人口大多没有“占籍为民”,其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使得他们在经营上往往不作长远计划,“食尽一山移一山”,耗尽地力后再迁徙别处。这种落后的游耕方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具有粗放的、掠夺的性质,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故有清一代,关于种植玉米、番薯等作物引起水土流失、淤塞河道、淹没田庐和为害农田水利的记载比比皆是。
二是浙江山区冶炼、采矿、造纸及烧制砖瓦、石灰、硫磺等手工业发展所引起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灾害。据光绪《遂昌县志》卷二《艺文辑存》描述,当地冶铁业对生态环境破坏极严重:“朝淘万斤铁,骸骨盈中途。暮铸万斤铁,千山尽焦枯。塚墓既被掘,地脉亦劚锄。乱石塞溪涧,泥沙填通衢。一旦山涨发,遂以坏田庐。往者遘水患,村舍成陂湖。”[20]660又如窑业,“窑户取泥处,久必成渠”,以致陷人田地,伤人坟墓[4]931,716。如余杭县,“颇闻数十年来,仇山开採石灰,近处墓宅咸受其凶”[13]。景宁县,“诸窑之取土伐岩,不无虞於崩洩,执业者当择幽僻闲旷之所为之,以无碍於田园庐墓”[18]290。
三是客商资本介入与控制浙江山区资源开发而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外地客商前来投资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以“淘金”为目的开发,往往层次低、程度浅,无法带动山区内更多加工业的发展,投资所获厚利也尽归客商,流往山外。当有限的资源或较易得到的资源消耗殆尽时,客商纷纷撤资停厂,山区手工业也就很快萧条下去。如遂昌县原有四座坑冶,今俱废[20]72。江山县,“兵燹后,各商皆复业,独业煤者因洞老山荒产汞未旺,至今停采”[21]。不仅如此,这种浅层次的、以纯粹耗费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唯一方式的开发活动,尤其是木厂、铁厂及薪炭业等,还给山区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常山县,“柴炭息倍称而木牙招致远商,构贫民奸利盗取,山几尽童”[4]931。於潜县,“邑中大半取食于山”,“自昔蔚若邓林,迩来亦稍零落矣”[11]312。
四、结 语
整个清代,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进入浙江山区,不仅缓和了周边省份人地紧张的压力,而且促进了浙江山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繁荣。然而,单纯的量的增长并不是山区开发的全部,由于不能遵循生态经济平衡的原则,盲目开发、过度利用的结果是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的破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想缓解人地矛盾,又想保护生态环境,两者做得同样好,是不太可能的。
清代浙江山区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在现今许多山区尤其是边远山区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尚多有存在。如何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开发现有山区资源时,做到既发挥其潜在优势,尽快摆脱山区贫困状况,又避免盲目开发,浪费甚至破坏山区自然资源,注意经济效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这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清]潘绍诒. 光绪处州府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63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2] 叶建华. 浙江通史: 第八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113-116.
[3]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篇: 第2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523-524.
[4] [清]李瑞钟, 朱昌泰. 光绪常山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56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5] [清]罗柏麓, 周树美. 光绪於潜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10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6] [清]秦簧, 邵秉经, 唐亚森. 光绪兰溪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52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511.
[7] 台北故宫博物院.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第八辑[M]. 台北: 台北故宫博物院, 1978: 2.
[8] 何横, 张高. 民国宣平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65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9] 李钟岳, 李郁芬, 孙寿芝. 民国丽水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61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726.
[10] [清]何乃容, 葛华, 潘树棠. 光绪缙云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66册. 上海:上海书店, 1993: 529.
[11] [清]嵇曾筠, 李卫, 沈翼机, 等. 雍正浙江通志: 第5册[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2] [清]徐名立, 潘绍诠, 潘树棠. 光绪开化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54册. 上海:上海书店, 1993: 645.
[13] [清]张吉安, 朱文藻. 嘉庆余杭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5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727.
[14] 余绍宋. 民国龙游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57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15] 吕耀钤, 高焕然. 民国松阳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67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347.
[16] [清]汪文炳, 蒋敬时. 光绪富阳县志[C]//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6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303.
[17] [清]宗源瀚, 敦式昌, 周学濬, 等. 同治湖州府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24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629.
[18] [清]周杰, 严用光, 叶笃贞. 同治景宁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64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19] 郑永禧. 民国衢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56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20] [清]胡寿海, 史恩伟, 褚成允. 光绪遂昌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68册. 上海:上海书店, 1993.
[21] [清]王彬. 同治江山县志[C] // 王海浩.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第59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248.
Zhejiang Mountain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Ecological Changes in the Qing Dynasty
YAN Xiao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Lin’an, China 311300)
In the Qing Dynasty, many immigrants swarmed into Zhejiang mountain areas. They reclaimed mountain lands, embarked on manual work and ran business. Their activities got involved in agriculture, handicrafts and commerce. They became the main force in developing resources in mountain areas and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Diversific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could b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Zhejiang mountain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ivities, which could also partly cause the gradual deteriora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ing Dynasty; Zhejiang Mountain A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hange
(编辑:朱青海)
K249
A
1674-3555(2011)05-0083-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5.01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09-22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070394);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B09LS08)
颜晓红(1974– ),女,江西九江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明清社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