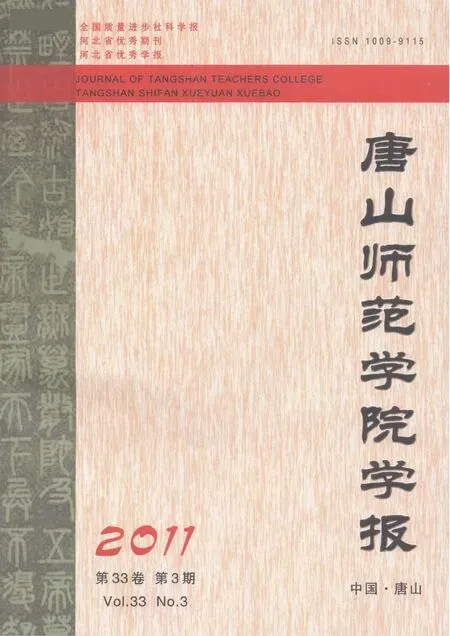唯物史观中劳动分工的哲学意蕴
2011-03-18杨长安
杨长安
(陇东学院 政治理论教学部,甘肃 庆阳 745000)
唯物史观中劳动分工的哲学意蕴
杨长安
(陇东学院 政治理论教学部,甘肃 庆阳 745000)
分工是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与古典经济学家存在着维度和旨趣上的差异,阐释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不仅有助于理解其深层次的涵义,展示其独有的视域,也有助于对马克思早期其他思想的研究和理解。
分工;异化;私有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分工作为经济学范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然而分工并不是经济生活所特有的,它在诸多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思说过:“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p35]较早对分工进行详细论述的,是斯密、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而马克思的分工思想则直接渊源于对斯密等人分工学说的批判和继承。
一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交换倾向和互相买卖产品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生产能力,人类正是由于“分工”才能通过交换彼此的产品更好的生存,才能有助于“类的优势和共同的方便”。
让·巴·萨伊在其《论政治经济学》中指出:“交换虽然不是基本的东西,但在我们的进步的社会状态下是不可缺少的。分工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分工可以增加社会产品、社会威力和社会享受……”
斯卡尔培克在其《社会财富的理论》中也指出:“人生来就有的力量:他的智力和他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而来源于社会状态的力量,则在于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在于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那些构成生活资料的产品的能力……排他性的私有财产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换所不可缺少的,交换和分工是相互制约的……”
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里把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可以促进生产的丰富,决定着产品的大量生产而且是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所以他认为分配给每个人的操作范围也必须尽可能地小。分工和使用机器也决定着财富从而决定着产品的大量生产,这是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
古典经济学家对分工和分工的出现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分工的出现是人类自然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有助于资本的积累。他们还认为只有自由放任的私有财产,才能创造出最有利的和无所不包的分工。而马克思的分工思想则与他们存在着维度和旨趣上的差异。
二
面对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马克思用历史的眼光将分工的发生和发展置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分工的状况与该阶段的所有制状况是紧密相联的,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1,p25]为论证此观点他提出了三种所有制形式。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n)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在这个阶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但私有制已发展起来。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后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充分发展。
第三种形式则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在农业中,分工因土地的小块耕作而受到阻碍,在工业中,各种手工业内部却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种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非常少的。
如果说斯密等人对分工缺乏历史性维度考察的话,那么马克思则侧重于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来论述分工,同时,他试图从“分工”入手来理解社会发展之谜。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对分工和分工的出现持肯定态度,他们看到更多的是分工的积极作用的话,马克思则看到的还不止是这些,他还看到了分工的另一面,他把分工、异化、私有制和国家联系了起来,进行深入的剖析,这正是马克思分工思想的特质,所以,马克思的分工思想还与古典经济学家存在着另外的不同——旨趣上的差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指出:“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工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2,p148]马克思还说,“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p37],而在私有制下,人的劳动已经异化,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本身、自己的类本质,还有工人与工人之间都处于异化之中。而分工和交换又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那么要消灭异化、消除私有财产也就必须消灭分工和交换,因为“分工是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不过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不过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的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2,p144]。可见,分工作为一种在异化范围内劳动社会性的表现,与异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有的学者就认为,私有财产是自发分工的产物,它处于劳动积累的必然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分工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认为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可见,分工只要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任何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特殊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受分工制约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就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1,p38]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提出消灭分工的思想,“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消灭分工”[1,p36]。
马克思还指出,分工的出现使社会关系共同体成为虚幻的共同体,导致了国家的出现,“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是建立在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的”[1,p37-38]。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对个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物的必然性和外在的联系,而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就必须代之以“真实的共同体”,而这只有通过消灭自发分工的办法才能实现,使个人向着完善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成为现实,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并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了竞争、分工等经济现实,指出它们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产物,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对抗性。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3,p139]在蒲鲁东看来,分工也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而马克思指出:“经济学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3,p143]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马克思据此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不但从社会关系层面分析了分工的弊端,同时,还敏锐地注意到了分工对个人的影响。就像他指出的“现在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3,p171]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引用了勒蒙泰《疯狂与理性》里的一段话,“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活动领域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的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
三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并且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p37]这段话经常被人当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图景的设想,并同如何看待人的未来分工问题联系在一起讨论。有人照本宣科,认为分工将被消灭,人想怎样就怎样,并且说马克思也提出了消灭分工的思想,其实,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涉及到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分工思想。
1. 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分工,是针对斯密等人的经济学分工思想的,斯密等人通过论述分工来为当时生产的私有制辩护,把分工视为资本主义私有关系的永恒规律,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而且只注重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各种生产活动的专门化分工,对分工所导致的人的,特别是劳动者的处境则没有予以关注,就像马克思说的“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2,p148]。“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3,p156]
2. 马克思所批判的分工,实际是对当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层物质生产关系的深刻批判,私有制下形成的工人分工,没给工人带来肉体和精神上的享受,而却让工人进入了异化状态,使工人变得越来越畸形,越来越片面,越来越成为生产过程中一个毫无生机的零件。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分工只能是“造就了工人,贬低了人”[4,p236]。
3. 物质生产活动包括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可理解为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理解为生产关系),而分工就是这两层关系的集中体现,人与物关系意义上的分工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提高的表现,马克思并不反对人与物关系层面上的分工,也就是说不反对生产力层面上的分工,相反,倒是对此进行了充分肯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p24]他还认为“分工是先前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1,p53]。而马克思真正所批判的,是由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强制自发分工所导致的异化,这种异化既有经济方面的异化,如异化劳动,还有政治社会关系上的异化,如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是一种桎梏的“虚幻的共同体”。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1,p77]而异化和工人的畸形等现象均属于此。
马克思早期的分工思想是一个很丰富的体系,马克思不仅充分肯定分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更注重私有制下的分工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特别是生产关系上的缺陷性(如异化、人的畸形和片面),并以毕生的精力探索解决的途径。同时,分工还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可以说,马克思所批判的诸多与分工有联系的现象,都内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张力。马克思把分工、异化、私有制联系起来,也就是对这层张力的深刻分析和批判,这也正是早期马克思分工思想的独有视域。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Materialism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YANG Chang-an
(Department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Teaching,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745000, China)
The division of labor w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Marx philosophy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Marx's thought on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lassical economist on the dimension and the intention. Explanations on Marx's thought of division of labor, not only helped to understand its deep implication and to demonstrate its unique point of view, but also helped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Marx’s other thought in he early period.
division of labor; alienation; private ownership; human's freedom full scale development
2010-11-23
杨长安(1975-)男,甘肃宁县人,硕士,陇东学院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B032
A
1009-9115(2011)03-009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