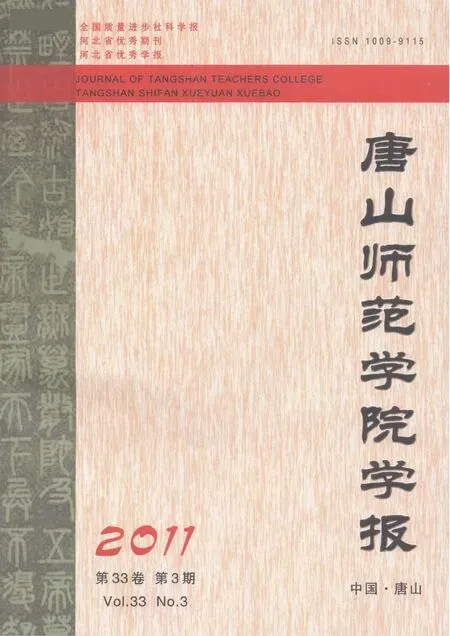从马化龙的历史际遇透析宣化岗宗教符号意义
2011-03-18张嘉倪
张嘉倪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从马化龙的历史际遇透析宣化岗宗教符号意义
张嘉倪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宣化岗是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教活动圣地,它的兴建与埋葬于此的第五代教主马化龙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背负“教主”和“贼首”双重身份的马化龙的历史际遇是伊斯兰宗教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场深刻互动,而正因马元章秘葬马化龙于宣化岗,并且据地复教,从此宣化岗便被赋予了独有的宗教符号意义。
宣化岗;马化龙;陕甘回民起义;左宗棠
宣化岗又称北山拱北,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北查家湾村,此拱北内有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第五代教主马化龙、第六代教主马进成、第七代教主马元章及其三弟马元超等宗教领袖的陵墓[1],并且是该教派讲经传道、复兴哲合忍耶门派之地,因此深受该派教徒的膜拜。
作为重要的宗教场所,宣化岗曾引起宗教及社会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多侧重于对其宗教地位及社会影响的探讨,但是对其兴建历史渊源中所反映的宗教与社会互动探讨不够详尽。
本文试图以埋葬于宣化岗的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先辈马化龙的历史际遇为线,结合档案文献记载、古迹碑刻以及个人实地考察所得资料,重新梳理与宣化岗有关的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及变革信息,以此探讨其所代表的宗教符号价值和意义。
一、马化龙与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
光绪十五年(1898年)马元章为先前秘密埋葬于张家川县北山的马化龙修建八卦圆顶拱北,自此“重宣教化振旧业”据地复教[2],这一举措凸显了马化龙在哲合忍耶教派中的地位和影响。然而这样一位宗教界领袖为何而殁,又为何要秘密埋葬?将他埋葬于宣化岗又和哲合忍耶教派的复兴有何历史渊源?我们不妨从马化龙所经历过的那段晚清西北回民起义中去探究这些问题。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渭南回汉械斗,回族杀陕西汉族团练大臣张芾,震怒清廷,其间又有陕西回民“布散传贴,且称奉上司檄,官兵刻期歼除回头,各庄回民闻而惊怖,群往附焉”[3,p109],从此揭开了晚清陕甘回民起义的序幕。继而“甘肃自宁夏发难,蹬而兴者,马化漋(龙)反灵州、马彦龙、马占鳌反河州、马桂源反西宁、马文禄反肃州……甘境之靖着,盖十无二三”[3,p107]。由此可见这场回民起义波及范围之广,而因械斗之事发展成为几乎席卷整个西北的回民反清起义,并不属偶然。
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人口数量已有相当规模,西北地区尤为聚集,然而以传统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形态决定了土地占有为生存之本,这对可耕土地资源原本就贫瘠的西北地区更显重要,因此,由于回汉人口数量比例的消长而导致的回汉土地占有利益冲突时而发生。同时,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生活习俗,西北回民逐渐形成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之势,而伊斯兰教信徒同汉族完全迥异的信仰和生活习俗使回汉杂处时必然产生诸多情感纠纷和隔阂。在清代时,回汉之间“往往有因极微之误会而使双方有感情之不融洽,于是一部分朝臣每因私怨,而妄指教徒为匪,挑拨离间,使朝廷未能深明回教之教义”[4,p115],于是回汉民族之间发生的利益、情感冲突往往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掌权者肆意夸大渲染,甚至被污蔑为叛乱而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
此时中国境内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体系也有所发展,传统老教之外又衍生出诸多新的教派及门宦,随之也产生了诸多教派之争。清政府为了抑制和分化伊斯兰教,“坚持‘扶此抑彼’和‘抚一剿一’的反动民族政策,终于迫使少数民族举旗起义”[5]。乾隆年间由于清政府用暴力偏袒手段干涉花寺门派和哲合忍耶门派之间的教争而引发的“苏四十三起义”就是清廷施行反动民族政策的直接恶果。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对哲合忍耶教派进行严厉打压,对教派领袖马明心及众教徒的屠杀严重挫伤了回族民众的民族情感,也在剿而不灭的哲合忍耶教徒心中埋下了很深的仇清复教决心。
经历了乾隆朝大劫之后,哲合忍耶教派秘密潜藏发展壮大,至咸丰时期马化龙初执教务,此时清廷正处于列强侵辱和太平军起义的内忧外患时期,无暇对伊斯兰教进行过于严密的控制,因此这段时期便成为了马化龙借助经商进行传教、积蓄复教力量的大好时机。他显赫的教主神权地位也为其传教事业增加了强大的号召力,“西宁、河狄、口外之回皆崇奉之,潜图雄长,非一日矣。既挟巨资,通贸易与西北各省及蒙古诸部,擅盐、茶马之利,而京师齐化门外、直隶天津、黑龙江、吉林……商之所至,教亦随之”[6]。历经数年苦心经营,在同治年间他已成为“富甲一郡,捐有武职”[7]的实力派人物。况且其人“宅心慈善”、“视汉民如一家”,“平时固赡穷困,里党翕然称颂。”所以“附和日众”[8]。又因“给教徒所传口唤,又往往自验,因此远近教徒皆奉如神明”[9]。而此时的清政府为维持苟延残喘之势,对贫瘠的西北地区却极尽搜刮压榨,民众越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自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集中财力支撑镇压东南太平军的军事活动大幅削减对西北的财政开支,甚至发生“协饷断绝”[10],同时,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打压下,太平军在战斗中逐渐失利,其中扶王陈德才部偕同捻军由四川向陕甘地区转移,这些起义军的到来让西北民众尤为震动,长期以来对清政府歧视压迫政策的不满以及积蓄已久的民族宗教矛盾促使众回民在共同的信仰号召下为捍卫其民族和信仰利益掀起了一场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哲合忍耶教派与清廷长期的历史积怨则使其成为了这场斗争中的主要领导力量,作为此时期执掌哲派教务的马化龙也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起义领袖。
二、“贼首、教主”——马化龙的历史角色
显赫的宗教地位带给马化龙神权号召力,哲合忍耶教派在乾隆朝大劫后对清政府的仇视成为了哲合忍耶教徒极力支持并追随马化龙对抗清廷的历史根源,而清政府的反动民族宗教政策则激化了广大穆斯林群众与清廷的矛盾。
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号召下一个以教阶为组织形式的回民反清团体形成,以马化龙为代表的各教派领袖成为这场起义运动的最高领导者,由他们派往各地布教的热伊斯以及由他们所领导的门宦下属成为基层领导者,广大信教穆斯林成为这次运动的主力军。马化龙以穆勒什德、总大阿訇“统理宁郡、两河等地军械事务大总戎”之名坐镇金积堡时“关陇诸回,视金积为向背”[3,,p110]。尤为震惊清廷的不止于此,在马化龙由金积堡至府城布署战事时,“合城回汉悉跪道恭迎,则见化漋(龙)坐大轿,拥卫多人,驰入公署,随传令部署一切,往数日始回金积”[3,,p112]。向来纠纷颇多的回汉民众在此时却能摒弃干戈,结同一心,臣服于马化龙麾下,不得不令人深思。
前文所述回汉矛盾大部分皆源于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而导致的情感隔阂,但是朝廷中却总是有居心叵测之人,借回汉械斗之事大加发挥,以“非其族类,其心必异”污蔑回民有谋逆动向,上愚朝廷,下离百姓。但观此时清政府对西北的竭泽搜刮、苛刻统治,西北回汉群众能够同仇敌忾对抗清廷并不是意外。更何况回教群众之中不乏有贤明如马化龙者,他们大都能遵循伊斯兰教义中“从善”的圣训,不存回汉偏见,以善待人。马化龙在灵州时始终“视回汉为一家”,并且坚持“重农事”、“少杀人”的施政方针,遂使灵州地区“遍野桑麻,渠堰纵横”,但是时任陕甘总督,负责西北剿回的清廷大臣左宗棠却认为:“回性犬羊,知畏威而不知怀德。”[11,p49]坚决执行清政府以武力对回民起义血腥镇压的策略。然而,马化龙以“善”为念的思想和爱民、惜民、众生平等的思想更符合西北回汉两族民心所向,所以回汉两族一心同恺对抗清廷是对晚清劣政极大的讽刺。
马化龙率众回反清便被清政府所不容,左宗棠评价马化龙时曾言:“化漋(龙)新教巨滑,而自乌鲁木齐、玛纳斯、肃州、西宁……东至黑龙江宽城子,凡新教之回皆听其指使,潜谋不轨者数十年,反形漏,国家必讨之贼也。”[11,p52]作为新教领袖,率众回反清而被清廷冠以“巨贼”之称,但是对于马化龙率众回反清是否如左宗棠所述是潜谋不轨已久,学术界颇有争议,有学者从哲合忍耶教派与清廷的历史积怨出发,认为在清廷对哲合忍耶教派严酷的压制和打击下,哲合忍耶教派要得以生存和延续,积极主动反清是其宗教发展的必然,但是笔者认为以马化龙在这场斗争中的思想和作为来看,却处处表现为被动防御。
在与清廷对抗之始,马化龙曾自述:“吾本念经人,遭逢乱世,为众推戴不得不维持桑梓,苟延残喘,俟东南军务平定,甘肃重见天日,必有贤明长官主持西北大局,届时吾将投诚,当一个太平百姓,于愿足矣。”[12]以此看来马化龙率众反清并非出于己愿,被众人所推戴、为形势所逼迫才使他不得己而为之。他寄望朝廷有贤明主政西北的思想充分地表达了一种民族自卫的无奈以及对安定、太平、开明之世的殷切期待。正因为有这种保守的思想,马化龙在这场针对清廷的战斗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提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在作战过程中他始终未曾放弃对清政府“投诚”的意愿,自与清军交战,他先后向清廷求抚数十次,并且多次代肃州、陕回民军求抚,但是他的投诚之心却屡次被清廷以“伙党尚聚,军械不交,”“款纳投诚以懈弛我使,而息养其锋锐”[3,p112]等理由或拒绝、或先讹其降而后食言剿杀。如此时战时和的反复,使本来就没有丝毫实战经验,又严重缺乏财资接应的西北回民起义军的组织力量和战斗信念渐渐涣散,清廷方面则由左宗棠亲自坐镇,所领湘军在其指挥下对回民起义军步步紧逼,最终起义军只能逐渐溃退,各守一隅。清军强硬的态度以及奸诈手腕最终使固守金积堡的马化龙的“求抚”之念成为了泡影。左宗棠言:“金积堡为陕甘必讨之贼,此时不早为之,所恐此后噬脐无及也。”[11,p52]金积堡一役成为了马化龙与清军的最后决战,回民军在被清军包围、外援断绝的情况下以死固守,伤亡惨重,面对已无回转的战局,马化龙最后“舍身”期望换来清廷对其众下回民的宽赦和同情。1871年1月6日,马化龙亲赴刘锦棠军营,具言:“念族众无辜者多,转禀曲宥,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无所恨。”[13]
三、宣化岗——穆斯林永恒的精神符号
清政府将马化龙及其子处以极刑,并将他们的头颅巡城示众,直至十年后才退归兰州府。时为德宗光绪八年(1872年),哲合忍耶教派创始人、第一任教主马明心之四世孙马元章在清廷血洗云南大东沟之后逃难至甘肃,得到投诚于清廷后被安插于甘肃省张家川县的原西北回民起义军“南八营”统帅李德仓的帮助,在张家川秘密传教,听闻马化龙之事,派人用重金将马化龙等人头颅秘密买回暗葬于张家川瓦泉沟清真寺内,后迁葬于张家川县北山并为其修建拱北和道堂,民国四年(1915年)马元章将埋葬马化龙之北山更名为“宣化岗”。
马化龙以“教主”和“巨贼”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晚清历史中,他既是晚清西北回民革命史中不可忽视的角色,更是伊斯兰教和中国社会交融对抗中的焦点人物。我国从单一华夏民族到多民族的大中华的形成,跨越了同中华文明的形成一样漫长的历史时空。昔日被视为“异族”的蛮夷戎狄皆已成为历史概念被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域内,在多民族共享安乐的和平盛世里,岂会还有“异族”之说?宽明、自由、平等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健全完善的社会制度,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各族人民所向往。正如清太祖康熙皇帝对其回教子民所持的态度“回民固有刁悍为非之人,而汉人中能尽无乎?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而以治众民者治回民。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赏善罚恶,上之政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刁顽凶悍之习,王法所不能容者,亦为回教之所不容,孝悌忠信之风,而各教之所乐许者,亦必回教之所共慕。倘自谓别有一教,估恶行私,则是冥顽无知,甘为异类,意典俱在,朕岂能为尔者宽假乎?”[4,p117]
宗教和世俗社会都以人之生在为存在前提,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以“仁”为念,顺应了民生之愿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当权者是儒家秩序的维持者,若以施仁政为责,则儒威不立而自立于民心,在儒威的感召下使得众心向善,社会秩序必会安稳,民族之间必然和谐融洽,而宗教只有在以“善”为念的教义体系之下,将宗教的特殊性完好地融入社会大环境中,去积极适应并改造自身,使教义理念和宗教体系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当代社会,我国能有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开放、自由、平等的民族宗教政策使各族人民各安其业,和睦融洽的共处于中华大家庭中实属历史上各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果实,也是当政者能够以史为鉴、心系众生的回报。而各族人民则更应“以善为习,以儒为化”,才能安享盛世之欢,为我们的祖国增添锦绣。
如今的宣化岗在马元章、马元超兄弟及其后辈哲合忍耶教派领袖的苦心经营下已成为了中国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教活动中心,其宗教地位和影响力以其充满生机的发展现状为见证,这里每年都要举行十多次大型的“尔曼里”纪念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以及埋葬在这里的哲合忍耶教派先贤,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信教群怀着对信仰的虔诚和对先贤的敬仰之情来此,使宣化岗成为了具有强大感染力和号召力的民族精神宣扬圣地。而凝聚在此的民族精神不仅仅只是广大穆斯林群众的信仰,更有他们对平等、自由、开明的理想社会持之不懈的追求,对善良、正义、敢为天下先的美好人格的尊崇。
[1]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A].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C].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265.
[2] 马国瑸,宣化岗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2.
[3] 杨毓秀.平回志(卷三)[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107-112.
[4] 傅统先.中国回教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15-117.
[5]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和门宦制度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279.
[6] 朱德裳.续湘军志[M].长沙∶岳麓书社,1983∶265.
[7] 柏景伟.柏沣西先生遗集(卷三)[Z].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8]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十一)[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 1990.
[9] 马仲雍.清同治年间甘肃回变中的马化龙[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74.
[10] 马鸿逵.西北两大问题[A].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C].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165.
[11]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左文襄公书牍(卷十)[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49-52.
[12]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十)[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 1990.
[13] 易孔昭.回民起义[A].平定关陇纪略(卷九)[C]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92.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An Analysis of Xuanhuagang Religious Symbol Meaning in the View of MA Hua-Long’s Encounters in History
ZHANG Jia-ni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Lanzhou, Lanzhou 730000, China)
Xuanhuagang is a shrine place of China “endure fits" Islam for religious activities. The constru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MA Hua-long’s burying here, who was the fifth leader of Islamic “endure fits” leading the Muslim uprising in Shanxi and Gansu Province during Tongzhi period of Qing dynasty. With the double identities, the religious leader and the traitor, Ma Hua-long's encounters in history was an interaction of Islamic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It is Ma Hua-long’s secret burying in Xuanhuagang and the restore of religion that gave Xuanhuagang a special religious symbol meaning.
Xuanhuagang; MA Hua-long; The Muslim uprising in Shanxi and Gansu Province; ZUO Zong-tang
2011-02-15
张嘉倪(1986-)女,甘肃省天水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K254.43
A
1009-9115(2011)03-008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