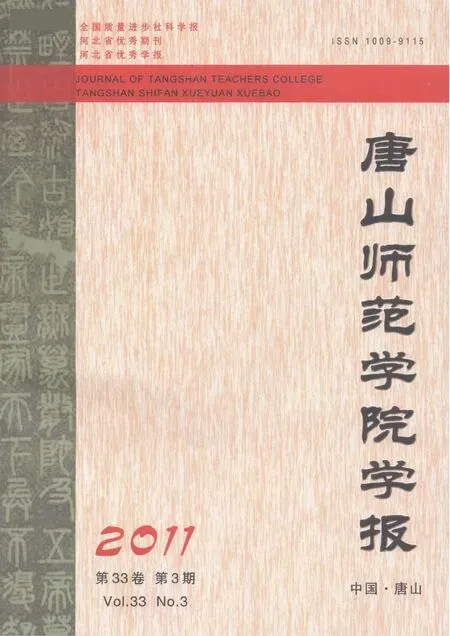民国茶馆里的莫谈国事
2011-03-18杨红兰
杨红兰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历史学研究
民国茶馆里的莫谈国事
杨红兰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民国茶馆,一个大众生活的舞台。在百家争鸣、战火硝烟的年代,它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往往悬起了“莫谈国事”的告白,然而“禁愈烈,而嗜愈专”,茶馆与政治其实有着许多的接触和联系。
民国茶馆;莫谈国事;禁而不止
老舍《茶馆》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当属三幕剧中一个始终不变的道具——“莫谈国事”的字条。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国的茶馆并非平静如水,而是充满着政治的硝烟,从对社会现状的批评到对国家政策的讨论以及政府为控制人们思想所做的宣传,这些上演于茶馆的话语,其实包含了许许多多说不尽的“家事、国事、天下事”。
一、茶馆之现状
(一)茶馆·茶客
民国时期,茶馆已是市民生活的舞台,它们既是娱乐消闲的场所,亦为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间。老舍曾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等。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1]。
1929年,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搞了一个《关于茶馆的调查》,指出“茶馆是市民聚会最方便而适当的地方。所以茶馆成为本市最发达而最多的营业”。据1933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光是汉口就已有茶馆1 373家[2,p279]。
民国茶馆不仅在数量上有优势,而且分布也较为广泛。据1 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至300人,小者亦可容数十人[3]。京都的茶馆更是建设广泛,民国时已扩延至什刹海的荷花市场和天桥的水心亭,以及北海的双红榭茶社和中山公园的金雨轩茶棚。上海的租界也有了闻名的畅园茶馆。
民国茶馆之所以有如此的规模和数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茶客的大众化。茶馆诞生之初,大多属高档消费区。规模大、格局气派,有雅座和单间,茶客均是不失斯文的长衫帮人物。然而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的财政支出出现了巨额赤字,八旗钱粮只能“半支”。“旗门大爷”开始撑不住门面,大茶馆纷纷倒闭。一些大茶馆中的“体面人物”,也就沦为了清茶馆中的“长衫阶层”。所以民国时茶馆中,占据更多江山的当属清茶清贫清侃的清茶馆,这类茶馆设施简陋、门槛低、消费低,茶客基本上是劳苦大众的“短衣帮”。
当这些下层百姓汇集于茶馆时,闲聊中不免要为日新月异的时局发出几句牢骚,而这正是各个政权所极力打击的目标。为了表示所谓的“本分”和逃避政府的追究,茶馆也就贴出了“莫谈国事”的告示。
(二)“莫谈国事”的告示
正值民国乱世,政权更叠,各种茶客闲聊之际,也就有了对时政的批评与讨论。然而专政的王权厌恶任何不同的声音,各个政权,无论是你方唱罢,还是我方登场,不变的依然是对民众的控制以及打击那些在公共场所尖锐批判政府的人。民国时期,军阀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样办法对付所谓的“破坏分子”。如1940年6月,成都警察称一些汉奸和流氓在茶馆活动,要茶社业公会提供“密报”[4]。由于政府经常在茶馆里收集所谓“情报”来惩办其批评者,为避免招惹麻烦,每一茶馆大多在最醒目的地方高悬起“莫谈国事”的告白。
袁世凯窃国之后,又企图由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来了个黄袍加身,一跃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由于做贼心虚,所以不断强化特务统治。京师警察厅、步军统领衙门、军政执法处属下的侦缉队纷纷在茶馆“坐桩”,缉查“宗社党”、“革命党”、“乱党”、“匪类”、“妖人”。凡是不利于独裁统治的言行也自然在缉拿之列,闹得只要有生面客人走进茶馆,掌馆即高声迎呼道“官爷来了,官爷里边请”,意在提醒聊得正起劲的侃爷“说话留点神”,来者说不定是稽查队。后来干脆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张贴告示“莫谈国事”,告诫侃爷别引火烧身。
其实,茶馆国事禁讳不仅在民国,其他时期也有。例如《癸丑纪闻录》在1853年正月三十日下记有,“……钱兰修云,昨至郡(嘉兴)完粮,有委员某公,伊戚也,云前日本府谕委员文人,向茶坊酒肆有谈时事,即拿禀办……”[5],只是这一禁令在民国更严厉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谈国事”的告白贴在茶馆本身就是对专制、对压制言论自由的一种无声的控诉。
(三)禁而不止
1. 喜谈国事
尽管政府的控制,政治仍然是人们所热衷的话题。那些喜欢在茶馆谈论政治的茶客,在成都被称为“茶馆政治家。在这里,茶客们抱怨生活的艰辛,愤怒政府的腐败,担忧时局的变化。
时至民国,北京西长安街西头有座二荤铺的大茶馆名龙海轩,教育界京派人士经常在此聚会,于茶后商议对策,久而久之京派就有了“龙海轩”之称。龙海轩茶馆也就成了教育界的京派议事厅。北海公园的双红榭茶社因距沙滩红楼不足二里,故新文化运动前后,成为北大师生经常涉足之地。所言所议“德先生”、“赛先生”,开始在幽州台上见古人迎来者。这些“新时期的儒冠们”给茶社注入了新的生机。
2. 不得不谈
《茶馆》里的常四爷,因为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老式特务宋恩子和吴祥子冤关了一年多的大狱。闻一多的《茶馆小调》中,老板也哀求顾客不要谈论敏感话题。
在民国虽然谈论国事要遭打击和惩罚,但是不谈国事,也未必平安无恙、万事大吉。有时因与国事缠得紧密,反而不得不谈。《茶馆》中始终恪守着“莫谈国事”处世信条的王利发,最终走上了茶馆被人吞并的末路,他发出了一辈子都没敢说出口的对生活、对世道的质问:“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他一心想摆脱国事的纠缠,做成发家致富的黄粱梦,然而国事如无情的洪水一样汹涌而来:军阀混乱、军警横行、饥民逃荒……一心改良,却越改越凉。他欲与国事保持距离,不仅不可得,反而终被国事给吞没了。资产阶级秦忠义怀着工业救国的抱负,“入世国事”也被国事吞没,工厂变为逆产。
3. 政府破坏禁令
政府禁止人们谈论政治,却又把茶馆当做大众教育和宣传新思潮的一个平台,以此来控制民众。如1941年,地方政府令各茶馆购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袖画像,设置讲台,配备黑板和国民党党旗、国旗,以此形式来宣传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观念[6]。
4. 各种政治势力
20世纪初,茶馆已成为政治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这在清末的保路运动中体现的非常充分。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茶馆便成为政治中心,每天人们聚集在茶馆,议论运动最新的发展。正如李劼人所说:“几乎每条街的百姓……都兴高采烈地蹲在茶铺的板凳上,大声武气的说。此时的茶馆不在是人们整天闲聊的地方,而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在这里,人们关心铁路国有化和对外贷款的问题。这场散了,他们又到另一个茶馆听辩论。”[7]
在鲁迅笔下的“华老栓茶馆”里,可以听到杀革命党人的传闻。在沙汀的“其居香茶馆”里,会认识旧社会袍哥、乡绅、保甲长之流的嘴脸。《沙家浜》中,春来茶馆则成了阿庆嫂掩护革命军人的庇护地了。在流氓恶霸势力操纵着的旧上海,茶馆有时也成了地痞流氓和白相人进行敲诈勒索,进行罪恶勾当的场所。旧社会的白相人有句口头禅,“阿拉白天‘皮包水’(上茶馆),夜间‘水包皮’(进浴室)”。“较场口事件”凶手刘野樵在大梁子开“群义茶馆”,就是特务打手的山寨。
二、茶馆与政治
(一)抵抗性活动
茶馆抗税在民国时期变得日益频繁。当税重难忍时,茶馆业主们便联合起来要求减税,通过自己组织的形式,无形中已进入了政治舞台。1928年底,成都茶馆公会召开会议,决定罢市抵抗警察强行征收“茶桌捐”。《国民公报》以《各茶社停业抗捐》为题,指出这是“和平请愿中之剧烈变化”。1931年,茶业公会还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公众陈述抗税之理由。1932年,另一个反税运动兴起,称“茶捐风潮”。1940年,当市政府宣布增税时,公会要求全体成员“绝不承认该税,抗拒到底”。虽然在大多数这些对抗中,政府占有明显优势,迫使茶业公会就范。但是从这些案例,我们发现集体行动使茶馆业可以发出更强的声音,从而促使政府认真考虑他们的诉求。
(二)公益活动
一些茶馆抓住时机,参加全国和地区性的赈灾活动等更多的公益事务,以提高其社会声誉。例如,如1909年,可园邀请若干著名演员演戏,将两天收入捐给甘肃赈灾。1910年,悦来茶园组织湖南赈灾义演,每票一元,1 400人购票看戏。1912年,万春茶园宣布将两天的演戏收入献作“国民捐”,动员人们踊跃购票[8]。
(三)反封倡新
对于一些新的行为,茶馆也是极力提倡和促进。例如,上海租界畅园茶馆组织“义务剪辨会”,于1911年12月31日至1912年1月2日的三天内,张贴告示说:“凡自愿前来剪辨的,修理成学生头,分文不取;理发完毕,每人在茶馆内当场赠吃大肉面一碗。如有人愿意答谢雅意,不取走所剪下的发编者,本会将代为变卖,捐赠军饷。”三天下来成效显著,自愿前来剪辨者竟有254人之多。
(四)下层政治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旦民事发生纠纷,本该属于法庭或衙门的职责。然而民国茶馆盛行“吃讲茶”,就是发生纠纷时不经法律手续,私下了结。所以,旧时重庆人又称茶馆为“理信铺子”(即民事纠纷调节处的意思)。最为有名的当属1930年重庆药材帮找洋人“吃讲茶”,要拉洋人下河吃水的故事。
(五)另类国事
地方戏作为大众教育的有力工具,总是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所以,戏曲改良成为一个政治的热题。在茶馆看戏,不再只是娱乐,而是与地方和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后,政治戏逐渐流行。如1912年,根据美国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在悦来茶园上演,改良精英试图用美国黑人的经历来阐明“适者生存”的道理。
抗战爆发后,茶馆里讲评书者,虽然仍讲人们熟知的故事,但加入了爱国和抗日的主题。此外,一些具有抗日新潮的戏剧也在各大茶馆屡次上演。如1920年12月,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以万春茶园为舞台演“新剧”[9]。年悦来茶园上演爱国佳剧《山河泪》和《还我河山》。
抗日战争中,茶馆政治更是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以茶馆作为宣传抗日和爱国之地,在那里贴标语、海报、告示,并监督演出和公众集会,茶馆成为了救国舞台。
国民党四川党部还制定《茶馆宣传实施计划》,作为战时宣传的一部分。其中规定,茶馆贴出《国民公约》。《国民公约》共12条,要求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背政府法令,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不做汉奸和敌国的顺民,不参加汉奸组织,不做敌人和汉奸的官兵,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不买敌人的货物,不买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4,p186-1431]。通过这些详细的规则和条文,来教化人们如何抗日爱国。另外,官方还要求茶馆提供政府指定的书籍和报纸。例如《解散新四军和整饬军纪》、《汪精卫卖国密约》、《大公报》、《中央日报》等等,用以谴责汉奸、动员民众、鼓吹国民意识以及宣传反共思想[4]。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莫谈国事”下的噤若寒蝉,还是抗战救国时的火热宣传,民国时期的茶馆从来都不是一潭静水,而是随着时代的风浪潮起潮涌。
[1] 老舍.老舍剧作选[C]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3-144.
[2] 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M].成都∶巴蜀书社,1987∶279.
[3] 胡天.成都导游[M].成都∶蜀文印刷社,1938∶69.
[4] 四川省政府.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Z].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1982∶1431.
[5] 董蔡时主编.癸丑纪闻录[A].太平天国史料专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78.
[6] 钟茂煊.刘师亮外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91.
[7] 李劼人.大波[A].李吉人选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171.
[8] 周止颖.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J].四川文史资料选辑,1987, (36)∶35.
[9] 茂昭.成都的茶馆[J]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1983∶178.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The “Don’t Talk Politics Here” in Republic of China's Teahouse
YANG Hong-l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The teahouse in Republic period of China is the stage of public life. In the age of wars and confliction, the teahouses often hung public statement —— “Don’t Talk Politics Here” in order to obtain the survival and the development. But it is invalid, the teahouse and politics have actually many contacts and relations which are inevitabl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ahouse; don’t talk politics here; appearances more than forbidden
2011-02-12
杨红兰(1983-),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K258
A
1009-9115(2011)03-00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