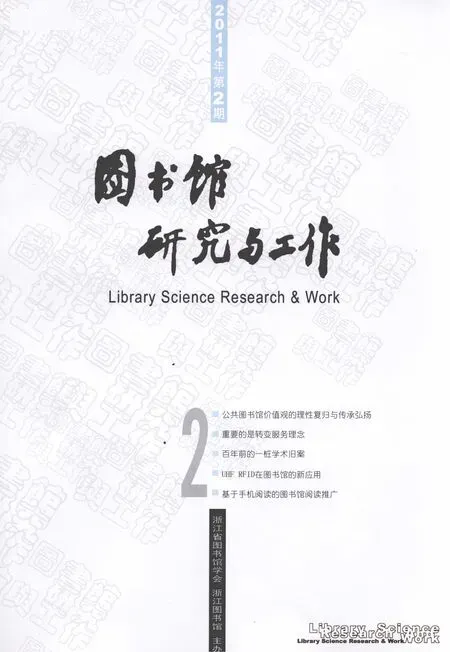百年前的一桩学术旧案——沈阳故宫满蒙文文献的发现和盗摄
2011-03-18钱婉约
钱婉约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作者信息〕钱婉约,女,教授,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近代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已为世人熟知。在近百年学术史上,堪与伯希和、斯坦因盗取敦煌文献事件相提并论的,是日本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对于前清沈阳故宫满蒙文文献的发现与盗摄。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这批关于满族历史与清朝初期史的文献,与敦煌文献一样,尽管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但深藏宫中,任尘埃堆积,不为人所知;二,作为本国的珍贵文献,也与敦煌文献一样,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首先是被外国的汉学家“慧眼识破”,并暗中巧施手段或借助政治力量盗摄取走的;三,与因敦煌文献的发现而有了世界性的“敦煌学”一样,由于这些满蒙文文献的发现,引起了日本对于满蒙学的研究,满蒙学因而在学术界渐渐开展起来。不同的是,沈阳故宫的文献不如敦煌文献那样内容涉及面广泛,时间上的跨度超越千年以上,它主要只是有关满清一族一朝的文化历史,因而,与敦煌文献相比,在学术史上的影响也较小,不为人熟知。
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近百年前的这段学术旧案吧。
东北沈阳故宫,即今沈阳故宫博物馆,是清初的皇宫,清朝入关后称“奉天行宫”。它始建于1625年,1636年基本建成。其后,乾隆、嘉庆朝又有增建。后宫的“崇谟阁”、“敬典阁”是保存清初实录、圣训、玉牒的地方,包括有关清朝开国史的多种文字的历史资料;西路的“文溯阁”是珍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
内藤湖南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奠基者之一。早年他曾在《万朝报》、《朝日新闻》等报社当记者,是活跃于明治中晚期政界、文坛上的有名的“中国通”,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迁、文化现象多有敏锐的评说。1907年起,他执教于京都大学文学部,成为京都大学东洋史第一教授和支那学的学术带头人。
内藤湖南与奉天结下书缘,最初是在1902年。这是他继1899年以后,第二次来中国访问。在奉天喇嘛教寺庙黄寺中,内藤发现了“东洋学上非常的宝物”——《满文大藏经》,以及其它满洲史料。但这时,实际上内藤还不懂满文、蒙文,所以,把《蒙文大藏经》,误识为《满文大藏经》。事实上,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无人懂得满、蒙文。但此次黄寺的发现,使他深感满、蒙语知识的重要,促使他当下在北京购买了有关满、蒙文的书籍,归而自学。
三年后的1905年,内藤湖南再次来到奉天,这时他对满语、蒙语已有基本掌握,这使得他此行能在文献上获得重大发现:在崇谟阁发现了《满文老档》、《满蒙汉三体满洲实录》(又名《太祖实录战图》)、《满蒙汉三体蒙古源流》、《五体清文鉴》、《汉文旧档》等有关满洲史的重要史籍。内藤当即将《汉文旧档》全部晒蓝图制版而归。内藤又拍摄了《蒙古源流》的蒙文部分。此外,在日本军方出面下,强行压价买下了黄寺收藏的明代写本金字《蒙文大藏经》,包括此行于北塔(奉天城北郊法轮寺)新发现的《满文大藏经》,一起带回日本,这两部满、蒙文藏经,藏于东京大学,惜后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烧毁了。
1906年,内藤受外务省委托调查间岛问题,在履行公务的同时,内藤更为积极地进行搜求史料的工作。在外交官的疏通下,内藤再次访黄寺,入崇谟阁、文溯阁,抄录并拍摄了这次及上次发现的文献。如《满文蒙古源流》、《西域同文志》、《旧清语》、《满文长白山图》、《盛京全图》等 。其中,《蒙古源流》的借阅与拍摄,曾遭到崇谟阁看守人的拒绝和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反对。内藤声称《蒙古源流》是调查间岛问题的关键资料,让当时的外相直接照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又由总领事以外交手段贿赂赵尔巽,才得以达到目的。
奉天访书的最重大收获是在1912年。内藤作为京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受京大委托专程赴奉天,拍摄故宫宫殿内珍藏的清朝史料。内藤从3月23日到5月17日,整整八个星期,都埋首在崇谟阁内进行紧张的拍摄工作,在京大文学部讲师富冈谦藏、羽田亨的协助下,又得到了在那里的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的帮助,共拍摄下一万张以上的胶片,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当然,这次的拍摄工作,是以1905、1906年的调查和发现为基础的,自从发现了《满文老档》等重要文献后,内藤久存翻拍带回日本研究的念头,七年后,终于如愿以偿。这里介绍拍摄下的《满文老档》与《五体清文鉴》的文献价值。
《满文老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两朝历史的编年文献,共 180册,记载 1607年——1636年间满清开国史事,有无圈点本、加圈点本两种文本,亦称新、老满文本,但内容基本相同。乾隆40年(1775)和43年(1778)分别对原本进行过整理、重抄,包括新、老满文本各一套。内藤于崇谟阁见到的即是乾隆年间的誊抄本,内藤说它纸质崭新,抄写认真。内藤拍摄了乾隆43年重抄本的全部加圈点本,共 4300张胶片。可以说,内藤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最早注意到《满文老档》史料价值的学者。他说:
“(《满文老档》的价值)如果不是在研究了4、5年之后,不是把它通读了一遍之后,是不可能详说的。但肯定极具价值。单就篇幅来看,太祖一代的实录,满文、汉文的同样都只有8卷,而《老档》则有20卷、81册,是实录的 10倍。……对此充分研究,一定能发现许多实录没有的史料。……关于满洲的史料,恐怕再没有比这个更精密的东西了,可以说它是有基本史料的地位,在历史上有非常的价值 。”〔2〕
它被拍摄带回日本后,收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另有副本藏于日本满铁调查部白山黑水文库。在二、三十年代,由内藤的学生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鸳渊一、神田喜一郎等人利用和整理,其中今西春秋先独立致力于翻译,于 1933年出版日文、满文对照本,题名《满洲实录》。战后,日本成立了《满文老档》研究会,由文部省出资,进行集体日译,从1955年到1963年,出齐全部七册。参加翻译的神田喜一郎、和田清、神田信夫等,都成为东洋史的著名学者或满学的专家。神田信夫在80年代访问沈阳故宫博物馆,亲眼目睹《满文老档》后,回忆说“(内藤湖南)先生在崇谟阁这栋楼中发现《满文老档》,……是清朝史研究史上值得记一笔的大事。……我长年研究《满文老档》,曾根据湖南先生拍回的照片参加过翻译工作,追本溯源,再一次深感先生的学恩。”〔3〕在中国,《满文老档》的翻译,最早是由满人学者金梁组织满、汉学人进行翻译,于1918年译成汉文,但卷帙过多,校勘未精,1929年择要以《满洲老档秘录》上、下编付印,不及全书二十分之一。其余部分,在1933-1935年陆续在《故宫周刊》上刊出。
《五体清文鉴》,是清朝时五大民族满、藏、蒙古、维吾尔、汉的文字的辞书。由康熙敕修,乾隆年间陆续成书。最早是满、汉对照,后加入蒙、藏文,最后加入维吾尔文,完善为《五体清文鉴》。此书只以抄本传世,藏于北京及奉天的宫廷中。此书按天文、地理、制度、风俗等内容细分为35部,是包括清代全国许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方出产等多方面的辞书。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历史价值。行家认为,其中维吾尔文部分最为珍贵。在此之前,内藤了解到,日本已有了满、汉《清文鉴》,满、蒙、藏、汉《四体清文鉴》,此次拍摄使日本拥有了最完备的《清文鉴》。在中国,1957年,民族出版社曾用故宫重华宫藏本出版过影印本。
关于这次拍摄,也颇有一番曲折,奉天宫殿对外国人调查先皇遗物,是采取谨慎态度的。内藤到达后,先是由领事馆与奉天都督赵尔巽交涉,内藤又私人出面,以多年前旧识的身份,送了赵尔巽和手下的孙外交官厚礼,公私夹击,并且还谎称只是拍摄文字书籍《清文鉴》,才得以进入宫殿拍摄。他们首先秘密借出《满文老档》,当全部拍摄完《满文老档》的4300张胶片时,他们立即还掉此书,又借出《五体清文鉴》。在续拍《五体清文鉴》之前,内藤去了一次大连,等两天后回来时,中国方面从总督到交涉使到具体管文书的官吏,都已改变了态度。内藤记到:“这《满文老档》都写了什么,中国的官员们并不清楚,连总督大概也不清楚,只知是用满文写的书籍而已。但日本人却特意进宫拍摄,大概是很贵重的东西,所以,默默地改变了注意,不再许我们拍摄。”〔4〕于是,内藤他们在秘密状态下,以10天时间赶拍完《五体清文鉴》的5300张胶片。并经再三请求,又再次借出《满文老档》,把检查胶卷时发现拍坏的200多张胶片,匆忙地在一天中补拍完。由于上上下下都拒绝再借书拍摄,本来打算中的《满洲实录》即《太祖实录战图》,便没拍成。
综上所述,内藤湖南对于沈阳故宫满蒙文文献的调查和发现,可谓独具慧眼、坚韧不拔,他是在中国人尚未认识其文献价值的时候,就捷足先登,或强行买卖,或私下抄录,或施计盗摄,想方设法弄回日本,从而促进或开启了日本中国学中满学这一独特的研究领域。他本人对于满清历史的研究,也往往是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发现前人所未发现的开创性工作,如他的《清朝初期之继嗣问题》一文,于30年代初被中国明清史专家谢国祯译成中文,成为清史研究中不易之定说。当然,由于近代中日关系处于不平等的、甚至是中国受侵略和被掠夺的地位,内藤湖南的奉天访书和巧取盗摄有时不免是依靠了外交强权而达成目的的。
回眸历史,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国家学术命运的昌盛或衰微,是与国家的强盛与否、人民的文化素质高低密切相关的。以史为鉴,我们在义愤于外国人的窃盗行为时,更应该“自坚门户”,懂得珍惜和守护自己的珍宝,否则,岂不辜负了这100年的光阴,历史的垂训?
〔1〕参见《奉天访书谈》,载《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目睹书坛》。
〔2〕《奉天访书谈》,《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目睹书坛》第304页。
〔3〕《沈阳忆湖南先生》,载神田信夫著《满学五十年》,刀水书房1992年出版。
〔4〕《奉天访书谈》,《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目睹书坛》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