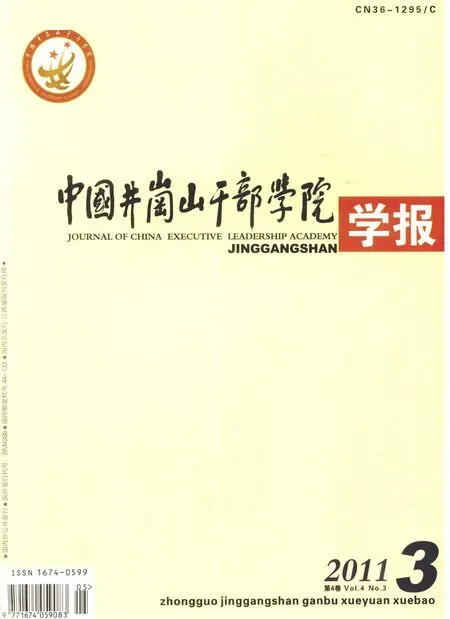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分析及控制策略
2011-02-18陶国根黄毅峰
□陶国根 黄毅峰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江西南昌 330003)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分析及控制策略
□陶国根 黄毅峰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江西南昌 330003)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孕育、发生、演变甚至结束都起着重要的影响。纵观近年来处置网络谣言危机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谣言时缺乏敏感度和预警性,缺乏舆论引导的积极性、主动性,缺乏总结反思和持续关注,不仅影响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顺利解决,甚至激化了矛盾,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针对网络谣言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网络谣言控制策略,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控制。
网络谣言;群体性突发事件;控制策略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发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往往伴随着谣言的大量滋生和迅速蔓延,特别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日益发展,谣言的传播速度有增无减,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更为突出,极易造成大规模的社会恐慌,甚至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因此,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与网络谣言之间的逻辑关联性
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在我国各地不断发生,从“重庆万州”事件到“贵州瓮安事件”再到“湖北石首事件”,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各地相继发生的这些群体性突发事件案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网络谣言的大量传播,网络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这是众所周知的),[1]P55从未有一场暴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激烈程度的激化。[2]P141网络谣言的蔓延特别是涉及范围很广的恶意网络谣言,会威胁到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一)网络谣言孕育产生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潜伏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潜伏期也正是网络谣言的孕育期,二者之间具有良好的契合性。通过对一些典型群体性突发事件案例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几乎在所有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期,我们总能在网络上看到对政府不满的闲言碎语,这种闲言碎语往往采取谣言的形式,通过论坛、微博等媒介散播对政府的蔑视、贬低、侮辱,或是对某些政府行为进行谴责。例如,在重庆万州事件中,有人称“打人者是公务员”;在贵州瓮安事件中,有网络谣言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在湖北石首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永隆大酒店老板走私贩卖毒品后被害的”。网络谣言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暴力和冲突,但它却充当了正在加剧的社会紧张气氛的催化剂。无论何时,只要网络谣言四处传播,超出了平常范围,或是网络谣言的恶毒程度变得更为严重,我们就可以把这当成是一场群体性突发事件即将爆发的征兆。网络谣言既然可以作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前兆,也就是说网络谣言有可能成为警告,提醒政府相关部门,必须积极果断采取措施去控制受到挑动的人群,否则,这些人很快就要走上激动、敌对、无法自控的道路。
(二)网络谣言加速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由潜伏期到爆发期有一个时间过程,而网络谣言毋庸置疑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得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期提前来临。网络谣言产生以后,如果没有权威机构予以澄清,就进入了传播阶段,所有参与传播的人都可以视为网络谣言的传播者。传播者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角色,一方面他接收谣言,另外一方面也努力地将谣言传播出去。在传播过程中,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它加以润色与修正,谣言从完全模糊和空洞的描写状态,逐步变得清晰和有形,被具体化和细节化。在这个时候,执政当局任何不当的行为都可能被放大,成为炸药桶,在网络谣言的点燃下发生爆炸,致使群体性突发事件提前到来。“通常,尽管不是一成不变的,点燃火药桶的火星就是具有煽动性的谣言本身”。[2]P142但在瓮安事件中,事实上是网络谣言最终点燃了这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集中爆发。网络谣言使当地群众长期以来积压在心中对政府的不满和怨恨爆发出来,随后他们采取了集体行动。短短几个小时,上万当地群众逐渐云集在一起,大火焚毁了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价值数百万的财产遭到损坏。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从表面上看似偶然,但实际上它是群众长期以来对当地政府的不满情绪所引发的,他们在网络谣言的激发下,采取了群体行动,最终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提前到来。
(三)网络谣言加剧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高潮期。“在一场骚乱的狂热中,谣言比平时传播得更快,但在这一疯狂的阶段,它们的内容里反映出明显的盲从。有时它们使人产生幻觉。人们用一种狂热的态度对拷打、强奸和谋杀详细描述,仿佛是为正在发生的行为进行解释,并加以报复的进程。”[2]P143对于普通群众而言,谣言是一个神秘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它迷惑人,征服人,引诱人。人们一旦相信网络谣言,介入网络谣言传播,就会立刻变成谣言集体行动中的群氓,被网络谣言征服、迷惑和淹没。然而,“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3]P37在某些煽动者的鼓动之下变得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变得疯狂。在他们没有被网络谣言迷惑之前,他们非常的理智,知道不能焚烧财物或阻挡交通,即便受到某种诱惑,他们也能够理性地抵制或拒绝这种诱惑。但是公众一旦被网络谣言征服,谣言将赋予他们一种神秘而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促使他们产生烧、杀、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即屈服于这种引诱,甚至他们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迷失自我。这种引诱会让他们在不考虑后果的情况下阻断交通、攻击政府、抢夺财物。所以,疯狂的谣言差不多就是暴力的口头伴奏,[4]谣言加剧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破坏性程度。而当网络谣言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政府部门就几乎难以控制局势。
(四)网络谣言平息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消退期。伴随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终结,各种网络谣言也将趋于平息。卡普费雷说:“谣言是某种背景的见证,如果这种背景发生了变化,谣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将立即停止流传。因为谣言失去了合理性”。因此,所有的谣言都是注定要消亡的,“事实上,在谣言终结时没有任何魔术。这种终结是结构性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谣言边活着,边衰竭。谣言自己制造了使自己消亡的动力。”[5]P113群体性突发事件得到平息以后,执政当局必将利用一切可用之媒体,揭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获取自己关注,想要知道,想要了解的一切信息。紧接其后,谣言这块巨大的集体口香糖,就会渐渐失去味道,而被公众所唾弃。在事实真相大白的一刹那,也就意味着网络谣言的终结时。事实真相揭示以后,人们就失去了对网络谣言的兴趣,不再议论网络谣言,传播网络谣言,因为人们已经知道它是谣言,所以就不再相信它,他们相信事实与真相,那些曾经被人们热衷议论并被广泛传播的网络谣言再也没有谈论的价值了。
总之,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群体性突发事件与网络谣言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网络谣言贯穿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全过程,它往往先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而产生,但却常常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平息之后才销声匿迹,它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孕育、发生、演变甚至结束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行为分析
纵观近年来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处置网络谣言危机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谣言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不仅影响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顺利解决,有的甚至激化了矛盾,使事态进一步扩大。
(一)产生阶段:对待网络谣言缺乏预警性和敏感度。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产生阶段是处置网络谣言危机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处置得好,可以有效防止网络谣言的产生或降低网络谣言的影响。因此,一旦条件具备,我们就应对网络谣言的产生、传播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建立必要的预警机制。然而,从实践操作来看,我们还缺乏这样的机制,主要表现在:首先,缺乏对网络谣言的收集制度。网络上往往谣言很多,但与我们工作相关的网络谣言究竟有哪些,有时我们并不知道,或者说,有时广大干部知道,但担负决策责任的领导可能并不知道,因为越是领导干部,听到的经过过滤的好情况、好消息越多,而对偏于负面的网络谣言则知之甚少。这就使相关部门领导往往处于对谣言闭目塞听的地步。其次,缺乏对网络谣言的评估机制。由于同一时期对某一相关部门可能会有许多网络谣言,但究竟哪些有关注价值,哪些将来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此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评估,以集中精力关注和应对主要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在党委政府决策中,决策者很少会考虑和评估网络谣言因素,有的领导甚至会和网络谣言反其道而行,以显示自己的工作魅力。这样,有时网络谣言处于放任、失控的状态也就毫不奇怪了。最后,缺乏对网络谣言的逐级上报机制。虽然宣传部门有舆情反映职能和渠道,但反映调查性问题多,而对于凭空流传的网络谣言则缺乏关注。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繁杂的行政管理事务已使许多部门难以应付,根本无暇去关注各种流言蜚语,自己也没有这个职责。这样,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氛围中,只有等网络谣言把蚊子传成大象,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才启动强制性的应急机制。事实上许多网络谣言都是最后才引起注意并动员各方力量加以平息的,这反映了预警机制的缺乏与后果的可怕。
(二)传播阶段:对待网络谣言缺乏舆论引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阶段是处置网络谣言危机的关键时期,政府若能在此阶段采取积极主动的举措,可以有效防止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产生或降低其危害性。但是,从实践操作来看,我们部分地方政府在此阶段的行为表现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首先,信息发布缺乏及时性和权威性。网络谣言传播得厉害的地方或领域,一定是政务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的地方或领域,因为一旦权威的声音微弱甚至缺失,那么各种失真的声音就会变成强势的声音。“谣言止于公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少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做得还很不够。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形成和传播,固然与群众的偏听偏信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正确信息发布的不及时、不全面。其次,对网络舆论缺乏有效监管和引导。上海市政府前新闻发言人焦扬有曾说过,“在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出自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5]P15由于竞争的需要和记者生存的需要,有些媒体不惜捕风捉影捏造假新闻,一旦这些虚假新闻先入为主地进入了公众的大脑,事后要改变这些看法往往是非常难的。因此,在群体性突发事件来临时,政府就无法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无法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和扩散。最后,网络谣言的处置方法欠妥。在网络谣言传播阶段,一些领导者只是满足于看不到、听不到谣言传播,试图用“压”的方法来解决网络谣言的传播问题,全然不顾谣言传播给各方造成的伤痛。事实上,在网络、手机等现代通信日益广泛,社会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环境下,一味的压制和打击只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但没有压制网络谣言传播,而且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三)终结阶段:对待网络谣言缺乏总结反思和持续关注。网络谣言或者说所有的谣言注定都是要消亡的,虽然它们其中的一部分仍然在环境合适的时候还会重复出现,或者新的谣言仍然层出不穷来填补那些已经消亡了的谣言所留下的空白,但是具体到某一个网络谣言的时候,其最终的命运仍然是被终结。终结阶段的特点是网络谣言虽然已经终结,或已失去作用,但谣言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许多“消毒”或弥补的工作仍要继续。如果这个阶段处理不好,就有可能为下一次群体性突发事件埋下隐患。从实践操作来看,我们发现政府部门往往忽略这个阶段的网络谣言处置。首先,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后续处理重视不够。不少政府部门领导在网络谣言危机结束后,容易放松警惕,会有松一口气的思想,认为所有工作基本可以结束。实际上,在网络谣言危机结束后,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网络谣言所造成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去消除,网络谣言事件造成的损失仍然需要我们想办法尽量去弥补。如乌鲁木齐“7·5事件”结束,我们仍然需要花很大力气去修补因事件造成各民族之间的裂痕,仍然需要努力去创造民族团结的氛围和维护良好的治安环境。其次,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经验教训反思不足。群体性突发事件结束后,一些政府部门主要领导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工作中存在的失误,有时甚至把事件的发生归结于自己的官运不好,遇到这样棘手的矛盾。殊不知,事件的发生,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事实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仅仅是民众不满情绪压抑已久的一次发泄,事件本身的原因只是导火索而已。因此,我们如果仅满足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本身的处理,而没有继续着力去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消除民众心中的疑虑,提高政府公信力,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阻止下次类似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谣言危机的产生。
三、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控制策略
网络谣言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之间存在着多么紧密的联系。必然的,为了控制后者,也就必须留心前者。[2]P145政府部门必须针对网络谣言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谣言控制策略,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控制。
(一)网络谣言事前控制:完善应急预案,做好网络谣言预防。网络谣言事前控制是指在网络谣言未产生前所采取的各种相应的手段以防止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产生的活动。网络谣言一旦产生,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辟谣所产生的成本也将非常庞大,辟谣的效果也很难尽如人意,而且,“谣言是不可以消除的”,一旦谣言产生,那么反驳的一方永远处于防御的被动地位。因此,对网络谣言控制的最佳方式就是控制前置,防止网络谣言的产生。首先,始终保持政治敏感,及时化解信任危机。政府部门要始终保持对各地社会事件的关注,提高政治敏感性,及时发现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关联因素和由此形成的隐患,及时进行疏导和化解。政府部门领导要经常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困难,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事实上,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产生,并不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如果民众对政府不够信任,或是其它方面的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得到化解,民众压抑着的愤怒可能就会以另一种形式,或在另一个突发事件中爆发出来。因此,关注民生社会,了解民众的实际需要和困难,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对于控制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次,建立网络谣言预警机制,完善网络谣言应急预案。突发事件预警是应急管理的关键一环,预警为人们躲避和对抗突发事件提供基本依据,通过采取各种准备措施抗击危机从而避免或减少损害。在这个预警机制中,要有人或机构专门把网络谣言作为重要社会舆情加以关注,搜集相关的信息,并划分轻重缓急呈报给决策者;有专门的程序要求决策者对重要网络谣言传播进行评估,剔除过分夸大的成分,并作为决策中需要考虑的民意因素;要建立重大网络谣言及时汇报上报制度。在网络谣言预警机制建设中,最主要的是明确分工和责任,建立互相沟通协调机制,始终保持对网络谣言的关注,以便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二)网络谣言事中控制:加强网络监管,公开事实真相。网络谣言事中控制是指在网络谣言已经产生后对网络谣言进行相应的处理从而降低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负面影响的活动。网络谣言就像洪水,一旦形成,宜疏不宜堵。首先,加强网络监管力度,有效管控网络媒体。在继续倡导坚持党的新闻工作方针、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主流媒体的基础上,要加大对非主流媒体、新兴媒体尤其是网络的管理。公民有在网络等新兴媒体上发表言论的自由,但必须以不得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安全和他人正常生活等为前提。网络给我们的生活带许多便利,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民主法治的建设,但也总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唯恐天下不乱,利用部分网民的不理性暗中煽风点火,滋生事端,危害社会稳定。如乌鲁木齐“7·5事件”,正是在以民族分裂分子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煽动和指挥下,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多种渠道,造谣煽动,挑起事端,煽动民族仇恨,激怒不明真相的群众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管力度,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非常规手段予以控制。例如在“7.5事件”发生后,为防止事态进一步蔓延,有关部门切断了新疆对外的网络联系,进行网络管制与通讯管制。网络管制期间,“世维会”失去了向广大群众传播谣言的平台,同时也对不明真相的民众通过网络散布“恐怖谣言”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有效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其次,及时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公开事实真相。网络谣言产生于信息封锁,而止于信息公开。只要及时公开,主动回应,所有的网络谣言都将随风而散。恐慌、焦虑等心态为谣言的形成提供温床,信息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又为谣言的传播形成了市场。要想有效控制网络谣言的扩散,必须以一种快捷的方式,快速及时地公开事件真相,以消除民众的疑虑和恐慌心理,使人们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相关信息,并做出相应的行为调整与应对。政府是公共信息最大的拥有者和控制者,为了避免网络谣言产生后的被动不利地位,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通过各种主流媒体积极主动公开相关信息,满足公众“知”的需要,这种及时主动公开信息的方式,不仅可以对信息的相对选择发布,而且可以争取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三)网络谣言事后控制:认真总结反思,消除网络谣言影响。网络谣言事后控制是指在网络谣言终结阶段对由网络谣言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全面的总结分析,防止网络谣言死灰复燃,继续造成负面影响的活动。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平息后,政府部门要继续保持警惕,防止网络谣言危机卷土重来,同时认真做好总结,反思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在事件处置过程中存在问题,以便为下一步政府的工作赢得主动。首先,妥善做好后续工作,着力消除事件影响。即使群体性突发事件平息之后,如果麻痹大意,网络谣言仍有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如湖北石首“6.17”群体性事件,在事件得到平息之后的第二天,在网络上出现了“永隆大酒店又挖出尸体”的新谣言,导致当天数百群众再次向永隆大酒店聚集。因此,政府部门要做好后续相关工作,尽量消除网络谣言已经造成的影响,并防止新的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改善和缓和因网络谣言带来的官民紧张关系。另外,认真进行总结反思,吸取事件教训,反思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化解或缓和社会矛盾,消除网络谣言产生的隐患。总之,控制网络谣言最为根本的方法与途径,乃是优化社会主义政治环境,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所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增加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及时公开人们关心问题的真相,用执政为民的突出业绩来安定人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政府公信力,真正赢得民心,也才能更有效控制任何形式的网络谣言危机。其次,注重宣传引导,提高民众辨别能力。有国外研究学者指出:“即使人们不相信谣言,也会受其影响,反之,人们也可能受辟谣的反面影响,即使相信辟谣是真的。”[5]P251因此,卡普费雷称辟谣为“一门棘手的艺术”。[5]P247造谣容易辟谣难。有效辟谣建立在公众对网络谣言的理性分析上,应当着重培养公众理性,从根本上提高公民的文化道德水平和法制意识,尤其要加强对谣言易感人群的教育引导。目前的谣言易感人群主要包括离退休人员、老年人、社会闲散人员和出租车司机等等群体。对于这些群体,要着重加强教育引导,如通过各种媒介手段来谈如何看待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在社会制造一种理性思考的舆论氛围,逐渐启发、培养公众的理性,提高其对网络谣言本质、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对网络谣言的“免疫力”。同时要加强对全体公民的教育,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水平,增强对网络谣言的鉴别力,努力形成崇尚事实、反对网络谣言的社会氛围。
[1]〔法〕弗朗索瓦丝·勒莫.唐家龙译.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黄毅峰.谣言传播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J].理论与现代化,2010(3).
[5]邹建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Analysis of and Strategies for Controlling Online Rumors in Unexpected Mass Incidents
TAO Guo-gen HUANG Yi-feng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Public Management,Party School of the CPC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Nanchang,Jiangxi 330003,China)
Very closed associated with unexpected mass incidents,online rumors penetrate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unexpected mass incidents and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ir gestation,occurrence,evolution and termination.Analyzing the practice of dealing with online rumor crises,we can find that some local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re not enough sensitive and alert to online rumors,not enough active in leading the public opinion,and do not draw enough lessons from unexpected mass incidents.These not only cumber the successful settlement of unexpected mass incidents,but even sharpen the conflicts and aggravate these incidents.So the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must work out different strategies,increase the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online rumor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online rumor;unexpected mass incident;controlling strategies
C933
A
1674-0599(2011)03-0087-06
2011-03-15
陶国根(1982—),男,江西南昌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黄毅峰(1977—),男,江西南康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领导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群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及调控机制研究”(10CSH041)、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10年)规划项目“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分析及其控制机制研究”(10SH4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朱文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