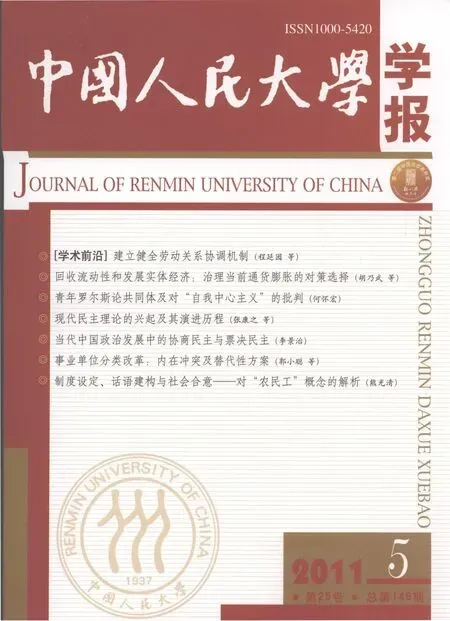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现状与问题
2011-02-09李丽林袁青川
李丽林 袁青川
所谓三方协商,是指国家(通常以政府作为代表)、雇主和工人之间,就制定或实施社会政策而进行的所有交往,也称为“三方合作”、“三方关系”或者“三方性”。[1]而三方协商机制则是一种协调劳动关系主体不同利益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早在1848年就开始在法国出现,经过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 r O rganization,以下简称ILO)的大力提倡,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劳工标准,逐渐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逐渐融入世界潮流之中,也开始尝试采用三方协商机制来解决劳动关系问题。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主要由政府主导的三方协商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尚处于争论之中,需要根据社会需要适当扩大其职能,协调好劳动关系。
一
三方协调机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一些国家为了有效处理劳资纠纷开始创建三方协商机构。法国早在1848年成立了一个劳动咨询委员会,使工人有机会参与政府有关政策的制定过程。因为开会的地点为卢森堡,因而也被称为卢森堡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困扰,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开始寻求雇主和工会的合作,设置了一些三方协商机构。20世纪的20年代,在一些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为了解决劳动争议,政府开始与工会或(和)雇主达成某些两方或三方协议。随后,引进三方协商机制的国家越来越多。[2]
三方协商机制的发展得益于ILO多年来的努力。1944年,ILO发表了《费城宣言》,重新定义了ILO的目标和宗旨,宣称ILO有“庄严的义务……推进……各种计划,以达到……工人和雇主在制定与实施社会经济措施方面的合作”。现在,“加强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仍然是ILO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
ILO推行三方协商机制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有关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使其形成一种国际劳工标准在世界各个国家实行。1960年,ILO通过了《产业和国家一级公共权力机构与雇主和工人组织协商与合作建议书》(第113号),建议各国在国家及产业层面建立三方协商机制。此后,ILO又在1976年通过了《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144号)和(国际劳工组织活动)三方协商建议书(第152号)。
ILO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关注三方协商的问题。在1996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国家一级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三方协商”问题被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各方就经济和社会决策中加强三方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在2000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三方协商问题再次被列入议事日程。2002年,ILO就三方协商和社会对话提出了解决方案。2008年,第97次劳工大会通过了《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在宣言中,ILO明确指出,社会对话和三方性(安排)是促进良好的劳动关系、加大劳动法的实施效果等工作的最适宜的方法。ILO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在谈到三方协商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时曾经这样说过:“在所有的地区,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社会对话与三方协商的价值。当政府和社会伙伴们一起设计政策应对这场危机时,这些制度具有更加特别的价值。”
此外,ILO还通过其他一些手段促进三方协商在各国的发展。这些手段有调查研究、信息传播、技术性会议、技术性咨询服务或技术合作。近年来,ILO在以下问题上都开展了类似的活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护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等。
截止到2011年6月30日,批准144号国际劳工公约的国家有131个,约占ILO成员国的72%。这些国家遍布全世界,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加蓬等欠发达国家。在亚洲,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等国家都批准了该公约。虽然在180多部国际劳工公约中,我国只批准了25部,但144号公约正在其中。我国在1990年就批准了144号有关三方协商的国际劳工公约。
按照144号公约的规定,凡批准该公约的国家,都“承诺运用各种程序保证就……有关事宜,在政府、雇主和工人的代表之间进行有效协商”。毫无疑问,有些国家虽然没有批准144号公约,但也设置了某些机构和程序,进行了有效的三方协商。例如,新加坡在1972年已经设立了“全国工资理事会”(NWC)这样的三方机构,但直到2010年4月才批准了144号公约。因此,可以说,三方协商机制是一种在世界各国被普遍采用的制度。
各国采用三方协商机制的形式可以分为两大类:最主要的一类是正式的机制,有常设的机构,通过正式的协商会议协调劳动关系;另外一类是非正式的机制,为了处理某个问题或者某个事件而成立临时机构,进行三方协商。
在那些采取正式的三方协商机制的国家,协商机构的设置存在较大的差别。在一些转型国家,以及一些在ILO推动下建立三方协商机制时间较短的国家,通常以某个正式的机构为主进行三方协商。[3]而在那些拥有三方协商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则可能存在多个三方协商机构。例如法国,既有讨论和协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也有一些针对具体问题而成立的专门的三方协商机构:国家集体谈判委员会,中央就业委员会,个体争议产业法庭中央委员会,职业教育、社会进步和就业中央委员会等等。日本在1946年成立了劳动委员会,由中央劳动委员会、地方劳动委员会(共47个)组成;在1970年还成立了“产业和劳动圆桌会议”,讨论工资、价格、就业和劳动权利等问题。由于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日本于1979年开始召开“就业问题政策会议”,三方针对就业政策、技术变革等方面问题交换意见。另外,日本在劳动部、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等部委及机构还成立了一些委员会,处理特定问题,例如职业培训、残疾人、家庭务工人员等问题。[4]
在有些国家,正式的三方机构还设置了分支机构或者专门的委员会。例如,奥地利的价格和工资联合委员会,在价格、工资及其他国际问题方面成立了分支委员会。匈牙利的利益协调委员会设有下面一些专门委员会:经济协商、收入政策、工资和劳工、劳动力市场、社会政策、信息委员会等。[5]
非正式的三方协商机制在各个国家都可能存在。在西班牙,从1977年至1987年的后佛朗哥时期,三方合作的主要形式就是签订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契约。20世纪8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首次召开全国性的经济首脑会议,使澳大利亚开始使用协调发展的经济政策。澳大利亚劳动党和澳大利亚总工会在1983年劳动党选举前签署了协议,该协议倡议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地区建立三方协商机制。
美国虽然没有正式的三方协商机构,但一直有一些非正式的组织在活动。美国著名的劳动关系专家约翰·邓洛普在1974—1975年担任劳工部长时成立了峰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他离任数年后依然在私人赞助下运行着,邓洛普出任了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主要讨论的是集体谈判之外的各种劳工政策问题。1985年,前任劳工部副部长马尔克姆·洛弗尔(M alcolm Lovell)建立了由工会领袖和企业界领袖组成的集体谈判论坛,这个组织一直存在,经常讨论改善集体谈判的长远战略。1993年,克林顿首次执政的时候有意打破在劳工政策上为时甚久的僵局,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名为“劳资关系的未来委员会”,也称为邓洛普委员会,因为约翰·邓洛普担任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创设的目的就是要探讨更新美国的劳工政策,设法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和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6]
一般而言,三方机构通常包括来自三方的成员,即工人组织的代表、雇主组织的代表和政府部门的代表。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就业问题,为此在1998年成立了“就业政策三方委员会”,参与协商的有来自雇主方的日经联、工会方连合的最高领导人和日本内阁的主要成员。[7]
由于许多国家存在多个总工会和多个雇主协会,因此,参与三方协商的工会和雇主方的组织可能有很多个。例如,韩国1998年成立的“三方委员会”,其参与者包括政府成员、三大政党成员、两大雇主组织的人员以及两个最主要的工会联盟的成员。[8]
三方协商委员会中经常会包括“独立的专家”(例如意大利、荷兰)以及经济和社会利益以外的其他劳动和资本的代表。例如,西班牙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虽然是三方机构,但也有一些转变。它包括三个群体的代表:前两个是工会和雇主机构,第三个是由一系列其他利益群体(农业、渔业、消费者、合作社)的代表和专家组成。日本设有数量众多的咨询委员会,例如中央劳工标准委员会和中央就业稳定委员会,参加这些委员会的除了日经联和连合的代表,第三方并不是来自政府部门的人员,而是一些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士,有大学教授和律师。韩国也有类似的安排。韩国的劳动法审核委员会包括来自韩国总工会(FKTU)的三名成员,来自韩国雇主协会(KEF)的三名成员,另外还有十名专家,也是由大学教授和律师组成。[9]
随着社会对话或者说三方协商的范围越来越广,从政府这个主体看,很多国家不再单独由负责劳动事务的政府部门充当政府的代表,还有其他的部委加入,例如财政部、教育与培训部门以及商业部等。在奥地利的工资和价格联系委员会中,政府代表来自农业部、经济事务部和社会事务部。澳大利亚的发展建议委员会就包括财政部的代表。喀麦隆的新的国家劳动咨询委员会包括国家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国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的代表,另外还有雇员、雇主的代表和劳动部。在津巴布韦,财政、商业、工业、采矿、农业等部门的代表也参加劳动咨询委员会。在有的国家,参加社会对话的不仅有相关部委的部长,甚至国家元首也参加协商会议,爱尔兰就是这样,日本也有这样的做法,即由首相或者副首相参加三方会议。
由于各国非工会化部门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需要吸收NGO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利益群体,例如妇女组织、青年和失业者组织的参与。一些国家已经把农民(例如比利时、印度、西班牙)、小企业的业主或是从事某些职业的人员(如比利时、荷兰)、自由职业者(如法国)、合作社的代表(如丹麦、葡萄牙)、社会团体的人员(如澳大利亚)、消费群体(如丹麦、西班牙)、环境协会(如葡萄牙)以及家庭协会的人员(如法国、葡萄牙)等吸收到三方会议中。因此,和“三方”合作相比,这种经济和社会机构更应该称为“多方”合作。[10]
二
世界各国如此广泛地应用三方协商机制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劳动关系问题,是因为在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中,需要三方协商机制来协调劳动关系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劳动关系的基本理论中,劳动关系的主体由“三方”构成,即劳方、资方和有关的政府机构。约翰·邓洛普认为,劳方这个主体包括非管理人员的雇员及其代表组织工会;资方是各级管理人员及其代表雇主协会;有关的政府机构不仅是劳动行政部门,更包括代表国家意志的立法和司法机关。[11]国际劳工组织是这一三方性的最好说明。各成员国的代表团由劳、资、政三方组成,三方都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机构,独立表决。
更重要的是,劳动关系的三方主体所追求的目标并不相同,利益也不完全一样。哈里·凯兹和托马斯·寇肯就明确指出,劳资之间从根本上存在利益冲突,他们拥有“不同的经济利益”。这种观点在劳动关系理论中被称之为多元论,是劳动关系理论的主流,也可以说,它是劳动关系规范分析的基石。例如工资和福利,对工人来说是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的收益,而对于资方来说则是需要控制力求最小化的劳动成本。在引进新技术这样的具体事件上,劳方和资方的利益也可能产生矛盾。新技术的引进能让企业保持竞争力不被市场淘汰,但对工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着丧失工作岗位。因此,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平衡三方的利益。[12]
协调三方利益冲突的机制有很多种。根据参与方的数量可以划分为单方机制、双方机制以及三方机制。例如,劳动法即是政府这个主体单方面协调劳动关系的一种方式,而集体谈判机制是劳资双方协调劳动关系的最著名方式。
以三方机制协调劳动关系既反映了三方主体利益的差别,同时更说明了决策的民主思想:在决定某些人命运的过程中,应该允许那些受决策影响的主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力求在决策中体现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在政府就劳动问题的决策中,应该允许有关利益主体——劳方和资方参与其中。由于直接民主的方式成本太过高昂,所以劳资一般通过其代理人工会和雇主协会参与政府有关劳动问题的决策过程。政府通过三方协商进行决策虽然不得不放弃一些权力和便利,但可以换取劳方和资方对政府所实施政策的支持,实现社会和谐。通过三方协商,政府也可以把矛盾转移出去,让劳资团体共同分担和化解劳资冲突。
从三方机制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各国三方机制的引入是因为存在这些社会需要。在20世纪60年代,困扰很多国家的是通货膨胀问题,各国政府为控制物价而实行收入政策。这一政策肯定会影响到劳方和资方的利益,同时收入政策的有效实施也需要这两大利益主体的支持,因此,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就收入政策与劳方和资方进行了三方协商。例如,在丹麦和荷兰,工会接受了工资限制以协助抗击通货膨胀。[1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时劳工委员会这个三方机构的产生也是社会需要的结果。当时美国的形势严峻,既要保证战争所需的产品的产量,又要避免罢工,避免工资与物价的上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罗斯福政府于1942年成立了美国战时劳工委员会。战时劳工委员会是一个三方机构,包括劳方和资方代表,而委员会的主席是中立人士。这个机构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1942年到1945年,战时劳工委员会成功地解决了2万多起劳资纠纷。战时劳工委员会还利用它的各个办事处使集体谈判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战时劳工委员会还充当了培训机构,培养了许多带头的调解人、仲裁人和政府顾问。这些人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对集体谈判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美国式的集体谈判模式,一种政府直接干预很少的谈判模式。[14]
1997年,韩国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解决方案引发了裁员潮和大规模失业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韩国政府和韩国的雇主及工会组织进行了三方协商,并且于1998年1月15日签署了“社会契约”。政府和雇主方承认工人的基本权利,承诺采取一些社会保护措施,而劳方同意削减工资并且在雇佣上给予资方一些灵活性,接受新的解雇制度。这份社会契约被认为对韩国经济的复苏起了重要作用。[15]
三方协商机制在今日的中国具有其他制度无法取代的作用。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我国已经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开始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在未来的若干年,我国还必须走完工业化的过程。转型时期的特点是新问题层出不穷,却没有既定的法律对这些问题进行规范,因为法律具有明显的延迟性。只有当一个新问题成为普遍性的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已经找到有效的处理方法时,才可能经由法律将这一处理方法强制在全国推行。很多劳动关系学者推崇集体谈判制度,认为它可以平衡劳资力量的不对等,改变“强资本,弱劳动”的态势,但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有赖于工会在企业层面的独立,工会能形成一种与资方力量相抗衡的集体力量。集体谈判的本质是一种双方的决策。而协商包括信息的分享、意见的咨询、利益的表达,有时候也能做到共同决策。集体谈判通常有明确的谈判事宜,例如工资或者工时等,而协商的主题却可以多种多样,其形式也多种多样。可以说,灵活性赋予协商更强的生命力。如果协商都无法进行,又何来谈判?
三
我国的三方协商机制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1986年劳动制度开始改革,劳动关系多元利益分化逐渐明显。在“砸三铁”、“优化劳动组合”、“国有企业改制”、“裁员”等多项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体制改革措施中,劳资冲突逐渐显性化。一些省市为了缓和劳资矛盾,首先尝试通过三方协商机制来协调劳动关系。这些敢开先河的省市是山东、山西和辽宁等。[16]例如,1998年,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为了解决在企业转轨中出现的问题,建立了一个由政府、工会和企业组成的稽查机制。
1990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ILO的《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我国遵守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在修订的《工会法》第34条第二款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为三方协商机制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2001年8月3日,“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我国开始在国家层面建立正式的三方协商机制。随后,各地在省、县甚至街道等各个层面纷纷创建三方协商机构。到2009年底,全国已经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1.4万个。其中,省级31个,地级313个,县级2 531个,县及县级以上地方共建立三方协调机制2 875个。[17]
在国家层面上,我国建立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三方组成。三方各自确定相对固定的机构负责人作为三方会议成员,不定期召开会议。自2001年到2011年6月底,共召开过15次会议。国家三方会议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原来在劳动工资司)设立了办公室,负责三方会议的日常工作,并于2006年决定成立劳动关系法律政策研究委员会、薪酬咨询委员会、集体协商指导委员会、社会保障政策咨询委员会以及劳动标准研究委员会五个专业委员会。但这些专业委员会并没有实际运行。
十年来,国家三方会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作用:
首先,推动了我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发展。国家三方会议在前13次会议中有10次会议涉及集体协商问题。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三方分别就《集体协商规则(草案)》征求了修改意见,在第四次会议上提交讨论,达成基本共识。会议原则通过了《集体协商规则》。三方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通知》、《关于贯彻实施〈集体合同规定〉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其次,三方为一些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提供了意见和建议。这些法律法规包括《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最低工资规定》、《集体合同规定》等。[18]
第三,推动各地进行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与工业园区的活动。这一活动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是我国的三方协商机制搞得最热烈、最受欢迎的一项活动。这一活动弘扬了先进,客观上对协调劳动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建立了信息分享制度。国家三方会议办公室不仅在会后编写《会议纪要》抄送有关各方,还定期编写《信息交流》,介绍各地落实国家三方会议精神、推行各种措施的情况等。例如,在第15期的《信息交流》上,先介绍了福建、北京、江苏、河北、广东等地“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的工作意见”,然后是苏州、连云港的一些具体做法,最后重点介绍了吉林省总工会开展的“共同约定”行动。这些信息的分享有助于各地建立健全三方协商机制,互相学习借鉴。[19]
地方的三方会议相较于国家层面的制度更具有灵活性。参加三方协商的主体除了劳动行政部门、企联/企协以及工会外,在一些地方也有国资委、经委等机构代表资方参与协商,如宝鸡市。辽宁省把工商联和外企协会纳入资方代表中。在上海市,法院始终参与劳动关系的协调工作。在上海市的区一级三方协商会议上,有一些著名的企业家代表资方参加。在宝鸡市,三方办公室设在劳动保障局的法规科。陕西省成立了劳动关系协调领导小组,由主管副省长担任组长。在很多地方,三方会议定期召开,如广东、西安、辽阳等地。
地方的三方会议也更有实效。在一些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要经过三方会议的讨论通过。笔者到陕西省调研时,有关方面介绍说,2008年在陕西省第七次三方会议上,各方就最低工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会上还发生了激烈争论。广州市的三方会议对最低工资标准要先进行协商,然后由政府颁布,协商过程中三方辩论激烈。上海市的三方协商机制作用之一是化解和预防重大的劳动纠纷,在一些欠薪案件中,三方协商机制有效地化解了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正式的三方协调会议,在我国还存在一些准三方协商机制。第一种是多方参与的协商制度,例如山东省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参与会议的除了党政机关、工会外,还有团委、妇联、人行等机构和组织。类似的还有“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第二种是政府与同级工会组织召开的联席会议,这些会议由省长或主管副省长主持召开,议题广泛,涉及从支持工会工作到就业、最低生活保障、民主管理等多方面问题。与三方协商机制不同的是,这些联席会议一般没有雇主协会的代表参与。
四
我国三方协商机制的建设明显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20][21]它沿袭了政府主导的协调劳动关系的传统方式,在劳方和资方的代表组织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职能过窄,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不能有效协调劳动关系主体的不同利益。
在我国的三方协商机制中,政府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三方会议“由政府部门的执行主席牵头(主持会议)”,办公室设在政府部门。因此,三方会议的工作,从计划到落实再到最后的总结,都由政府部门主导。三方协商会议讨论的议题,如集体协商、和谐企业、劳动监察等等,都是政府所定义的“劳动关系”工作,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三方办公室所在的司局要开展的相关工作。在多方或政府与工会的联席会议中,政府的主导性更加明显,既没有资方代表参与,劳方代表的人数与政府人员相比也少得可怜。
政府的主导性得以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劳资代表组织的不完善,其独立性与代表性都受到了质疑。[22]《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参与协商的“代表性组织”是指“享有结社自由权利”的雇主和工人组织。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劳动问题专家将结社自由视为三方协商的基本条件。雇主和工人组织只有在具有“代表性”的前提下,才能够代表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行事,三方协商的结果才能够经由这些组织贯彻执行下去。
然而,我国的工会依然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本职能没有进行改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劳动制度,劳动者的就业待遇和就业条件由国家统一决定,使工会丧失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必要性,仅成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一角色的基本定位并没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发生改变。在2008年修正的《中国工会章程》中,仍然保留着“桥梁和纽带”的用语。虽然工会宣称自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但基层工会的建立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各级工会领导人的任免绝少取决于会员的意志。有些工会主席虽然通过选举产生,但选举仍流于形式。在工人与企业的劳动争议中,还能见到在一些案例中工会主席充当企业方代表的事例出现。陈峰教授用“四方”来表达工会与会员关系的割裂,很具有说服力。[23]
在国家三方协商机制中仅由企联/企协充当雇主组织的代表也是不足的。企联/企协的成员多为国有企业,其领导人员多为退休的主管过经济工作的政府官员。由于其性质确定为“非营利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法人”、“国际雇主组织的中国唯一代表”,其资金来源受到很大限制,影响了它的协商能力。多年来,另外一个组织——工商联一直在谋求成为雇主组织的代表,能够参加国家三方会议。在2011年5月召开的“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第一次执行主席会议”上,三方已经原则上同意增加工商联作为雇主代表参加三方会议。工商联的加入能弥补企联在私营企业上的代表性,但对于成员企业的影响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雇主组织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另外,我国的三方协商机制已经从国家到街道在各个层面得以建立,但在县以及县以下的行政单位中,雇主组织普遍不健全,一些地方不得不用国资委、经贸委、个体企业协会等组织来代替。这样的“资方”代表如何与政府和工会进行平等协商呢?
工会或资方代表性不足会直接影响到三方协商机制的有效性。这一点世界各国均是如此。英国之所以对三方合作失去信心,部分原因是由于英国的总工会“不能成功地传达”三方协商的结果。[24]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工人组织的代表只有韩国总工会的人员,事实上,韩国在当时还有一个规模较小但比较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会联盟——韩国工会联合会。由于不能参加三方协商,韩国工会联合会对社会对话多持批评态度,直到1996年受邀参加韩国的产业关系改革委员会后,其态度才发生转变。承认韩国工会联合会是一个社会伙伴这一举措被韩国学者认为是韩国迈向真正的社会对话的一大进步。[25]
在我国也不断有学者质疑三方协商机制的实际成效。在国家层面上的三方会议,会期只有一天,开会的次数也没有按照最初的设计开满过四次或三次的会议。[26]从会议纪要看,这为期一天的会议每次都有三方领导人的讲话、工作汇报以及人员变动的说明,留给三方进行讨论和磋商的时间非常有限。以《劳动合同法》为例,在国家三方会议第十次会议的纪要中这样总结道:“三方积极主动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好有关立法工作,在修改《劳动合同法》草案、起草《劳动争议处理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媒体的报道却是“两大外商组织——欧盟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同时将各自的建议和意见递交给全国人大”,并且威胁“撤资”。国内的企业在无法发出声音的情况下,纷纷规避法律:华为公司出现了“辞职门”,中央电视台解雇了大批临时工,劳务派遣意外地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说明三方会议就《劳动合同法》的协商并不那么有效。
我国三方协商机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协商会议的职能过窄。在2008年制定的《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中具体说明了三方会议的工作内容,包括:推进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企业改制改组过程中的劳动关系;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劳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劳动争议的预防和处理;企业民主管理;工会组织和企业联合会组织的建设以及其他问题共七大项。一些重要的劳动关系问题并没有列入其中,例如就业问题、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等等。在三方会议的实际运作中,这些列入“制度”的项目还有很多项没有进行实质的协商。例如,在劳工标准中,除最低工资标准在某些地方的三方会议中进行过协商之外,其他如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保险福利待遇、职业技能培训等均无所作为。
从国家三方会议参会人员的构成中也能反映出协商会议的职能过窄的问题。政府方的参会人员在前12次会议中主要是三方协调办公室所在司局的人员。当三方办公室由劳动工资司更改为劳动关系司时,参会人员也随之变为主要是劳动关系司的人员了。在制度设计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除劳动关系司之外应该有“办公厅、法规司、调解仲裁管理司、劳动监察局、国际合作司等相关司局负责人”参加会议,但实际情况是从没有出现所有这些司局负责人同时出席会议的情况。[27]结果是,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不仅由政府主导,而且仅仅由政府中的劳动行政部门主导,进而由其中的劳动关系司主导,其效果可想而知。
如果对比国外的情况,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更加明显。有些国家最主要的三方协商组织名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委员会或者类似的名称。这类组织一般处理的是比较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例如,在奥地利,社会对话的领域包括收入政策、社会政策、物价与工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社会福利、劳动法、工作创造与培训、就业政策等。这些广泛的经济社会问题包括以下几类: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以及经济增长问题;经济结构的转变问题;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及财政政策;就业政策;性别平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生产率与经济竞争力;税收和财政政策;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与社会保护;处理来自外部压力要求改革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例如向市场经济转移、地区一体化、结构调整和减低贫困的政策等。[28]
很显然,我国三方协商机制所存在的问题根植于我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劳动制度进行全面改革,要对一些劳动法律法规进行修订。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然而,即便是在不改变现行的法律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我国的三方协商机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进行某些改革:
首先,适当调整三方会议办公室的设置单位,可以考虑将其放到具有综合行政职责的部门。因为劳动问题的解决可能涉及的不仅仅是劳动行政部门,还可能涉及财政、教育等多个部门。目前,该办公室全部为兼职人员,应当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拨付专门的经费,设立独立的人员编制。这样,也可以将三方协商的主题适当放宽到就业、工资等劳动问题上。
其次,对于政府在三方协商中主导性过强的问题,可以参照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让律师或者学者充当公众利益的代表,与劳方和资方的代表进行讨论和研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意见;也可以参照欧洲某些国家的做法,强化三方机制的研究能力。在开会讨论某些问题之前,应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调查研究,为三方的协商提供准确的事实和材料。
再次,适度强化高层面的三方协商功能,没有必要要求在各个层面都建立三方协商机制。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应当允许各地进行尝试,不必要求所有地方都遵循同一模式。
最后,在国家层面上,参加三方会议的人员没有必要事先作出明确的规定,应该根据所讨论的议题由各方自行确定参加会议的具体人员。如果各方能就有权参加投票的人数达成一致,对于各方参会人员的数量限制就没有必要遵循对等的原则。
总之,我国的三方协商机制尚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但它迈出了走向社会对话的第一步。我们相信,协调劳动关系主体利益冲突的社会需要必将促使它不断走向完善。
[1]国际劳工组织:《国家一级有关经济与社会政策的三方协商》,国际劳工大会第83届会议,报告六,国际劳工局,日内瓦,1996。
[2][5][13][24]Treblicock,Anne(ed.).Tow ards Social D ialogue:Tripartite Cooperation in N ational E-conom ic and Social Policy-m aking.Geneva,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1994.
[3]Ludek Rychil,Rainer Pritzer.“Social Dialogue at National Level in the EU Accession Countries”,wo rking paper,ILO,Geneva,2003.
[4][7]Suzuki,Akira.“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union Wage Coordination and Tripartite Dialogue in Japan”.Harry C.Katz,Wonduck Lee,and Joohee Lee.Ithaca(eds.).The New Structure of Labor Relations:Tripartism and Decentralization.New York:ILR Press,2004.
[6][14]哈里·C·卡茨:《集体谈判与产业关系概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8][9][15][25]Choi,Young-Ki.“Experiencesof Social Dialogue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in the Republic of Ko rea”.working paper,ILO,2000.
[10][28]Ishikawa,Junko.Key Features of N ational Social Dialogue:A Social Dialogue Resource Book.ILOGeneva,2003.
[11]Dunlop,John T.Industria l Relations Systems.Boston,Mas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3.
[12]约翰·巴德:《人性化的雇佣关系——效率、公平与发言权之间的平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20]乔健:《中国特色的三方协调机制:走向三方协商和社会对话的第一步》,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2)。
[17]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发展状况统计公报》,载《中国工运》,2010(5)。
[18]汪洋:《我国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现状、问题及改革思路》,载《经济研究参考》,2006(44)。
[19]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办公室编:《信息交流》第15期。
[21]Shen,Jie,Benson,John.“Tripartite Consultation in China:A First Step towards Collective Bargaining”.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2008,147(2/3).
[22]Simon Clarke,Chang-Hee Lee.“The Significance of Tripartite Consultation in China!”.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2008,Vol.9,No.2(Winter).
[23]Chen,Feng.“Trade Unions and the Quadripartite Processof Strike Settlement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010,201.
[26][27]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办公室编:《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纪要》(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