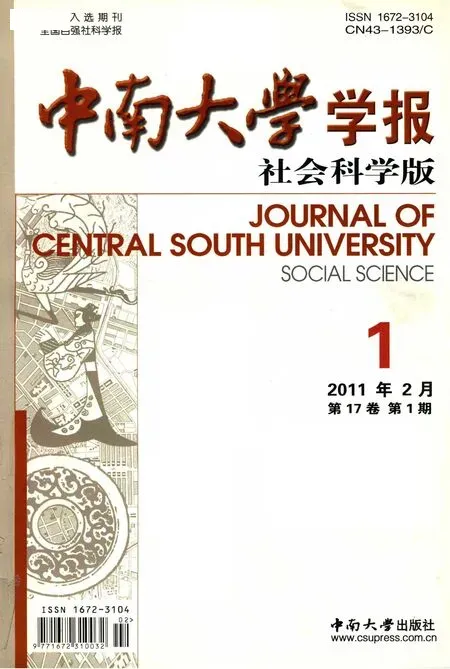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
2011-02-09罗显勇
罗显勇
(重庆大学电影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重庆,400044)
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
罗显勇
(重庆大学电影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重庆,400044)
台湾小说中的“酷儿书写”始于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等作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邱妙津、朱天文等为代表的新世代“酷儿”作家,一反传统“酷儿”书写的悲情和自恨,改以昂扬自信的笔调探索“酷儿”情欲和性别的游移流动,大胆描绘“酷儿”自身独特的性感经验,从“边缘”发声,挑战中心和权威,采取一种边缘化的写作策略,以“出走”的行动叛离中心找寻自己,以激烈的“自杀”的手段对中心提出抗议,以“谐拟”的方式来颠覆中心的建构。她们的“异端书写”,冲击了理性规约下的性别藩篱,并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在文本中呈现各种“酷异”的情欲状态的组合和迷乱的身份认同,在充分开放的情欲场域中,凸显出汉语写作中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长期潜伏着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特质。
台湾小说;白先勇;邱妙津;朱天文;“酷儿书写”;文学革命;“现代性”
一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王德威在他的著名论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提出的晚清文学中“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一段时期以来颇受学界注目。王德威对“五四”以来形成的单一现代性,线性前进的时间观和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史观提出批评,他认为自太平天国前后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间的晚清文学,历来一直被视为传统逝去的尾声,或西学东渐的先兆,对其定位均在其向现代文学的开端即五四“文学革命”发展的过渡性意义。而晚清,则是一个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存在着太多的蜕变可能,这些可能性相互角力与竞争,体现在文学中,便是晚清小说中千奇百怪的创作实践所体现出来的多重现代性。这一时期的文学体现出众声喧哗、多声复调的特点,不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充满种种实验冲动、与丰沛的创造力,而且在文学生产的诸方面均透显出现代性的多重可能,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蔚成大国的晚清小说中;然而,“五四”以后,“感时忧国”的写实主义传统的确立,逐渐窄化并压抑了晚清文学中的种种现代性的释放,同时也不断压抑着“五四”及30年代以来的种种“不入流”的文艺实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因此,需要对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1]。
王德威的这一论说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现代性”、“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有何特殊之处”等重要的学术命题。本文拟从反思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成因、蔚然成风、以及酷儿小说家的艺术创作心理出发,论述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特质以及面临的种种艺术上的缺憾。笔者认为,台湾小说中的“酷儿书写”其实是汉语写作中“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被压抑的现代性”隐讳而曲折的流露,当台湾“酷儿书写”以新词语和新意义出现,不仅在话语领域引起冲突和波澜,而且经过种种中介进入社会实践,甚而成为社会变动的思想动力,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
台湾小说中的“酷儿书写”,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白先勇的《月梦》《青春》《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等小说中进行了尝试,而后林怀民的《蝉》、李昂的《回顾》《莫春》、朱天心的《浪淘沙》《春风蝴蝶之事》、白先勇的《孽子》、玄小佛的《圆之外》、光泰的《逃避婚姻的人》《青涩的爱》等小说对“酷儿”主体性特质进行了大胆的书写。但是整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台湾小说中的“酷儿书写”,不管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显得单薄,即使是最负盛名的男性“酷儿”经典小说《孽子》虽然在发表的当时曾经引起台湾社会文化心理的强烈震撼,但囿于当时保守的社会舆论,对《孽子》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家庭伦理、父子关系、青少年成长等主题或现代主义叙事与美学形成的探讨[2],而小说中暗含的“酷儿”情欲、性别操演等主体性意识,则被评论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风潮。李慧敏的《开刀》、凌烟的《失声画眉》、李岳华的《红颜男子》、曹丽娟的《童女之舞》《关于白发以及其他》、林裕翼的《白雪公主》、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苏伟贞的《沉默之岛》、董启章的《安卓珍尼》《双身》、纪大伟的《膜》《牙齿》、邱妙津的《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杜修兰的《逆女》、朱勤的《花影:男性版》、张亦狥的《淫人妻女》等“酷儿”小说在官方所设的文学奖中频频获奖,暗示了一种新的创作风潮——对主流价值观的颠覆挑衅的禁忌性书写、对“酷儿”自身主体性存在的边缘化情欲书写——得到了主流文学的承认与接纳。
“酷儿”一词来自英文“queer”,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张小虹等人译作“怪胎”;台湾大学外文系就读的洪凌与纪大伟将之译做“酷儿”。“酷儿”一词的出现,带动了对“queer”或“queerness”的讨论,翻译者们对“酷儿”内涵和外延之理解、与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殊的性别政治观,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出现的最重要的一份民间文化研究刊物——《岛屿边缘》中有过详细的论述。在台湾,“酷儿”这个跨国、跨地域的文化现象与研究倾向,几乎全面地形塑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字快感。
在西方理论界,“酷儿”最早出现在著名女权主义者劳瑞蒂思提出“酷儿理论”的概念之中,在1991年《差异》杂志的一期讨论“酷儿理论”专号里,首先使用“酷儿”这一用语的劳瑞蒂思认为,“酷儿”如今已不再被视为一种游离于主流的固定的性形式之外的边缘现象,不再被视为旧式病理模式所谓的正常性欲的变异,也不再被视为多元主义之外的对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酷儿”已被重新定义为他们自身权利的性与文化的形式,虽然它还没有被定型,还不得不依赖现存的话语形式。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登上历史舞台的女权运动和“酷儿”运动对“权力”形成了一种反叛,对“把个人定义为某种特殊身份并固定在某种社会地位上”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
人们在“酷儿”运动或“酷儿理论”的研究中,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的“常态”“主流”的挑战。在他们看来,“酷儿”是极激进的一种策略,特别是提倡大声自豪的公开现身在所有人面前,并且挑战任何主流霸权,这一挑战“主流”“常态”的策略行为其实也同时挑战了中心、权威的单一认同取向。从福柯的《性史》到其他结构主义学者的研究累积,松动了原本僵化已久的二元对立思想,对于性及性别的思考注入多元性,“酷儿理论”的出现及发展更是为学术圈中性别研究去边缘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世代的台湾“酷儿”们拒绝任何狭义的身份认同,而是主张:我是酷儿,我在边缘与主流之间游移;我拒绝任何既有的分类,我不要你的认可,别在我的面前,我们酷儿自然会站在你面前。
台湾自中日甲午战争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惨痛的历史经历也正是现代台湾民众‘亚细亚孤儿’悲情意识产生的历史根源。”[3]这种“亚细亚孤儿”悲情意识逐渐被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台湾社会中普遍显出的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所冲淡。在社会运动、学术研究及论述圈中,许多先前受到压抑的运动与族群都纷纷抬头,并逐渐巩固各自的身份认同与发言空间,因而一连串有关主体性的研究风潮就此展开,从女性主义、酷儿研究到性别议题、后殖民主义等研究都在强调认同与主体的重要性。在这个新的研究思潮里,台湾的“酷儿”社群在文学、电影、戏剧和学术领域方面尤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台湾的“酷儿”运动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以及学院论述与社会运动的结合,逐步从个人情欲的私领域将认同政治议题转向公共领域。台湾的“酷儿”研究在大量学习西方理念后,杂糅了东方及台湾本土经验模式,形成在台湾的社会运动史上有异于其他社会运动的模式,讨论的层次已经不在于欧美的思潮究竟是否适用于台湾社会,而是台湾的酷儿研究在台湾的可能性——在这块美丽之岛的边缘土壤中孕育的酷儿,正在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展现其神秘之姿。
二
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酷儿”小说不仅自视“酷儿”主体的边缘化,更试图表达出对于父权中心的反抗,即对现存真理、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化与历史的形成脉络、性别认定的二元对立、经典的树立等的反抗。面对如此封闭的父权中心,台湾的“酷儿”作家采取一种边缘化的写作以对抗中心的策略,即以书写青春的耽美、沉沦,试图叛离中心找寻自己,以激烈的“自杀”的手段来缅怀漂浪的青春及游移的灵魂,从而对中心提出抗议,并以“谐拟”的方式来颠覆中心的建构,甚而以“酷儿”的性别操演、自觉的主体意识策略性“攻占”父权中心位置。
1994年获得第一届中国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并且入选当年中国时报开卷版年度十大好书的朱天文的长篇小说《荒人手记》书写了一个年届四十的“男性酷儿”的身份发声,作者以深入灵魂的笔触探索男性酷儿小昭的挣扎、认同、忏悔与救赎。朱天文曾表示,以小昭这样一个年老色衰,而又屡屡为情欲所困扰的男子为小说创作的对象,其目的是探讨女性的情色问题。“诚如某些论者指出的,《荒人手记》虽然标榜写情欲,其实却是彻底的反情欲的。”[4]正因为这种反情欲的情欲“意念”主导了写作,使得全书通篇未曾让肉欲赤裸裸地以它本来的面目呈现,总是被刻意的规避,化为美感意境。于是在《荒人手记》中,肉欲被转化为情欲,再被化为一幕幕唯美的色境。叙述者小昭以一个阴性化的男性酷儿现身,集“男性的肉身/阴性的灵魂”于一体。他自觉是一朵阴性的灵魂装在阳性的身躯里,其精神活动充满了阴性特质。小昭认为,被凝视的阴性,与被凝视的阳性,并存于酷儿身上。因此,由于酷儿对美的崇拜与耽溺,他们都有受虐和耽美的倾向,为了避免不再受到伤害,他们不再付出感情。在小昭困陷于身份的认同迷宫找不到停靠的港湾时,另一位激进的酷儿阿尧已参加台湾酷儿运动多年,是一个快乐的男子,在生存哲学中采取了一种战斗的姿态。而只想与自己的恋人永桔白头偕老的小昭则被阿尧的激进、愤懑吓坏,更惊骇于阿尧年龄老大却依然纵欲、挥霍。小昭则回归传统、社会规约。作者用一种明净的笔致,来写最肉感、最情色的内容。对小昭而言,全然逐色于固有的伦理道德规范之外的肉体行乐,是一种道德的罪恶、信仰的崩塌。但自己却又陷入了不由自主的寻求肉欲的满足与激情过后的无边空虚的两难处境。因此,对小昭来说,思考肉欲自身的价值是超越精神困境之所在:肉欲本身并非价值所在,甚至是某种价值之否定。内外的分裂及其相互否定造成了巨大的存在张力,在连串的否定之后,小昭冀求辨证的融合以超越存在的困境,攫获价值以达致救赎。
《荒人手记》透过小昭歌咏阴性美学,以“耽美”来理解男性酷儿圈“残酷”的情欲生态,虽然对此生态小昭颇不以为然,但它彰显了男性酷儿的爱情游戏,绝不同于主流社会中的男、女的权力和宰制关系,同时以此挑战主流社会对于阴性、女性的贬抑,并为男性酷儿的正当性伸张、正名。而相对于《荒人手记》,邱妙津《鳄鱼手记》中的叙述者拉子(在台湾女性酷儿以“拉子”自许)则是“男性化的女性酷儿”。拉子虽然似乎比小昭激进、愤懑,但却比小昭更受困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而陷入身份的认同迷宫。自怜、自恋的小昭,尚能沉湎于心灵的一角做一个沉思的男性酷儿,并展现其阴性美学的魅力,但是拉子自苦、自恨、自残,她以“男性化的女性酷儿”身份建构女性酷儿的主体,而将“女性化的女性酷儿”视为传统社会体制下的“正常人”,认为“女性化的女性酷儿”们终将回到主流社会传统婚姻的“正常”轨道,于是狠心拒绝自己的情人——“女性化的女性酷儿”水伶的爱并将她赶回“正常的”父权世界的那一边去结婚生子,她在写给水伶的信上剖析道,“男性化的女性酷儿”与“女性化的女性酷儿”在主流社会的处境大不相同,作为“女性化的女性酷儿”的水伶仍是社会烙印之下的“正常”女性,水伶给予拉子的爱仍是一种阴性的母体之爱。因此,以“男性化的女性酷儿”身份出现的拉子却始终无法超越两人之间的爱情,遂绝决地把“女性化的女性酷儿”水伶“驱赶”至父权世界以改变水伶“喜欢女人”的“谬误”,但是水伶却在失恋后选择了一个代替拉子的“女人”,而非拉子一厢情愿所以为的“男人”。这彻底打破了主流社会的婚恋可以“治愈”水伶的迷思。然而,拉子虽内化了主流社会婚恋的观点,但在情欲的选择上却叛离传统的主流社会婚恋的机制,致使拉子绝望、怨恨,这正是她爱欲间充满矛盾扭曲之所在。
面对强势的父权中心,传统的酷儿们如小昭、拉子等躲在社会阴暗的角落以“边缘人”的身份发出“边缘”的声音是一种消极而温和的抵抗方式。不过,也有以激烈如“自戕”的手段,来表示对于父权中心的愤恨与不满。“由于怀才,所以遭谤,女性作者在古代社会倍受委曲。”[5]台湾新世代的女作家不满于女性作者在父权社会中遭受的禁锢,遂以一种桀骜不驯的姿态来书写女人彼此间的情感连结与欲望流动,她们书写青春的凄美、漂泊,灵魂的游离与无所归依,她们的“现代性”书写,展示了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一种“漂泊离散”(diaspera)世界情感。
台湾作家纪大伟曾详细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作家“酷儿”书写中展现出的“漂泊离散”的情结。纪大伟指出,一个人性爱对象的选择,不只是单纯个人的心理认同或心理防卫,同时也是社会抗争、历史压力、文化禁制下的产物,它与其他社会上种种的意识形态一直是纠缠不清的。现代酷儿的“漂泊离散”情结并不全然是出自个人意愿的自由选择,其中社会对于个人的掌控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现代酷儿的“漂泊离散”情结并非决定于离开家园与否。而内化于心的流放漂浪之感,更甚于外在的放逐形式。
在杜修兰的小说《逆女》中,詹清清与丁天使两人相爱却得躲躲藏藏,喜欢一个人却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出来,甚至还要制造出有男生追求、有男朋友的假象,唯一的理由就是害怕“酷儿”身份被拆穿,害怕社会歧视的眼光,即使不识字如丁天使的母亲,虽然不明白什么是“酷儿”,不清楚它被社会如何定位,但是从小到大所被教导、被灌输的父权思维仍然让丁母觉得“酷儿”听起来好像脏兮兮的,丁母尚且如此,何况深受父权文化教养、熏陶的其他社会精英及大众呢?
最后,詹清清与丁天使被勒令退学,在这些人的认知中,“酷儿”不仅会“破坏校誉”,而且就像是一种“传染病”,会不断地传染开来,所有人无不恐惧害怕到了极点,所以必除之而后快。辅导员像是押犯人一样押着詹清清与丁天使穿过校园,一路上的同学,不认识她们的是讶异,认识她们的是鄙夷,周围同学的那一双双的眼、那一张张的脸,无法看清,却又仿佛可以感觉到会随时逼近啐一口唾沫到这两个相互爱恋的女子的脸上。这种无形的、道德上的批评与歧视甚至胜过于法律的制裁,不必经过审判就能宣告罪行,是比死刑更残酷的无期徒刑。
越是被排挤、孤立,两人就越是只能紧紧相依,相互取暖,彼此的不安全感,遂用性来试探两人对爱的真诚度,以自己的身体作承诺。然而,身份一旦被揭穿,就连相互取暖这简单的“奢望”都将被剥夺。被退学后的詹清清开始变得精神不稳定,最后选择以割腕自杀来结束她年轻的生命,在遗言中,她愤怒地对父权社会提出最严格而凄厉的怒吼,“我们并不伤害别人,为什么他们却要伤害我们?”
詹清清与丁天使面对的是一场文明与蛮荒的战争:女人要摆脱父权的压制,不但女人必须反抗男人的宰制,更要女人可以看见彼此间的情感连结与欲望流动。倘若女人不能够独立于男人自我生存的话,不可避免地将一再重演女性在父权下的“就擒”和“就范”的过程。因此,詹清清与丁天使在追寻、肯定女人彼此间的情感连结与欲望流动的同时,也是在找寻自我的定位。它预演了女性在自生自保的要求下,是可能独立于男性而生存的,女人应该认同女人,而此种认同包含了情欲、性欲、政治……等等。詹清清与丁天使不满于主流社会塑造出来的女性角色、女性形象,那不是女性真正的自己,于是选择割腕自杀来结束年轻的生命,这无疑是对于父权社会“男欢女爱”的最大挑衅与挑战。
三
邱妙津在《鳄鱼手记》中自恨而悲情的书写笔调,不仅为作品抹上了浓厚、沉重得近乎喘不过气的悲剧色彩,同时更指涉父权社会对“酷儿”的无知、恐惧、压迫和窥视的心态。在作者的另一部小说《蒙马特遗书》中,叙述者近乎自虐的自我告白亦令人感到震撼与惊悚。《蒙马特遗书》引用了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亚历山大大帝》中一个典型的乱伦情节:亚历山大从小爱他的母亲,后来和母亲结婚,母亲穿着一袭白色新娘礼服因反抗集权政治被枪杀,亚历山大一生只爱这个女人。对叙述者而言,也许她不曾意识到这个画面的乱伦暗喻,但她却不由自主被它吸引,而致命的吸引力则来自于对父权秩序及弗洛伊德男性沙文主义式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拒绝,但是一方面她又坚持“清规戒律”的存在,无法冲破心灵的束缚而痛苦不已。从《鳄鱼手记》因为不能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而衍生自残、自恨的情绪,到《蒙马特遗书》作者与叙述者的完全重合无间,我们看到作者的心理纠结因为感情的重击而一步步地盘根错节,终至自成封闭体系的状态,在作者看来,死者的阴影仿如幽灵笼罩大地一般,无所不在地占领了作者的心灵,作者困惑地纠缠于文本中不断浮现的死亡本能,死亡变成一种困苦的偏执,甚至是无关乎爱情的挫败,因此作者选择了在花季般的年龄自杀。《鳄鱼手记》中的主人公鳄鱼、《蒙马特遗书》中的叙述者都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告别这个社会,就如同作者邱妙津以“自杀”结束自己生命一样!这也许不是“退缩避战”的懦弱,反而是从中凸显了父权社会对女性酷儿的压迫与歧视,使其丧失生存空间和勇气。
然而,邱妙津却在小说文本中创造出另一种戏谑、调侃、如古希腊美少年般自恋的后现代书写风格。相较于《鳄鱼手记》中自恨而悲情的叙述者,鳄鱼角色的创造,不但为悲剧色彩浓厚、沉重得近乎喘不过气的书写笔调,带来一丝喘息的空间,同时更是对父权社会进行窥视、调侃与解构。第二手记第八章以鳄鱼暴露的狂想挑逗社会大众的窥视欲,进而讽刺人们一方面故意而虚伪地表示冷淡、不屑,一方面却又偷看《独家报导》和《第一手消息》,以满足对于鳄鱼的好奇。面对社会大众的窥视,鳄鱼害羞娇媚地感叹道,大家到底是何居心呢?竟然被这么多人偷偷喜欢,真受不了,好——害——羞啊!穿插于小说中的“鳄鱼”片断,不但反制了父权社会的窥视,而且借由鳄鱼身体的演出嘲谑父权社会的暴力,正如台湾女性主义学者刘亮雅所言,鳄鱼诙谐夸张的表演是书中最酷异的部分。在第三手记第四篇里则嘲讽台湾政府以保护国格为理由,禁止并封锁对鳄鱼的报导,“鳄鱼”片断渐渐发展为尖锐的讽刺寓言,因为“鳄鱼”已经不是“生物学”上的“鳄鱼”,而是借以指称“女妖精”“女性酷儿”的邪恶意象。作者借用“鳄鱼”形象,其核心主题是来指控父权社会将女性酷儿丑化、妖魔化、污名化。父权社会对女性“酷儿”异己化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作者通过“鳄鱼”之口,嘲笑戏谑父权社会“恐同”幻想的荒诞不经,并深刻指出父权社会如何透过台湾官方机器及媒体的宰制,遂行其无知霸道的恐怖政策。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书写中,被建构出来的女性形象也“独立自强,但更强调其在个性特征上善良、柔弱、忍让和自我牺牲的一面,而通过女性形象再现的传统‘女性气质’——摄人心魄的美貌、憧憬爱情的女子、忠贞不二的妻子、无私奉献的母亲,无不辉映着事业有成、视野开阔、果断强健的‘男性气质’。”[6]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的“酷儿书写”当中不难发现,对边缘族群的关注、为自身寻找合法的“主体性”的带有抗争姿态的激情书写,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男性气质”的解构与嘲弄。“酷儿”“政治与身份认同”“女性意识”等主题的开掘,使得台湾的新世代的女性作家们走上了一条激情与反叛的书写之路,在无所不在的权力运作机制中,边陲对于中心的对抗与解构将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从酷儿的现身到身份的认同,由于强大父权机制的压迫,其中引发的焦虑、被迫失声,以及种种被妖魔化、污名化的不平等对待,在朱天文、邱妙津等人的酷儿书写中,其繁复纠葛的情感与悲抑沉痛的形象,无不提醒社会大众“情欲大不同”的事实真相。拉康曾说:“男性与女性之间没有任何清晰明确的界限:主体的欲望不同,具体的性特征就不同。性差异总是超出单纯性别上的不同,而且不仅仅是单纯性别上的不同(gender difference)。”[7]当小说家面对父权社会对性别与情欲所设置的禁锢与禁忌的时候,书写本身即是心灵解放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在对强权社会的翻转、嘲谑,以及在情欲政治上的玩弄、批判,都比之前更加挑衅与挑逗。而酷儿作家则透过小说人物与情节的举证,颠覆了过去“男性酷儿‘阴柔’”“女性酷儿‘阳刚’”等传统刻板的角色扮演与配对关系。台湾新世代的酷儿作家们在张扬女性情欲、翻转父权社会“男性气质”的同时亦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女性乌托邦世界,正如朱天文在《世纪末的华丽》中的书写:“……年老色衰的米亚有好手艺足以养活,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以重建。”[8]
[1] 王德威. 想像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3−17.
[2] 曾秀萍. 孤臣·孽子·台北人: 白先勇同志小说论[M]. 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民92): 32−34.
[3] 罗会均, 王栋梁. 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 缘起、影响及其化解[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5(5): 604.
[4] 朱天文. 荒人手记[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 260.
[5] 潘碧华. 男女有别: 朱淑真的纯女性书写[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4(1): 77.
[6] 李琦. 叙事话语与意识形态: 对女性媒介传播策略的解读[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2(6): 103.
[7] 伊丽莎白·赖特.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9−80.
[8] 朱天文. 世纪末的华丽[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133.
Abstract:Queer writing in Taiwanese novels begins from such writers as Bai Xianyong in 1960s. During 1990s the new-generation queer writers represented by Qiu Miaojin and Zhu Tianwen adopt an anti-traditional strategic writing policy and highlight queer’s unique experience. These queer writers abandon the melancholy and self-resentful writing and explore queer sexuality and gender fluidity in a bold and challenging way. They protest the mainstream of the society and attack orthodox heterosexuality with a marginalized point of view, trying to find their ego by escaping from the authoritative center. They protest the center by committing suicide and deconstruct the center through parody.Through unorthodox queer writing, they intend to break through the rational gender border, exhibit various queer sexuality and call for gender identity in the feminist position. Their queer writings exhibit the modernity which has been repress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10s.
Key Words:Taiwanese novel; Bai Xianyong; Qiu Miaojin; Zhu Tianwen; “queer writing”; literary revolution;“modernity”
Modernity of Queer Writing in Taiwanese Novels in the 1990s
LUO Xianyong
(Department of Dramatic and Cinematic Literature of Film Academy, 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 China)
I206.7
A
1672-3104(2011)01−0159−05
2010−04−14;
2010−10−15
罗显勇(1971−),男,重庆大足人,文学博士,重庆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台湾文学与电影.
[编辑: 汪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