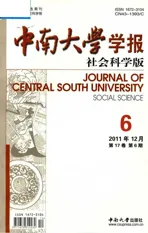《三言二拍》的生态伦理观念
2011-02-09杨宗红
杨宗红
(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广东广州,510632;贺州学院,广西贺州,542800)
《三言二拍》的生态伦理观念
杨宗红
(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广东广州,510632;贺州学院,广西贺州,542800)
三言二拍继承了先秦神话、魏晋六朝志怪及唐传奇的生态题材和生态精神。因其商业性与通俗性特征,小说的生态题材充满了浓郁的生态伦理观念。这些观念主要以教化的形式出现,涉及到生态良心、生态正义、生态义务等诸多方面。重新体认三言二拍的生态伦理观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言二拍》;生态伦理;教化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生态问题日趋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日益受到重视。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说道:“根据中国人的观念,天和地,世界万物以及人的生命,道德以及自然现象,构成了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在对于自然的控制方面,我们欧洲人远远跑在中国人的前头,但是作为自然的意识的一部分的生命都迄今在中国找到了最高的表现。”[1](308−309)中国人的生态智慧在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而文学作品则成了生态哲学的诗意表述,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就是生态的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纯然的景物描写还是动植物的拟人化表述,乃至于仙境洞窟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随着‘人类纪’的到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紧迫、更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文学现象以及文学的历史,同样应当在这个统领全局的视阈内重新审视。”[2](181)基于此,本文试以我国古代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为例,探讨分析其中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
《三言二拍》中涉及人与自然关系且具有生态意蕴的主要篇目如下:《拍案惊奇》卷三七《屈突仲任酷杀众生》,《喻世明言》第三十四卷《李公子救蛇获称心》;《醒世恒言》第六卷《小水湾天狐诒书》,《醒世恒言》第五卷《灌园叟晚逢仙女》;《警世恒言》第五卷《大树坡义虎送亲》;《警世通言》第二十卷《计押番金鳗产祸》。这些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题材,有的是小说的正话,是以故事的形式宣扬人与自然相亲的,生态教化是小说的主要意图;有的是小说入话中的一部分,或是正话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在入话诗及插入的议论中,则明显表明教化意图;还有一些篇目,有关生态的话语只是偶而提及。在这些教化中,作者流露出有关生态良心、生态正义、生态义务等诸多生态伦理观念。
(一) “众生皆有命,畏死有同心”
儒释道三家都重视生,重视生命的正常性。《周易》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最基本的德。天地之所以如此浩淼广大,在于其厚德载物,涵容万物,并使之各不相害。儒家追求“仁”,“仁者,人也”,仁是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真正的仁者爱民,爱人,并将此心推而及物,仁民而爱物。董仲舒云:“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春秋繁露·仁义法》仁心所至,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篇》),后来的理学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也是对仁的发挥。道家提出“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天地》),“积德累功,慈心于物;……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太上感应篇》)之语。[3](13)佛教以慈悲性看世界,倡导众生平等,反对杀生。
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家几乎都受到儒释道的熏染,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他们的小说以反映市民的生活为主,充满了现世关怀。[4]小说家将爱人利物的情怀推广到物,“众生皆有命,畏死有同心”,将人好生恶死之情推而广之,倡导对其它生命的关怀。凌濛初《屈突仲任酷杀众生》就是劝人关爱自然生命之作。[5]在入话诗中,作者首先表明观点:众生皆有命,畏死有同心。何以贪饕,冤仇结必深。接下来议论道:
话说世间一切生命之物,总是天地所生,一样有声有气有知有觉,但与人各自为类。其贪生畏死之心,总只一般;衔恩记仇之报,总只一理。
小说还对“天生万物以养人,食之不为过”之论加以驳斥,指出此乃是以人为中心论的腐说,并反问道:“那虎豹能食人,难道也是天生人以养虎豹的不成?蚊虻能嘬人,难道也是天生人以养蚊虻不成?”凌濛初认为,牲畜皆有灵性,都贪生畏死。入话中,两牛知道自己将要被杀后,一牛不吃草,“只是眼中泪下”;另一头牛同样不食,见有人来,“把双蹄跪地,如拜诉的一般”。作者说这些“怕死的众生与人性无异的”故事,希望“随你铁石做心肠,也要慈悲起来”。作者刻画了一个为了口腹之欲,不断杀生的屈突仲任的形象。屈生好杀,为了更好的吃法,不惜凌虐动物,花样百出。“或生割其肝,或生抽其筋,或生断其舌,或省取其血,道是一死便不脆。”小说家让屈生入冥受罚,让被杀众生向其讨命,再放其回生,让他向众人讲述杀生之报,以致好些人都生了放生戒杀的念头。小说最后,用偈语道:
物命在世间,微分此灵蠢。一切有知觉,皆已具佛性。取彼痛苦身,供我口食用;我饱已觉膻,彼死痛犹在。一点嗔恨心,岂能尽消灭?所以六道中,转转相残杀。愿葆此慈心,触处可施用。起意便多刑,减味即省命。无过转念间,生死已各判。及到偿业时,还恨种福少。何不当生日,随意作方便:度他即自度,应作如是观。
凌濛初等并非一味宣佛,但是,他赞成佛道的爱惜众生之说,并以六道轮回、地狱受罚等报应观告诫世人,人应以度己之心度物,“众生皆有命,畏死有同心”,以慈悲之心看众生,物虽至微,亦系生命,人欲积德累功,应仁民爱物,不可贪杀。
(二) “万物皆有情,不论妖与鬼”
人类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的时候,常常过分夸大人的主体性。对自然的敬畏弱化了,或忘记了自然的能力与灵性。实际上,动植物一样具有灵性,具有主体性。谭峭《化书》云:“禽兽之于人也何异?有巢穴之居,有夫妇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鸟反哺,仁也;隼悯胎,义也;蜂有君,礼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6](41−42)小说家以故事告诫世人,“万物皆有情”,自然与人类是平等的,人类不能在自然面前为所欲为。在小说家笔下,动植物均有情感,虽为异类,多具人情,其感情之丰富,智慧之发达并不亚于人。
“万物皆有情,不论妖与鬼”,站在自然的角度,自然都是具有主体性的,它们都有灵性,有喜怒哀乐,也有爱恨情仇。对物有恩,物会报恩,倘若伤物害物,则物会报怨。朱熹曰:“动物有血气,故能知。植物虽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见。若戕贼之,便枯悴,不复悦怿,亦似有知者。”[7](199)《醒世恒言》第二卷入话故事中,三兄弟要分家,商议准备将门口的紫荆花树也砍了分。[8]当时,紫荆花开得极其茂盛,次日去砍树,见“枝枯叶萎,全无生气”,将手一推,树应手而倒,根芽俱露。及至兄弟和好,不再分家,也不再砍树时,“其树无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以前更烂漫”。如果这个故事不过是对入话诗中“紫荆花下还家日”的解释,其主旨是宣扬兄弟友爱,算不上是有意识的生态表达的话,《灌园叟晚逢仙女》则就是有意宣扬人与自然相亲了。头回故事中,杨花、桃花、李花、石榴花化成人聚于崔玄微家,面对封十八姨(风),歌声中充满容华易消歇的惨淡。小说直言道:“只那惜花致福,损花折寿,乃见在功德,须本是乱道。列位若不信时,还有一段《灌园里晚逢仙女》的故事,待小子说与列位看官们听。若平日爱花的,听了自然将花分外珍重。内中或有不惜花的,小子就将这话劝他,惜花起来。”可见,作者讲述这个故事,就是要人惜花爱花。
植物有情,动物更甚。《小水湾天狐诒书》作者开篇议论道:“蠢动含灵俱一性,化胎湿卵命相关。得人济利休忘却,雀也知恩报玉环。”站在物皆有情的角度,小说家主张以平等之心待之,反对刻薄待物。这个入话诗是对全文主题的概括。在入话叙述杨宝救雀故事后,再引诗云:“黄花饲雀非图报,一片慈悲利物心。累世簪缨看盛美,始知仁义值千金”。正话故事讲述了王臣在小水湾见两狐看书,以弹弓伤一狐,并夺其书。狐狸要不回天书,于是变成王臣的家人,设计使王臣家计由富余变为贫困,并夺回了天书。在这里,人不是主角,而是陪衬。狐以其变化的能力及智慧将人玩于股掌。小说将人的兴衰得失与动物命运挂钩,其目的在于劝告世人:“须学杨宝这等好善行仁、莫效那少年招灾惹祸。”“闭口时须闭口,得放手时须放手。若能放手和闭口,百岁安宁有八九。”《计押番金鳗产祸》写作目的亦是如此。计押番钓一金鳗,金鳗言它是金明池掌,并言:“妆若放我,教当富贵不可言尽;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死于非命。”计妻不知就里,杀了金鳗。后来,计押番一家果然死于非命。小说结尾总结道:“大凡物之异常者,便不可加害。有诗为证:李救朱蛇得美姝,孙医龙子获奇书。劝君莫害非常物,祸福冥中报不虚。”
《大树坡义虎送亲》中的勤自励好杀虎,忽遇一黄衣老者,云:“好生恶杀.万物同情。自古道: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郎君何放必欲杀之?……郎君若自恃其勇,好杀不已,将来必犯天道之忌,难免不测之忧矣。”后勤自励救一陷于阱中的虎,因从军十年不归,未婚妻被设计嫁与他人。虎夺女还勤自励,以偿救命之恩。结尾说道“但行刻薄人皆怨,能布恩施虎亦亲。奉劝世人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此处虽说是“饶人”,结合小说,又何尝不是指物呢。换个角度而言,把物当成人看,以待人之心去待物,弱化人的中心地位,重新确立自然的主体地位,才能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正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魅力所在。李约瑟曾经评论道:“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对中国人来说自然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应该了解它的统治原理,从而使生物能与它和谐共处。”[9](338−339)
(三) “人既为鱼,鱼复为人”
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化,在先秦神话中有很多记载。这些记载实际上是天人一体,人天为一的形象化表述。人天为一有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人是自然之物,与其它生物一样都为自然之子。人生于自然,而后归于自然,人之行必须合符自然规律,在生命观表现方面,便是“人与天一”的生态观。其次,相对论的观点。“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再次,天人相应的观点。“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淮南子·精神训》),汉代董仲舒亦言:“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诸多的原因,使人们相信,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指出:“对于东方人来说,自身和世界是同一事物,东方人几乎是不自觉地相信,在人和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和谐。”[10](37)
就话本小说所见,精怪经常化为人,与人交往。倘若不是特殊原因,根本不知道其为非人。王臣所见王福等家臣,王臣的兄弟,虽为狐所化,但与人有何区别?《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九中,一狐化成蒋生的意中人与之交往,居然没有人发现其异样。还有一些人物即是动物投生,如吴越王为蜥蜴转世,郭威真形为蛇等。也有人化为异类者,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化为蝴蝶(《喻世明言》卷二七头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薛录事鱼服证仙》与清初小说《醉醒石》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原形》。薛伟本是天上谪仙,其回归天庭之途居然是化鱼。薛伟化鱼的深刻内涵不在于谪仙凡尘受劫,而在于对于“万物一体”的体认。未化鱼之前,人是人,鱼是鱼,人与鱼有形体之别,空间活动范围之差,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有生态地位之殊。化鱼之后则消除了这些差别,人即鱼,鱼即人,人与鱼无二。之所以要薛伟经历化鱼的过程,乃在于要他破除物我之别,认识到人与物只有形体之别,而本质上是一样的。破除物我之别,才能达到“齐物”,才能真正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从而实现逍遥的神仙状态。用小说的话说:“识破幻形不碍性,体形修性即仙真”。
高才生化虎的故事表面上是劝人不要恃才傲物,细读之,依然是人与物不二的生态观。李徵化虎,因心怀不满,脾气暴躁,具有虎之气性。未化虎之前,是人形虎性。及至化虎后,痛不欲生,又眷念、担心家小,欲复原形,常思为人之种种,又牵挂遗稿之不流传。形虽虎,心犹人,久之好食肉乃至以人味为最美,又是虎性。人形虎性,虎形人性而虎习,李徵是虎,虎为李徵,二者只有形体的差别。
尽管,话本小说的人与异类互化故事已经超越了先秦神话的混沌而浓郁的生命意识与生命的一体化存在的状态,更多的表现出一种道德理性和神道设教的成分,化异类故事主旨不是出于生态教化;然而,小说营造的氛围,还是给了民众一种感觉:人就是物,物就是人。在合于道的情况下,万物是一体的。这种体认,虽不是小说家的目的,在客观上却将生态观念输入到民众的意识中。
(四) “修仙径路甚多,须认本源”
中国民众普遍信仰神仙。《说文》解曰:“仚(仙的古体),人在山上,从人从山。”《释名·释长幼》解“仙”曰:“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11](72)神仙是人与自然亲近的符号载体,是自由逍遥的象征,成为神仙,就破除了时空限制,消除了物我差别。“神仙本是凡人做,只为凡人不肯修”(《恒言》卷三八),“修仙径路甚多,须认本源”(《恒言》第四卷)。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存空间行善,爱民仁物,这就是“本源”。话本小说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善报,这些善报都是人们认取“本源”行善的结果。《抱朴子》有云:“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12](53)只要认取本源而行善,普通人也可以成仙。对普通人而言,爱惜身边之物,同样也是本源所在。《素履子·履仁》曰:“或救黄雀,或放白龟,惠封于伤蛇,探喉于鲠虎,博施无倦,惠爱有方,春不伐树覆巢,夏不燎田伤禾,秋赈孤寡,冬覆盖伏藏,君子顺时履仁而行,仁功著矣。”[13](703)
在话本小说中,以爱物而成仙者首先当推《恒言》第五卷中的崔玄微与秋先。崔玄微在所居庭院遍植花木,僮仆无故不得入。后因庇护桃李花等免于风残,花精教玄微服食花英,得道仙去。正话中,秋先惜花如命,在他园中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常感叹花日之短,“看他随风而舞,迎人而笑,如人正当得意之境,忽被摧残,巴次数日甚难,一朝折损甚易。花若能言,岂不嗟叹。”他讨厌摘花之行,“枝一去干,再不能附干,如人死不能复生”。因为护花,与恶霸张霸发生冲突,引来牢狱之灾。结果,张霸被花仙惩罚而毙命,秋先则因惜花有功,故以花成道,年龄转少,又被上帝封为护花使者,“但有爱花惜花的,加之以福,残花损花的,降之以灾。”《西湖二集》第二十九卷头回中,吴堪生性爱惜门前溪水,常于门前以物遮护,再不污秽。“晚间从县衙回来,临水看视,自得其得”。因能“敬护泉源”,也成仙而去。同书卷二三中,杨廉夫救金鲤,死为蓬莱都水监。
“昔时柳毅传书信,今日李元逢称心。恻隐仁慈行善事,自然天降福星临。”并非所有爱物惜物的行为都能成仙,但都必定有好报。李元见众小孩打一小蛇,将其救下,原来那蛇乃龙子。龙王感其恩,将女儿称心送与李公子,李元在称心的帮助下考中科举(《明言》第三十四卷)。在《恒言》第六卷头回中,杨宝救一受伤之雀,将其养好,饲之以黄花。那雀化为人,赠杨宝玉环一对,言:“掌此累世为三公。”一老者爱惜字纸,得赐寿一纪,又令曾参投生于其家,使其富贵(《二刻拍案惊奇》卷一头回)。赵雄敬重字纸,阴功浩大,得到了文昌帝君的护佑(《西湖二集》卷四)。在小说家看来,立足于当下的生态实践,亦可以成就自己人生理想,如成仙、长寿、富贵等。
二
话本小说中的生态教化不是偶然。明朝政府重视生态,倡导植树造林,多次下令禁止滥砍滥伐滥捕,但因种种原因,自然生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清清,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15](16)马文升《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伐木,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16](528)再如明代江南虎患严重,虎故事也颇为流行,陈继儒、王稚登为此编撰了虎故事集《虎苑》和《虎荟》。虎患严重,虎被杀也就严重。嘉靖十年冬,“广海有虎暴,知县张文风募人搏之。文风悬赏募搏 虎,虎皆夺魄,见羊豕亦不敢近,槁死者六,患遂息”。[17](40)“……即日下令日:六乡之民,有能捕虎一者,赏银五两。民喜赏,争设机槛计捕之,弥月,生致虎十有二,悉歼之,患遂除。”[18]“獾毛缉以为裘,轻煖乃胜于氆氇。”[19](42)由于要向上进贡野生动物皮革,一些野生动物捕杀也很严重。人对金钱的追求,对华屋的奢侈享受,对口腹之欲的满足都会导致动植物的减少。在小说中,也多载有动物被杀的情况,如《大树坡义虎送亲》中的勤自励与他的朋友“射猎打生为乐。曾一日射死三虎。”《聊斋志异·九山王》中,曹州李某放火烧狐狸无数,《醒世姻缘传》中,主角也是曾被射杀的狐狸转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的浸润,必然使民众关注自己生活的自然世界,时代生态状况又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话本小说家以故事的形式对劝诫民众善待自然,其来有自。
话本小说是市民阶层兴起的产物,因“说话”而产生。它不同于志怪传奇,只是文人才华的自我炫耀,或文人的感悟与消遣。基于说书场这一特殊环境,话本小说更关注在场听话者的精神需求与心理世界,更具有开放性与互动性。讲话者与听话者的“在场性”决定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协调。互动对话的结果,体现在小说形式上,便是头回故事和入话诗词的产生,以及中间不断出现的进行故事干预的插入语,从而营造说话场的良好人际生态。说话是一门技艺,是谋生的手段,商业追求的目的使小说题材不仅符合说书者自己的兴趣,更要迎合听众,具有很强的娱乐功能。后期的拟话本小说依然具有商业目的,商业追求的创作中,仍有虚拟的“说书场”存在,只不过由原先的面对面的交流的场景发生转移而已。古代小说中,最能反映生态的是神怪类题材,而这类题材又常与儒释道的鬼神观相伴相随。自宋以后,三教相互交融,又催生了更多的民间信仰。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对神灵的崇拜,对自然的关注。小说中的生态故事不仅仅是说话者(或作者)个人的主观选择,也是听众(读者)共同参与选择的结果。
话本面对的是普通民众,是说书人与听书人共同在场(或隐性在场)这一特殊环境。在进行文学审美的过程中,说书人的干预固然有引导听众的道德审美之用,但作为后者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于是乎,小说的主观向度可以为之提供审美参考,而故事的“客观”叙述则留给读者以广阔的思考空间。所以,小说中的动植物的神异叙事所包含的生态内涵远非作者主观所限。
话本小说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教化意味。冯梦龙以小说“喻世”“警世”“醒世”,陆云龙以小说“型世”,嗤嗤道人以小说令世人“警悟”等。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中说道:“从来说书的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14]就是以诙谐幽默著称的李渔也是“以雕龙之才,鼓风化之铎。”[20](382)
关于通俗小说的作用,公奴在《金陵读书记》中亦言:“以小说开民智,巧术也,奇功也,要其笔墨决不同寻常。常法以庄,小说以谐;常法以正,小说以奇;常法以直,小说以曲;常法正襟危坐,直指是非,小说则变幻百出,令人得言外之意;常法如严父明师之训,小说则如密友贤妻之劝。”[21](8)在小说中,自然、自然规律被神圣化,人与自然相亲相依。通过文学审美,通过传统小说中神化的自然观,小说将万物平等、万物有灵的观念传输出去。摒除所谓的迷信因素,具有生态教育意味的话本小说可以唤醒世人重新认知世界的和谐内涵,体会“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和不以人害物,不以人灭天的思想。在小说审美中,人们会自然而然的体认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让人能尽其性,物亦能尽其性的生态内涵,这对构建生态和谐社会应是大有裨益的。
[1] Hermann Keyserling: 《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C].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2] 鲁枢元. 百年遗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J]. 文学评论. 2007(1): 181−186.
[3] 冯国超. 太上感应篇[C].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4] 杨宗红. 明清之际话本小说家的宗教情怀[J]. 天中学刊,2008(3): 75−78.
[5] 凌濛初. 拍案惊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6] 谭峭. 化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7] 朱熹. 吕祖谦. 朱子近思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 冯梦龙. 醒世恒言[M].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9] 潘吉星. 李约瑟文集[C].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10] 汤川秀树. 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11] 班固. 汉书艺文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5.
[12] 葛洪著, 王明校释. 抱朴子内篇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3] 张弧撰. 素履子[A]. 道藏(第21册)[Z].
[14] 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15] 曾国荃, 张煦等修纂(光绪)山西通志(卷66)[M].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643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16] 陈子龙, 等. 明经世文编(卷6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7] 新会县志(卷三)[Z].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18] 汪森. 粤西诗载·粤西丛载(卷7) [Z].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 [明]桑乔. 庐山纪事(卷1《通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9.
[20] 孙治. 蜃中楼序[A]. 吴毓华编著. 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C].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21] 王钟陵.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小说卷)[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Abstract:Vernacular novels named Sanyan and Erpai inherited the subject matter and spirit of ecology in the Myth of the Pre-Qin Period, Ghost Story of Liu Dynasty and Romance of Tang Dynasty. The subject matter of vernacular novel was full of tremendous cultivation meaning because of the commercial and colloquial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ally speaking, it holds that everything has life and feeling, and the education of eco-ethics,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education of person and object are combined into a union together with the ecological practice education of“recognizing the origin”. Because of the special form of vernacular novel,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eco-ethics education is much more popularized. Thus, a re-acquaintance with the ecology idea of morality cultivation has som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Sanyan and Erpai; ecological morality; cultiv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Ecology Cultivation of Sanyan and Erpai
YANG Zonghong
(Chinese depart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10)
I242.3
A
1672-3104(2011)06−0204−05
2011−06−26;
2011−10−28
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间信仰与明清话本小说的神异叙事研究”(11YJAZH112);广西教育厅项目(200911MS252)
杨宗红(1969−),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贺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