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三题
2011-01-16山西宋葆臻
山西 /宋葆臻
陕北三题
山西 /宋葆臻
桥山谒陵
旅游车驶上西延高速,一座泼洒着浓浓古意的千年帝都就甩在了我的身后。几天来,我游荡在秦砖汉瓦的缝隙间,沉醉于随处可拾的历史碎片,却总也纠缠不清文明的渊源。直到旅游车戛然停靠在浩气森严的轩辕庙前,我才恍然醒悟,我要追寻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公孙轩辕。
我的心开始震颤,我已经清晰地呼吸到扑面而来的祖先的气息,这气息犹如历史的烟云一样缭绕在我的周边。沮河桥是我现在站立的地方,沮河水从我的脚下缓缓地流过时,我明显能感觉到从远古一路走来的沧桑在我激荡的心房里撞击。我抬眼去凝望那座青灰色的花岗岩建筑,那么古朴,那么庄严,流畅的线条突显着东汉画像石的风格。它背靠着的,是凝重雄沉的黄土高原,这一片黄天厚土,埋藏着一个民族五千年的积淀,这一座祖宗宗庙,见证过华夏文明孕育的瞬间。
我不能再等待,澎湃的渴望早就跃出了胸膛。我一步跨入庙门,去瞻仰那棵尽览人间兴亡百代盛衰的古柏,它高入云天,树冠如盖,历数千年风雨浇注依然苍翠不衰。我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就在方寸之间领略过它的风采,眼前这株黄帝手植的轩辕柏,不正是《黄帝陵》特种邮票的第三图吗?我的情思如涌泉一般流淌,我忆起1983年的清明节,正是《黄帝陵》邮票首发的当日,我收到了从黄陵邮局发来的原地封,信封右上角鲜红的戳印曾寄托过我青年时代无限的憧憬。我有一丝惆怅,人生这么短,我却挨过了如此漫长的等待,我也有一丝欣慰,虽然我姗姗来迟,但毕竟终于有机会向它顶礼膜拜。此刻,站在古树的浓荫下,我伸手去抚摸那完全龟裂的树苔,苍劲的质感顿时划过我的手心,树身上密密地隆起的“疙里疙瘩”在我的手下轱辘轱辘地转动,就好像滚滚碾过的历史车轮。我围着树绕来绕去,久久地端详它粗糙的树身和虬曲的躯体,不由得在心里吟诵着宋代贤臣范仲淹的优美诗句:“沮流声潺潺,柏干色苍苍”。这苍苍茫茫的树色,是几千年雪雨风霜渲染而成,这走过千秋万代的古柏,风吹过,雨打过,雷霆轰过,可它依然顽强挺立,直指苍穹。我慨叹它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总让人联想到华夏子孙饱经磨难却愈挫愈奋的民族精神。
我轻轻移动着脚步,穿过浓荫掩盖下的古老庭院,在名曰“诚心亭”的过道上肃立了良久。两旁朱红色的亭柱上,镶嵌着一副醒目的楹联,“诚朝圣地人文祖,心祭神州儿女情”。我想“诚心亭”正是这样的去处,因为我在朗诵这幅对联时,仿佛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就在身边集聚,灵魂像经历了一次信仰的涤荡。我顿时严肃了起来,掸了掸尘土,正了正衣冠,屏声静气地走进了人文初祖大殿。
轩辕黄帝的浮雕像被供奉在精致的玉石神龛里,金黄色的缎带又给久远的传说平添了几分神秘。导游正滔滔不绝地重复黄帝乘龙升天的故事,但我怀疑她的讲解是否太过于离奇,我当然没有能力像秋雨先生那样去“猜测黄帝”,我只是依稀想起明代有一位叫李梦阳的诗人好像说过“黄帝骑龙事杳茫,桥山未必葬冠裳”的诗句。我更愿意相信,作为“华夏民族实现第一次文明腾跃的首领”,黄帝肇启文明所书写的传奇对于民族的传承具有的象征意义,以他拒绝混沌洪荒的胆识和勇气,的确无愧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这样的荣誉。
从轩辕大殿出来,我汗流浃背地行走在通往桥山山顶的石阶上,举目遥望山巅,如炙的烈日烤晒着铺天盖地的苍松翠柏,数千年的雨露滋润,哺育得满山树木郁郁葱葱,叶茂枝繁。《史记》云,“黄帝崩,葬桥山”,黄陵县中也有传说,说黄帝早已驾鹤成仙,此处埋葬的仅是黎民挽留他时从他身上扯下的衣冠。我不想去考证究竟应该相信传说还是相信司马迁,我需要做的是快步走向刻有“桥山龙驭”四个大字的明嘉靖石碑前,秉烛焚香,跪拜祭奠。站在黄帝陵墓巨大的封土前,我也开始学着对文明展开一番遐想和溯源。我想,当以黄帝为代表的先祖开创文明先河之初,文明还是一株刚刚植根的小苗,而如今,它已成为越五千年而不朽的参天大树;我又想,如果没有那时黄帝们的披荆斩棘,文明必定还得在混沌中孕育更长的时间。我抬头问天,上苍无言,谁能说得清黄帝葬处的上方还是不是五千年前的那一片蓝天?
壶口听雷
车过宜川,地貌骤变。目光透过车窗,蓦地进入视野的,是一根根柱状的土塔,矗立在深不见底的沟壑和壁立千仞的峁梁之间。好一阵兴奋,不由得喊了一声信天游。我抬头向青天,真的是白云悠悠尽情地游,我低头向山沟,却不见风沙茫茫满山谷。前方,一丘又一丘,是比信天游还要绵远悠长的黄土高坡。我的心狂跳不已,黄河的咆哮声已渐渐传入耳鼓,我开始想象这条波浪很宽的大河,是怎样从巴颜喀拉山的冰峰里涌出,挟带着青藏高原的雄蛮,卷挟起广袤大漠的荒凉,在晋西北的老牛湾拐了个弯,然后不舍昼夜,一路奔腾着向南。
我惊呆了,晋陕峡谷突兀地横亘在两岸对峙的峰峦中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能把吕梁山的西南端一刀切断。黄昏,苍茫的暮色笼罩在峡谷的上空,与黛青的群山互为背景。快要沉落的夕阳染红了悠悠飘荡的白云,瞬即与黄河激起的水浪融合在了一起。
现在,我终于站在了靠近飞瀑的岩崖间,浑黄的河水正从悬崖上向下跌落,巨大的落差迫使河水跌入万丈深渊的涧底时发出隆隆的响声,犹如雷声滚滚,犹如万马奔腾。我想象不出,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黄河水怎么突然就被束成了一壶,继而倾泻下来,变成了一个喷涌着黄流的水帘子。俯视涧槽,壶底开始冒烟,夹带着泥沙的水雾冲天而起,再洒向周边时如夜空中滑过的流星雨。
我赶紧张开双臂,去拥抱黄河壮阔的气概,去体味黄河诗化的灵魂。我站在飞瀑的一端,面朝对岸放声高唱,黄河的水千年年地淌,黄河的河水怎就这么黄?可声音瞬间就被瀑布的气浪吞没了。我索性坐下来,再一次放飞遐想的翅膀。站在巉岩怪石上那个飘逸的诗人,是什么磅礴的力量才让你发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畅想?还有那位面目清秀的年轻人,该有多么顽强的信仰才让你奋不顾身地奔赴到这里,指挥着一群聚集在黄河之滨的优秀子孙,高喊着“怒吼吧,黄河”去挽救一个民族的危亡。这老祖宗用它洗过脸的黄河水,孕育了一个民族的肤色,而被这条河流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不就像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早已沉淀在了民族的血脉里?
夜幕低垂,天气突变,乌云从峡谷的两边压下来,越来越低的浓云很快就与飞瀑激起的水雾连成了一片。我们驱车回返,停步在“十里龙漕”的下方。不远处黑漆漆的黄河谷底,依稀可见嶙峋的巨石在激流中巍然屹立。沉沉的夜色覆盖着墨染的黄河,夏夜的静风吹过来一些泥沫的气息。借着两端微弱的灯光,我颤颤地颠在通往传说中“山石为禹所凿”的“孟门山”的铁索桥上,脚下的黄河虽不似瀑布那般狂躁,却依然显示着清晰的力量。迎面是一尊大禹治水的塑像,那伟岸的神态告诉我什么是坚毅和安详。默默地伫立于大禹的身旁,思绪也成了脱缰的野马。我仰望大禹,想从他身上去寻找黄河特有的沉重而丰富的内涵。当一条暴戾任性的大河被一个人驯服得多少减轻些威力,他无疑就是将荒蛮蜕化为文明的先驱,只是这样的搏斗还仅仅是开始,因为文明的开创从来都需要前赴后继。
夜晚,我躺在陕北的窑洞宾馆里,黄河的咆哮已变得轻微,像一个疲惫的夜行者歇下来喘息,但仔细倾听,依然能听到它貌似平静的心律或许暗藏着更大的杀机。我没有猜错。我还来不及沉沉入睡,一道亮光闪过天宇,耳际间猛然爆发了一声突如其来的炸雷。这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经历,在陕北,在壶口,我听到了终身难得一闻的撕心裂肺的刻骨铭心的震耳欲聋的惊雷。雷鸣电闪中,暴雨倾盆而下,越下越急,电光闪闪,照彻苍穹。窑洞镂空的格子窗外,横空劈过的闪电,时而如吐着火舌的金色巨蟒,时而像蹿上蹿下的银色小蛇。一声又一声的炸雷接踵而至,紧锣密鼓,时而如天兵下凡,杀声震天,时而又密如炒豆,噼里啪啦地在热锅里翻滚。周围,峡谷、山崖,进而整个高原,都在这山崩地裂般的巨响中战栗。我的心划过一丝胆怯,或者是对这条生命之河的本能的敬畏。尽管我无数次梦想过和这样壮观的场面相遇,但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候,我还是无法克制内心的恐惧。
天亮了。新一轮朝阳喷薄而出,高悬在奔流不息的大河上空,万道霞光涂抹着两岸宽厚凝重的灰暗山脊,壮丽的景观被浓烈的紫外线装点得更加动人。我站在西岸的高岗上,放眼再看黄河上游,已是洪流泛滥,澎湃汹涌,昨天走过的河滩、岩蹬早被洪水荡平,不见了踪影。黄河又一次暴露出它恣肆的本性,却也把晋陕大峡谷的岩石断层冲刷得愈发显现着摄人魂魄的坚韧气质。
巴士缓慢地行进在壶口通往宜川的山路上,隔着车窗,我目送着母亲河渐渐地远去。暴雨过后,路基多处塌陷,我们不得不迂回绕行,却仍然被横七竖八地倒卧在路上的大树拦住了去路。昨夜的万钧雷霆把数十棵大树或一劈两半,或连根拔起。清障车杳无消息,等待也是徒劳无益。一筹莫展之际,我看到了一幕感人的场景,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从不同的旅游车上下来,朝着相同的方向奔去。有人吹起了哨子,指挥人群搬动着躺在路上的残树。热火朝天的场面感染着人们的情绪,我也迅速加入到齐心协力的劳动大军。不知从哪边传来一声嘹亮的劳动号子,苍茫寥廓的陕北高原随即响起了“吆嗬,吆嗬”的回音。在一片号子声中,狼藉地横陈在路上的残枝断树被众人拖下了沟底。那一刻,我的眼睛模糊了,迷茫的视野中,是黄河滩头拉纤的纤夫,赤裸的背膀上青筋暴起,古铜色的脸盘宛如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他们艰难地迈开步子,迎着风,接着浪,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叩首,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忽然,领头的艄公扯开了嗓子,千山万壑间顿时回荡起悲怆的船夫曲:
——你晓得,天下的黄河几十几道弯嘞……
圣地寻梦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了一阵后,终于奔驰在通往延安的高速路上。侧目凝望窗外,雨后的阳光照耀着绿草茵茵的高原轮廓,远近的山峦蒸腾出一团团潮湿的雾气。植被茂密的高原竟然看不到一块裸露的黄土,真的如歌中所言,“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了。从车窗外呼啸而过的,是一个个深嵌在心坎里的地名,洛川、瓦窑堡、南泥湾……每一处地名都是一幅壮阔恢宏的历史画卷。终于,浓荫密裹的半山腰上,一排呈弧状分布的红色大字如同五线谱的音符一样跃入我的眼帘——“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的心又开始怦怦地跳了,我无法不激动,我怎能不激动呢?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还有哪个地方能像延安那样热切地牵动着我的向往呢?那时候,我站在小学语文的课堂上,用稚嫩的童音声情并茂地朗诵“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我早就把这块神圣而炙热的土地装进了行囊。那巍巍宝塔和滚滚延河互为辉映的经典美学构图,无数次地震荡过我的眼球,敲叩过我的心扉,只是我迟迟未有机会亲仰这座早已心驰神往的圣地。
我根深蒂固的“红色情结”在四十年日升月落的轮回中膨胀,虽然我知道有时候目之所及或许会抵消深深地刻在童心中的牢固梦想,但期待亲历的欲望依然不可阻挡。因为,延安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符号,哪怕是一次不经意的触及都会揪动善感的心灵,都会打开记忆的闸门。
——清晰地记得,冬日暖烘烘的阳光下,我捧着《战地新歌》,听“话匣子”里嘹亮的女声独唱,然后放开歌喉,“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来,快把咱亲人迎进来”,心中就涌起慷慨激昂的情怀,想象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豪迈。
——清晰地记得,春水荡漾的小河边,我展卷把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眼中浮现出八角帽上照耀中国的红星,巨人高擎的手臂抒写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激昂,还有“美髯公”的胡须,蕴藏着庄严的内涵和坚定的信仰。
现在,我终于来了,终于能亲眼看看这仰慕已久的圣地了。我迫不及待地从车上跳下来,伫立在延河桥头,让长久驻留在我心底的画面一幕幕闪过。
巍巍宝塔,沐浴在酷夏笔直的阳光下,依稀可见宝塔的古砖被战火熏染、炮弹划伤的痕迹。滚滚延河,已无法验证我先前的想象,我看到的只是宽阔的河床。我漫步在王家坪和杨家岭的革命旧址,去感受“红都”十三年的辉煌,领悟无处不在的信仰的力量,总能看到奋斗的理想在朴素的生活中闪光。我想弄明白西北高原吹响的号角,是怎样鼓舞着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去追求自由和解放,以至于“奔赴延安”成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魅力色彩的时尚。
穿行在历史的空间里,我常常是激动的,可我也会时时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惆怅。
我为找不到历史的实景而惆怅。我努力从文字、图片和实物中寻找一段鲜活的历史,却总显得苍白无力。
我仰望宝塔山,宝塔微微倾斜,我俯视延河水,延河几乎断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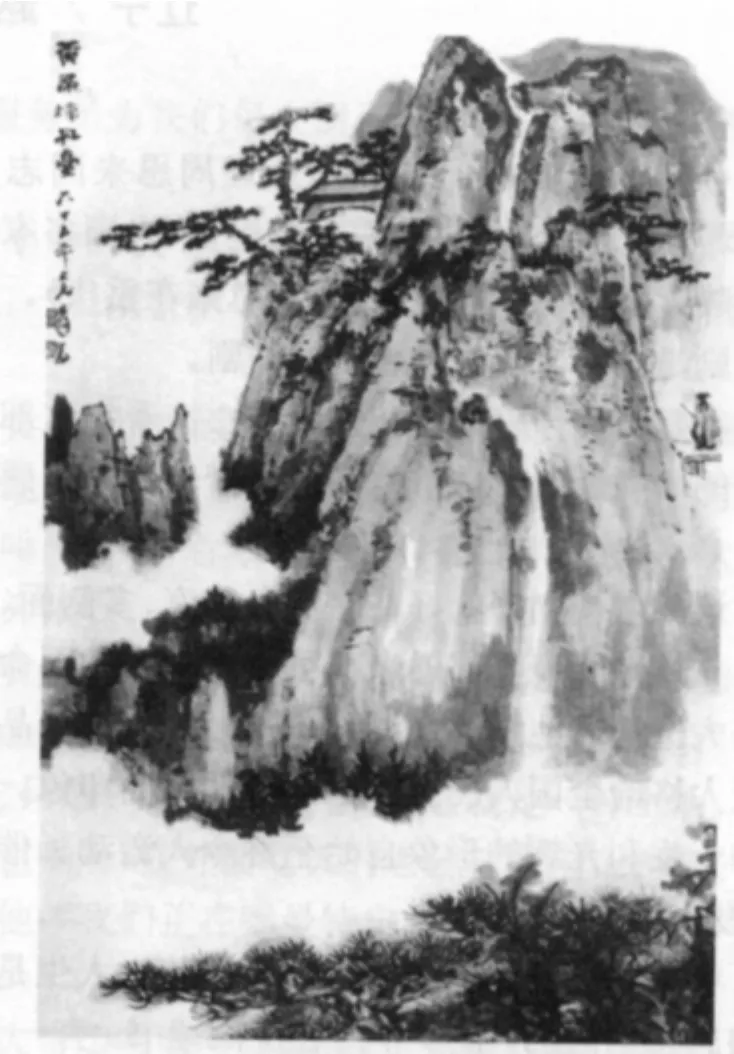
时代的风雨,把一代热血青年深沉的脚印清晰地留在了红彤彤的圣地,我却听不到抗大学生雄壮地合唱“黄河之滨聚集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纺车静静地摆在那里,没有人在上面纺纱线,更没有人唱起“手摇着纺车吱咛咛咛吱咛咛咛嗡嗡嗡嗡吱纺线线呀么嗬嗨”。
王家坪的土台子上,看不到秧歌剧“兄妹开荒”,枣树飘摇的嫩枝下,只有几个陕北的后生,伴着稀稀落落的腰鼓唱了几句滋味不浓的陕北民歌。
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里,摆设依然如故,我却再也找不回“鲁艺”和“七大”代表们匆匆走过的脚步。
窑洞前的石桌椅旁,不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更听不到爽朗的笑声和浓重的湖南口音,我只能一遍遍地重复那句经典的更像是绝唱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我明白,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篇章,延安也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如今的延安,大楼高耸,商铺林立,充溢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当硝烟散尽,蹄声远去,这里的一切早已幻化为一个民族的记忆,无论褒贬都是传奇。不论你的目光凝视到的是她的哪一处,都能找到惊讶的理由。你不会忘记,在陕北这块沟壑纵横的苍茫大地上,有过糜子和谷子间飘扬的理想,也有过波峰和浪谷间闪耀的信仰。这还不够吗?我想我不必为看不到历史的画面感到惋惜,而更应该为延安滚滚迈向现代化的步伐感到欣慰。延安,她的沧桑,她的变迁,是一个民族在经历过艰难困苦后蜕变的缩影,是一本世世代代读不尽的鸿篇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