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幽灵的女性写作
——在北师大当代新诗研究中心“女性诗歌”论坛上的发言
2011-01-05吕约
□吕约
作为幽灵的女性写作
——在北师大当代新诗研究中心“女性诗歌”论坛上的发言
□吕约
这间会议室,四面墙壁上挂满了死去的男性大师的画像,我们在这里开一场关于“当代女性诗歌”的会议。墙上挂着这么多男人,死去的黄种男人、死去的“父亲”,这是打击女性写作,还是激励女性写作?
当代新诗研究中心成立仪式的第一个论坛,设置的主题是“当代女性诗歌”,这是否意味着女性诗歌是“当代新诗”的吉祥物?还是说它有辟邪的作用?吉祥物是不伤害人的,可爱的,面带微笑的,辟邪则是吓跑各路怪物的猛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吉祥物,它本来是猛兽,但脸上是挂着笑的。
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来说,“女性写作”是吉祥物还是怪兽,至今悬而未决。但在现实之中,它的位置和形象,更像一个幽灵。
幽灵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位置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它让人心神不宁,既打发不走,又解决不了。这个叫“女性写作”的幽灵,往往只在开研讨会时才存在,而且还不在现场,仿佛在隔壁的屋子里。因为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可能存在一种叫做“女性诗歌”的东西,所以每年要召开很多研讨会,来召唤这个幽灵。
“女性写作”的幽灵
具有自觉的女性性别立场或价值诉求的女性诗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在中国,给汉语文学带来了刺激,也带来了很多“性别麻烦”。对于“女性写作”的描述、解释和价值判断,一直充满分歧,从80年代一直争议到现在,争议了二十多年,都没有得出什么稳固的结论,更没有达成共识。第一代女性诗歌的研究者似乎都已经疲乏了,厌倦了。比如80年代中期最早提出“女性诗歌”说法的唐晓渡先生,刚才就避而不谈自己对女性诗歌的新想法,而是向我们(女性自己)提问,让女性自己提供对女性诗歌的新解释。可见,女性诗歌所带来的“解释的麻烦”,还将延续下去。
80年代中期,以翟永明、伊蕾她们为代表的女性诗歌出现时,就像出现了长着两个头的美杜莎:一个是女性形象的神秘化,一个是女性形象的世俗化。对翟永明诗歌中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的解读,总是与“黑夜意识”绑在一起,仿佛女性就是黑夜的代言人(这导致了一个问题:90年代之后翟永明面对日常经验世界的“白昼写作”,难道是对女性意识的背叛吗?)翟永明诗中的女性形象,通常被读解为女人的原型,或女人渴望返回的本源。那么,从发生学来看,诗中的“女人”为什么要寻找自己的本源,而不是像舒婷诗歌那样找到“祖国”或“爱人肩头”?寻找女性生命的本源,即对“被遮蔽的女性自我”的寻求。因此,这个“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的女性形象,首先是一个女病人的形象:我感觉我自己有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主人公一会儿说“我是个病人”,一会儿又反问,“不,难道我真的有病吗?”当女人以“女人”为主题写作时(《女人》组诗),既是对女性身份的自我确认,还是对潜在对话者——男性文化——的质询,“如果你们是健康的,我就是有病的。”我是个病人,那么怎样治疗自己?治疗的方式,一是成为通灵者(两个世界之间的使者),二是成为完满者(如同创世的女娲)。女病人-女巫-女神,这是巫术式的救赎方式:告别健康人的行列,成为“患病者”,患病的结果是“通灵”。
翟永明的诗歌,创造了神秘主义的女性形象。神秘主义是一种极端自由的加速转变形式。将女人的形象神秘化,这是一种加速转变的方式,将自己加速转变成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形象。然而,在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主导的时代,神秘主义叙事面临一种危险,就是很容易变成精神治疗对象,或精神病理学的研究对象,容易被禁锢或隔离,关进文学历史研究中的“妇科”病房。
与翟永明的诗歌同时诞生的,还有一种诗歌类型,就是追问“病因是什么”。这种诗歌在萌芽时,常常容易被忽视。伊蕾写于1986年的组诗《被围困者》,呈现了女性被围困的现实处境、女性对被围困的感觉(房间/墙/栅栏/锁链/禁锢),以及幻想的解决方式(逃亡/疯狂/爆炸/死亡冲动),也创造了女性作为“被围困者”的形象。被围困者,与翟永明诗中“没有杀人者,也没有幸免者”(《女人》)的描述形成了呼应。如果说翟永明的诗歌创造了“通灵的女病人”的形象,那么伊蕾则展现了病因,就是女人为什么会成为病人——因为她被种种有形无形的力量所围困。其中,那种难以名状的无形的力量(比如家庭晚餐餐桌上座位排列的“金字塔”结构),构成了更深层的“病因”。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残雪的小说《突围表演》(1987),与伊蕾诗歌《被围困者》之间构成了互文关系。或许男性对“被围困”这个词也很有认同感,在现实生活之中,男人也经常会感到自己是被围困者。但如果说男性主要是被社会权力秩序围困的话,女性除了被社会权力秩序围困之外,还被男权文化、男权话语以及无处不在的目光所围困,因此,女性所处的包围圈更大。以伊蕾的“被围困者”形象为先兆,90年代女性诗歌的“日常经验化”与叙事化,进一步开拓了中国女性经验叙述的话语空间。在90年代至今的诗歌写作中,翟永明式的女性生命经验寓言(生死、白昼黑夜,时间主题),与伊蕾式的女性生存经验叙述(生命经验的空间化展开),交织融汇在一起,为汉语诗歌带来了性别对话的活力。
然而,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女性诗歌”在中国发展了二十多年,当下的生存境况却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有些方面在恶化。首先,就女性主义诗歌运动的群体性而言,女性结社、刊物的出版以及女性诗歌的批评研究,甚至不如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情况,比如日本、韩国都有“女诗人协会”,台湾有叫“女鲸诗社”的社团,由几代女诗人组成,有持续的出版物。而在中国大陆,无论是作为女性主义的文化运动,还是女权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都比较贫乏。“女性写作”作为80年代兴起的反抗文化整体中的一支,在90年代以后遇到了新的困境,出现了挫折乃至倒退。其中,除了宏观的政治、社会原因,还有微观权力的作用。宏观权力显而易见,而微观权力对人的影响和塑造,却往往容易被忽视。比如我们现在身处的这间四壁挂着“死去的黄种男人”的会议室,对于一名女性来说,也是构成个体生存背景的一种微观权力。但这种具体的、细节化的微观权力关系,却经常被忽略不计。
80年代的反抗文化在中国并没有完成,又碰上了市场经济与文化的商品化,老问题没有解决,又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宏观和微观权力交织在一起,很多宏观权力还改头换面以微观权力的形式出现,形成了很多陷阱。我注意到,一些早期受益于“女性”标签的作家,比如王安忆等已经进入文学史的女作家,在被迫回应“女性主义”的问题时,形成了一个通行的表述模式:我不是女性写作,而是作为人的写作。女性作家为什么采用这种自卫式的表述模式?一种原因,是进入主流文学史的策略,进入男性话语主导的“历史叙事”的冲动,压倒了女性自觉的性别诉求(这也涉及到文学史撰写的方式,文学史的叙述怎样安置女性写作?)另一个原因,就是文学商品化与大众文化对“女性写作”的利用与榨取,导致许多女性作者一方面被市场利用,另一方面又试图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市场,从而加剧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总体困境。这是写作的困境,也是批评研究的困境。
面对压抑,有一个通行的应对模式,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压抑-转移-升华”的模式。女性写作同样也掉入了这种应对模式:因为遭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压抑”,于是转移(文学史、市场),既而“升华”。这种转移和升华,有时候还采用了“倒错”的形式。这样一种压抑与转移的模式,作为社会文化病理学,值得关注。这就是女性写作幽灵化的历史过程:从“一间自己的屋子”出发,成了“可能在隔壁的屋子里”。
作为幽灵的诗歌
事实上,我们很可能不知道“女性”是什么,也不知道“诗歌”是什么。就像“女性意识”如同一个身影飘忽的幽灵一样,作为人类反抗文化的一部分,诗歌也是一个幽灵。在权力和资本统治的现实之中,诗歌处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状态。我们在这个会议室里能感觉到自己是个诗人,走出这个会议室,走到大街上、市场上、公司里,就不知道或不确定自己到底是谁了。正如帕斯所说的:诗人在现代社会,成了一个“谁也不是”的幽灵。
不管诗人是什么,诗首先是一个不安地提问的声音,对一切貌似“理所当然”的事物进行提问。压抑之物,往往是以“理所当然”的形象出现的,比如权力逻辑、资本逻辑。诗歌这个幽灵和女性意识这个幽灵的共同之处,就是让单一意义的垄断者产生动摇,让这些单一意义的裂缝中,生长出更多的生命迹象。一些人类共有的特质:无意识、梦幻、死亡冲动、个人的精神危机,这些难以命名的事物,都是坚硬世界的“裂缝制造者”。与其称为“女性特质”,不如叫阴性特质,也许是人类共有的,但你没有充分意识到,或者是因为生存的必要性而进行自我压制的。在此意义上,女性意识与诗歌意识的共同之处,是成为单一意义沙文主义的解毒剂。
诗(文学)不是按订单提供意见的机器,它的根本使命是呈现并捍卫人的复杂性。女性主义的价值诉求,可以理解为:追求平等,保持差异。平等指的是权利的平等,差异指的是性别的差异。文学的使命是捍卫复杂性,反对任何牺牲差异的简化。中国人吃够了简化的苦头,任何一种简化的口号都很容易将人绑架,而且,口号越是简单,绑架得就越快。如果说文学有什么使命,那就是对人的差异性存在的呈现和捍卫,使得人们不容易被打着单一口号的骗局所绑架。这就是诗歌(文学)写作的必要性。
还是让我们回到“一首诗的发生”上来吧。我写过一首以“女人”为题的诗,叫《致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一位女性解读者认为,这首诗表现了三种冲突:国家的、种族的、性别的冲突。概括得很全面。但对于诗歌来说,任何一种解读都是一种简化方式。社会历史批评关注“写什么”,形式主义批评关注“怎么写”,符号的意识形态批判,则关注“为什么这样写”。对于作者来说,“为什么这样写”的追问,是一个最难回避的问题。那就通过这首诗,试着回答“为什么这样写”的问题吧。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到巴黎,一个女人冲进去要破坏仪式,法国警察把她抬走了。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一个穿着现代时尚服装的妇女,在大庭广众之下,在镜头中被抬走了,还没有冲进去就被抬走了,她在挣扎和尖叫,露出一节肚皮。也许她是作为一个人在反抗,但却是作为一个女人被观看:人们通过镜头画面,在观看这幕戏剧化场景的同时,也在观看她的身体细节。一种被观看的反抗,其中有两种权力的交织,一种是宏观的政治(国族),一种是“观看”行为中的微观权力——男人,还有女人,都在观看镜头中的这个女人,有意识的,无意识的。作为对这种“观看政治”的反讽式回应,我在诗中既呈现了被观看之物(女人的各种身体细节),也对观看的目光进行描述,通过对观看的观看,将“观看”陌生化,使之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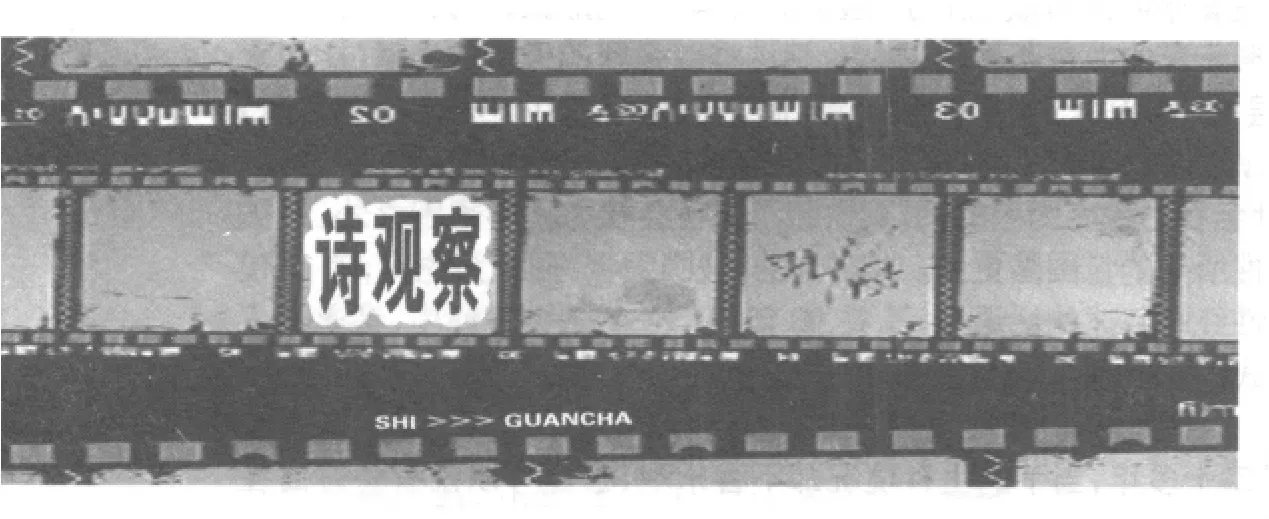
女性写作的语言使命,是“诗与真”,创造一种更本真的生命语言;女性写作的文化使命,则是在批判与修正男权文化及其话语机制的基础上,创造性别对话与交融的可能。同样,诗歌话语也是与文化其他部分,以及与文化整体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不仅仅是“破坏仪式”的对话,还是修复和创造语言的对话。
在女权主义运动最早取得社会成果的那些国家,性别问题主要是作为文化问题,以及微观权力问题而存在。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女性问题同时作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而存在。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个语言问题。
2010年全世界最大的明星是“章鱼保罗”,据说它成功地预测了世界杯重要比赛的结果。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寓言:如果男性不能得救,女性也不能得救,最后的预言家会变成一只章鱼。希望女性诗歌与女性写作成为文学的吉祥物,也成为世界文化的吉祥物。

(本期封面用图选自《艺术与设计》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