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时
——对诗歌与世界之关系的一种看法
2011-01-05刘波
□刘波
当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时
——对诗歌与世界之关系的一种看法
□刘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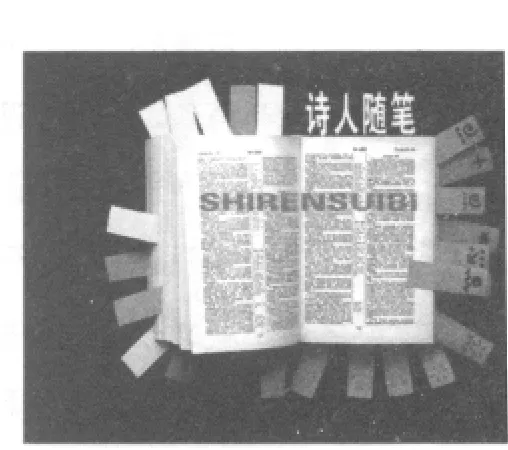
当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不无遗憾地说出“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时,我们在现代性规约下的生活,也已经变得机械而模式化,寻常品之,淡然无味。已经完全被量化的日常生活,何以获得生命的光鲜?一群人的失落与绝望,在所难免。
1918年,梁济正准备出门,恰巧碰到了儿子梁漱溟,于是两人谈起了关于欧战的新闻,梁济突然问道:“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对这个世界是有期望的,但世界真会如梁先生所言的那样变好吗?如今,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坏,当然,也没有变得更好,这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时代。只是,世界不再令人着迷,似乎已是既成事实。我们如何能在这种困境里再次获得突围的可能,如何将刻板的生活资源转化为诗意栖居的激情和力量,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此时,我们需要冒险,需要创新,需要探寻世界另一面可能存在的精神之境。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韦伯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困境。物质的丰盛已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世界的要求,对自我的阅读和审视之机应运而生,可是我们的精神与文化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借助于文化的力量来挽救人类的精神滑坡,已经变得迫在眉睫。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叙事文学也已经毫无征兆地堕落了,小说不再关注人类的终极价值,要么是鸡毛蒜皮的过日子文学,要么是怪力乱神的玄幻想像,其对人类精神本根的探索已经变得极端琐碎,乃至苍白无力。此时,我们还有可慰藉之处:诗人与诗歌的存在。诗歌在“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的时代,充当了拯救人类灵魂的文化角色。只有遏制诗歌不再变得功利化、意识形态化与极端庸俗化,诗意世界的维持或许才成为可能。
历经纳粹浩劫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放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颇带情感色彩的话,有一种对生命悲悯的深刻感悟。话虽这么说,但当时人在经历了那场旷世灾难后,仍然控制不住地抒写着他们心目中神圣的诗行,仍然在以诗歌作为悲伤与愤怒的发泄出口,是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因为诗歌作为语言之精华,它与人类的存在是同步的,它与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悲伤,共同构成人类情感的重要一极。有人说,灾难面前,诗人不能缺席。此言一方面道出了诗人的文字责任,另一方面也为诗人增添了道义的压力:诗歌作为情感的倾泄方式,诗人应该承担人类面对灾难和悲痛时精神疏导者的角色,因为这一时刻,整个社会所处的精神状况是脆弱的,最容易在瞬间崩溃。除了物质上的援助之外,他们在情感上的伤痛,需要诗人通过写诗来抚慰。此时的诗歌,替代并承担了宗教信仰的责任。
德国另一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早在1945年就写出了他的名著《时代的精神状况》,将西方社会的精神困境从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结论现在看来都不为过时,仍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与理论上的指导意义。雅斯贝斯的存在主义哲学,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悲观,但并不是消极的悲观,因为我们听到了他于“人存在着”的境况中有所突破和训诫的真实呼喊。雅斯贝斯笔下的西方困境,正是我们现在仍然在经历着的现实,即使海德格尔这位清醒地得知人类存在困境的哲学家,他也得面对未来的世界;虽然他对雅斯贝斯有所推崇,也有所保留,但他也从内心里尊重荷尔德林这位抒情诗人关于“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理想。诗意地栖居,人类心向往之的感念,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人对此怀有敬意。而当速度成为我们的敌人时,慢不下来的生活节奏,让人感觉不到任何“诗意”存在的氛围。诗意,虽已部分地成为纸上往事,可是现实的生活,总得继续。
当“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这句话,因为时代的压力与人们的眼界宽广程度不同,而缩小为当“生存已不再令人着迷”时,就是欲望本身控制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欲望与诱惑,有时也难以完全抵制,我们周遭硕果仅存的那点诗意,会因人类理性的参与而变得稍稍丰富,这是日益世俗化的世界,唯一能带给我们的精神慰藉。
我们并不奢望奇迹发生,尤其是文学上的奇迹,而当我们去消费苦难,将对悲剧的体验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时,这正是一种文学人生的扭曲体现。文学虽然不主张唯道德和唯伦理主义,但一定是有个底线的,因为道德堕落,谎言喋喋,真相就成为一种虚幻,自古以来皆如此。由是观之,文学不能将我们的灵魂引入谎言充斥的黑暗,否则,人类几千年关于善的精神积淀,必将功亏一篑。我们精神世界里永恒的、不变的常道,仍然是时代和这个社会所无法逾越的创造,唯有它在支撑整个人类精神空间的架构,让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秩序怀有一份探索与追问之意识,这或许才是我们对这个无趣世界的真实体验。
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考利在其《流放者归来》一书中,真实地道出文学历史的无聊和文学前景黯淡的背景下,这个世界在为一代人提供沉沦的理由。他这样写道:“文学,我们所干的这一行,是靠它的伟大的过去而活着的。使我们感动的象征、爱情、生离死别的伟大主题都已经用过,而且枯竭了。所有一切似乎都已经说过,我们又能到哪里去找新的主题呢?文学已把全世界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由于缺乏营养,它正在逐渐死亡。任何东西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我们只得去写边缘经验和反常事件,要不然就只得用自己的巧妙的、辩解的手法把人家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除了次要的主题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考利的焦虑与悲观,都在他向我们诉说的文学主题枯竭的困境中得以显现,这一困境正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难题。我们的作家和诗人们,创作了不计其数的作品,但越来越趋向于模样化,平淡而无聊,轻浮而乏力,其间无美学的创新,无难度的跨越,真是如此,似乎就没有再写的必要了。这个世界,在考利眼里,连文学的主题都已变得重复和乏味,的确是不再令人着迷。但是,我们知道:只要这个世界还有人类的存在,精神文化创造的动力就不会泯灭。
当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时,毕竟我们还有文学,还有诗歌,还有那些优美的、永恒的汉语言可供软化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的精神得到另一种方式的滋养。
我们不用抱怨这个时代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创作好诗的机遇,因为聪明人都知道,最好的时代就是当下,尤其对于诗歌来说,更是如此。诗人侯马曾说过:“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最好的时代就是他所身处的时代,既是被迫,也是选择。”但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本就不多,而既能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又能充分利用这种环境的诗人,更是寥寥无几了。
在诗歌面前,抱怨是无济于事的,悲观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所能做的,要么是坚守,要么就是放弃。此外,没有中间路可走。
诗歌中有你全部或部分的信仰,你定可以选择它,尊重它,与它相厮相守,与它荣辱与共。否则,你就放弃。对于那些既要坚守,还要抱怨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已没有必要再做一个诗人,哪怕是一个蹩脚的诗人。我们劝他尽可以去做一个与诗歌无关的生活者,否则,他就必须承担一种保持艺术和精神高标的责任。
一旦选择留下来坚守,虽然这个世界本就已不再令人着迷,但在诗歌的存在上,它还有希望。在一群混杂的文字书写者中,该关注国家的关注国家,该关注集体的关注集体,还有一部分人去关注个体,关注个体的生命与存在,关注个体的困惑和疑难。对这些俗世个体的关注,本就是和宇宙、终极相联的,它关涉语言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同时也强调精神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见证。
当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时,我更为欣赏和推崇诗人对社会、对世界最为独到的个人看法,而不是像一些张扬、高调的诗人那样,沉迷于集体记忆中作“公共的、远方的想像”。相反,个体言说的价值,相比于毫无诗意可言的集体记忆书写,更能彰显出启蒙的意义。诗人朵渔的诗歌,就是以呈现个体的状态,表达了他对人之存在的追问和探查。比如,他在诗中写道:“他像一个牵线木偶/在四月的阳光里蹒跚学步/半个身子倔强,半个身子/灌满了体制的水泥”(《下场》)。被体制压抑的人最后无可避免地走向苦难的悲剧结局,这种当下的现实经过了诗人的意象化处理,几乎道出了很多身陷其中而浑然不觉者的真实处境,即使是像“一个牵线木偶”一样麻木了,也还努力地在“体制的水泥”的重压下挣扎。而一首《妈妈,您别难过》,就是一部个人屈辱史。“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略带耻辱/所有的职业,看上去都像一个帮凶/妈妈,我回不去了,您别难过/我开始与人为敌,您别难过/我有过一段羞耻的经历,您别难过/他们打我,骂我,让我吞下/体制的碎玻璃,妈妈,您别难过/我看到小丑的脚步踏过尸体,您别难过/他们满腹坏心思在开会,您别难过/我在风中等那送炭的人来/您别难过,妈妈,我终将离开这里/您别难过,我像一头迷路的驴子/数年之后才想起回家/您难过了吗?……当我不再回头/妈妈,我不再乞怜、求饶/我受苦,我爱,我用您赋予我的良心/说话,妈妈,您高兴吗?”从对当下的描述,到对自己屈辱人生的回顾,从念叨于个人的渺小与卑微,到整个人生态度的转变,都是因为体制太过强大。作为一个以文字为职业的人,我们不足以抵抗体制的重压,而只能忍辱负重地吞下“体制的碎玻璃”,这就是一个人的宿命,不论他身处何种困境,终究只是西西弗斯,终究只是堂·吉诃德,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着这样的反抗者,坚持必要的拒绝,不妥协,不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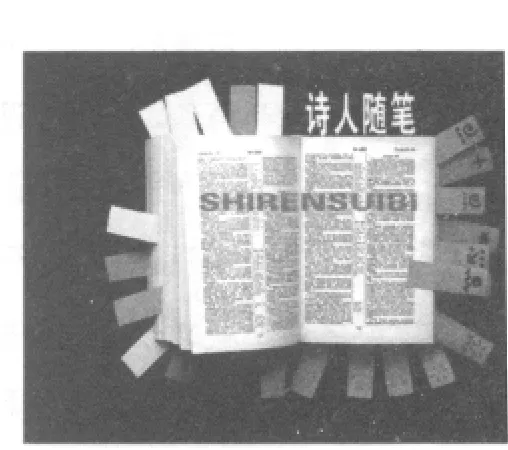
另一位先锋诗人余怒,他的抒写也是在对力量的把握上准而狠的,他曾决绝地说道:“不管诗坛的潮流如何变幻,我们写我们的。”“我们写我们的,意味着不在意、不接受、不妥协、不屑,意味着我们的方面就是这样了,我们是不会改变的,最终改变的将是你们。我们是熊,‘你们是鹦鹉’,我们‘不使用你们的语言’。”这种决绝的精神,就是诗人在这个已不再令人着迷的世界里,所表现出的反抗姿态。在《个人史》中,他将绝望抒写得如此富有力量,直指人心,确非三两天的历练所能成就。“今天写什么?/今天写绝望。/好的,绝望。”这是诗人经过长期思考与对周遭事物不断领悟之后的抉择,在艺术的独立性上,他拒绝合作,并承受痛感。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余怒敢写,也勇于触及人生中那些尖锐而又未明的区域。相对于其他诗人抒写人之表面的绝望来说,余怒开门见山,长驱直入,以自己独立的诗歌自觉,完成了富有现代感的诗意抒写。在别人没有胆识去参透的地方,余怒突破了各种难度和障碍,由个人感受直抵真实的生命存在。
当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时,我们就需要这种反省的力度,这样决绝的断裂,在诗歌艺术上这种拒绝合作的姿态,正是对我们缺乏力量的生命世界最好的回应。
(选自“诗生活”诗论家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