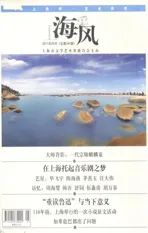被遗忘的时光
——在现代戏剧谷壹戏剧大赏上的表演片断
2011-01-04文/影子
文/影 子
被遗忘的时光
——在现代戏剧谷壹戏剧大赏上的表演片断
文/影 子
“是谁在敲打我窗,使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升出我心坎。”
晚上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你刚才讲出我名字的时候,观众席里就有了反应,最即兴的一种是——“谁?”,你好,我叫影子。
猜我刚刚在后台看见了谁?“蔡琴”,可我并没有找她签名或者合影的冲动,她也没有。我不好意思面对她,作为音乐剧专业人士,经常有人问我邓丽君和蔡琴谁唱得更好,谁更“高雅艺术”一些,我总是想了又想,然后回答他们,邓丽君是歌女转正,蔡琴是学生下海,跟我一样。
有关邓丽君的音乐剧已经有了,我曾经面试过邓丽君这个角色,老实讲,自从演完快男评委以来,我还没有碰到过这么不适合我的角色。不过我想,如果排音乐剧《无间道》,可以由我来扮演蔡琴,蔡琴扮演她自己的形象大使。
为什么?因为全中国人知道的唯一一个音乐剧表演演员就是我,好比全中国人知道的唯一一个指挥表演大师是舟舟。另外,全中国人知道的唯一一部音乐剧是《猫》,全中国人看过也并不知道那就是音乐剧的音乐剧是《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the Music,《音乐之声》这个作品应该多看,应该成为怀有远大梦想的中国音乐剧从业人员的座右铭,a warning, the gesture, 因为《音乐之声》里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我们的使命和前途,far(发), a long long way to go。
但音乐剧的命运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总说中华民族是能歌善舞爱听故事的民族,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如此悠久的戏曲传统,唱念做打,比如京剧,那就是中国的音乐剧呀,所有人始终期待京剧能为本土音乐剧蹚条路出来,所以去年梅兰芳大剧院要演一个叫《我之深处》的戏,大家都很关注,还以为是音乐剧《阴道独白》的中文版,改了个和谐的剧名。后来一打听!敢情两码事儿。
传统与现代结合,这一点,还就是上海人思路开拓。比方沪剧,就没有人家沪剧不敢演的,古今中外,上天入地,毫无顾忌。沪剧改编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卡西莫多给埃丝美拉达献花,埃丝美拉达接一首咏叹调,“哎哟展货呀,嘎好看呃玫瑰花!”。
关于音乐剧的中文版,我眼下正在排练的这个音乐剧堪称正宗了。全英国团队,West End Production,这个戏一经上演,中国音乐剧离跟百老汇接轨也就只差二里地了。早知只差二里地,我就不必绕远路了。五年前在芝加哥,我深夜接到国内的长途说,你赶紧回来吧,中国眼看就要成为百老汇的加工厂了,你还在那儿挣什么血汗钱?我迅即决定回国,我买了一张肯尼迪机场出发浦东机场到达的单程票,飞机票。我原本可以从旧金山走,比较近,但是为了纪念我音乐剧梦想最初的起始点,我打算再次拜访纽约。在JFK候机的时候,我经过一家二手唱片商店,在一筐2.99美元的旧唱片里翻出一张唱片,唱片的标题叫“为什么我要告诉你我去的是上海?”我买下了这张唱片,百老汇巨星Doris Day获1956年格莱美最佳女歌手的录音。付钱的时候,看见柜台上堆着当天的《纽约时报》,财经版的头条上写着“New York is the world, but Shanghai is the future of the world……cause Shanghai will get the money”,我望着标题心潮起伏,然后挣扎着打电话给我的Travel Agent,刷卡买了一张从浦东机场转机首都机场的联程票,同我那13箱的行李一起绕道家乡浦东去了北京。我和上海在浦东走散。
北京居大不易,没有北京户口,还不算外籍演员。不过一开始他们觉得我是,大概是因为我“非人艺”的表演风格以及“非人间”的说话风格。直到他们发现我不是,更糟糕的是,不是外国人却是上海人。Oh my god,You are not外国人,please don’t speak外国话to me!
六年在北京,坚持写一个上海话题的专栏,六年在北京,坚持演一些上海话题的戏。“世钧”,曼桢道,她的声音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就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注意,这不是一个讲春运的戏,是音乐剧《张爱玲》。
张爱玲讲,世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一种爱是为了别离,那是你同你的家乡。有时候我会极度厌恶一个城市,当它看上去像上海的时候。某个街角,一个雨天。很多年来,我在世界的别处跑,在北京住,在舞台上生存,是为了有一天能回到这里活着。你知道,当我在这个城市出生长大的时候,我可从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居然会是个梦想。
梦想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最要紧的是戏剧谷出机票把我带回到我的城市,带回静安寺。我母亲出身培文公寓,父亲出身华山路枕流公寓,来不及了,就近把我生在南洋医院,所以我的起点是卢湾,终点可能是静安。历史上,卢湾的产科多,静安的剧场多,他们俩倒是一桩从中只角爬到上只角的美满婚姻。好像我们在枕流公寓的邻居。那时候满城传,王文娟嫁给孙道临,住在枕流,孙先生在家开英文,王文娟则用绍兴官话,如“道临啊,请侬奈冰箱里面边摆黄油的盒子里边的大头菜沓兹乳腐挪过来过早饭”。Yes,Madam。
静安是我的新业态,卢湾是我的原生态。昨天下午我去复兴路走走。北京来的地产商正起劲地拆房子呢。他居然管这个项目叫复兴复兴计划。他们拆了几十栋房子,包括一座教堂优美的裙房,那座教堂叫做诸圣堂,建于1925年,我的曾外祖父是三个建造者之一,曾外祖父是拉丁裔美国传教士。第二年他的儿子,我的外祖父在上海出生,混血儿,真正的上海人。小时候,每天黄昏,我都要同外祖父一起沿复兴路散散步,经过教堂,教堂优美的裙房,长城电影院,我第一次登台的少年宫,去往复兴公园的草坪和长椅。关于这个公园,据说下一个要被复兴复兴的就是复兴公园。在遥远的北京,我们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群,代号“电马”。电马,你一定记得,从前在公园的北墙下有整整一舞台的电马,那个时候,没有人叫那个“旋转木马”,叫电马。
电马被拆掉了,虽然你觉得这件事最起码应该跟每一个以为电马会永远在那儿的孩子打声招呼。但你也必须承认,谁也不能骑在电马上长大,成熟,变老。就像小时候在儿艺演戏,我以为演戏是永远的事情,有次排《海的女儿》,我演巫婆,台词搞得不得了,我骑在电马上昏头六冲,朝在铁栅栏外等我的外公喊,Is life on stage always this hard, or just when you' re kid?“Always like this.” 他回答。
昨天下午,站在“电马遗址公园”里头,我还在想,如果它们还在,我一定还挑墨绿底子画着彩虹的那匹,然后得意而低调地骑在上面,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头等舱”的感觉。我甚至想,我有一点钱了,我可以订做一匹我自己的宝马,墨绿的底子上画着彩虹,独家冠名,上面写“影子,驾校开除,自学成才”,谁也不许抢,只能让我一个人坐在上面哭。
啊,那些黄昏,那些被遗忘的时光,演出就要开始啦。说到演出,这个世界经典音乐剧《二里地》有个全球接轨的规定:同一角色的另一组演员必须在不上场的演出时间里化完妆换好服装在不超过剧场三四个街区的范围内待命。在这个区域里随便你做什么。可以看电影,但请不要关机。可以喝咖啡,但请自己埋单。出于对公园的偏爱与性价比的考虑,七月里头,上海中心区的市民们能亲眼看见一身维修工打扮的我在人民公园的路灯下溜达。那个公园历史上有过跑马,从来没有电马,没有电马上方的那圈电灯泡,甚至没有星星,城市高楼头上的天空没有星星,但是不远处,舞台上灯火通明,那灯光就是最抽象的星光,最浪漫的灯泡,要你想象,叫你爱上它。
每到黄昏就会想起故人故事,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不管他是不是出生在这里,这可真是个伟大的城市。比如,吕凉,他不是上海人,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以为他是。那年我17岁,大学两年级,那天一道见面的还有精神尚在精肉不在的孙甘露先生,还有我们已经失去的朋友曹小雷先生,大家混在一起冒充上海人。我当时告诉吕凉,我会唱你演的一部电影里的插曲,我真的会。他意外极了,以为没有人会对一个演话剧的人干过的任何事情感兴趣。那一年距离他演这部电影已有10年,现在又过去了15年,25年啊,你也让我意外极了,那居然还是你担任过男主角的唯一一部电影。其后25年他活在令他爱恨交织的舞台上,我猜是这样的,爱恨交织,而“我还年轻”的借口渐渐地都不管用了,证明我外祖父说的没错,Life on stage can be always so hard,为此吕凉获得过壹戏剧最佳男主角,是啊,除此奖赏,我们又怎能去记住一个角色,一次舞会,一份爱情,一个城市,那一首歌。
“这是春天的傍晚,一个温暖的傍晚,街口的路灯下,站着一个单身汉……”
梦是可以叙说的,但只有歌能听懂梦的涵义,岁月是不能言语的,唯有舞台能复述它的最真实的故事。谢谢你们,让我回来重听并续写这个故事。

影子 音乐剧演员。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后留学美国,相继在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及罗斯福大学学习戏剧及音乐剧舞台表演。主演的剧目包括《金沙》《我曾有梦》《我》《妈妈咪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