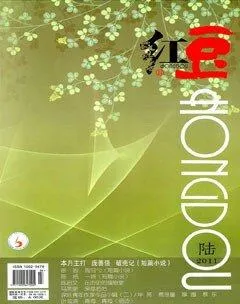黄焕红小散文
2011-01-01黄焕红
红豆 2011年6期
红木
让时间来说话。说出一棵树的前世与今生,说出一段木头日久弥坚的品质。
在时间的长河里寂寂打坐。看日升日落,月盈月缺。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任凭风雨敲打,雷电加身。一棵树,坚忍多年,静默不语,只把身骨,挺直,站稳,站成生命无法坚持的高度、宽度与厚度。
沿着清晰可辨的纹理,一再探寻。一段木头满面霜华,沧桑拙朴,却坚硬厚实,圆润饱满。历经千年风霜以后,千年的木香幽幽袅袅弥漫开来。生命如果可以如红木,那么所有深深浅浅的印痕、沟壑,以及本色里残存着的一些粗犷残缺又算得了什么呢?
以红木为材,去繁就简,去粗存精,加雕,打磨,成屏、成桌、成椅、成床、成柜……红木就具备了亲近众生的质地,拥有了令人赞叹的品质和更加不凡的气度。
树者,木也,成红木,是极品、精品、真品,因而,千年留芳,千古馨香。
尘埃里的花
在—个村落边,一条小道旁,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朵花。
是一朵不知名的小花。安静的容颜,一枝独秀,从路旁稀疏的草丛中艰难探头,向阳,并保持微笑。
我蹲下身,把手中的镜头慢慢靠近那张笑脸。微距里,定格成的画面中,柔软舒展的花瓣上,分明缀满了一些浅浅淡淡的尘土。
我的花,我的美丽而安静的花朵,此刻,仍在我的眼前身下安静且美丽地绽放。
是不是,有多少的艰辛,就有多少的背负?有多少的苦难,就有多少的沧桑?
那些沉积在风中的忧伤,如影随形。原来,根本就无法躲闪抑或遗忘。
人生化境。又是谁,在风里学会了坦然,有坚持,不放弃?
我依然能够看见,那朵花,在风中摇曳、轻舞、微摆,安然,恬淡。
生命里,想要有多少次顽强的绽放,就该具备多少次的坚忍与勇敢。
那个寂静的下午,邂逅的那朵小花,教会我坦然面对,淡然处之,安静生活。
与一朵小花相遇
从山中往山下赶路,被脚下路边草丛中一朵不知名的小花所吸引。
雨后的清晨,谷深林也幽,山清石更静。偶有凉风拂面,可听得草木轻语,露珠微颤。那朵白色的小花,就静静地立于道旁,悄悄地看我。
想起那个山坳里那座破败的土屋前那个背背篓回家的小姑娘,也是素色旧服,清瘦面庞,清澈眼眸,清寒之中遮不住的清纯本色,让人突然之间心里就莫名地疼痛起来。那一刻,我想我该帮她的。
于是,我用我的相机,把它留下来,连同那份纯真与纯净,想留住。我不知道,那朵小花,能够感动多少人,就像我不知道我能帮那个小姑娘走多远一样。
爬山虎
在山里,一棵草,屏住气,使劲往上爬。
我曾在儿时居住过的屋子后院围墙上见过它们。它们和我一起长大。
我住在院子里,它们住在院子外,隔着一堵墙,我们对望。
我也曾认真地打量过它们,它们细长的手脚努力抓着斑驳的围墙,再用一些翠色填满走过的路径,然后,继续往上。
我能看见它们眼中洋溢着的对光热和蓝天的向往与渴望。
我能听见它们使劲的声音。
爬山虎始终高过我的头。我希望自己能够赶上它。
我也曾把手伸给了它,我想摸摸它的脸。
它回了我—手的诱惑,还有向上的力量。
它对我点头,微笑,却始终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我终究还是没能赶上它。直至今时今日。
辗转多年。偶尔,也会想起一棵爬山虎,想起它努力攀爬的模样,想起那些被它用翠绿或霜红叶片覆盖不住的痕迹,那些斑斑驳驳的岁月,那些曲曲折折的印记。围墙上空,半山崖畔,一棵爬山虎,曾经与—缕阳光幸福对接。
在山中,乡下,再次与一棵草对视,也再次被一棵草托举目光。
归家
我从外面回来,我想念一只牵扯过我裤角的狗和一只会生气的小母鸡。
我想去探访村后列队齐整的水稻,还有那些正在扬花的豆角果树。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阳光把我团团围住,拥抱着我,寸步不离。
有脚步,就在田埂边上,一个叠着一个,深深。我踩上去,地上却没有留下我的足迹。风雨只记住了谁的脚印呢?
一只鸟儿,在一棵树上,为另一只鸟儿梳头,唧唧喳喳,谈着恋爱。我没有去打扰它们。
路边草丛中,有一朵花,又一朵花,朝我看过来,它们都不说话,只对着我笑。我俯下身,细辨,却发觉,没有一张是去年的笑脸。转身的时候,我记住了把它们的笑容给自己带上。
爬上山岗,穿越草丛,我想站得更高,看我的村庄,还有前路。可狗尾巴草摇曳的手执意伸进了我的视线,我就无论如何也走不远了。
那条养人的西江河,还在村子的东头拐弯,仍又浩浩荡荡地远去。河水这一回头,就养活了村庄世世代代。
树荫下,有一群蚂蚁正在赶家。它们齐心协力搬运着一粒玉米,忙着储备粮食,还没有空跟我说话。
只有一头老牛,安静地躺在村口的老树下,停止了反刍。它定定地看我,好像记起了我。它浑浊的眼睛让我想起我那慈祥而亲切的祖父。
田地里,依旧忙碌着弯腰弓背、埋头耕耘的乡里乡亲。这里,我看不见那些指手画脚、坐吃闲饭的主儿。
夕阳下,凉风习习,有蝶轻舞,有叶蹁跹。我看见村子上空腾起些许炊烟,村庄于是变得温暖起来。
夕阳西下,我仍做一个归家的孩子吧。
菊
秋里的菊,是季节里最亮丽的风景。
黄的、白的、红的、粉的、淡的、雅的、艳的,单瓣的、卷散的、舞环的、球型的、莲座的、龙爪的、托桂的、垂珠的、垂丝的,平瓣的、宽瓣的、爪瓣的、筒瓣的、针瓣的、丝瓣的、钩瓣的、扭瓣的,短发的、披肩的、薄衫的、实心的、吊带的、长袖的……这个季节里的菊,直让人看得心神恍惚。
菊科女子实在是不简单的女子。
行走于古典诗词里,菊凌风傲霜,独立寒秋,品格高洁,是花中君子。
行走在山野坡冈上,它们看似清瘦、纤弱,实则坚忍。它们相互簇拥,轻易就开成一片、一坡、一山岗,开成漫山遍野的星星点点的黄,或者白。
以花入药,菊性凉,味甘苦,有疏风、清热、明目、解毒之功效,具备了清火、去燥、宁神、定心的品质。
现如今,菊已大摇大摆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它们走进培育基地,走进医院,摇身一变,迅速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华丽转身。它们或大气,或雍容,或美艳,或华贵,千姿百态,千种风情,万般妩媚,轻易就舞动成五彩斑斓的风景。
多元的世界,造就了多元的菊科女子。
无法简单地说出爱与不爱,喜欢或是不喜欢。
多年以后,走进药店,抓摸一些草药时,突然就想念那些开放在山野里的一大片又一大片怒放的菊。
狗尾巴草
靠近村口的土坡上,有一丛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
心念转动间,脚步不知不觉已停下。
很多年了,狗尾巴草一直长在心里。乡村的土地上,尽是一些滥生的野花野草。狗尾巴草是最不起眼的一种,却常常为我所瞎念。细细长长的叶,细细长长的颈,托着狗尾巴一样毛茸茸的穗,在风里轻轻地摇,款款地摆。若是雨天,还能看见毛穗上串足了一排排亮晶晶的珍珠,倘若出太阳,便折射出一道又一道五彩斑斓的光,很是可爱。每次看见它在风中招手、点头、微笑,便觉得那是最开心最幸福的日子。
乡村的童年生活,日子不会孤单寂寞。那些有狗尾巴草相伴相随的时日,心上总是结满了日夜飞翔的梦。
再见狗尾巴草,它那平静素朴的脸,让我突然间就想到了阔别已久的亲人,一颗在外奔波劳顿已久的心也很容易地就想起了那些单纯祥和的日子。
站在一丛狗尾巴草前,寻找旧日时光,寻找一些远去的人和事。
记忆里那个能用狗尾巴草编织戒指和小狗的邻家妹妹现今流落何方?
经常用狗尾巴草追我痒我直至把我弄哭却在我摔伤后仍会背我回家的小哥哥今安在?
曾经在狗尾巴草摇曳着的安然恬淡的梦境里喂养出来的内心平静而今哪里去找?
把手放在心口,对着一丛狗尾巴草,轻轻说出疼,和叹息。
故乡,童年,梦想,似乎伸手可及却已面目全非。
注定在乡村,再次被一丛狗尾巴草牵引,招手,唤回。
时光老去,岁月之手,已将沧桑刻在谁的脸上?
折一枝狗尾巴草,倾听岁月流逝的声音,再做—个关于童年的梦。
梦里,有阳光的味道,有花草的清香,有风的抚摩和雨的关照。
卑微如狗尾巴草,其实和我一样,只是这个尘世间最普通最平凡最微小的个体,没有人关注。但我想,有梦想地活着,真实地活着,应是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了吧。
蜗牛
负重行进,总比不背负盔甲,心里踏实。
年少的心,不会懂得尘世的风雨有多大,人世的变数有多快,也不会知晓生存的压力和生活的艰辛,也总以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去承受一次又一次的风险和挫折。
很多次恶作剧地去触碰那些雨后爬行的蜗牛,笑它们身负重荷,看它们颤抖着柔软的躯体,惊慌地退缩触角,然后,再怯怯地抬头,张望。它们憨笨可爱的模样,曾清晰地刻进记忆里。
一次次地玩耍、戏弄、伤害,蜗牛忍让、躲闪、逃避,终于,它们不再能够相信我们,拒绝前行,选择退缩甲壳,保全自己,不再轻易走出防护。
童话故事里,蜗牛妈妈与小蜗牛的对话仍在耳边:毛毛虫没有甲壳,但它可以变成蝴蝶,有天空的保护;蚯蚓没有甲壳,但它可以穿越泥土,有大地的保护。蜗牛没有天空和大地的保护,背负重壳,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
很多年以后,才逐渐明白,自己也正慢慢地变成了一只小蜗牛。
—个雨后的下午,一只小小的蜗牛爬上了我家的阳台,再次爬进我的记忆,再次爬进我的视线。
它厚厚的甲壳重压在身,长长的触角小心且努力地向天空探寻,柔软孱弱的身体紧贴地面,正一步一步缓慢地向前爬行。
我知道它有着和我同样的对梦想的渴求,有着和我同样的对前路的猜疑与戒备。
我从它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忍隐、迟疑、迷惘的内心。
多想向它问声好。
窗外,有风吹过来,小蜗牛收紧了身子,然后,再伸直,继续爬行。
有雨,仍要下。
窗前,剩—个我,和一只小蜗牛,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