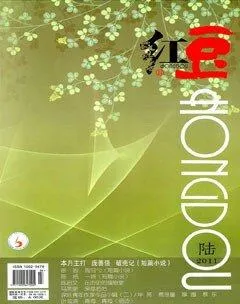成人礼
2011-01-01厚圃
红豆 2011年6期
好多年前,仙桥街的尾巴上开了一家剃头铺。剃头铺挨着池塘,房子破旧,后墙有一截浸在水里,夏天好凉快。池塘的边上有座小庙,供着百爷公。百爷公其体管什么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它会保佑人畜平安。池塘的水绿得发黑,滑腻腻的,阳光在波尖上涂抹、跳跃,远远望去如无数水珠在巨大而肥厚的荷叶上滚来滚去。池塘四周,养鱼人用白灰画了一个个圆圈,说是吓水獭的人脸。水獭爱偷鱼,吃得肥滚滚,一旦被养鱼人逮住就会被剥皮破肚,用南姜、豆豉焖煮下酒。
在我的印象中,那家剃头铺的西墙挂着一面四方大镜,底部水银驳蚀,还有一片熟牛皮被蹭得肮脏油亮。镜子下面有一木架,窄窄的像道暗影,上面杂乱地放着剪刀、推子、梳子、剃刀、粉扑、耳耙一类扭食的家伙。屋子不大,光线却不错,一大早,阳光便穿过后窗,落在断砖砌成的水池上。那水池有三尺高,臂展长,客人剃完头就踱过去,坐在条凳上等待冲洗。对于有些男人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俏丽的老板娘阿娟就要出场了。她扭动腰肢,跷起小拇指,托一瓶兑好的香皂水,那仪态犹如观音娘娘手持净瓶欲以甘露滋润万物。黏稠的香皂水一点点地滴到客人的头上,凉浸浸麻酥酥的。她纤长的手指开始来来回回地抓挠,那样子好像乐师对着古筝投入地弹奏。泡沫开始蓬松起来,雪花般地覆盖了“黑草地”。无论严寒酷署,总有暖暖的清水从壶嘴飞下,渗入头皮,汪开来,顺着发绺、鼻尖落入水池。水池的出水口很小,有时被成团的头发堵住,漂着泡沫的水便流得极慢,在铁丝罩上堆起了白白的花儿。
剃头铺的老板叫杜顺,四十上下,刀条脸,小眼睛,高瘦个儿,爱喝酒,每回喝得像个红脸关公。就这样,他带着股很冲的酒气给客人剃头。别看他醉醺醺的,却从未失手过。老杜的老婆,也就是阿娟,比他要年轻十几岁,又细又挑的眉毛,两只眼睛会说话,嘴巴跟抹了蜜似的甜。仙桥街人都知道她是邻镇的,因家庭成分不好被耽误,只能凑合地嫁了。
那些臭男人想阿娟,又不好意思来,就打着帮衬老杜的旗号。我倒是不想来,每回老杜总要我让这个让那个的。可是我又不能不来,谁叫他是我父亲的把兄弟?
我要说的是一个夏天的中午,日头很毒,热气贴着地皮颤动,房屋像快要燃起来一样,街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四周很静,静得听得到木头因曝晒而裂开的响声。我混混沌沌地坐在那条被无数个屁股蹭得锃亮的长凳上,两条悬空的腿不停地甩动,接榫处发出了吱吱乏味的叫声。我在等该死的大脖子老赵。
老赵的脖子上有个红亮的大瘤,走起路来歪着脑袋像只觅食的番鸭。
在这么—个炎热的中午,连爱说爱笑的阿娟也打不起精神来,两三个盘碗在她手里叮叮当当地转动了老半天,中间还停下来发了一会儿愣,魂儿不知游到哪里去了。洗完了碗筷,她又从门后抽出把苕帚,弯下腰慢腾腾地将一团团的发丝扫成一堆。
有道白亮亮的影子如肥鱼般游进了我眼睛的余光里,我的腿一下不动了。
阿娟扫了—会儿,突然抬起头来瞪了我一眼。
“小东西。”她扯了扯领口低低地骂了一句。
我的目光呼地飞开。
剃头铺隔壁卖水果的张小妹说,阿娟的胸脯有那么高,是偷偷往奶罩里填了海棉。
张小妹曾经是仙桥街最引人注目的靓女,身材火辣,胆子又大,到处显山露水的,嫩后生见了都脸红。自从阿娟嫁过来后,她就迅速黯淡,再也没市场了。有一天,我和小永几个在街心水泥地上钉了枚镍币,然后躲到一边观“景”。那天日光如水,假如说大街像一条宽阔而空虚的河流,那枚崭新的镍币就是熠熠发光的小贝壳。阿娟来了,她一弯腰,两大半白滚滚的奶子就从领口袒出来。天哪,要是张小妹看到了肯定也会惊呼:一山更比一山高。
好不容易盼到老赵起身,我赶紧上前把座位霸住。可是,让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我的哥们小永被他父亲拎着耳朵像头肥猪嘟嘟囔囔地撞进来。
“反了你,小小年纪学人家剃什么流氓头。”他父亲粗着嗓门骂,感觉却像在指责老杜。
刚才在外面我才碰见乌强,他笑嘻嘻地凑到我耳边说,小永的小鸡鸡痒了。这回肯定会倒大霉。
老杜摊着手解释:“你儿子非要我照着电视里的明星剃,香港人就喜欢这种派头,长头发,大鬓脚。”
我们镇文化站有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都把几条街的老人小孩全吸引过来,闹哄哄地挤成一堆跟烤火似的。
“老张,你说怎么弄?”老杜瞪着眼睛满脸的不高兴。要每个人都来返工,都要他剃上两遍,那生意还怎么做?
小永的父亲说:“就平头,越短越好。”
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把位子让给了小永。
小永不肯坐,老杜就拿出往瓦罐里装酸菜的架势硬把他压进去。屁股都落到椅子上了,他还装模作样地挣扎几下,像要竭力挽回一丝脸面。他父亲可不像老杜那么客气,大手一叉把他摁了个牛饮水,两只眼睛只能盯着自己的脚尖。
老杜就趁机上推子。那个黑糊糊的家伙如拉犁的牛从小永的头顶呼呼走过,排下一道道青白的头皮。有好几回小永抬起头来,狠狠地剜了他父亲一眼,嘴里念念有辞,像在诅咒他不得好死。
剃平头就像割草,是件粗活,没什么好讲究的,转眼间新潮的小永又恢复到过去土里土气的模样。我过去拍拍他肩,安慰他说:“剃得不错。”
这句话一箭双雕,既抚摩了小永的疼痛,又拍了老杜的马屁,等会儿他好专心给我干活。
专拣软柿子捏的小永对我凶得像条狗,“不错个屁!”
我才懒得理他呢,一屁股落在被他坐得发烫的椅子上。
老杜胡乱给我系上一件脏乎乎的罩衣,见我的目光还尾随着小永,就毫不客气地将我的头扳正、托住,生怕掉下去一样,然后往后一仰,觑着眼,摆出一副认真观察、谨慎人手的姿态,就好像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发型师。
我正要说点什么,他突然又撒手不管了,踮着脚尖溜到一边去。
老杜就这衰样,在他眼里我永远是个屁股都不会擦的小傻冒。
待他慌里慌张地跑过来,阿娟的咒骂声已经席卷而来,“死酒鬼!‘好吃不如懒做’,干脆关门算了,你赚的钱还不够买酒喝……”
老杜浑身散发着酒气,一声不吭地用指甲奋力掏着自己的耳洞。
我不喜欢老杜用蜡黄的长指甲把我的头皮抓得沙沙直响,我更受不了他耳洞里的那撮黑毛。有一次我忍无可忍地问:“你为什么不把你、你耳朵里的那些毛……剪掉?”
他嘘了一声,故作神秘地说:“你不懂,这叫厕上樱花——算命先生说过,旺财!”
“旺财还用得着给人剃头?”我皱起鼻子不屑地说。
“闭上你的臭嘴。剃头怎么啦?行行出状元,捡破烂的还成破烂王呢。”
“算命先生还说你喜得贵子,怎么就没见你生出来?”我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这下可真捅了马蜂窝,谁不知道阿娟嫁给老杜好几年,肚子始终没有变化?老杜就天天打她,没夜没日地捣腾,最终还是没有效果。听说阿娟一怒之下跑到医院做了检查,回来后老杜就矮了三分,酒越喝越多。
大家心知肚明,老杜变得那么怕阿娟,一定是被她抓住了什么把柄。
我的话无异于往这对夫妇的伤疤上撒了一把盐。阿娟气得快不行,要不是老杜拦住,她非得给我一耳光。
“我们不想要,啥呢?要是生了个像你这样的儿子,不把我们气死才怪呢。”老杜故意这么说,又大声问我,“快说,留长点还是短点?”
“你能给我剃小永的那种头吗?”
“平头?”
“飞机头。”
我铆足了劲儿说。
他足足看了我一分钟说:“喔喔,你不是也想让我返工吧?老子吃饱了撑着啊。”
我要作出回应,就听到门边传来一阵响响的脚步声,屋里暗了一下,有个人进来。
“肖镇长?”老杜扭过头去,烫到了似的叫起来。
镜子里出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穿着短袖的白衬衫,皮肤黝黑,抹过发蜡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苍蝇在上面怕也站不住脚。他的样子看上去要比老杜年轻个好几岁。
老杜停下了手头的活弓着龙虾腰问:“你都好久没来了,又去城里开会?”
镇长凑到镜子前察看着布满红丝的眼睛,敷衍地说:“上头来人,陪他们四处转转。生意还好吧?”
“还好还好。”老杜边说边推我,见我死死抓着扶手不肯动,就压低声音说,“小子,快下来,让大人先剃。”
我摸着阴阳头愤怒地抗议:“我的头是不是要剃到晚上?让了一个又一个。”
“去去去,一边呆着。”老杜赶牲畜似的朝着我低吼,又仰起脸,像跟我又像跟镇长说,“领导的时间多宝贵呀,操心的可是大事情。”
我一离座,老杜就拿起毛巾抽了几下,不知道是在清理椅子上的发屑还是在给它降温。
“早上还掐着指头算,快一个月,镇长的头发也该长长了,我差点就叫阿娟去请你呢。”
“阿娟呢,出去了?”镇长坐下来架起一条腿问。
老杜还没回答,就有轻轻的几声娇笑在空气中丝缕般地扯开来。
“在呢,您老人家一来就跟查户口似的。”
阿娟从后边的茅房急匆匆跑出来,双手还在给裤腰侧边的小带子打结。午间的疲态在她脸上一扫而光,生火,煮水,泡功夫茶,动作麻利得很。茶熟了,她又一小杯一小杯地端给镇长喝。茶香在空气中弥散,把我馋得不停地咽口水,却没人招呼我喝一杯。看着这对势利鬼,我的肺都快气炸了。
镇长的头终于剃完了,老杜解开系在他身上的罩衣哗哗地抖了两下,空气中似乎充满了纤细的毛发,把我的鼻孔弄得痒痒的。接下来该轮到阿娟给镇长洗头了。
我凑上前,可镇长并不急,他坐在那里稳如泰山,边咕噜噜地喝茶边冲着阿娟笑,“呵呵,这茶不错,不错。”
“哪有这样吹嘘自己的?”阿娟的声音跟叫春似的,听得我一身鸡皮疙瘩,“这可是您上次捎来的‘一枝春’呀。”
“瞧我这记性,哈哈,刚刚人家还给了几包好烟,惦记着给老杜捎来,没想到一转身就忘了。”
镇长的目光还在阿娟的脸蛋上赖着不走。
“不用不用,您看您已经把我们照顾得这么周全了。”老杜赶紧说。
镇长站起身来,转了转脖子,甩了甩胳膊,活络一下筋骨,爽朗地说:“谁叫咱俩是老同学呀。”
见到我抢到座位上,老杜狠狠地推了我一把,就不再说话,嘴巴绷得紧紧的,对着我的头东一剪西一剪叉干草似的。头发纷纷扬扬地从我的眼前飘落下来。
虽说老杜从不收我的剃头钱,我还是窝了一肚子火。下次不来了,这点钱老子又不是掏不起。我在父亲面前不止一次地发过这样的牢骚。父亲有父亲的道理,他说叫你去不是为了省钱,你去是给杜叔叔“做脸”。
我知道,男人与男人之间最讲究的就是面子。
很快,阴阳头变成了青皮梨。我对着镜子转动着脑瓜,准备给老杜挑刺,没想到水池那个不易察觉的角落一下子闪人镜子里,跳进我的眼帘。阿娟的屁股像口大锅挂在那里,有只手在上面又捏又掐,像在检查篮球的气儿足不足,够不够弹力。我敢说,那只手绝非阿娟的手,阿娟的手纤长白嫩,哪有这么粗的骨节和筋络?我吓得赶紧闭上眼睛。不可能,一定是看走眼了。我使劲地夹了夹眼,又忍不住扭过头去。我突然的举动把老杜吓坏了,他拿着剪刀的手悬在半空中,眼睛也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我还没看清楚,脑瓜就被他粗鲁地旋过来。
他的双手扶着我的肩,不停地战栗,那种战栗像冷到了极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老杜哪还有心思干活?他面如死灰地僵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着镜子里,惊讶、沮丧,还有一种被逼入死角的恐惧。
镇长洗好头,缠了条雪白的毛巾,看起来像个阿拉伯人。他趴在水池边上,由阿娟替他松骨。极少有客人得到这样的优待。阿娟合起手掌一心一意地敲打着他的脊椎骨,那声响和镇长的哼哼唧唧变得格外刺耳。
镇长过来时,那里早就虚位以待。我坐在条凳上,屏住呼吸,心里有种预感,某件惊心动魄的事就要发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老杜替他的老同学重新披上罩衣,又细心地在他的脖子上垫了条干净的毛巾,调整好椅背,两只手搭在他肩上轻轻一按,他就斜斜地滑下去,眼睛微闭,那惬意的样子像在沙滩上晒太阳。
老杜开始往他的唇上、腮边、下巴抹肥皂水。我看见镇长不停地咽口水,喉结处像毛根没拔净的鸭脖长满了青蓝色的胡茬。
老杜转过身去挑了把剃刀,对着那块熟牛皮使劲地蹭几下,像戏里“白鼻头(花花公子)”玩折扇一样绕着虎口旋了几转,半空中立刻画出一圈圈白光。
阿娟不经意地抬头,碰到老杜的目光,像被什么击中,差点叫出声来。她的手下意识地扶住池沿,帮着发软的双腿托住身体。
老杜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似笑非笑,这种怪怪的表隋谁见了一辈子都忘不掉。
镇长还在闭目养神,对慢慢逼近的危险浑然不觉。他听见老杜响响地咳了一声,似乎往地上射了口浓痰。
“老同学,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老杜从喉底挤出的声音发出微微的颤抖。
镇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蹙了蹙眉头。自从他当了镇长,老杜就再也不敢以老同学相称了。
“什么事?”
“阿娟的体检报告是不是你找人办的?”
镇长像被噪音吵醒了一般,微微睁开眼。老杜的脸离他极近,都变形了,像要把他的脸压成饼子。
“我让那条‘母狗’怀上了。”老杜轻轻地说。
“你当真拿那个寡妇试了?我不过随便跟你开了个玩笑。”
镇长压低声音说,眼珠子直往下找,眼皮底下的刀柄渐渐地清晰起来,这时他才感觉到脖子上挂着的那一丝冰凉,如细细的寒风掠过。他的心忽地沉了下去。
“我哪敢不听您的?镇长大人。”老杜明白,自己果真上了这对狗男女的当。
“你要干什么?”镇长将收回的目光狠狠地掷到老杜的脸上。
“我想听你说实话。”
“你想听我说实话?好,我说给你听——李老三把你踩在脚下,是谁把你拽起来让你骑到他的脖子上去的?是谁给你开的剃头铺?是谁帮你讨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是谁他妈的一年到头对你有求必应让你活得像个人样?老子,是老子!狗杂种,这些就是大实话。”
镇长面无惧色。他当过地雷兵,早把生死看得比纸灰还轻。
“你对我的好,我念你一辈子。”
老杜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剥光了衣衫,羞惭难当直淌虚汗。
“好,做人不忘本就好。”镇长大声说,像在给这件事下结论。
“可是,阿娟已经是我的老婆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老杜嗫嚅着说。
“哼,不一样?”镇长发出了冷笑,“她要是生得了孩子哪还有你的份?做梦去吧!”
老杜的手又开始抖起来,然后是肩膀、胳膊和牙齿。老同学,他的大媒,原来是把他当成垃圾桶,玩够了就把阿娟丢进来,想玩了又捡了回去。他真想一刀切下去,让鲜血喷溅,再转身干掉那个贱人,然后自己结果自己。可是,他被镇长那股理直气壮、视死如归的气魄震住了,竟老半天不敢动弹。
“没有我,你能给她什么?”镇长缓缓地闭上眼睛,平静而又安详,“老杜啊老杜,你是拿剃刀的,我是拿公章的,这就是命。如果你不认命,我也不认命,这个世界就会乱套了。”
“乱套?乱套?”老杜哑着声,把这几个字搁在嘴里嚼着,仿佛可以嚼出什么滋味来。
“给我快点,他们还在等我开会呢。”
我看见老杜挺直的身板像个遭火烤的鱿鱼干,蜷曲,收缩。他的手开始滞重而缓慢地移动,前前后后忙活开来。
凝固的空气像解了冻,哗啦啦地流动出声音。
阿娟长长地舒了口气,苏醒过来一般,眼睛红红的,鼻尖也红红的。她捡起掉在地上的毛巾一瘸一拐地晃到后头去。
“老杜,你今天的手脚真不利索。”镇长用调侃的语气说。
老杜犹豫了一下,哼哼哈哈地敷衍:“细心一点好,细心一点好。”
剃完头,镇长摸出几张崭新的钞票用力拍在木架上,背起了双手大摇大摆地走出那道窄门,没一会儿又折回来朗声说:“我那辆单车要换了,什么时候叫阿娟过来骑走吧。”
四周很快又恢复了阒静。
老杜不知喊了几遍我才回过神来。我朝门口望了望,证实再也没人来了,这才战战兢兢地爬上椅子去,用镇长的余温温暖着冰冷的屁股蛋。
老杜默不做声地给我收拾了一通,说:“好了。”
“还没剃胡子呢。”
就为这事,我已向他交涉过无数次。
“小猪光溜溜,哪来的毛呀……”
老杜故作轻松地说,跟以往不同的是,他真地拿起了剃刀。
“好你个老杜,终于没把我当孩子了。”我得意地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羡慕梁山好汉们那一脸的胡须。男人不长胡子就没了威严少了霸气,一点都不阳刚。听老人家说,用生姜给孩子擦眉毛,眉毛就会长得又快又密,我也试过用生姜搓唇边、下巴。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看看有没有长出硬硬的胡子来,结果手指掠过处仍是些软软的绒毛。
老杜从没这么认真对待我,他将肥皂水抹到我的唇边、鬓角下。我能感受到他粗糙的手指掠过我娇嫩皮肤时的灼热,还有肥皂水渗入我嘴角的咸味。他俯下身来,一身浓重的汗臭、酒臭快要让我窒息了。他一只手托住我的下巴,剃刀自鬓角凉凉地掠过。我仿佛听到刷刷刷的响声,看见胡子大片大片地落下来,脸上的皮肤变得洁净、光滑,散发出肥皂水的香气。
自始至终老杜一言不发,那一会儿给我的感觉却像漫长的一年。
剃完了,他狠狠地将剃刀钉在木架上,走开了,刀柄还在微微颤动。
我吐了吐舌头,抻着脖子摸了摸剃过的地方。皮肤有点紧绷绷的,像长了层壳。我相信只有用这样的大剃刀刮过,胡子才能变硬、变粗,莽莽丛生,我才能真正长大或^。
阿娟过来了,紧抿着嘴,颤动着手里的圆口刷子掸去我脖子上的碎发。她还弯下腰来鼓起腮吹了又吹,一股抹了酒精似的清凉顺着脊梁骨一直痒到我的脚趾尖。
临走时我掏出自己的零花钱,学着那个镇长响响地拍在木架上。
“谢了。”我挺起小胸脯大声说。
一出门,就看见老杜坐在铺窗前的—个石墩上,手里晃动着一只空瓶子,眼窝里闪动着两大朵混浊的泪花。
“和尚,别以为长大了就会有好日子,做梦吧,哈哈哈……”
很冲的酒气散进了老街混蚀的空气里,凄怆的笑声在我耳边飘荡着,经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