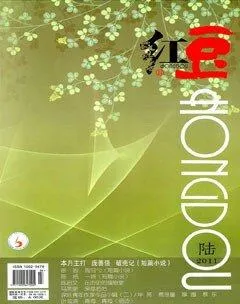深慈若厉
2011-01-01马笑泉
红豆 2011年6期
除夕那天,依照多年的惯例,母亲和三位舅舅都率领着一小家人,齐聚外公家吃团圆饭。一大家人围坐在餐桌边,不待斟酒,气氛便已和暖。只是今年的餐桌边,少了外婆清瘦的面容。谁都不提这件事,大家都秉承传统,在年尾用笑语和祝福来冲淡一年所承受的辛苦和伤痛。但在间歇性的沉默中,我仍无法避开这样一种悲凉的感触:亲人离世,就意味着她再也不会和我们—起吃团圆饭了。她去了—个凡间任何交通工具都无法抵达的地方,无论我们多么想把她接回来,她多么想回来,都做不到了。
民国二十一年农历三月十八日(1932年4月27日),外婆出生于新邵巨口铺栗坪—个没落地主家庭。这种出生背景注定是两头遭罪:新中国成立前未能享受地主家小姐锦衣玉食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段时间里却要为此空名而饱受政治歧视。外婆一岁多的时候,曾外祖父就因吸鸦片烟死去。曾外叔祖们想谋夺本来就不多的田产。曾外祖母被逼得无法,只好抛头露面去打官司。出门的时候,外婆拉住她的衣角不肯放。曾外祖母—脚把她踢倒,然后头也不回地上轿走了。官司一打就是六年,终于还是赢了。而曾外祖母的这一脚也烙在了外婆心上,后来她跟儿女们多次说起此事,语气中饱含复杂的感慨。当时由于经济窘迫,外婆和长工家的女孩们一样,从小就要学习绩麻、纺纱、绣花、勒袜子底和做鞋。这全套女红功夫在中国南方农村传承了千年,到了外婆这一代,应该是大面积传承的最后—代了。到了母亲这一代,便是不会的属于正常现象,会的倒成稀罕人物了。我小学和初中时冬天穿的棉鞋全是外婆坐在门口,戴着个铜制顶针,用已被时光浸泡得黑黄的木夹板紧紧夹着鞋底,借着天光(她舍不得开电灯)一锥一线纳出来的。到了2008年冬天,我女儿出世,还能享受到外婆缝制的小棉内衣和小棉内裤。一年半后,外婆去世,家里就没人能做这些东西了。随着她们这批人的相继离去,一个纯粹的手工年代将最后彻底地消失。那些在各个旅游景点开设手工作坊的年轻一代,只不过是对祖辈们的劳动进行徒然的缅怀和模仿而已——手工制品如果脱离了日常生活,成为了点缀性的商品,那么,它就先已在精神上死亡。而那些令人惊叹的技艺,都是在漫长的日常操劳中积累起来的,决非匆促培训一两个月就能领会的。没有日常性作保证,技艺中最精微的部分势将消亡,只留下—个似是而非的外壳。当年外婆在寂寥的青砖宅院中埋头制作女红时,当然无法预见她所潜心操练的技艺大部分在一个甲子之内就将成为绝响,如同她无法预见自己日后的命运。
能够读到初中毕业大概是地主家庭带给外婆的最大恩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初中生比今天的本科生更容易找到工作。1950年,十八岁的外婆来到隆回岩口小学担任教师。在三十五年的教师生涯中,她在一所又一所小学之间频繁地调动。退休后一总结,竟然在十六所小学教过书。这些小学大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鸟树下完小,千古坳完小,桐木桥完小,荷香桥小学,新田小学,竹叶小学,砚冲小学……这些地方后来我多半去过,除了在县城里的群贤小学外,其他都是群山环绕的乡间小学。我去的时候起码是通了毛马路,能够坐在中巴车上一路颠簸而行。在外婆那个年代,很多地方是没有通车的,只能肩挑手提一路步行。累得腰酸背痛不说,还要担惊受怕,因为四周山深林密,人烟稀少。解放初期,湘西南一带,土匪尚未绝迹,华南虎们都还在世,更别说豹子、野猪和狼这些适应性更强的猛兽了。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漂亮女教师,提着背着大堆家当,独自走在荒凉的山区,这样的场景,如果是出现在张艺谋的电影中,那当然会显得很有诗意,如果是出现在现实中,只能让人觉得有几分残酷。好在外婆的孤独不久就结束了。第二年,她调到隆回县立五小(今天的滩头完小),遇到在那里工作的外公。两人是那个年代的帅哥靓女,又有相似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外公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可谓一见钟情,半年时间就订下终身。只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要服从革命的需要。1951年下学期,县教育局一声令下,颇具干才的外公调县立二小(今天的六都寨完小)当校长。1952年元月,外婆翻山越岭,从滩头步行近百里来到六都寨,于19日在区政府与外公领了结婚证。在2011年的开端,我看到五十九年前的那位青年女教师,在冷得呵口气就能结成冰的冬天清晨出发,在由青石和红土构成的似乎永无尽头的山路上穿行,惊叹着是什么给了她如此的勇气和激情!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两个字:爱情。那时外公虽然当了校长,却是一贫如洗,连结婚那天用的蚊帐都是找同事借的。但他们无疑是快乐而满足的。清贫的年代,纯粹的爱情。写到这里,我开始有些理解老谋子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山楂树之恋》虽然拍得过于唯美,但那个年代的爱情相较于今天,确实简单许多、纯净许多。在这一点上,老谋子是对的。而正如老谋子所拍,那个年代的恋人虽然所求甚少,却注定要承受今天80后、90后小恋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压力。虽然不一定要以死亡作为结局,但生之艰难却无法逃避。原因无他:简单的爱情碰上了复杂的政治,还有创业年代的艰苦条件。
1952年上学期,组织上照顾夫妻关系,外婆调到六都寨鸟树下完小。刚免去两地奔波之苦,外公却突然病倒。他左腋和胸前生了两个大毒瘤,最严重时一天要流脓一大茶杯。疼痛让他无法工作,不得不停职到鸟树下完小养病。当时还没有实行公费医疗,停职期间又无工资发,真可谓贫病交加。乡间普遍认为这种病难以治好,有的人劝外婆趁着年轻,还没生小孩,早做打算。外婆不为所动,除尽心服侍外公之外,还四处访医。老天爷被她的苦心所感动,让她访到了僻居于司门前赵家垅一位姓赵的中医。他有家传秘方,善治无名肿毒。但那种药得用新鲜草药现配,无法长时间储存。外婆有时星期天清早出发,步行到四十多里外的赵家垅拿药,晚上回来后还要强忍疲惫,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外公洗净伤口,贴上膏药。经过大半年的调养,外公的病竟然初步痊愈了,连赵大夫也认为是个奇迹。此后两年倒也顺遂。1954年鸟树下完小搬迁到千古坳,母亲在这里出生。不久外公被调进城里,任县教师联合会主任。1956年调桃花坪完小(今天的东方红小学),担任校长和支部书记。组织上为让他尽心干革命,把外婆调进了城里的群贤完小。那时的干部,从上到下都有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劲头,恨不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能为革命建设作贡献。1956年学校放寒假,外公却没有寒假放,被调到六都寨修马路。就在他以大队长的身份带领几千民工奋战在北风呼啸之中时,数十里外有个婴儿发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声啼哭——那是我大舅出世了。因为是寒假,没有女教师做伴,也没有接生员在场,而且还是倒胎。在那时候,我想外婆肯定感受到了人生最大的无助和恐慌。她终究是捱了过来,只是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也许就从那一刻起,她作为女人的柔弱开始被剔除,慢慢形成一种刚强,甚至有些冷峻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打击中迅速淬火、定型,成为她抗击艰难岁月的利器。
就在这年寒假,外公被定为内部肃反对象。挨了一番批斗后,又被“充军”到偏僻的桐木桥完小。在那个年代,背上了政治罪名,就意味着前途全毁。外公本想好好干一番事业,未料横遭冤屈,难免心灰意懒,甚至冒出了想自杀的念头。外婆也受到株连(看来这种连坐法古今通用),从城里调回乡下。她没有丝毫怨言,带着儿女陪伴着外公,让他重新萌发生之勇气。熬了大半年,组织上终于调查清楚了:外公的历史情况与入党前交代的完全一样(小地主家庭出身,1949年10月,高中未毕业就投笔从戎,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49军青年军政干部学校。一年后因病复员,回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于是内部肃反对象的帽子被摘掉。1957年下学期,外公又调回城里,官复原职。外婆则被安排去新化师范学习,算是对她遭受株连的补偿。一切似乎又走上了正轨。那时谁也料不到,走上正轨只是暂时现象,“脱轨”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反而成为了中国的常态。
1966年明,“文革”开始了。时任隆回五中校长的外公作为基层当权派兼“地主”,无可避免地被打成“走资派”。外婆又一次受到株连,先是被从荷香桥小学调到新田小学(这里面还含有挟私报复的成分——外婆曾向当时荷香桥小学的校长廖××提过意见,廖一直怀恨在心),后来又被调到条件更差的竹叶小学,再后来又相继调到曾家坳回龙小学、滩头区里山小学。这些学校的校舍不是祠堂就是庵堂,阴气极重。一到晚上,更显得清冷阴森。外婆带着幼小的儿女睡在这种古老的建筑里(竹叶小学所在的祠堂连门都没有),总会听到一些来历不明的声响,内心的惊恐可想而知。而外公正在百里外的地方“靠边站”,无法给予她安慰和保护。外婆只有把惊恐强行压在心头。在脸上呈现出镇定和坚强,以使偎依在她怀里的儿女们安心。白天教完书后,她带着儿女们上山砍柴。星期天又带着他们走了十几里山路,到镇里买米买菜。母亲能够辨识许多种树木和蘑菇,就是在这时学会的。不过她的乡村记忆痛苦大于快乐——走在外面,随时会遭到“地主崽崽”之类的辱骂;待在校舍,总担心冷不防从什么地方窜出一条蛇来(古老的祠堂和庵堂都是蛇爱盘桓的地方)。而最令她记忆深刻的,就是外婆不能容忍她表现出一点女儿家的娇弱。一旦她想撒点娇,立刻就会遭到严厉的呵斥。几十年后,母亲回忆起这一点,仍然无法掩饰地表现出伤心和失落。我也曾为此而愤愤不平(我跟着外婆生活了六七年,对她的这种性格深有体会)。但现在想来,外婆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的性格渐渐地就变得跟压力一样坚硬。这种被对象同化的现象,应该是心理学上—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吧。
1972年,因为地方教育战线上能做点实事的人太少,外公又被重新起用,调隆回九中任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外公被批斗了六年,虽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仍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那是个太没安全感的年代,连官居极品的国家主席都可以被随意打倒,更别说一个从八品小吏了。他只有埋头苦干。而外婆继续在遥远的山村小学带着儿女过着艰苦的生活。她理解外公的苦衷,从没有发过什么怨言。外公得以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1973年,他带领全校师生,把九中从山界乡老屋村的石山上搬迁到天福乡的三八水库旁边。上头看到外公革命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又发了一回慈悲,把外婆调到离九中比较近的紫阳区砚冲小学,后来又调到更近的天福小学。经过了七年的生别,全家人总算能在一起过日子了。曾经年轻美丽的外婆已经人到中年,黑发中掩映着人生的霜雪。
1978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外公白手起家,创办了五七大学(后来又改为农民中专,现在校舍全部被纳入隆回九中)。1981年下学期,他受命调到隆回一中创办省重点中学。同年外婆调回群贤小学,结束了她漫长的乡村教师生涯。长期过于清苦的生活,过多地损耗了生命元气。站在讲台上,她时常眩晕,经医生诊断,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症。无可奈何,只有在1985年提前退休。退休后并没有清闲下来,而是忙着带外孙和孙女。父母离异后,我被判给父亲。而深陷赌博的父亲并无能力抚养,又拉不下面子把我让给母亲。经过一番协商后,我便被送到外公外婆家里,实际上是由母亲负担生活费用。从十岁到十五岁,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难掌控、变化最大的时期。外公性格开朗,对我日益明显的青春叛逆还能持有宽容的态度。外婆在我眼中,却成了一个苛刻的法官,对我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都要严加斥责:从吃过晚饭后总要磨蹭至天黑才肯做作业到在穿衣镜前多站了两分钟;从冬天放学归来进屋时做瑟缩状到走路时喜欢勾着头且横起眼睛看人;从为三岁的表妹出头打了邻家小男孩到在学校里跟人合伙把一个体育特长生打得脸肿得像南瓜;从数学考了三十几分到书包里面夹带没头没尾的武侠小说……外婆的斥责并不能使我乖一点,我照样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这让她更加愤怒,斥责声一次比一次急促地响起。在我的记忆中,初中三年几乎没有一天没挨过她的骂。而她对表妹们可和气得多。于是我怨气满怀,有时以不吃饭或出走表示抗议。每次出走,都是小舅骑着单车把我找了回来。读了几本文学书后,我还发出了“寄人篱下”的悠长感叹,让外公听到后哭笑不得。现在想来,说这句话应该自打嘴巴——当时要不是他们收留我,我还真没有好地方可去,只有学高尔基走上流浪之路了。虽然也有可能成为作家,但那得遭受多少苦难呢?
1994年,因为学习成绩实在糟糕,母亲决定不顾父亲那边亲戚的反对(他们也就是在这件事上表示一下对我的关注),把我带到邵阳去。考上中专后,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和弟弟一起回来住上一阵。虽然几乎每次回来,我都要跟外婆怄气,但下一次还是照样厚着脸皮来了。每次回来,我都会在天楼的葡萄架下长时间地独坐。屁股下吱呀作响的小竹椅依然是过去的那把。在这里,我看了多少闲书,发了多少回呆,已经数不清了。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在这里,我能真切地触摸到最初的少年时光。无论我的回忆是惆怅也好愤懑也好,委实都无法割舍。
外婆把我和弟弟寒暑假回来住视作一种定例。有时回来得迟一点,她就会打电话给母亲催问。在我上班之后,就没再惹过她生气了,反而经常得到她的表扬。主要是我闭门读书不爱跟外界来往的做派很对她的胃口,用她的话说,就是不到社会上去“乱和”。“文革”时期的遭遇让她对外界有种驱之不去的警惕和怀疑,这种警惕和怀疑暗暗传染给了我,让我过早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从而有意识地和它保持着距离。我天性中有挥霍的因子(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但因为少年时代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她的节俭影响了我,平衡了我挥霍的天性,至少我能够做到不做无谓的浪费。有时我会带—些不穿的旧衣服回来。外婆很欢喜,说我晓得惜物。她把这些旧衣服洗干净,再分送给乡下的亲戚。后来当我打算从旱涝保收的县级人民银行调到报社时,颇受到了一些阻拦。出乎意料的是,外婆晓得后,居然并不反对,说,只要有门正式工作就好。我悟了悟,便明白外婆是担心我完全抛下体制内的工作。看来在她心目中,我还是当初那个顽劣的少年,现在的一系列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期待,让她非常之满意。我已经正式跳出被挑剔对象的行列了(外公和母亲一直都在这个行列之中)。2004年,我买房子的时候,外婆支援了我一万块钱。那时物价清平,邵阳最好的小区房价才每平米一千元再搭个零头。这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太清楚她的节约了,真正是打着补丁过日子的,连牙刷用到快秃了还不肯换一把。而以她那点微薄的小学教师的退休工资,要攒多久才能攒到一万?我晓得她始终有点愧疚,认为当初应该把我带在身边读完高中才对。其实根本没什么应该不应该。对于—个辛苦了大半生的老人来说,她有什么义务要继续把孙辈们带大呢?然而在外婆这老一辈人心中,无论他们付出了多少,都永远存有一份对他人、对后辈未尽的心意。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比我们更年轻的“80后”、“90后”们,却总是觉得别人欠我的。要说代沟,这就是最大的代沟。
把二表妹带到上小学后,外婆实在应该歇一歇了。外公是个喜欢逛四方的人,很想带她走出偏僻的湘西南,到全国各处看一看。母亲和舅舅们觉得她大半生基本待在家乡,也很希望她能看看外面那个以超速度在变化的世界。然而一个现实问题让大家都感到为难:外婆连坐在单车后座上都晕车。也就是说,她受不得任何颠簸。唯一能让她适应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要坐火车得去邵阳,而邵阳离隆回有一百多里。如果时光倒退二三十年,外婆还能拿出走山道的劲头,用两条腿把自己运过去。但现在,她稍微走快了就会气喘,连刚上小学的表妹想摆脱她的追赶都很容易。商量来商量去,大家只能遵从她的意愿。外婆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出去走一趟,用她的话说,是要看看子女们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母亲在邵阳,大舅在长沙,二舅在西安,只有小舅一家长期住在隆回陪在他们身边)。她是个做事细致的人,在动身之前四处打听预防晕车的方法,最后竟被她访得了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秘诀。动身那天,她起得很早,而且坚持不吃早餐。上车前就服了晕车药,落座后立刻闭上眼睛,努力让睡意把自己包裹起来。虽然抵达邵阳后仍感到不适,但至少没有呕吐。饶是如此,她还是在母亲家躺了半天,才恢复过来。第一关总算通过了。邵阳市区富有古韵的景点双清公园、东塔公园和水府庙都在城东一带,母亲家在城西的百春园,相隔有五六里路。这点距离,坐公交车也就是几站路而已。但外婆不能坐公交车,只能走路。她观光的兴趣不大,只是让母亲陪她走到三里外的城南公园看了看,便算是来邵阳一游了。接下来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火车站。当时火车南站还没有修建,从百春园走到老火车站,有十五六里路。外婆是无论如何不肯坐汽车的。那就只有重走长征路了。通过学鹤翔桩把身体练棒的外公提前一天将征途走了一遍,估算好了时间,连沿途休息的点都踩好了。去火车站的那天,先把行李用车子运过去,大家再陪着外婆慢慢地走。走上一阵,她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微微地喘着气,面容平静,什么都没说。但我想,她应该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山道上独自跋涉数十里乃至上百里的情景。那时她是孤单的,前路坎坷,但是能走。现在有亲人们陪着,前路平坦,却快走不动了。在与时光顽强地抗争了数十年后,她终究又开始回归到了最初的柔弱。
坐火车到了长沙后,大舅先让司机开车把外公连同行李送到住处,自己陪着外婆走了两个多小时。好在当时他住在南门口,而不是更遥远的高桥。长沙的好景点多半在河西。考虑到湘江大桥上狭长的人行道同时还是非机动车道,大舅没敢带着外婆到河西去。所以她只是在湘江边上散步时看看江中的橘子洲头和江对面的岳麓山,便算是游览了长沙。坐火车到西安后,她也就是上离二舅住处不远的老城墙走了走,连大雁塔都没去,更别说华清池和兵马俑了。她是真正实践了自己所说的:看看子女们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多月后,外婆回到了隆回。我们都明白,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
虽然外公很想再出去走走,但怕外婆孤单,只有在家里陪着她。两人以练习门球和在天台上种菜来打发清寂的时光。他们住的楼房是外公退居二线后,由外公和舅舅们凑钱修的。虽然有三层,但前后都有楼房,采光度不好。尤其是两位老人住的一楼,正午都仿佛黄昏。外婆又舍不得在白天开灯,所以长时间生活在半明半暗之间。这楼房还有个特性,就是冬天极冷。要给他们装空调,一听说开一小时起码耗一度电,外婆吓得连连摇头加摆手,似乎装的是定时炸弹。2007年,小舅调往邵阳任市中国银行副行长,大家都希望外公外婆搬到邵阳来。外公思想开通,对于搬迁一事。是无可无不可。外婆却不肯挪窝,说是在隆回生活了几十年,熟人多,到邵阳去,连个打门球的地方都不好找。外公便只有依着外婆的意思。已经去北京当职业画家的大舅想着把两位老人留在隆回实在不放心,便用卖画的钱在邵阳买了套四室两厅的房子。母亲受托将它装修好后,小舅便把外公接过来看。这套房子在一楼,采光度好;屋后有一小块地可供种花种菜;地理位置也是绝佳,跟小舅家在同一个小区,离我住的小区只有三百米,离母亲住的单位宿舍只有五百米;至于家具、家电,都配全了,且都是高档货,只等着两位老人前来享用。外公动了心,回去后跟外婆一说,外婆还是不同意。在她看来,目前的居住条件比当年住庵堂、祠堂要好上百倍,她是很知足了。大家只有轮番劝说,我也加入了这支劝说马拉松队伍。2008年,外婆终于转了念头。动身的时候,她还想把陪伴她多年的旧家当全搬到邵阳来。我们告诉她,新屋里样样齐全,已经摆不下其他家具,她只要带些衣服过来就可以了。外婆默然良久,最后只有恋恋不舍地跟那些用了十几二十年年的桌子、板凳、三门柜和沙发告别。
外婆实在不是享福的命。才住进新居几天,就发生脑中风,右边身体瘫痪,说不出话。幸好抢救及时,几天后又恢复过来。然而肺部却发现有问题。所谓的专家拿着片子说有阴影,但又做不出确诊。想送去长沙的大医院诊断,但外婆已经虚弱得像张薄纸,根本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在邵阳所谓最好的医院住了个把月,便接回家中调养。大家都期待上天怜悯她一世操劳,能够痊愈,多享几天福。外婆每天都要服药,隔几天就要吊水,一个人慢慢地变得枯干。所幸精神还好,走路也不成问题。刚毅的外壳被病痛消磨殆尽,她开始变得像个小孩子那样软弱。母亲如果有一天没有过去,她就会打电话来。母亲每次服侍完她要回家时,她会叫着母亲的小名,要她再多坐一会。我女儿茜茜出世后,外婆说,要是我身体好一点,每天还可以帮着带一下,语气中透着些不甘心——她已把操劳看成了天职,现在无法劳作,便觉得没有尽职,心里不自在。茜茜长得像个洋娃娃,甚得外婆喜欢。她对母亲说,我蛮喜欢茜茜,你要多带她过来。这种直接的温情表露,在外婆的一生中,是很少见的。她习惯了把对亲人的爱隐藏在终日的操劳和严厉的管教中。而就在她开始把自己柔软的内核呈露出来时,却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跟她早已逝去的阿姨和姐姐一样,外婆没有逃脱家族基因遗传的天罗——她得的是肺癌,而且到了晚期。再次住院的时候,我带茜茜去看她。那时她正忍受着极大痛苦,头脑却仍清醒。她以虚弱的声音连喊了两声宝宝,又盯着茜茜看了一会,然后说医院里病气重,要我快带茜茜走。这就是外婆的风格。哪怕到了生命尽头,她还是事事为亲人着想,并为此克制着自己的情感。她完全可以抱着亲人痛哭,把一生所受的委屈,把对死亡的恐惧部宣泄出来。但她没有,仍然镇静、隐忍。她表达爱的最后方式,就是交代母亲,把自己大半生积攒下的十三万元钱平均分给子女。
2010年4月29日上午11点,外婆逝世于邵阳市中心医院,终年78岁。
初六上午,一大家人前往市郊雨溪桥公墓祭拜外婆。那天晴暖不似冬日,大舅一家三口却都穿了厚厚的羽绒服。他们是特意穿的。原因是外婆生前总是埋怨大舅画画赚了那么多钱,怎么每次总是穿得单瘪瘪地回来。她不太明白艺术家的穿着习惯,也不相信那些看似轻薄的衣服有着良好的保暖功能,只是执拗地关注着儿子儿媳和孙女是否穿得厚实。她大半生都是在为这些实在的细节而操心,并固守和捍卫着从艰难岁月中得来的经验。如今她终于可以不必操心,获得了终极的安宁。在她墓前摆好供品。点燃香,烧了纸钱,晚辈们又轮流跪拜,祈愿她在另—个世界活得好。另—个世界是公平的,简单、干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外婆在那里必然得到善待。因为她一生克己、敬业、勤劳、俭朴,憎恶懒惰和腐败。这些德行,在任何世界都是值得尊重的。
2011年2月23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