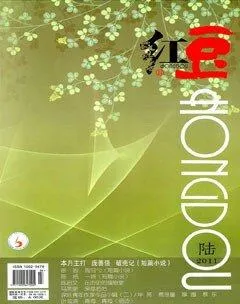青花瓷
2011-01-01魏晓英
红豆 2011年6期
我的母亲是在我十岁的时候死掉的,她死的时候我只有十岁。
我的母亲喜欢一种瓷器,青花瓷。所有青花瓷的东西她都喜欢,仕女图的瓶、鲤鱼的碗、汉隶书的小酒盅都是她的最爱。我的父亲是个皮货商人,她认识我母亲的时候我母亲还是个学生,据说我母亲是校花,父亲在南方做生意,他用这些瓶瓶罐罐打动了小他十多岁的母亲,跟他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北方。我的外公外婆就她一个女儿,因为母亲远嫁,哭瞎了眼。
有一段时间,在我记忆的那段时间,父亲给母亲从南方运来了许多许多的青花瓷。许多的青花瓷在日光下闪着清冷的光。那一次,我的父亲也回来了。他给我的母亲带来了螃蟹。晚上,母亲在餐厅里有滋有味地吃着大个的螃蟹。父亲一脸的疲倦。风有些凉,吹进来转个圈圈,是圆圆的圈,又慢悠悠地荡了出去。保姆走过来对我的母亲说,别吃太多,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母亲笑笑。母亲笑起来很好看,她对准新郎和善。我相信我的母亲是善良的,是温柔的。
母亲在淡绿色的罩子下欣赏她的那些宝贝,她不能冷淡发着青光的器皿。在母亲的世界里,她好像只关心这些冰冷的东西。
那天她坐在灯下欣赏着瓷器,我的父亲坐在屋子里听流行的歌唱和外面河里的蛙鸣。父亲满脸的疲倦。风令人难以察觉地进来,昏乎乎的灯光显得湿润而飘忽。母亲在灯下仔细地、小心地抚摩着父亲为她带来的那些青花瓷,她小巧玲珑的鼻尖上渗出铂金般的汗珠子,碎银子一样的。
父亲踏着光虚虚的进来,眼屎还粘在眼角。他没有看我,他不喜欢我这个女儿。
你先看吧,我去睡了。
半夜里,我被母亲的尖叫震醒,我看见母亲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猫恐怖地翻滚。母亲送进医院的时候,就死掉了,死的时候刚三十岁。我没有舅舅,我母亲被医生判成食物中毒后埋葬了。她死的那年我刚刚十岁,上小学四年级。
我觉得那个冬天太长了,长得眼睛里发了霉。
半年后,柳翠翠,我的继母进了家。我这才知道父亲早就有了儿子,也就是说母亲还在世的时候父亲就有了别的女人,已经给他生了儿子。他的儿子已经三岁,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已经三岁了。
于是我在家里成了个多余的人,是我父亲多余的孩子。母亲死后,我每日每夜地守望着月光,守望着母亲留下的一屋青光,守望着母亲留下的最爱。它们正在静静流动的光中破碎。
守望,成为我的全部生活!
在母亲去世的那些寂寞的日子里,各处有一种霉潮的气息。我长久地坐在这种气息里。我常常想到那天的螃蟹。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内里却似乎含了无限的玄机。我苦苦地纠缠在这些事里。
一切源于父亲带回来的女人,一个比我父亲小二十多岁的女人—柳翠翠。
一切源于父亲带来的弟弟,弟弟已会迈着小脚走。
那真是—个多事的季节。那时院子里很空寂,夜气有些阴凉,院子右边的杨树像一口锅盖下来,一直盖下来。而院外的一道道屋脊模糊不清,好像有蝙蝠在那里飞,其间还有许多如墨一样的树冠。这个景象我非常熟悉。所有的日子几乎就是这种情景。
我茫然地看着屋子里的瓶瓶罐罐,青光映在我的脸上。
这个季节,这个日子,与我有关,与我的弟弟有关,与母亲留下的青花瓷有关。
这些漂亮的青花瓷,它同我的母亲有关,它是我父亲从南方运来的。听母亲说那里与我们这里隔了千山万水,从这么远的地方运来的青花瓷一个就是我家当餐具用,再者就是供母亲欣赏。因了母亲的喜欢,以至于我们家里用的碗、碟子都是这种色调,摆在角落里的也是这些瓶瓶灌灌,它们在阳光下闪着青幽幽的光。这种光刺得我常常睁不开眼。这些东西运来不长时间,我的母亲就死掉了。看来这些青花瓷在出发的时候就带来了某种不祥。只是,只是我那个小父亲十来岁、喜欢这种东西的母亲忽略了这一点。母亲死后,这些闪着青光的瓷器依旧放在我家别墅里的角角落落。我的叔叔,我那个年轻十足的叔叔,我那个每天和柳翠翠打麻将的叔叔,经常拿走一些瓷器。不过,叔叔这个拿并不长。有的小东西它真是太独特,太好玩了,比如一个汤匙,它的上面是个骷髅头,看上去不可怕很古怪,难怪我的母亲会喜欢,难怪她会被这些青花瓷迷找不到自己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一切都具有不祥的信息。当时家里的每个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是不祥之物的传闻是在我出事之后才有的,于是我的叔叔,我那个来打麻将的叔叔再也没有从我家里拿这些好看的青花瓷,并且把偷偷拿去的东西又拿了回来。这是以后的事,在这里我不想说。
在灾难发生之前我一直是个胆小怕事、缩手缩脚的女孩。继母柳翠翠对我还算可以,我和弟弟相处得也很和谐,只是叔叔和父亲不喜欢我。可是,无论怎样,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日子里我还有自己的安宁,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喜欢母亲留下的那些沉静、飘逸的东西,还可以无拘无束地看柳翠翠晾在升降衣架上的胸罩,我对带着蕾丝花边的胸罩有着好感和神秘。
出事的那个日子,天气暖融融的,空气中飘着油烟的气息,散发着刺鼻沤腐气味的垃圾桶前有许多苍蝇迷地飞着。
那个时候,继母柳翠翠在和叔叔他们打麻将,父亲去谈关于皮货的销售问题,我在欣赏母亲留下的物件。我越来越喜欢这些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的物件。我真是越来越喜欢。真的。假若没有这些飘逸的青花瓷,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假若母亲不喜欢这些物件,就不会嫁给大她十多岁的父亲,就不会有我。可是,可是……没有了假若,假若那天的日光不是那样的暖融融,那些物件就不会吸引我,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但那天的阳光暖融融的,母亲留下的仕女图的嫣然一笑令我着迷。我用尽力气拿起了桌上的精致瓶,它在日光的照耀下闪着诱人的光泽,瓶上的汉隶书是那样的飘逸。我痴迷地欣赏着,忽然就看见了跑过来的弟弟。
我的手哆嗦了一下。
瓶落了下去,它发出的不是清脆声,因为它没有落在地上,它落在了我弟弟的头上。
我是无心的,我真的是无心的,我是胆小的,是软弱的,我和弟弟是和谐的。我是喜欢这个活泼的弟弟的,尽管我拒绝着柳翠翠。真的,我真的是无心的。我怎么知道他会来?我怎么知道他会来呀?但是,他来了。如果我没有看见他来,如果我的手不哆嗦,那么,我的弟弟就不会死。可是我看见了,我的手哆嗦了,瓶砸在了弟弟小小的头上。美丽的瓶碎了一地。
从此,活泼的弟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个有着仕女图的花瓶带着最后的温度砸在了弟弟的头上。血像黄昏下的夕阳一样染红了那些碎了的瓷片。生命,是这样的脆弱!
我呆了,我呆了,很久很久,我才发出尖叫,像狼—样的尖叫,我抖成一团。
继母柳翠翠听见我的尖叫时,她正自摸了白板。她奔过来看见躺在血泊中的弟弟,脸色变得异常苍白。我的叔叔也跟了过来,他帅气的脸铁黑。我看见柳翠翠和叔叔手忙脚乱地把满头是血的弟弟抱起来,我看见柳翠翠的脸上,身上全是红色。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发现我的时候,我飞快地逃离了事故现场,一路跌跌撞撞地奔,没有目的。我看见柏油路上的车快速地飞奔。在城区的郊外,我像一条丧家狗一样趴在一块冰凉的石头上,我的汗打湿了石头。
父亲得知弟弟死掉的消息是在黄昏。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正在同客户谈皮货销售的父亲,把皮子撕了。听说谈货的客户见皮货不结实,也走了。是叔叔给父亲打的电话。父亲总会知道的,没有人阻止他知道,他总会知道的。看着老远走来的兄弟,他的兄弟穿的是西装革履,我的父亲无限悲凉地说,我真是命中无子、命中无子呀。他没有去看我死去的弟弟。
我是在冻了一天一夜昏迷后,被一个捡破烂的人送到派出所,被叔叔带回家的。我在梦里总是梦见弟弟满脸血污地追赶我。当我苏醒过来时,我听见继母柳翠翠摔器皿的声音。我想坐起来看看,看看是什么被摔碎了,可是我的腿好沉,头好疼。我听见柳翠翠说,这些破东西,这些不祥的东西,都是这些鬼东西害死了我的儿子。我听见柳翠翠鬼样的哭。
我的眼泪顿时冲眶而出,弟弟死后我第一次流泪。泪水在我的脸上肆意地淌着,悲伤在我的体内升腾。
死气笼罩在我们全家的头上,以后我似乎再没有看见如那日般暖融融的阳光,就算是阳光明媚也不能给我家带来好气氛。十月的天渐渐凉了,黄叶落得像金。我的父亲老了,他仿佛是一下子老的,头发全白了,生意也不顺利。他经常出错,经常忘东西,先是把老花镜放在母亲睡的卧室里,找遍了屋中所有的角落也找不到。—件衣服要穿很久。谁也不敢提弟弟的名字,似乎那名字是一枚炸弹,都回避着。柳翠翠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打麻将,最后自摸的那块白板还像英雄一样竖在房间的桌子上。在她把母亲留下的最爱摔碎以后,躺在床上—个月不能动弹!
弟弟以及那些美好都随着这次意外走了,漂亮和飘逸、温暖和快乐这些明快的词语只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在无意中毁了全家人的希望。
谁都知道,弟弟是父亲的命,是父亲的心,是父亲的唯一,是他身上不可或缺的物件。父亲的三个老婆,只有这个柳翠翠给他生了个儿子,他一直把这个孩子当做希望养着,每次回来都给他买好多玩具,陪他玩耍。我永远忘不了父亲把弟弟搂在怀里的情景,他脸上的笑容似乎只是给这个希望的,这个孩子是我们全家、全族的希望。叔叔一生无正经职业,娶了老婆都没有过一年的,没有哪个女人甘心为他生子。几个本家生的也都是千金。我真是把父亲的希望毁了。
是我用一个瓷瓶把生活毁掉了。是它改变了许多人。谁也无法想象,要是我的弟弟活着,我们全家是一幅怎样的景象!父亲快乐地做着生意,柳翠翠安详地相夫教子,我也自由自在地上学。弟弟死前,柳翠翠对我还是可以的,她给我买的一双带有动物图案的袜子我至今还没舍得穿。弟弟呢,他是那样的天真可爱,无论是家人还是来串门的都非常非常喜欢他。那时我真有点嫉妒他,可是我真是无意的,现在我宁愿死掉的是我。
在这以后,柳翠翠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女人,她成了个恶气十足的女人,用难听的话骂我,骂我那死去的母亲,骂被她弄碎的物件。她对父亲凶得就像一只母老虎。她邪火越发越大,就如同年夜里燃放的烟火,早在点燃之前就憋足了劲,把我们炸得灰飞烟灭。
叔叔在柳翠翠打碎所有的青花瓷后,就把从我家偷偷拿走的物件搬了回来,放在了那堆碎了的瓷片上,还从家里带了个黑塑料布,用它盖了盖。从破洞里露出的一道道青光,它带着让人不可名状的色彩。
我的叔叔再也不喜欢这些破东西了,他说我的母亲就是因为喜欢这些不祥的瓷器才死得那么早。父亲为母亲运来的青花瓷彻底在我家的角落里消失了,没有了青花瓷就像没有了母亲一样。
我的泪水簌簌地飘着,我知道这仅仅是我生活的开始。柳翠翠,一个被仇恨点燃的女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也不清楚,我在这么多的仇恨里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终于下雪了,我一个人缩在角落里。透过窗户我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轻飘飘的雪花使院子里显现出银白色的世界,墙角里那些碎裂的物件披上了银装。我再想找一点母亲留给我的美好,哪怕一点,一点点也没有了。停留在上面的雪花分解成珍珠滚下来。天真冷呀,供暖的煤还没有到。我听见父亲的声音里有着太多的无奈和苍凉。对他这种苍凉的声音我感到惊俱。我想,父亲的衰老与我有一定的关系!
断断续续的几场雪之后,房屋愈加素白起来。在重叠的廊檐和黑红的院墙中,与渐渐变得虚弱的阳光有些相似。风狠狠地把雪甩下来,不断有轻飘飘的小白花飞进来,裸露的碎片看起来有些忧伤。柳翠翠的胸罩我再也没看见过。自从弟弟死后,柳翠翠再也没有逛过商场,她没有买新的有蕾丝边的胸罩。
柳翠翠看来是发誓要为儿子报仇。有一次她把猫拉的屎让我吃,我不张嘴。我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的亲人。我的叔叔冷冷地看着我,他用力把我的嘴掰开,柳翠翠狠狠地把猫屎塞进我的嘴里。恶心让我呕吐起来。柳翠翠撇撇嘴,叔叔也踹了我一脚后离开了。我吐得一塌糊涂。从此以后我吃什么再也没有了饭的滋味。想到母亲,想到母亲留下的最爱,我还是淌下泪来。泪水簌簌地落着,如窗外的雪花。
原来美好和爱是这样易碎的,它改变了母亲的命运,它也把我的一切都改变了。它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风是脆弱的,是没有理想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如天边的黄昏,他的生意也在渐入冬季。他的背明显地驼了下去,看上去比柳翠翠要大三十多岁。年轻的柳翠翠看他的目光是厌恶的。
没有了儿子的父亲是孤独的,没有了儿子的父亲是寂寞的,没有了儿子的父亲没有了斗志。
冬天的夜太长了,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他似乎是想谈别的却没有找到,就这样说了出来。
来打麻将的叔叔有些鄙夷地看着他,说,你的夜是太长了。父亲没有理他。
在这件事发生以后,没有了儿子的柳翠翠变得喜怒无常,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又大发雷霆。没有了儿子的柳翠翠让我恐惧。
日光和以前一样,风还是有些脆弱。院里的长椅,屋子里的吊兰以及幸福树都在远去,使得我在空旷中平添了几分忧伤。我预料中该发生的事,或许本来是细微的变化,都没有如期来临。我茫然地看着飘过来的光,那是我家院里杨树枝漏下来的细光。我一直都不喜欢院里的杨树,它笼盖四野的虬枝让人觉得阴森,透着某种不祥。
柳翠翠和叔叔的笑声从远处飘来。随着消失的笑声,她出现在我的房间里,我不禁哆嗦了一下。柳翠翠来到我的身边,穿着高跟鞋的脚狠狠地踹在了我的腰上,我疼得摔在地上。我禁不住呻吟起来。
地上的阳光逐渐弱了下去,白得格外刺眼。我的父亲阴沉着脸站在虚假的影子里,他用一种不确定的声音说,翠翠,别再这样了,好歹她是一条命啊。柳翠翠撇了撇嘴,她是一条命,我儿子的命就不是命了?说完,柳翠翠踏着细细的光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听见父亲重重地叹气,带着无奈。这无奈在叹气之前就已散开。这一声叹息似乎传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我看见我的父亲打了个寒战。他站起来,在那堆破烂的碎片中捡起一片,报应啊,报应。声音在虚虚的光影里很快消失了。
日子渐渐地长起来,天气也变得柔和了些。叔叔天天来打麻将,他的皮鞋发出噔噔噔的声音。头发上喷的发胶有种糊焦味,就像我吃东西的味道那样恶心。
冬末的空气里开始有了点春的气息,叔叔和柳翠翠都守着自己眼前的牌,柳翠翠一手托腮,另一只手轻轻地用麻将敲着大理石的桌子。这种声响时常地把她带到一个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地方,从嫩叶里漏下来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柳翠翠自摸了一下,白板,她夸张地把这张牌举过头顶。
柳翠翠抬起眼,她看了看打牌的其他三人,她觉得他们都像得了麻风病的人。她忽然哭了起来,脸上的胭脂、嘴角的口红让她变得花花绿绿如鬼。其他的牌友见此,悄无声息地走了。只留下叔叔在劝说,你是不是想起了那日?你是不是又想起了儿子?
柳翠翠抬起头,恶狠狠地说,是,是,我在梦里已杀了她几千回,我还要生儿子。
叔叔拿过毛巾,生吧,我让你生三个儿子,我会让你生。
柳翠翠这次的改变更加疯狂,我愈发地恐惧。我一直在害怕她对我的仇恨会一直无休止地持续下去,我一直害怕她还会对我做出什么。我整日惴惴不安。
这个日子还是来了,柳翠翠现在脾气变得格外暴躁,那个还有着一丝温柔的女人不见了。她是在春天到来之前对我动的手。春天来了,蛙在刚化冻的河里嘶哑地叫着,有种绝望的意境。我擦地板擦得精疲力竭,走出我的房间时我觉得格外冷。我穿了一件厚的衣服,这件衣服让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打寒战。
冬天,这个该死的冬天不肯离去,春的迹象一点也没有显露出来。我静静地坐在屋子里,我像狗一样地擦着地板。我每天就是把地板擦干净,擦不干净柳翠翠就会让我舔。我注意到天花板上有了小虫子,有了小虫子说明季节还是在按规律走。
那个日子跟平常没有两样,没有风,那些被柳翠翠摔碎的瓷片爬进柳翠翠的手里,它们闪着冷冷的青光。
我像狗—样爬到客厅里,直到柳翠翠到来。我看见红拖鞋的时候,我才感到一股阴冷袭来。我看见她手里拿着破瓷片,我看见鱼在裂片上的煎熬。我的心惧怕到了极点。我转身想往外面爬,但我还是被柳翠翠抓住了。她用带着我所钟爱的鱼的瓷片,深深地、深深地在我的脸上划过。我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是有一股咸咸的液体滚进我的嘴里。我跑了出去,我看见父亲惊愕的表情。我晃了晃,昏了过去。
这一天是我面目变得狰狞的开始。
我被父亲送进医院里,脸上的伤很深。医生说我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了。从这一刻起,美丽离我远去。在我入院的这些日子里,没有—个亲人在我身边,父亲花钱请了个护工。护工是个五十多岁的乡下妇人,她对我的态度恶劣,说我本来就不该做人,该托生成猪。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她的嘴里有股酸腐味。
她和医生说我像只老鼠,她说她从小就讨厌老鼠。因为小时候她的母亲只顾着去和父亲粘在一起,根本没有时间照看她,夜晚来临的时候老鼠总是来咬她,她的一只眼是瞎的。她说我的样子就像一只老鼠。
她给我拿来的饭是别人吃剩下的。我捧着小米粥,眼泪哗的一下子全落下来。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走到外面,外面真好。医院里的味道让我只想呕吐。站在树下,我嗅到了甜甜的气息,嫩芽在枝头悄悄地绽放。朝远处看去,四野一片春的景象,有些模糊,有些希望,更多的是忧郁和寂静。笔直的柏油路伸向天的尽头。一切看起来是这样的迷茫。野外的河水已经化了冻,在轻轻地流淌。看来季节是真的到了春天。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脸上的伤疤开始疼。它的疼是在我有了知觉之后。天色变成了灰白,远方一切灰蒙蒙的。我忽然感到一种空荡荡的恐慌。我无目的地向南走着,一直向南走着。在一个小村一个城市里过着夜,躺在小村的破屋下。我非常饿,我非常渴望有一碗热热的粥,然而黑糊糊的夜只有天上的星星如影随形。躺在城市的霓虹里,我非常疲惫,非常渴望有一张舒服的床,然而闪闪烁烁的霓虹里,只有汽车的鸣笛声。
不知走了多久,我来到一个小镇,我看见了母亲所喜欢的物件。我倒了下去。醒来,我看见一个白发老人。
老人说,你吃了两盘饺子。
老人说,你睡了整整两天。
老人说,你的口袋里有我们的东西。
我的眼里流下泪,我听见远处传来好听的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你隐藏在窖烧里千年的秘密,在泼墨山水画里,你在墨色深处被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