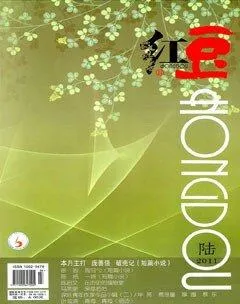邻居丽芬
2011-01-01徐行者
红豆 2011年6期
丽芬二十二岁那年夏天,怀上了孩子。
孩子在十月间出世。在这漫长而炎热的七八月份,她都一直呆在房间里。
我在广州,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丽芬。我和我的丈夫韦纬都是南方大学的毕业生,在我丈夫毕业后的第七天,也就是我们俩结了婚刚六天,我们就搬到广州来了。那时正是七月份。一天早晨,从厨房的窗户跑进来了一只黄猫。它先跳上厨房的桌子,接着就用它的两个前爪洗了洗脸。几秒钟后,—个梳着两条乌黑短辫子的女人也从窗口钻进来了——至少是上半截身子从窗口探了进来。她—把揪着那只猫的脖子,然后才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事情来得这样突然,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嘿了一声。
这时,她开了口:“嗨,我没想到房子里还有人。”她把手伸到身后去比画一下,“我厨房的窗户和你家紧挨着。我是从太平梯过来的。哼!这只猫。”她揪着猫脖子摇晃了一下,“希望你别见怪。”
我说:“没关系。”
“你应该在这个窗户上安装几根铁栏杆。要不然呀,谁都可以从这儿进来。”
“是呀,我也这样想的。你要愿意就这样进来坐坐好吗?”
“当然愿意。”她把上半截身子退了出去,然后把两只脚从窗口上伸了进来。她的肚子不但很大,而且滚瓜溜圆,她像个篮球越过了窗台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她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姿势。她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说:“请原谅。下回来就从大门进了。”
下回,其实也就是第二天,她真的走大门进来了。而且打那以后,她几乎每天都来。
丽芬长得很漂亮。她那乌黑的头发平常总是蓬蓬松松地散披在肩上,就像她那块披肩上垂着的丝一样,又直又亮。她的眼睛呈黑色,她的皮肤是那样白,看起来竟像有点透明似的。她假装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美。有一次,她把手臂伸了过来,一双柔软细嫩的手掌向上一摊,对我说:“还记得那个模特吗?我就有点像她。”她穿着条短裤,披着一件袒胸露背的上衣,同时还披着一条披肩。从她那胳膊上、腿上以及胸脯上,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曲曲弯弯。从横交错的淡蓝色的血管,就像漓江上的河流。她用一种厌烦的语调说道:“他们可以把我送到医学院去当循环系统的模型了。”
丽芬通常都是在近午时分才到我这里来。每天上午的时间她都花在她所说的“舞蹈”上。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当一个舞蹈演员。现在仍然每天坚持在她丈夫利用楼梯扶手做成的一根临时凑合着用的横木上进行练习。
她每次练功时,我在厨房里都可以听到钢琴的伴奏声——都是肖邦、斯卡拉第这些名家的曲子。
丽芬爱看每天连续放映的电视连续剧。我看了两集以后,也跟着上了瘾。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叫《家里那些事》。这部连续剧每天放映时,我们都要看,从来没有落下过。看完了戏,有时我们就看书,但常常在看了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后,丽芬就要想点什么事儿跟我聊聊。她经常向我讲一些她小时候的故事,一讲就是那么长。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脑子就像一锅粥,往往不能把她的或她父母亲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同剧中人的故事区别开来。
他们的生活都带有同样的戏剧性成分。或者不管怎么说,丽芬在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总要赋予它们戏剧性的色彩。有时她所讲的,并非真有其事,而是她虚构出来的。有一次,她对我说,她有一个哥哥,但不幸患白血病死了。没过几天,她又说,她根本没有哥哥。当时她对她哥哥的一些情况,对她哥哥病中的痛苦,她都刻画入微,讲得非常详细。丽芬向我讲述她所编造的有关她哥哥的故事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么深刻,以致我竟信以为真。
我想她所讲的许多有鼻子有眼的事儿,可能都是她精心杜撰出来的。因为在我的生活经历中就从来没有遇到过。她说,在她只有十一岁的时候,她的父母亲就离婚了。她在童年时代留下的最难忘却的记忆,就是她的父亲跟她母亲大吵大闹的情景——醉酒、互相指责,随后则是流着眼泪要离婚。
从我们的住房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广州公共交通的种种繁忙景象。穿越中山街区的高速公路从我们卧室的窗户下面斜穿而过;在我们的住房以西,相距不过半个街区的地方,则是跨越这条高速公路的上海路高架大道;北大机场的跑道,正冲着我们住房这个方向,飞机起飞时,几乎像要擦着我们房顶飞过去。
韦纬是广州人,从未离开过广州市。因此,他大学毕业后,就想在广州住。他想当个建筑师,并且认为广州就是实现他的理想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在一年以前搬到这个城市里来的,他当时正要把他住的那套房子退掉,他写信给我们谈到这个问题,这套住房是在五楼上,阳光充足。我们虽然还没有看过这套房子,但韦纬却坚持租下来。他用浓重的广州的腔调拖声拉气地说:“桃子,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住起来觉得不合适,我们随时都可以搬走嘛!”当你要说服他时,他那南方味儿就更足了。他的劝说总算没有白费劲。我是南宁人,特ZXxowpwwm9QvvY+EPDghzggeKy5Imwtrnd5EgFsXm70=别喜欢听南方那种柔和的腔调。在韦纬的劝说下,我表示同意了。于是我便申请转学到广州去,因为我还有一年研究生才毕业。
韦纬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他给一家大公司设计房屋结构。晚上,他还去上研究生的课。我要等到秋天才上学。在这段时间,我就操持家务,显显当家庭主妇的本事。我用新买来的真空吸尘器来打扫卫生,还给韦纬熨衬衫等。我还搜集廉价购货券(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商品广告,持之购买该种商品时,可以受到优待)。有时也去买几块便宜的猪肉,并向卖肉的人请教怎样做扣肉,怎样烹调鲜蹄膀、肚子、腰子和鸡肝(卖肉的人管后面三样叫杂碎,一提起来,他就眉飞色舞,津津有味)。
丽芬针对我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地说:“你那么累,做什么?”她的房子里经常都是乱糟糟的,她厨房里的洗涤槽很深,就像洗衣盆一样,放在里面的脏盘子要是还没堆得很高的话,丽芬总是不肯洗的。她的丈夫叫杨过,离开这里有四个月了——他在部队服现役。丽芬说,他幸好有这份差事,要不然,他会去做什么?
丽芬和杨过是在大学里结识的,当时他们都是一年级的学生。他们是大学毕业那年来到广州的。丽芬说:“我以为自己已怀孕了,所以就决定双双来到广州结婚。但是,后来当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怀孕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广州。”杨过刚开始想当个演员,后来他在一个汽车陈列室工作。丽芬说:“据杨过自己讲,他透过玻璃观察着许多来来往往的、各式各样的人,从中懂得了不少有关人性方面的问题。”他俩就是在那年春天结婚的,也就是在杨过要去部队服役之前不久。可丽芬这一回确是怀有身孕了。
我问她:“你没结婚就怀了孕,你父母亲对这事儿不在乎吗?”我真无法想象,要是我的父母亲听到这样的消息,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
“哎哟,他们当然在乎。”丽芬答话的语调表明她有点诧异,对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还用得着问吗?
八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当杨过回到家里来度周末的时候,我们四个就坐上韦纬的大众牌汽车开向广州海滩。杨过身材矮小——还没有丽芬高——长着一头浓密的金黄色鬈发,眼睛呈深色。他机灵麻利,健壮有力,一打开话匣子就没个完。他抽的是没有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还喝了很多啤酒。我觉得他也许有点紧张。这是他头一次和我们一起玩。丽芬跟他不一样,她很自信,但是又很谦虚。
我们正沿着长岛公路驱车疾驰的时候,杨过向丽芬问道:“丽芬,你戴的那副墨镜是从哪儿搞来的?”这副墨镜很时髦,镜框大得把她的那张小脸都给遮了一半。
“这是我生日那天父亲送给我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
杨过说:“不怎么样。”
丽芬哦了一声,接着就把墨镜取下来向肩头后边一扔,从车窗扔了出去,然后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们离广州海滩越来越近,来往行驶的车辆也越来越多。到了南国大道,我们的车几乎都走不动了。杨过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讲述他的部队和战友们的故事。在他觉得自己讲得来劲儿的时候,他就用装啤酒的瓶子轻轻地捅一捅韦纬,甚至还把啤酒往韦纬的脖子里灌。
我们到达海滩时,已将近四点,看到很多人在往海滩奔。韦纬和杨过跑去跟人家一起玩沙滩足球,下水去游泳的就剩下丽芬和我。这时浪很大,浪头还没有往下落,我们就已站不住了,水也很冷。于是,我就赶快上岸来,但丽芬却说,这些日子在市里热得够呛,现在觉得很舒服,所以,她仍一个人呆在水里。我问她,这样对肚子里的孩子是不好。她说,不要紧,只要她觉得好,对孩子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同时闭上眼睛休息了几分钟。我睁开眼睛时,丽芬已经漂出去好远了。我已看不见她的脸,只见她像浮标那样随波逐流地慢慢游动,她向我挥手,我也向她挥了挥手,但她仍—个劲儿地向我挥手。我心想,她也许没有看见我吧,于是我就站起身来再向她挥了一次手。而这一回,她却把两只手都举了起来不停地挥动。这时我才明白出事了。显然,救生员也发现了这个情况。他跳进了翻滚的海水,干净利落,毫不迟疑地向着目标游去。当他和丽芬一起回到沙滩上来的时候,丽芬浑身冷得直打哆嗦,她那一绺绺湿漉漉的头发不断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我们转过身子朝着放毛巾的地方走去。一边走,她一边说:“真窝囊。游泳游了一辈子,没想到今天竟这样出洋相。就是这个肚子,弄得我失去了重心。”她穿上衬衫,把头发梳了梳,然后走下沙滩去和杨过会合。她没有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他。
九月,我回到了学校,我再也不能经常看到丽芬了。十月份,丽芬到故乡桂林生孩子去了,而杨过这时却住在广州,因为部队在广州附近搞海练。
丽芬生的是个女孩。他们给她起的名字叫杨宝宝,这是照着丽芬的母亲的名字起的。一天晚上,杨过和丽芬带着杨宝宝到我们家里来吃晚饭,当时杨宝宝才出生五六个星期。在这整段时间里,她一直没睡。谁说话,她那双深黑色的大眼睛就谁着谁。丽芬小心翼翼地抱着她,生怕她那脆弱的小身子受委屈。
打从这次晚餐之后,过了没几个星期,在一个傍晚时分,丽芬又走了过来。她敲门的时候,天已快黑了。我听见门外有人,不禁有点奇怪。因为在我们这幢楼房里,平常难得有人串门,这和周围住的邻居很有关系。
当我把门打开的时候,我就说:“嗨,丽芬!请进来。你好吗?”她手里抱着的杨宝宝还没有醒。丽芬穿一条蓝色的斜纹布裤子,一件网领短袖紧身汗衫,肩上披着的还是她母亲的那条披肩。她显得又黄又瘦,眼圈变成了深褐色。
她说:“还可以,但我觉得,唉!”接着她就哭了起来。
我找出一瓶漓泉啤酒,给我们俩都各倒了一杯。丽芬喝了一两口以后,就没再哭了。“哎,真叫人伤心。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不走运。”
“也许你有点累了吧。是不是孩子把你搅得睡不着?”
“不,她很乖。她一觉就睡到大天亮。我只是觉得很苦闷、很丧气。我想,这也许是有了孩子以后的正常现象吧。”
我问她:“杨过在哪儿?”
“他最近可忙啦!准备转业了。”
丽芬接着说:“我们需要钱。我想叫他回来做点大事。”
后来,我把丽芬来串门的情况告诉了韦纬,他说:“你就别为这事担忧了。我妹妹生了头一个孩子后,还哭了六个星期呢。”韦纬的这个话,不但没有解除我对丽芬的担心,反而更使我挂念起丽芬来了。
几个星期以后,丽芬又来到我们家。她这次是来告别的,他们要搬到市南部商业区附近的半岛花园去。她说:“上一次一时感情激动,忍不住哭鼻子、抹眼泪的,真是抱歉。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她的情绪看起来显得好些了,韦纬的看法也许是对的。
她说:“我们搬到这个新地方后,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在一座楼房里,我们租用整整一层,前后相通,房子后面还有个花园。”听起来他们的新居很高级,末了她说,“你一定要去我们那儿瞧瞧。”
我说,那当然,那当然。嘴上虽然这么讲,但我心里明白可能不会去。我说:“很想念你。”
丽芬说:“我也很想你嘛!”
第二年夏天,韦纬和我也搬到市南部商业区去了,但不像杨过和丽芬他们那样靠近商业区的中心地带。
八月底的一个晚上,杨过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举行的一个晚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和丽芬的消息。在晚会的那天晚上,我们先到了—个明友家里去吃饭,然后才去丽芬他们那里,这时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们按了按电铃,没人应声,但门已开了,我们就走了进去。里面有十来个人。房里烟雾弥漫,黑洞洞的。每个人的肌肉都显得那么放松,好像他们的骨头都散了架似的。
杨过走了过来,张开两只胳膊紧紧地把我们俩人都抱在一起。他说:“哎呀,老朋友,也久没见了。”
韦纬问他近况怎么样。他同答说:“没事儿,没事儿。”好像他让我们都不要为他们担心。
我们没看到丽芬,杨过再三问我有什么“感觉”。不—会儿,他也不见了。
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我走进了一间卧室,想从这里往外看看那个花园。没想到丽芬就在那儿。她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背朝着我,靠在一个穿着黑色尖头皮鞋的男人身上。她的头发往前垂了下来遮住了她的脸。我走过去在她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她把头转了过来。
她说:“啊,是你。我不知道杨过邀请了你。你的脸色怎么这样不好!”
我说:“你好吗?”
她耸了耸肩,“你看,挺好的。”
“杨宝宝在这儿吗?”
丽芬做了个手势,指了指那个几乎被一堆箱子挡着的小床。看起来好像开箱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喏,她就在那儿。不管什么地方,她都能睡着。”
那个男的插嘴说:“只好这样。”
丽芬没理睬他,也没把我们向他介绍。
我问她:“住在这儿怎么样?”
“很好。杨过做得不错。”她往前靠了靠,打开了一只箱子,里面装的尽是衣服,都做成一小捆一小捆干草似的。
我问道:“放在这儿安全吗?”
丽芬说:“这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没人感兴趣的。”
“丽芬!,’那个男人又嚷了起来,语调带有警告的味道。
她说:“哦,知道了。好吧,告诉你,我们的猫死了,因为它吃了一片安眠药。”
“哎哟,丽芬!”那个男的又拉开了嗓门。
她说:“幸好不是杨宝宝。”
“丽芬,住嘴,别再往下说了。”
“她是我的老朋友嘛。”
“可你简直是个蠢货。”
丽芬有点畏缩了。
“婊子,到这儿来。”那个男人的腔调比刚才缓和了一些。丽芬乖乖地朝他走了过去。
我对她说了声:“好了,谢谢你们的邀请。”就退出了这个房间。
到了外边,我把丽芬和我刚才那段对话向韦纬复述了一遍。韦纬说:“听起来,那个男人不像是个好人,丽芬就是愿意让别人摆布。”
两年以后,一个深秋的下午,我到离中山路不远的超级市场去买东西。正当我急匆匆地推着一辆采购车在过道的一个拐角地方转弯时,恰好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一辆小车。推车的原来是杨过。自从那次晚上以后,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他呢。“是你!”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显得比以前苍老了——脸上的肉皮已较松弛,额头上已隐隐约约添了几丝皱纹。
“杨过,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他又一次地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住。“见到了你,我也觉得非常高兴。我正想给你打个电话呢。现在我们又是邻居了。”
“你搬到这儿来了?还跟从前一样?丽芬好吗?我真想见到她。”
“我们离婚了,她还呆在商业区。”
“啊!非常遗憾。”
“但是,我现在正在重新振作起来。”杨过继续往下说,“我已有工作了,晚上在一个小区当保安,不过,白天我在做保险代理人的工作。”
“你还在干——你知道,另一件事儿?”我往四外瞧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在听我们讲话。
“麻醉品吗?”杨过粗声粗气地说,“这玩意儿做不得,我一有了工作就洗手不干了。”
我换个话题问道:“你和丽芬,到底是谁离谁呢?”
“丽芬,而且她把杨宝宝也带走了。她说她需要离开一下,她从来都不能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有—个人和他们呆在一起,那就是阿西。他是和我—起做生意的伙伴,我们的房租就是他帮付的。一天,丽芬宣布她和阿西要到武汉去,阿西在那里有熟人。他们到那里去就是和这些熟人住在一起。她说她或许还会回来的。”
“阿西这个人怎么样?”
“人倒是不错。可是在武汉的情况却很糟糕,丽芬她似乎想要戒掉麻醉品,可是她已陷得太深了。我很担心杨宝宝,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的眼光落到了靠近我们的那个货架上,好像在提醒他来此是买东西的。他拿起了—个罐头,随手把它扔到了他的小车里。
“哦,听我说,咱们一块儿去吃顿午饭,好吗?我很想了解你们的情况。你觉得怎么样?”
我倒很想同他一道去一因为我希望多知道一些有关丽芬的事情。但我心里很难受,就借口说:“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改天我们再找个时间聚一聚,好不好?”
“好吧,一言为定。”他又再一次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韦纬在上海找到了工作。学校放假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去上海。
一天晚上,我们沿着中山大街走着。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杨过。他站在一条小马路上正在把几个手提箱装进汽车里去。一个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小女孩,看样子只有四五岁,她的头发又脏又乱,脸也没洗干净,站在旁边望着他。韦纬和我走过去向他们打招呼。
杨过神情沮丧,他说:“你们认识杨宝宝吗?”这个小女孩把手伸了出来和我们握手。我问丽芬怎么样了。
杨过说道:“她已经不在了。”他的声音低得连杨宝宝都听不到。韦纬当然也没听见,因为他正在跟杨宝宝谈话。他对孩子们总是这样的,仿佛孩子们都像他那样已经长成大人了。
“不在了?”我咕噜了一声。
他迅速地抬起了头做了个姿势,或者,也许他是向着那条河,向着西方点了点头。当他发现我还不明白时,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她已死了。”
“啊!杨过。”我不禁惊叫起来,但他已走到杨宝宝跟前去了。
他指着杨宝宝说:“她现在还不懂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都不清楚。她一直睡不好觉,好像吃的几种药都超过了剂量。他们都说,也许是个意外事故。”
我问杨过是不是我可以帮点忙,但他说不用。现在他要把杨宝宝带到他父母亲家里去,他也打算在那里住一些日子。
我们向他告了别,韦纬一点也没听到杨过谈的关于丽芬的一些情况。
过了—会儿,我们回到家。上床后,我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脑子里老是想着丽芬。我想起了那天在广州海滩的种种情景,那么生动,那么鲜明,简直可以说是历历在目。于是情不自禁地叫醒了韦纬。他迷迷糊糊地听着我讲述丽芬的故事。
韦纬说:“但是,亲爱的,即使你知道了,你又有什么办法?即使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又能帮什么忙呢?”
“韦纬,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我总是可以帮点忙的。”
他说:“我就不这样认为,丽芬老是要往倒霉的路上走。她就是这样一种人,她总想去碰碰运气。但是,她自己做的事,她是清楚的。”
—个星期以后,我们就离开广州到上海去了。我们再也没听到杨过的消息,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和他取得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