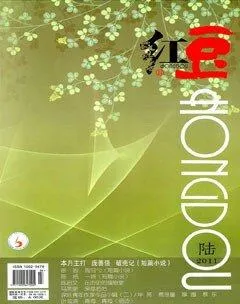一线
2011-01-01陈纸
红豆 2011年6期
古时,大街上,阳光灿烂如金,在瓦当与瓦当之间,激喘。身边,行人如织,盛世华衣,映亮城池。几张织布机,一家缝纫店,和着人语与市声,在空中,如流水一样,悠悠飘飞……
邓若兰从梦境中醒来,是在下岗的第二天。
两天前,她从工作了整整十年的谭市纺织厂退了下来。不过,是清退。听说,厂里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十年前,她母亲刘秋云也是从那里退了下来的,她做了整整三十一年的纺织工人,在岗位上光荣退休了。
邓若兰从顶替母亲刘秋云进入谭市纺织厂的第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要做得像母亲一样好。她仿佛从母亲身上接过了那份心情、那份气质、那份经历。她坚信,她的人生,也会像母亲一样,密密实实、眼花缭乱、忙忙:碌碌、顺顺畅畅,有头有尾地走下去。
不想,这根拉了十年的纱线,“咔嚓”一声,在这里断了。
起初,邓若兰没有太在意。她当时从容地走在车弄里,那根纱线断的时候,邓若兰与它只有两米的距离。她快步走上去,灵巧地接上了。
厂长目睹了邓若兰接线的全过程。邓若兰就是在厂长的眼皮底下接上那根纱线的。那根纱线断的时候,厂长刚好经过那里,那根纱线就断在厂长的眼皮底下。厂长的眼皮眨了一下,睫毛一闪,那根纱线就断了,就像琴弦,“嘣”的一声,好像是厂长使的力。那根纱线,把厂长的步伐打乱了,厂长前走也不是,后退也不是,脚步一时钉在了那里。他的脸色被眼皮和睫毛拍打了一下,由深黄变成了浅红,脸上松弛的肌肉,慢慢地收拢了。
邓若兰向厂长微微点了一下头,机敏地闪过他的身子,把那根纱线灵巧地接上了。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好像厂长的眼皮眨了一下,睫毛一闪,那根纱线就接上了。他的身子,很快地淹没在绵长、缜密的织布声中了。
直到厂里通知说要改制,要裁员,邓若兰也没有太在意。她根据直觉判断,最先裁掉的可能是那些年纪大的,而自己,三十三岁,正是黄金时期,论能力,自己也是拿过两次厂里的“劳动模范”和一次市里的“三八红旗手”,就是把厂里所有的人都裁掉,也轮不到我——她有时在心里有点内疚地这样想。
邓若兰一点也不在意自己,她心里只有不忍,不忍那些与她一起在机器的声响中跑来跑去的姐妹。不知谁要走,谁走她都不舍。这种感觉。只有在亲戚朋友去世时才有,可她不想在厂里有,不想那么快就有。
有一天,蒙蒙细雨中,邓若兰从电单车上,看见两顶白帽子,一高一低,像淋湿的云一样,沉沉的,又有点急的,向她跑过来。她们跑了五六米,她才看清,“白帽子”是她同车间的两个工友。高个子工友跑在前面,矮个子工友拼命追赶,矮个子一直努力地把雨伞向前伸,想为高个子工友打伞,因为有风,或者是跑出了风,雨伞斜斜的,歪着脖子,雨水像断了的线一样,从伞沿斜斜地、慌慌地飘落下来。高个子工友双手捂在帽子上,她的脸撞上了邓若兰的脸,矮个子工友的伞也撞了上来,把邓若兰和高个子遮了起来。高个子工友右手用力一挥,那把伞像一只软弱的风筝,轻轻翻了两个跟头,躺在了地上。矮个子工友不去捡伞,而是也把双手捂在帽子上,盯着高个子工友看。
高个子工友拉住邓若兰的车龙头喊:他妈的就我们三四个人好欺负,说我们工作不努力,放他妈的狗屁!矮个子工友在一旁拼命点头,她头上的帽子由白色变成了灰色,软软地贴在毛发上。邓若兰看着她的脸湿漉漉的,说,快把伞捡起来,不要淋湿了。
雨越下越大,由蒙蒙细雨改成“滴答”作响了。矮个子工友不理她的话,一把抓住邓若兰的手。高个子工友放了车龙头,跑到车后面,去推邓若兰,还喊,我们找厂长评理去,问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少站了一分钟岗,什么时候漏接了一根纱线。我们泡在车间的一线工人反倒下岗,他们大吃大喝,反倒是高薪。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理?她的话又追着邓若兰问了一句:你说嘛,天底下还有没有这样的理?
慢慢地,邓若兰把她俩的话听明白了,把她俩的意思弄清楚了。她只觉得脚下越来越软,越来越没力气,大串大串的雨线从她的衣领,一直渗到背脊。她觉得手也越来越冰凉,她的整个身子飘飘的,被她俩—拉一推,摇摇晃晃,随时都要摔倒。
邓若兰的身子一扭一扭的,她的头一扭一扭的,她的话也是一扭一扭的:没有吧?没有吧?凭什么?凭什么呀!她的话语把路两边的树也摇得一扭一扭的,把厂房的窗户也摇得一扭一扭的。
邓若兰说,就是因为那根纱线吗?就是慢了那一两步吗?邓若兰像是自言自语。那两位工友没听懂她的话,仍一拉一推,把邓若兰的身子推拉得一扭一扭。
邓若兰的车子一扭一扭,好不容易把她俩甩开。矮个子工友也不再拉了,指着公告栏上一张白色的纸,让邓若兰看。邓若兰不到两秒钟,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她才相信是真的。她把头上的白帽子抓在手,揉成一团,她把上嘴唇与下嘴唇也咬成了一团。她没有随另外两名工友往前走,而是扭过头,往回跑。
这时,雨竟停了,旁边的树叶被翻得“哗哗”作响。邓若兰把帽子抱在胸前,让一身青色的工作服挺直了起来,脚下的黑色平底布鞋像在碧波荡漾的湖水里航行的船,一翘一翘,摇荡着,向前。
两位工友三步并作两步,在后面追着。她们一边像鸭子拨着清波似的,一边冲着邓若兰喊,往哪里走呢?厂长办公室在后边!
邓若兰好像没听见,仍是往前小跑。跑着跑着,哭声就甩出来了:厂长欺负人,不能因为一根纱线就这样欺负人。
两位工友都喊,邓若兰、邓若兰,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
邓若兰说,我不要你们管。
两位工友把步子由三步并作两步,改成三步并作一步。高个子工友说,厂里把你开除了你还不管?矮个子工友说,我们不管,我们的饭碗一起完。
邓若兰抹了一把眼泪,回过头,在原地转圈。
高个子工友说,噫,你个邓若兰,吓蒙了不是?厂长办公室在那边。
矮个子工友冲上去拖住邓若兰。邓若兰不随两人走,扶起电单车,把方向盘一扭,要往上骑。
矮个子工友把她扯了下来,说,去哪里?不去评理?
邓若兰不说话,掐了一把鼻涕,又转了两个圈,上了车,往厂外的方向走。
邓若兰走到厂门口,停下车子,朝厂里看了一下,又朝厂外看了一下,停了四五秒钟,掏出手机,说,妈,在家吗?我想去找你说说话!
邓若兰看到母亲的背影时,她母亲刘秋云正走在天桥上。邓若兰在马路的这一边锁好电单车,走上天桥,母亲那身青色的衣裤便撞进了她的眼帘。母亲的发髻像一座隆起的、骄傲的、坚实的小山包,她的身材饱满得一颤一颤,让邓若兰既熟悉又陌生。邓若兰看到母亲的脚下,一双黑色的鞋随着她的双脚一抬一放,若隐若现。邓若兰把目光移到自己的脚下,看着看着,鼻孔里的汁液又流了出来。她狠狠地抽泣了一下,眼眶里的水却没能止住,冰凉凉地,渗了出来。
邓若兰一只手捂住眼睛和鼻儿,冲上去,用另一只手夺母亲手臂上的菜篮子。母亲身子急疾一扭,头猛地一侧,见是女儿,把脚步顿住,把眼睛瞪大,今天休息,不上班啦?邓若兰不回答,只盯着母亲的前身看,突然说,家里没黑色纽扣了吗?母亲低头,顺着女儿的目光,也盯着衣服说,掉了一颗,就再也找不着了,问了几家店也没卖了,想想也是,现在的商店,哪还有我们以前的工作服卖?我真是傻呆了,没法,只好安颗白的。母亲宽宽的脸上泛起了笑意,不要紧吧?不难看就行。邓若兰摸着那颗乳白色的纽扣,说,好。母亲把笑意又漾开了一点,说,好什么好,你们新的工作服才好。母亲说完,抬起一只脚,轻轻地踢到女儿邓若兰眼前,又说,退休时的三双鞋,穿烂了两双,这双也洗得发白,起毛了。
邓若兰若有若无地“嗯”了两三声,又说,好。说完,把母亲搂紧,直到上了二楼。母亲打开家门,放下菜篮,系上围裙。邓若兰静静地看着,当母亲的前身围上那块白色的围裙时,邓若兰“哇”地哭出声来,说,妈,你以为是在纺织车间呀?
中国纺织工人担负着满足人民衣着需要,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支援农业技术改造的光荣任务。全体纺织工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的红旗,高举不断革命的红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不断改造自己,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化技术水平,以冲天的革命干劲,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最大的力量。
——《几句简单的话》·陈少敏·1959年
这本巴掌大的《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如今仍躺在邓若兰母亲刘秋云的梳妆盒里,被梳子、发夹压着。本子的封面是浅绿色的,封面上的图是黑白的。图片上,一位纺织女工,戴着白帽子,白帽子是一朵比头更大的白云,把半头的发丝像薄雾一样,笼在里面。女工穿着短袖的花格衫,围着白色围裙的,露出白藕一样的两截胳膊。刘秋云看不清她裤子的花色,图片上的裤子只是画成了几条竖线,与两旁的织布面卷起的风的样子一样。
刘秋云能感觉到这幅静止的照片中急速旋转的声音,她的耳边一片轰鸣。她知道,那是她生活的主旋律。
那名纺织女工,右手放在织布机的纱线上,左手轻轻抚着一捆织成的布面,脸微笑着。她的神情让刘秋云的脸上也有了微笑。这时,刘秋云觉得那个女工就是自己。
刘秋云每天都把这种微笑写在面前的镜子里,窗外的晨光像柔软而洁白的布面,滑进房间来。躺在床上的邓若兰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景。在她心里,那一缕缕微笑,那一缕缕晨光,就是母亲的全部,也是她未来的全部。她渴望这一天快快到来。她知道,母亲可能也希望那一天来到。母亲踮脚,轻盈地闪出房间后,邓若兰还笼罩在一片白色的、光滑的童话里。
记忆中,邓若兰自懂事起,就认为母亲是位细腻聪明、勤勉能干的女人。细腻聪明、勤勉能干这样的词语,用在纺织女工的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很小的时候,邓若兰看到母亲刘秋云在暗黄的灯光下,用几根金钢针、一团绒线,双手上下翻飞,纺出各种美丽图案的针织品,把她和父亲,还有自己,打扮得清爽宜人,包裹得温暖舒适。
母亲在灯下的那副端庄从容贤淑的神态,成了邓若兰童年里又一帧美丽的图片。
邓若兰的童年,很少见到父亲。父亲在地质队工作。长年累月,奔波在野地。每次回来,父亲像探看新娘一样兴奋,邓若兰看到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满脸绯红。母亲很少问他在外面如何如何,只是捧出在父亲外出的时间里她编织的小背心、小绒线裤,一件件,抖开来,像云儿一样,铺在父亲的身上,比画着,测量着,用父亲的话说,比地质队出身的他还细心的样子。
邓若兰曾问母亲,你爱父亲吗?刘秋云轻轻点了一下邓若兰的头,说,傻丫头,不爱有你吗?邓若兰又问,你不怕父亲跑掉吗?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说,你将来懂得织毛衣就晓得了。邓若兰眼睛瞪得大大,跟织毛衣有什么关系呀?刘秋云说,织毛衣,最要紧的是,要掌握绒线的松紧度,紧了,针织品会板结,不柔软;松了,就稀拉,没章法,不暖和。母亲刘秋云摩挲着手中的毛线衣,声音像线绒那么软、那么细,她说,松紧度适应的针织品,才既平整大方,又柔软舒展。我和你爸也是一样,太近了,绊脚,太远了,怕分离。母亲刘秋云又叹了一口气,说,拉好手中的线,不松不紧,不远不近,方能不离不弃,懂吗?
六岁的邓若兰点点头,又摇摇头。她仰起头,在邓若兰的眼里,全是母亲刘秋云。在邓若兰的眼里,母亲刘秋云就是她的衣食住行,母亲刘秋云就是家,就是她心里的全部。她没见母亲求过别人家做过什么事,即使是父亲在家的时候,她也没听到母亲说,要父亲做什么。
那时的母亲刘秋云已是市纺织厂工作七年的女工了。
刘秋云有时会把邓若兰带到厂里,那是邓若兰感到最奇妙、最自由的时间。奇妙的是,厂里的轰响,在邓若兰听来,像悦耳的音乐,丝毫没有烦躁的感觉。她蹦蹦跳跳,把母亲刘秋云的手晃得麻滋滋地生疼。
邓若兰觉得母亲刘秋云天生就是做纺织女工的料。她想,母亲双手连针织都能做,还不能守着自动化机器做吗?——当然,这是邓若兰长到十几岁时的想法。那时,她看到母亲轻快的脚步,突然这样想。她这样一想,突然又觉得有点小残酷。因为,她也看到了母亲脚步没有轻快的时候。她也看到了母亲回到家捶着腰和背的时候,这时,她就希望母亲的厂里停电,永远地停电。
邓若兰跟母亲去厂里时,真的遇到了几次停电。停电,其实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纺织厂经常发生的事。邓若兰记得,那时大人不叫“停电”,而是说“避峰”,它一般在上中班的时候发生。特别是夏季的傍晚,到用电高峰时,轰鸣的纺织机,像一群突然坠落的大鸟,因停电戛然而止。
这时,邓若兰往往蹲在厂房外的花圃边玩,一直嗡嗡的声音像突然掐了一下,断了。邓若兰侧起耳朵,才知道,整个车间一片寂静和朦胧。接着,她马上能听到女工们的叫喊声。邓若兰拼命地往厂房里跑,她听到那些叫喊声,回荡在车间宽大的空中。还有一些叔叔,用纺管敲打铁皮箱,“嘭嘭”的声响,仿佛是一种宣泄或者是短暂的呼气。
车间里的高温,让每个人的衣衫都湿透了,大家都在叫喊。她们一边叫喊,一边冲出车间,在空旷的地上乘凉。遇到晚上停电,抬头看暮色的夜空,星星若隐若现,草丛里,萤火虫儿飞舞。这时,刘秋云便靠在墙跟上,让脸微微仰起来,迎着轻轻吹来的风儿,脸上的每一抹光泽都在与夜风摩娑,像抚摩每一根纱线,每一寸布儿。她听到了那种摩娑的“沙沙”声,在她内心的最深处响起。她的脸亮亮的,是被她的眼睛点亮的,她耳畔听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她的心花,在夏夜里,在女工们带着汗味的迷人气息里,默默绽放。
邓若兰更多的时候,是看到母亲在车间里忙碌的情景。对三班制的工作,刘秋云是深有体会的。她不停地在车弄里来回走动,纱线断了,要灵巧地接上;纱管满了,要飞快地—手拔下满绽的纱管,一手插上空纱管;粗纱没了,要通知扛纱工,扛纱工要肩扛着沉重的粗纱筒,高高举起,放到纺纱机的顶上;纺车坏了,要跟班机修工及时修理好。刘秋云的车间有一百多部纺纱机,一百五十多个工人,她们分工明确,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一百多台纺纱机的热量,使整个车间像个大蒸笼,温度常常达到四五十度,降温的办法就是从外面运来数十斤重的大冰块,放在木盒里,安置在车间的各个角落。
那时候,刘秋云清楚地记得,一休息时,人手一本《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这本巴掌大的小书,由纺织工作出版社出版,1959年增订的。车间主任组织她们学习本子里的织布工作法,比如如何巡回、如何检查布面、如何检查经轴、如何检查机械和停台方法等。刘秋云看着主任大声地念着本子上的文字,她把那本子夹在她的手掌上,她能背得出那些文字,好像每个字就是一根纱线,她每天抚摩它们,看着它们从她的眼前像光阴般穿梭往复。
后来,刘秋云把那小本子放进了梳妆盒里。梳妆盒表面,慢慢起了皱纹,她的脸,也慢慢爬上了皱纹。邓若兰说,妈,你该歇歇了,我来接你的班吧。刘秋云摸着女儿邓若兰那双长长的、纤细的、白白的手说,你也就是只能吃这门饭……
门关着,没有锁。柔软的绸被,一铺一折,成了节气的实物标本。主人说:采桑去。养蚕去。织绮去。她看着她进门的姿势,像孔雀开屏。她对自己说,还有没有开始?天地有大美,水落石不出,丝丝缕缕,只是往日的记忆而已……
直到母亲刘秋云喊邓若兰到厨房里去端蛋花西红柿汤,邓若兰才真正抑制不住,又一次哭出声来。刘秋云转过身,看到女儿邓若兰双手揉搓着那顶白帽子,满脸都是泪花儿,湿漉漉,发着光。刘秋云说问,兰,你今天怎么啦?说着,她的脚步紧紧地牵到女儿面前去。
邓若兰扑在母亲怀里,说,我就是想当个纺织工人,我一直在努力地工作,像你一样地努力工作。我也不比别人落后,我甚至比很多人要先进,可为什么要我下岗?刘秋云一听,把目光慢慢地定在对面的墙壁上,一动也不动。许久,她才说,不关你比别人落后不落后。邓若兰擦了一下母亲的手背,那上面,滴着她的泪。邓若兰的头仍低着,那是为什么?刘秋云说,碰上你了。刘秋云把女儿推到饭桌边,又说,现在的事呀,人与人,比不得。
邓若兰说,连你也不站在我这边。刘秋云说,我站在你这边有什么用?当初我让你去考大学,你不是不去?你不是非嚷着要顶我去纺织厂?说着。她在女儿邓若兰的肩上拍了两下,说,下午我就去跟厂长说说。停了三四秒钟,她又说,唉,不知厂长还认不认得我这张老脸,我在厂里的时候,他是车间主任。邓若兰说,妈,我知道,你千个不愿万个不愿,你还是不要去了,现在是我的事了,不该叫你管。刘秋云说,了解你妈就好。说完,她叹了口气,脸上拧起了几丝笑意,又拍了两下邓若兰的肩,说,明天我给你织一条披肩,一米的,白色的,上面织花的,一片一片,翻起花瓣,保证好看。
邓若兰仍盯着墙壁,目光定定,为什么厂长刚好经过那里?为什么恰恰断了一根纱线呢?刘秋云说,不是那根线的事,不关那根线的事。邓若兰说,那我以后怎么办呢?刘秋云说,那能怎么办?找其他事做,找其他工作。邓若兰说,除了纺纱织布,我还能做什么?刘秋云说,你妈做了一辈子的纺织女工,天天盯着那根纱线,很快就走完了。你也要学你妈,除了纺纱织布,就不会其他?邓若兰说,我喜欢几百号人在同一个车间的热闹,我喜欢机械嗡鸣的喧嚣,我喜欢大集体企业的荣耀。刘秋云说,那是因为你只走了一条路。刘秋云把女儿按倒在凳子上,又说,先吃饭吧。
丈夫听说邓若兰下岗了,脸色不阴也不晴,这让邓若兰更觉得难受,她认为,丈夫的那种闷心反倒堵在她心口。她希望丈夫说点什么,哪怕是骂一句厂长也好呀,但丈夫一句话也没有说。
丈夫在一家报社做发行员,每月挣一千二三百元,不知是让他觉得羞愧呀还是什么原因,他主动把每天早上和下午接送女儿的事揽下来。现在,邓若兰说,我没事做了,明天起,我来接送女儿吧。丈夫点点头,还是没说话。邓若兰又像被人推了一把,逼上了一个更狭窄的角落,她甚至感到了呼吸困难,胸口胀闷得慌。她想喊,想大声喊,想替她丈夫喊,想喊得比车间里的机器还响。她真的想张开嘴,可看到家里的地板呀、桌椅呀、电视机呀、电冰箱呀,都瞪着眼睛,看着她,在等着她喊,邓若兰觉得它们是在看她的笑话。邓若兰脖子一缩,却喊不出来。
第二天,邓若兰把女儿送到学校。回到家,想再睡会儿,可睡不着;想看电视,脑子里掏空了一样,记不下东西。她坐在客厅里,她实在呆不下去。她看了一下墙壁上的钟表,时间好像也与她作对,才到七点多十五分钟的位置。她又回到床上,决定干脆好好想想未来怎么办。谁知,她没想到一个开头,反倒迷迷糊糊睡着了。
从梦境中醒来,到了上午九点多了。她又洗了一把脸,感觉心越收越拢,家里没人,四周空旷。她想起在车间里,那么多机器,那么大声响,把四周塞得满满当当,好像除了她的身子是空的,周围全是满的。但她也没觉得逼仄,而是脚步轻捷,游刃有余,好像一个偌大的舞台上,就她一个人在表演。她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休息时,与同事们讲几句话,开个玩笑,那话语,那笑声,仿佛能直冲云霄,到达九天。
现在没了,好像是一根纱线,勒住了她的脖子,绊了一下她的后路,让她一下子喘不过气来,让她来了一个踉跄。她感到脖子越勒越紧,让她窒息;她的脚想到了挣脱,她终于奔向了饭桌,把一碟豆芽炒肉片和两个馒头吃了个精光。她把一根根豆芽绞在一起,用尖利的牙齿狠狠地咬。她听到了满嘴的呻吟,她感到了快意。她第一次尝到了胜利者的滋味,她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邓若兰决定出去走走,骑着电单车出去走走,走到没有了电为止,然后,找个地方,快速充电后,再回来。
不知为什么,邓若兰第一想到的,是往城郊方向走。她奇怪自己,不再像刚才那样,怀念那一片喧嚣,好像只一瞬,她要寻找的,竟然是安静。
早上的光线,晶莹透亮。出了闹市,她第一次感到,一尘不染的清明,在她的生活中还是有的。太阳从硫磺色的云缝中,滤出一道道黄中带红的光柱,斜斜地,射到地面上,映得树叶闪闪发亮。已是十月底了,这座城市的气温前两天经过短暂下降后,今天又缓慢回升了。所有的树叶似乎都没有掉,到处都还是绿意。邓若兰感觉,这是生活在南方城市中唯一的庆幸。
现在看来,这唯一的庆幸,成为了她重要的焦点。
邓若兰没有想到,树林离城市这么近,或者说,中间只隔着一条快速环道,是快速环道隔断或连接了宁静和喧嚣。宽宽的六车道的快速环道也成了邓若兰心情的分水岭,把她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时,邓若兰对快速环道充满了感激。尽管她能想象得到,在飞机上看它,只是像一根细线而已,现在,她对它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和美好的回忆。
四周长满了树,邓若兰踏进林子,头上没有天空,林子把整片天空吞没了。邓若兰贪婪地呼吸,大口大口地吸气,大口大口地呼气。她在树与树之间疾走,她朝着幻想中的另一片林子跑去。她坚信,林子一定连着林子,她突然找到了一种不由自主。
然而没有,出了这片林子,眼前豁然开朗,所有的绿意矮在她的正前方。邓若兰的目光不用抬高,也不用放低,那一团团一簇族、浓浓的密密的绿意——叶子的绿意无限地、肆意地铺陈开来,一望无际,微笑着,站立着,注视着邓若兰。
没有林子,邓若兰没有感到失望。邓若兰觉得,这是她第一次为“欠缺”找到了一个不失望的理由。她不去想电单车放在哪个地方,她自顾往前跑,沿着湿湿的、软软的田埂往前跑。身旁那些闪动的叶子,像展开的手掌,在向她致以欢迎的礼节。
她在绿意中,看到了掩映着的十几二十幢房子。邓若兰的脑海里立即蹦出两个字:农家。她沿着桑叶掩映的那条田埂,像掐准了一根线一样,沿着线头,一直走去。
村子里很静,静得让她陌生,又让她舒坦。邓若兰把呼吸调到最自然的状态,她感觉她的呼吸也很静。
邓若兰寻到一家离桑叶田最近,甚至可以说,是紧挨桑田的一户农家走去。门没有关,她喊了一声“有人吗”,没人应答。她轻轻地踏了进去,简陋的屋子,可说是—尘不染。她先是看到了—个擦得雪亮的平底锅。接着,又有一只有脚的小烧锅,两样东西,并排站着,像一对友好的姐妹,腼腆而娇羞地,挂在火炉边。
穿过一条一米见宽的小巷,走了五六米,邓若兰浸入了一片亮光里。她抬头一看,头上有一天井,四四方方,把屋里照得通亮。邓若兰紧走几步,见有—个四十多平米大的厅堂。厅堂中摆着一台木制的机子,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坐在机子前,一手摇着车子,一手扯着棉絮,随着车子悠悠地转动,一根长长的棉线,便从她手中的棉絮里,变戏法似的走了出来。
邓若兰认得,那是一套木质纺织机。她双眼放光,不由自主地冲上去,说,我来试试。
……嘁哩喀喳去轧棉,一边出的是花种,一边出的是雪片。沙木号,牛皮弦,腚沟夹个柳芭椽,枣木槌子旋得溜溜圆,弹得棉花朴然然。拿槌子,搬案板,搓得布绩细又圆。好使的车子八根齿。好使的锭子两头尖,纺的穗子像鹅蛋。打车子打,线轴子穿,浆线杆架着浆线椽。
——《棉花段》·歌谣
邓若兰接过农妇手中捻着的那根纱线,学着摇了起来,但摇不到三四圈,手中的纱线便断了。邓若兰的心咯噔一下,那农妇却轻笑了一声,露出一口白白整整的牙,说声“没事”,拾起地下那根断了的线,右手在嘴唇上一沾,两个手指一搓,便接好了。
邓若兰说。我只会使用自动纺织机,不会人工的。农妇接过邓若兰的话说,这台织布机是我奶奶的奶奶传下来的,少说也有一百五十年了。接着,她牵着线,走远一点,又说,枣木做的,外边擦了桐油,很结实。
邓若兰蹲在地上,侧着身子,看农妇熟练的动作,瞧她手中的那根线,好像永远抽不完、扯不断。她又想,那根线呀,就像一个人,他知不知道脚下的路,是走呀走呀,走不完?他知道有时一不小心会断吗?他担心吗?他害怕吗?邓若兰想呀想,她去看农妇的脸。农妇一边笑着,一边也朝她看。
邓若兰突然觉得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了。她看懂了我在想什么吗?如果看懂了,那她的笑是什么意思呢?
邓若兰去想那笑的意思了。她觉得自己很少对别人的一个表情认真地想过。以前,只是对母亲的一举一动想过,她都是被母亲的一举一动牵着往前走的。她以前,也很少对车间以外的一辆纺纱机留心过,或者她压根儿就没想过,车间之外,还有别的纺纱机。
还有那根线,以前,在厂子里,纱线都是机器在转动着抽的,有多长有多细,她好像从来没有时间仔细看。现在她觉得有时间看了,她觉得她的周围,除了空气,就是那根纱线,就是时间。她第一次作为旁观者,看着一根线,从另一个人手中拧出来。她觉得时间被秒针、分针和时针拉慢了、拉长了,拉成了一首抒情的《啸花段》。邓若兰从那根线上,转移到农妇的脸上。那张脸笑过之后,这会儿,平静得不起丝毫涟漪,像无风的、舒缓的湖面。
邓若兰的心中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羡慕。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她再一次把自己的呼吸与那根纱线连一起,找到了合拍的节奏。她不再责怪那根纱线了,先前的那种紧张、愤懑,像一团浓墨般粗大的棉絮,此时,被一点点释放出来,化成了一缕轻盈盈、柔软软的细线。
邓若兰又听到农妇细声说,抽线,也不是越长越好,当棉线缠到一二两重时,就要从锭上取下来。
农妇的右手往回摇着纺车,抽出的棉线,便乖巧地缠在了锭杆上。然后,她停下纺车,把一团棉线从锭上取下来,再将棉线从坨中一根根拉出,缠绕在织布机的木棍上。用稻草扎成的刷子。顺着线轻轻刷,不一会儿,就把不顺溜的线梳理顺了。
农妇歪着头,对邓若兰说,这是织布前的一道工序,叫刷线,就是将四百八十根经线的线头,分别穿入织布机刷柱里的每个缝隙,经过缠线、提经,使上一层经线平整顺溜,为开始织布做最后的准备。
农妇还没有坐在织布机前,邓若兰的耳边就响起了“咣当咣当”的声音。农妇见她侧着耳朵的样子,说,我还没开始呢,你听到的,是别人家的。农妇又说,村里有三十套纺织机,有五十多位妇女会纺纱织布,我们自己纺纱,自己织布,拿到圩上去,不够卖呢。
邓若兰访遍了村庄的每家每户,她看到了一台又一台的纺织机。它们一律都是木头的,棉线都是一根一根地纺,粗布都是一校一校地织的。
邓若兰看着它们,像一位位稳重古朴的历史人物,她一遍遍地抚摩那些粗布,厚实,平整,经纬分明。她闻到了一种灿烂的阳光味道,和芳香的泥土气息。邓若兰还发现,与她以前操作的机器织布比,手工织布仍有其独特优势,机器织布只能织四个缯以内的,而手工织布则可以织到六个缯、八个缯,所以,对织布工的要求更严,稍有疏忽,布面的花纹就会错乱。
邓若兰看着看着,她觉得这座叫“思华”的小村庄越来越大,自己变得越来越小。先前的自豪、得意稀释了许多。“咣当咣当”的织布声,是“咣当”有声的雨点,敲击了她的心坎,也滋润了她的心田。
此后,思华村不断发生一些新鲜的事儿。先是,那里的农妇,被一位城里来的下岗女工组织了起来,技术不断出新,会织各种色线交织成的各种几何图形的粗布。接着,思华村人又学会了在粗布上手工缝边和手工绣花,用粗布裁剪,做成各种家纺。后来,工艺又更进了一步,在手工缝边和手工绣花的粗布上,采用针织工艺,勾织出各种图案,再抽掉部分棉纱,形成镂空,做成一件件精美实用的艺术品。再后来,思华村的手工纺织家纺走向了谭市。听说,谭市流行一种奇妙的凉席,是用粗布织成的,睡在上面,既美观时尚,又舒适凉快。而这种“空调凉席”,据说就是出自思华村。
此时,思华村四周的桑叶,又摊开了宽大的手掌,一片片,把整片天都染绿了。思华村的“咣当咣当”声似乎比以前更庞大、更雄浑,像激越的鼓点,响彻云霄。
又是一个有阳光的清晨,又是在桑林的田埂上,一个女人拉着她的女儿,指着前面的村庄,跟在身后的丈夫,紧跟上几步,贴得妻子更近些。
这个女人,穿着一件粉色的人工短粗布衫,胸前织了一排小巧的满天星,下面勾出细细的叶子,旁边还有一朵大花,大花的花蕊用粉色的小珠子串成,烘托着她下身的一条人工粗布的吊带裙。
她感觉自己走得很快,但女儿的脚步比她还轻盈,好像一只燕子一样,跳到了母亲前面。她的目光在母亲的身上跳跃了两三下,说,妈妈的打扮真好看。
女人说,那妈妈用手工也给你织一件,好不好?
女儿甩开母亲的手,蹦跳着叫起来,好呀好呀。
起风了,那个女人仰起脸,风在她的脸上滑翔,抚平了她的眼角的褶皱。眼及之处,绿浪翻滚,大音有声。
女人的手,被女儿拉着,她一边往前走,一边回过头。她的思绪越过桑林,跨过快速环道。她在想呀,当初,母亲刘秋云如何鼓励她,在谭市的古城路上,经营起了她的“若兰家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