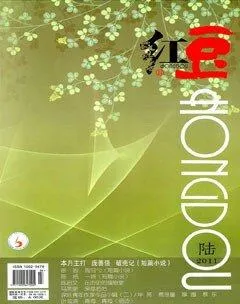破壳记
2011-01-01庞善强
红豆 2011年6期
我一定要做这事,到时候会有个大转机的。
——弗兰茨·卡夫卡(1912)
好像是我刚刚做了个什么手术。是的,是做了个手术,只不过这手术不是在医院里进行的,而是由我自己背着人在那间不到七个平米的小屋偷偷来完成的。我甚至怀疑自己咋还有这样的天赋,完全不像别人说的我是条狗。狗怎么能给自己做手术?即便是人,也难能翻转手臂,像裁缝般在自己的脊背上游刃有余。我却做到了。我把身体上所有无端长出来的许多似疱疹恶肉都一切割下来。空洞的伤口就那么裸露在外肆意地张扬着,我却不见一滴血,亦不觉得疼痛,只是心里有种异样的难受。当然,我还是那般活蹦乱跳,忙着去做那些肮脏的琐事,没有一点要死的迹象。这真是很奇怪。听人说,得了这样的病会持续高烧、呼吸困难、四肢无力,直至脏器衰竭死亡。可是,我并没有这些不祥征兆,即使有那么一点恶心及呼吸压抑,我潜意识一直认为,那不是我病了,是因为我工作在这样的场所,时常见到那些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秽物。问题是,我现在的身体分明已被划割得千疮百孔,我甚至能看到我破损的心脏还在顽强地跳动,以及有一缕看似柔和温暖的光线穿透了我的肺叶。
伤心啊!我怎么能连娘给予我的一个凡胎肉体都不能保护好?我真的很没用!然而,最令我尴尬不安的是,我怎么会染上这种病!这让我以后如何再做人!我先声明一点,我的祖上都是善良正直的农民,祖辈们没有一点坏名声,从来都没有。他们虽然穷,但那廉价的身体一向健好,像是一个个打砸不坏的碌碡,所以这病断然不会是祖上遗传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做过那种事情,我发誓。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年龄还小,最主要的是我骨子里从来就没有过那种歪念。
我明显地能感觉到,有风像一条条冰冷的虫子钻^体内。我冷到了极点,寒战连连。我仅存的肌肤、肋骨和脊柱难以抵御这种无休止的侵蚀,我得想个办法,给自己残破的身体包裹一个壳。可是,我寻找来寻找去,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东西来裹住我的伤口。事情往往是这样,好像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有了新的发现:避孕套难道不是可以裹住我伤口最好的壳?避孕套这东西我小时候就不陌生。当然,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叫避孕套这个怪名,只管它叫“气球”,更不知道它的真正用途。不过,我可以软缠硬磨给娘说上一堆好话,讨得两分钱,然后去村上的小卖店买上两个。你也许会想象不到,我能把它吹得很大,大到里面可以容纳我的整个身体,再—撒手高高抛起,让它像麻雀一样去高高飞翔。可是,在我高兴之极,往往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突然会起了风,“气球”顺着风向到处乱撞,挂在树枝或其他什么带刺的物体上,就那么啪的一声猝然爆裂,随后就是我无尽的失望,却换来娘的一段欣喜。娘到晚上闲下来的时候,也顾不上揉搓整日忙碌肿胀的寒腿,轻轻拨亮那盏老旧的煤油灯,把爆裂的“气球”口子上那圈较粗的橡皮筋小心地剪下来,然后再在上边细心地一圈一圈缠上红色的丝线,这样就可以用它扎娘那绺灰黄的马尾辫了。直至我到这家娱乐城打工后,我才正式改了口,再不管避孕套叫“气球”了。我真是很无知,亦没见过什么大世面,避孕套这东西怎么会那么多?废弃的避孕套已在娱乐城后面的那片凹槽里堆成了一座小山。无数硕大的苍蝇欢欣鼓舞地飞过来飞过去,它们喊着统一的号子,嗡嗡嗡的,瞬间它们的躯体被滋润成了饱CVtqwEBtvKkBmQLbqd94GQ==满鲜艳的绿色。我在娱乐城先前也有过两次较体面的工作,后来却沦为专门打扫倾倒这些秽物。刚来的时候,我看着那堆山一样的东西很是心疼,怎么会把如此多的“气球”抛之于荒野?那是多少的钱?可以为多少的孩子带去童年的快乐?又会为多少的母亲姐妹做多少精致的扎辫套?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我见到的那些秽物彻底否决了,甚至我不住地恶心呕吐。再后来,我见得多了,就是再想吐已经吐不出来了。
现在,我却不得不用到这个东西了,为了堵住我那四处通透漏风的身体。当然,我绝对不会用那些沾染了秽物的避孕套,我得找一个小时候玩过的那种完好无损的“气球”。在娱乐城工作,找到这样的—个“气球”并不难。我很快就从遗落在床上地上的那些东西中挑拣出一个自认为最干净的“气球”。我小心地用它把整个身体裹起来,我以为这样我还是一个完整的自己。但是,这样做还远远不够,人们还会透过“气球”看到我残损的身体。我得尽量用得体的衣服完全掩盖住我的身体,我害怕人们看到我身体上被挖出来的千百个窟窿,然后就谣言四起,说我是一个如何如何不检点的男孩。问题是,我的确没有什么得体的衣服,像我这类在娱乐城干粗脏活儿的人,店里是从来不给发工作服的,我唯一可以替换着穿的那身衣服,还是娘在世时给缝制的,这身衣服我很少舍得穿。城里的人们说,我穿上这身衣服那么老土,一看就是乡巴佬,一看就是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看就是瞎鳖丁。而我现在更惦念这件衣服的好,穿这样的土色布衣就没有人会把我和那些喜欢追花惜月风流倜傥的男人联系在一起,他们怎么会穿这么朴素的衣服?我有了我的自信,也敢抬起头来光明正大地做回自己。
奇怪的是,如此豪华的娱乐城里突然出现了无数硕大油光发亮的老鼠。它们看到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居然抬起两只前腿向我频频点头致意,似存感激。随后,成群结队的老鼠大摇大摆地在娱乐城里到处游走,每到一个房间就爬在污物筒上舔食里面的秽物,甚至几只老鼠为避孕套上粘连的秽物而厮咬。怎么会有如此多如此大的老鼠?这样的场景似乎又在哪里见过。我终于想起来了,大约是在爹去世前的那几个晚上,家里天天闹鼠灾。我爹得的是“黄病”,浑身上下皮肤泛着黯然的黄,尤其是那眼睛更是黄得吓人。我娘砸锅卖铁带着爹去求过几个大夫,回来后泪眼婆娑着说,你爹的病没治了,只能躺在炕上等死了。我爹说,咱家就这一根独苗,我走后你再找个伴儿吧,要不孩子怕是难拉扯成了人。我娘只是流泪,流着流着就控制不住情绪了。她喋喋不休地说,我不会再嫁了,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儿子拉扯大的。其时,爹已吃不进任何东西,眼睛塌陷着,只有一丝悠悠气。但是,爹并不显得痛苦,甚至还有一丝安详在脸上。那时,我尽管还特别小,却一直陪侍在爹的身边,爹不睡,我就更不能睡。娘看着爹虽长吁短叹,但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伏下身子鼾声如雷,娘为爹已经熬塌了身子。我就坐在爹的身边,认真再认真地端看着爹的眉眉眼眼。我知道爹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我想尽可能把爹的音容深深烙在心里。爹会不时地发出些异样的声音,再细听声音却不是发自爹的嘴里,而是在地上的角旮旯。果然,—会儿从屋子的不同角落里窜出来许多硕大的老鼠,它们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微光。这些老鼠似乎一点都不害怕我,任凭我拍打炕沿墙壁它们还是窜来窜去。老鼠们聚齐后像是发布一个什么会,然后都聚在一个尿盆边,它们争抢着舔食盆里的东西。一连四五天,老鼠们天天如此。第六天的晚上爹永远地走了,那些老鼠竟然也奇迹般地彻底消失了。现在宾馆里突然出现了这么庞大的一群老鼠,难道是又会有人要死吗?是谁?当然,我断定一定不会是我,因为我的身体尽管成了漏风的筛子,但是我感觉尚好,我更清楚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品行不端的事情。那会是谁呢?
我开始陷于深深的恐惧与不安中。其实,这种恐惧的心情不是现在才有的。自打我觉得长大了,告诉娘我必须得出去找自己的出路,踏上了异乡漂泊的旅途后,这种惴惴不安一直伴着我的左右。只是,最初我四处求职,还是找不到一份工作,便担心我会像—条流浪狗饿死在街头。而现在,我更担心的是,我能否从一条狗的卑贱姿态努力向人的境界过渡。当然,我说的是那种有尊严感的人,否则我宁愿自己是条狗。
但是,狗也是有三六九等级。每天从我的面前会走过许多优雅的先生,和挂着珠光宝气的女士。他(她)们或牵引或抱着一只打扮得人时的漂亮的狗,它们都有温馨的名字,或叫阿黄,或叫虎子,或叫宝儿等。我却没有名字,我只有—个属于我的代号:047。有没有名字倒无所谓,我只求能有份稳定的工作,能填饱我永远处于饥饿状态的肚子。我太容易满足自己。不过,在此之前,我有过自己的名字,但那名字也仅仅是刚离开家乡后自己姑且知道。对于—个长期生活无着落的城市流浪汉,谁还会在意你是哪的人,或是你叫什么名字!这样落魄的日子过得久了,我便也忘却了自己还有个人名。
终于有一天,具体的日子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那天的阳光很迷人,一位黄发碧眼的老人走到龟缩在墙角的我面前,严肃地告诫我说:“你一定要努力去做事,到时候会有个大转机的。”
我在混沌无助中似有所悟。我真的站立起来了,我觉得我的四肢还是那么强健有力。接着我忍住饥饿,再次去四处寻找着做事。我先后去过许多大小的工厂工地,或简单或富丽堂皇的店铺。我努力地向他们推销自己,我说我还很年轻,我的年轻给因长久流浪而变得猥琐的形容遮盖了,我有的是力气,可以帮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祈求他们给我一份哪怕是肮脏繁重的工作。
“滚出去!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无论是到哪个地方,无论是见到凶恶的汉子,或是看上去和善的老者,他们都显得没有一点耐心,不等我把话讲完,就极不耐烦地把我连推带搡驱赶出去。这样的话像一柄柄刀刺在我的心上,我痛到了极点,但是我最终还是不得不选择像狗一样灰溜溜地离开。
我开始怀疑那位老人所说的话,我沮丧颓废到了极点,便打算依旧重复以前浑浑噩噩四处流浪的日子。恰逢四月初八,杨柳依依,和风日丽,多么美好的日子!街头上的善男信女老老少少都向位于清远街的北寺拥去,他们去乞求神灵能带给他们好运。我忽然也意识到了什么,就裹好自己粗布烂衣走向了北寺。我知道所有祈祷的人里没有—个人比得上我的虔诚;我也知道,所有祈祷的人没有一个人的祈祷心愿比得上我的简单,神似乎不需劳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完全满足我的心愿——我只求神灵能给予我一份哪怕不是工作的工作,我为此而能填饱早已干瘪的肠胃。可是。我竟没有见到万能的神。我还没有走到神的所在,就被接连不断的愤怒斥责声喝退了:“滚开!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叫花子!”人们的呵斥声不断地在我的耳边荡漾着,一点一点撕扯着我的心。我终于明白了,我已经沦落为—个叫花子了。我怎么成了叫花子了?而我觉得自己此时更像是一条流浪狗。我步履沉重地走到一个其臭无比的水坑边,水中的我蓬头垢面的,一身衣服肮脏褴褛。我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我赶忙用臭水坑里面的水,去洗涤满头满脸的污浊,然后又打开随身携带的布袋,换上了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那身布衣。我惊奇地发现我像是换了个人。我终于得以兴高采烈地拜见到了神,我哀伤无比地向神展示了我瘦骨嶙峋的身子。然后,再满心欢喜地带着奢望打算寻找可以填饱肚子的工作。我果真出奇地幸运。我刚走出北寺,步下第十级台阶,就被一个穿着考究的人挡住了去路,他随手把—块骨头抛在地上。我实在太饿了,如获至宝,贪婪地吮吸着残留在骨头上的残汁和星星点点的肉腥子,然后再满怀感激地跟在那人屁股后,随时等待他再施舍给我一截骨头,或是半个窝头。那人得意地笑了,说,一看你就是一条忠于主人的狗。我是一条狗?终于有人看出了我是条狗!我欣喜自己能遇到了“伯乐”,并很快果断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狗,又怎么样?能吃饱饭的狗自然也是幸福的狗。我为得到那个“主人”的肯定而极度兴奋,我甚至立刻趴在地上,晃着屁股摇尾乞冷,祈求他允许我能永远追随在他左右。那人却说,可惜你不是一条好狗,有你在我的身边,我会很没面子。不过,你倒不是一无用处。他说,你可以去我的娱乐城做些事情,但前提是,必须永远保守狗的忠诚。我当时高兴坏了,我真的要感谢圣明伟大的神!同时,我也要感谢那位黄发碧眼的老人:“你一定要努力去做事,到时候会有个大转机的。”我极相信这位老人的话,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努力做到从狗再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从此,我成了娱乐城起早贪黑爱岗敬业的047号。
娱乐城生活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惬意欢乐,相反我过着比做流浪狗时更胆战心惊的日子。
有一天,娱乐城的外面聚集了很多人,现场有些混乱,人们都把目光瞥向了这栋楼,神色那么慌乱。这些人都是娱乐城的员工,因为他们的身体上都挂着和我一样如同狗的编号,其中还混杂着几十个靠出卖肉体赚取利润的“鸡”。这样把她们说成“鸡”,我总感觉对她们是莫大的侮辱,可是别人都这么叫,我作为一个狗辈无力改变她们的现实。眼见娱乐城那栋楼歪七扭八摇摇欲坠,霓虹灯却依旧闪闪烁烁疯狂张扬,好像是整个世界马上有被颠覆的危险,并且不断从娱乐城的墙体中往外渗血。那血汩汩地流着流着,“鸡”们就—个个脸色苍白委靡不振,不久后都干瘪如柴。过了须臾,娱乐城又恢复了往日的繁盛与安详,员工们有条不紊地做着手中的事,“鸡”们照旧妖艳若花,带着一股股热浪往来穿梭于各个房间。
这是怎么了?我问自己。可是,我根本弄不清其中的缘由。听人说,这家娱乐城过去是市里—位领导的亲属开的,故不见任何离奇的事。现在,刚换了个老板,就是那位施舍给我骨头,唤我为狗,然后又拉我进娱乐城的人。自打他接管了这摊子,许多的怪事就接踵而至。娱乐城的老板似乎也很茫然无奈,每天到各个寺庙,去给财神爷、关老爷、土地爷等主宰他命运的神进献香火。他在神的面前却也颇似一条狗,他甚至不惜放下架子,用舌尖去舔神裸露在外的肢体。可是,不管老板如何祈求神灵,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发生。有人说,还是现在的老板舍不得多花几个香钱,难以打动诸神,要不就是他本人的秉气低(压不住邪气)。
按理说,娱乐城发生什么事情和我们这些在下里打杂的狗不应该存在因果关系,可是,事情往往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我们几十个打杂卖命的狗,开始本来和娱乐城看家护院的几条真正的大狼狗同食一锅饭,该是沾了那些狼狗的光,我们的碗里居然偶尔有肉。后来连续发生了几桩事情,我们只好另开炉灶了。我们的伙食再不如那些狼狗,要不就是等狼狗吃剩后的残渣才是我们的正餐。这里,不妨先说说娱乐城发生的几件事。
好像是娱乐城来了几辆颇似消防车的车,但那些车怎么看都是活脱脱的甲壳虫,行动慢不说,警笛的鸣叫声还盖不住娱乐城里“鸡”们放荡的浪笑。几个穿制服的人楼上楼下不停地查看,但总是有十几个妖艳的“鸡”柔若祥云款款,伴在左右。当检查人员打开消防水闸后,从里面源源不断地冒出了油。怎么会是油呢?我当时就大惊失色。我到娱乐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专管消保安全的设备管道。也就是每天要不间断地查看,防止有人动这些设备的任何—个部件,当然也包括我。娱乐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执法人员理所当然先要审讯我。我本来饿瘦的身体还没有得到恢复,看到这种架势更是慌得没了魂儿。我的身子像一片残败的树叶,轻飘飘地一摇一摆,似乎永远保证不了自己安全站立的姿态。我是那么委屈,整个消防管道原本都是水,可是老板在短暂的时间里就积累了很多油,多到没地方放了,最后想来想去就把油贮藏在消防管道里。老板说这样做是最安全的,还让我严守秘密。正当我六神无主的时候,老板竟突然出现了,先是暴打了我一顿,说我这条狗是如何如何不尽责,娱乐城怎么会有这么多油!分明是我盗窃了他人的油贮藏在管道里。我是那么地不堪一击,很快就瘫倒在地上。几个甲壳虫一样的东西高高举起坚挺的喙,把管道里的那些油都吸干了,它们的体型瞬间变得硕大,随后慢慢地挪动着身子,走了。
我好冤啊,我怎么能是偷盗的贼?即使是我真的有这个能力,我为何不用这些油中的点滴去喂养我干瘪如树叶的身子?这世间似乎还没有一个窃贼甘愿瘦骨嶙峋去做一个吝啬鬼。可是,我是老板招来的一条狗,狗是从来没有话语权的,狗得忠于主人。不知怎么了,我忽然竟有了潜意识,是那种狗与人角色过渡转换中,一种模糊的,但又不能确认的潜意识。我总觉得还会有事情发生,所以,我得小心再小心地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害怕丢掉了这份工作后的饥饿和孤独。更主要的是,黄发碧眼老人的话还是在耳边萦绕:“你一定要努力去做事,到时候会有个大转机的。”所以,为了这个转机,我必须得忍辱负重,我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QCmoBuvddpaPgEXOFBNhIJsmIlZ3Xjctu8en7RzbKZo=。
这事过后,老板马上更换了我的工作,他让我负责娱乐城的“紧急预警”。也就是说,让我密切注意娱乐城外面的动向,一旦发现有可疑的执法检查人员到来,就赶决按响预警警报。老板告诫我,你得拿出狗的敏锐与机智。我哪里敢怠慢,只得高昂起脖子,尽量地抻长挺直,双耳不断调整方向去收纳外面异常的声音,眼睛一刻不停地盯视着娱乐城门外。
可是,我的运气是那么糟糕。没多久,娱乐城的大门被封了,原因是涉嫌非法经营。当时的情况是:我的确是以狗的机警与敏锐发现了娱乐城门外走进了几个不同寻常的人,这些人和来此消遣的嫖客不一样,他们故意显示出那一身的凛然正气。我当时就果断地摁响了警报。问题是,有几个“鸡”已经听到了楼道里“预警”的反复警报声,但是,她们却没有丝毫的紧张,或者试图赶快躲避,而是依旧赤身裸体地缠着那些狂欢的嫖客。只是,在她们的表演中,又多了—个手执画笔的看客,旁边是花花绿绿一碟一碟的颜料。之后,执法检查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答辩。检查人员说,她们涉嫌卖淫嫖娼;“鸡”们却说,她们正在搞人体行为艺术。当然,行为艺术中包含性行为艺术,难道艺术的本身就是法所不容?毕竟,“鸡”们是斗不过执法者的,法是执法者熟稔的可以让你生,又可以让你死的法,那法总是会引经据典,细到第几条第几款,你纵然花言巧语也难脱其中的框框。不过,莫担心,任何事情都是有转机的。娱乐城刚封了一天,老板就押解着我去投案自首了。老板指着我的脊梁对执法者说,他的职责就是监督与防范娱乐城的不轨行为,娱乐城出了这么大的性质恶劣的事情是和他分不开的,事后他还把那些“鸡”都放跑了,以消灭罪证,实在是法不能容。我当即像狗一样哀号起来,并试图想大呼冤枉。执法者早看出了我的动机,说,天下哪有犯法者甘愿服法呢?我当日就被拘留了,而娱乐城的大门当日又豁然大开,“鸡”们依旧光鲜照人歌舞升平。
我很为自己鸣不平。娱乐城的这些“鸡”是老板不间断招来的,出事后,我眼见老板把那些“鸡”都藏匿起来了,是他嫁祸给我的。可是,我是老板招来的一条狗,狗是没有话语权的,即使有,谁又肯相信狗嘴里会吐出人言呢?
我呆在监牢里,才知道天下还有这样的好去处,竟然还给我饭吃。有饭吃多好,我何苦再出去给别人去当一条狗!此次事情的发生,对我而言,是来之不易的幸福,我开始惦念这监牢的好。可是,没几天我又被从监牢赶出来了,能让我出去的人还是娱乐城的老板。他对我说,因了你这条狗,花掉了我很多银子,你倒好,躲在监牢里享清福了。你还得给我回娱乐城干活去,啥时候你为我挣回了那些损失,你才能离开娱乐城。
就这样。我成了一条负债累累的狗了,我不清楚我得为老板再干多少时日,才能离开那个娱乐城。我只能用我虔诚的态度与努力工作,去争取我某一天的自由。
老板说,他当初果真没看错,我不是条好狗,我不能胜任重要的工作,只能去打扫倾倒娱乐城的垃圾。这样,我每天只能与成堆像山的避孕套为伍了。
但是,我还是愈来愈感觉到自己潜在的危险了,我不仅是老板任其招来呵去的一条狗,更是随时有可能成为一条“替罪狗”。但是,我就是明白了这个理又能如何?我唯一可做的,就是祈祷娱乐城不再发生什么事情,而我自己必须小心再小心,我不容许自己出一点差错。虽然耳边依然还会响起黄发碧眼老人的那句话:“你一定要努力去做事,到时候会有个大转机的。”但是,我现在再不敢有丝毫的奢望了,我知道那个转机可能永远不会属于我。
046突然间病了,说是得了那种可怕的病。她怎么会得了那种病?
046号,是一个体质弱小的女孩,可能是因为和我同期被老板招进娱乐城的,也可能是她太瘦弱了,我向来格外地关注她,我管她叫小女孩。我们这些在娱乐城打杂的下里人,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编号,我们都不清楚彼此的名字和籍贯,老板也不允许我们私下里打听。我不清楚老板这样做的目的。
小女孩负责娱乐城的床单被罩清洗工作,眉宇间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她每天没日没夜地干,整个人似乎又瘦了一大圈,而手指的关节却一天天在肿大。
起初。娱乐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小女孩会得那种病。原因很简单,她本身是如我之类干杂工的狗,怎么会有人对一条狗施以青睐?可是,后来随着病情的发展,人们发现她的确是得了那种病,而且已经病入膏肓。她先是因长久洗那些床单被罩几个手指都破裂了,接着破裂的手指化了脓,身体便出现了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红斑,然后就是持续高烧不退,然后又呼吸困难,没几日便卧床不起了。
很快娱乐城传出了许多的说法,有人说小女孩半夜三更偷偷溜进客人的房子;有人说小女孩仗着自己是处女,得了三百元钱卖了自己的身子;还有人说,小女孩耐不住寂寞,和看家护院的狼狗发生了媾和,狗和狗交配似乎更天经地义些。
可是,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一直不认为她是个轻浮的女孩,她分明像我的邻家妹子,憨朴勤劳而又纯洁。可是,该怎么解释她得的那种病?我陷于了疯狂绝望的猜想中不能自拔,并试图想为她讨得一些公道。但是,我是一条无能的狗,所有的狗只有等待被人宰割的命运,我们似乎并不能改变自己,更改变不了别人。
女孩的生命危在旦夕,却没有人带着她去看病就医。我是一条分文没有的狗,我有的只是因愤怒而装腔作势咆哮的利齿,但是,我的利齿在老板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我唯一可做的,就是为小女孩找出得病的真正原因,然后还给她一个清白的名分。
娱乐城里来了这么多的老鼠,它们为争抢避孕套上的秽物而厮咬。有只老鼠的前爪被咬破了,老鼠的伤口上沾满了秽物,可怜的老鼠竟然转了几圈就倒地毙命了。我终于明白了,小女孩不就是因为手指破裂沾染上这种带有病毒的秽物才感染上了那病?我决定为她澄清事实,为她挽回名声。可是,我是一条狗,有人会相信一条狗的言论吗?
小女孩在她被隔离的那间小屋死去了,老板却异常地镇静。当日,她的遗体就被几个人拖出去掩埋了,但娱乐城里的人们不清楚女孩被掩埋在哪里,也不知道女孩真正的名字,以及她的家在何处。纵然是我狗急跳墙,想去状告老板,替小女孩伸冤,可是,我不知道小女孩的任何底细,我的作证显然是苍白无力的。我能做的,只能是像狗一样仰头长号,去祈祷小女孩冤死的魂灵。然而,更多的人还是诅咒,指责小女孩是如何如何不检点,她的死纯属活该。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替小女孩申辩,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身上竟然也长出了许多的红斑恶肉。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也得了那种可怕的病?可是,我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做过那种事,身体上的任何部位也没有破裂,我怎么会沾染上那种病?我在极度的慌乱中躲进了小屋。对于死,我不再怕了,我怕的是人们顷刻而至的闲言碎语。慌乱中,我用一把小刀把身体上所有的疱疹恶肉都切割下来,这样我似乎又成了—个健康的人。但,不管我的身体现在怎么样,我确信自己没有得那病,因为我没有高烧呼吸困难,有的只是心里难受。
好在我用避孕套把自己的身体裹起来了,好在穿上了娘给我缝制的那身衣服,我还是一个外表完整的我。虽然我有自信心,但是还是害怕裹伤口的避孕套会突然破裂,害怕稍有闪失,就会让人们看到我残破的身体,那让我以后再如何做人?甚至再没有了做一条狗的权利。所以,我得小心再小心,我必须得保护好这个要命的壳。
有消息传出,娱乐城里的老鼠感染上了HIV病毒。什么是HIV病毒,我并不清楚,但是我隐隐觉得,这个病毒和我身体的病变是分不开的。
娱乐城忽然来了十多个身穿防疫服的人,他们的整个身体都裹在洁白的防护服里,嘴上带着防护面罩,背上扛着—个蓝色的打药筒。娱乐城的老鼠们惊恐之极,密密麻麻四下里逃散。防疫^员手执喷雾枪,对着老鼠强劲地喷洒着药物。须臾,硕大的老鼠死了一大片。
我竭力躲避着那自茫茫的一片雾,尽管我不清楚那片雾对我有没有伤害,但是我害怕那强有力的雾会吹散娘为我缝制的那身衣服,更主要的是会吹破我身子裹着的那层壳。我如同未死的老鼠一般慌不择路四处躲藏,但是那雾依旧紧跟在我的身边。我一着急就喊出了一嗓子:救命啊!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震惊了,原来我不是真正的狗,我还会说人话。但是,我还未来得及庆幸时,就一脚踩空,整个身子随即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我的那个要命的壳砰地爆裂了。
待我睁开眼时,我发现自己赤身从床上掉在了地上,我的四周还是那不到七个平米的小屋。身上也没有避孕套做的壳,而且身体完好如初。
一缕月光从残破的窗棂中倾泻而人。我努力地稳定着自己惶恐之极的情绪,心想,我可能是做了个怪梦。我不住地祷告。
但,黄发碧眼的老人依稀还在我的面前。他说:“你一定要努力去做事,到时候会有个大转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