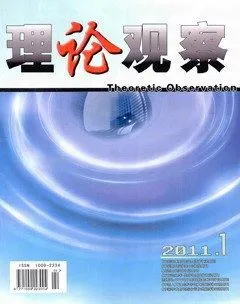“回家过年”对农民工的意义
2011-01-01牟来娣
理论观察 2011年1期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143-01
“过年”作为中华民族的一枚“印章”,早已植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了。在物质日渐丰裕的现代社会,当城市人感叹“年味”越来越淡,质疑“我们为什么要过年?”时,农民工“回家过年”的热情却并未减弱。那么,“回家过年”对于农民工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家”的抚慰
“家”是扎进中国人心灵土壤中的“根”,也是安顿人们灵魂的精神故乡。对于漂泊于城市,长期难得心灵归宿的农民工而言,“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城乡分治,一国两治”的大背景下,为了生存,农民工只得暂别亲人,只身一人或带着残缺的“家”,在“他乡”的城市辛苦打拼,候鸟般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虽然他们“肉体的生存”已得到确证,但“身在”城市的他们,“心灵”并没有安顿下来,对子女和父母的那份“爱”和“牵挂”也没有随着身体的空间位移而发生任何移动。身心的分离之感和撕裂之痛,已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所以,每当春节来临,他们大都会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名义,急不可待地踏上“回家过年”之路。
在“家”中,他们享受着自由自在的惬意,团团圆圆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他们可以尽情地倾吐和宣泄压抑已有的情感,可以暂时远离艰辛打拼的疲惫和无根漂泊的苦楚。
在“家”中,他们还通过为孩子买新衣、给压岁钱、陪孩子玩、聊天等方式弥补他们本应给予的父母之爱,由此减轻他们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对孩子的愧疚感。同时,他们也通过给父母买礼品、付赡养费、拉家常、分担家务等方式表达对父母的关爱和孝敬之情,让老人的精神得到慰藉,也弥补儿女对留守父母的一种心理亏欠。
可见,“回家过年”对于农民工而言,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精神“返乡”和心理“补偿”。“回家过年”犹如一碗“心灵鸡汤”,为他们重返城市积蓄了必要的心理能量。
“网”的重构
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系,需要一定的相互合作和走动。而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间的“业缘”纽带已明显松散。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的背景下,由于空间的阻隔和利益的分化,人们长年的分离,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缘和血缘观念的淡化。而过年期间,他们走亲串友,使有点疏远的亲情和友情得以再次确认和维护;而村落成员通过互致问候与祝福以及参加舞灯、搭台唱戏等集体娱乐活动,使这种村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得以重新体验和维系。
在人们地缘与血缘纽带得以维系的背后,还有一股嵌入其中的“信息流”。过年期间,农民工谈论得较多的还是他们在城市中如何生存和就业的话题。这些来自全国各城市就业的体验与经验,在此得以汇聚与交流,形成一股“信息流”。这股“信息流”对于农民工而言尤其重要。他们常常会根据在过年期间获得的信息和既有的社会网络,理性地做出像明年是继续外出还是留守,去什么城市,从事哪一个行业之类的决策。这一点,我们既可以从各大城市中出现的“温州村”、“河南村”等“抱团”现象看出,也可以从农村里外出就业者从事行业的同质性中得到佐证。
“位”的确证
在就业的过程中,农民工压抑着对“家”的思念,深藏着对子女及父母的愧疚,漂泊于城乡之间。但在过年时,他们已将一年的辛劳转换成回家的礼品,孩子的压岁钱和来年的学费等,来表达为人父(母)的“爱”或为人子(女)的“孝”,从而真正担当起家中“顶梁柱”的角色。这种家庭中的“位”,可以说是农民工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所在。这种角色的成功扮演,使他们在外辛苦打拼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确证。
家中有“位”,村落中也不乏“位”的确证。这种“位”是通过村落成员问的相互交流、亲戚与邻里间的礼品互送、除夕夜的烟花燃放、高档商品的购置等得以显现。与这种“位”相应的是个人价值的大小和社会地位与声望的高低。这种“位”的确证,带给农民工的既可能是一种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可能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会成为“农民工”之间“你追我赶”的动力。
“桥”的搭建
农民工以过年为平台,重新确认和编织地缘网和血缘网的过程中,除了传播城市就业信息之外,还会谈论全国各城市的变迁,城市人的生活观、婚姻观、生活方式、流行元素等。这些观念与信息,就在房前屋后的交流中,并肩上街的闲聊中,茶余饭后的谈天中得以碰撞和分享。所以,过年又是具有不同生活经历与阅历者在此相互影响与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农民工的这种交流,既是推动其思想和观念变革的重要媒介,也是沟通城乡的一座“桥梁”。
综上所述,“回家过年”对于农民工而言,既获得了“家”的抚慰和“网”的重构,又实现了“位”的确认和“桥”的搭建。但这种在平常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意义,农民工却要以“回家过年”的名义才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