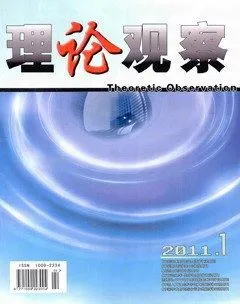由“心灵”本体到“意”本体
2011-01-01徐大威
理论观察 2011年1期
[摘要]以中、晚唐为界,中国诗歌意境发生了形态上的演变,即发生了由盛唐诗的自然“心灵化”形态,发展而为宋诗的自然“意理化”形态。这一转变的思想根源在于禅宗强调主观精神主体性的“顿悟”说。这一形态演变的规律是,诗歌创作由以呈示“心灵”为本体,演变而为以呈示“意”为本体。这一形态演变的结果是,以意为本体的诗歌创作,体现为三个特点:即以书本中的自然取代了原始自然;以技巧取代了天然;以意理取代了情思。宋诗的自然意理化,是诗歌意境的异化形态。
[关键词]意境;心灵本体;意本体;景物意理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1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116-02
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与演变,其根源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作为物质实体的人与自然,在唐代乃至整个古代中国,基本上是和谐地、稳定地、平衡地共处于生态环境之中,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唐时期,伴随着禅宗对于主观精神主体性的强调,诗人的目光逐渐从外在自然而走向了内心世界。与此相应,原始的、本真的自然便为诗人们所遗忘了。呈现在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往往是“书本中”的自然,诗人们更以技巧和意理为创作旨趣,张扬着自我主观精神的主体性,从而遮蔽了自然给予心灵的多样性。取消了自然多样性的宋诗,最终走向了唐诗的反面,最终导致了诗歌意境形态的式微。中国诗歌意境生成与演变的规律,即在于由心灵主体性向知性(智性、意理)主体性的嬗变。
一、禅宗与盛唐诗:景物心灵化
禅宗发现了人的“心灵”,确立心灵为人之绝对的主观精神本体。它认为人的心灵即“佛性”,才是与生俱来的人之为人的本性。因此,禅宗主张“顿悟”成佛说,目的便在于使精神从儒家的“仁”学(社会)和道家的“道”论(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刹那间进入个体本体(心)与宇宙本性(佛性)圆融一体的无差别境界,从而获得瞬间即永恒(我即佛)的直觉感受。惮宗的心性论,在哲学认识论上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当其渗透在审美、诗词创作领域时,它所高扬“心”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却从另一个侧面(即主体性)、为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突破作用,堪称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民族美学识别标志的诗歌意境形态正是在禅宗美学的影响下得以创生的。
盛唐诗歌意境的创造,不再预设一个形而上的“道”,而是直观“心灵”,以心灵之眼,而非感官之眼,亦非形上的“道”之眼来直观自然造化。用心灵来直观、照亮自然,自然造化、自然美便不是单个的物象,也不是“道”化的自在之物,而是与心灵美互相印证的“另一主体”,此一特点可以概括为“景物心灵化”。而意境的定义,则可概括为是,诗人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藉由直观心灵而生成的一种天地神人共舞的审美境界。
一般地,盛唐诗歌意境具有三种审美特征,都体现出了“景物心灵化”的特征。下面我们结合具体的诗作来看。
一是,情景交融:
李白《春思》: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杜甫《燕子来舟中作》: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王维《书事》: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米。
以上三首小诗,景物都充分心灵化、主体化了。李白诗中的“春风”,不知为何来到主人公的“罗帏”中,增添了主人公的烦恼,景物本身不是“道”的呈现,也不是“物”的呈现,而是另外一个“我”。杜诗中的“小燕子”,为了安慰诗人的寂寞,竟然翩然来到舟中,暂歇在船樯上。王维诗中的“苍苔”竞欲攀到诗人的衣上来。在这些诗中,自然与人非常亲和、友好,情景交融而相契无间,生成了一种天地神人共舞的审美境界。
二是,思与境偕:
王维《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白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韦应物《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以上三首小诗,都体现出禅宗美学的“空灵”的特点。诗人用心灵直观自然,面对的不再是对象化、客体化的世界,而是整体的、大全的宇宙自然造化。“水穷”之处正是“云起”之时,世间万物都有生灭、有聚散,只有那空的、永动的造化才是宇宙的本体所在。李白诗歌的题材是送别友人,然而该诗没有送别时忧伤的情感,反而给人一种崇高和壮美的力量,宇宙自然的运动、变化,这种恒在的本体,开拓了诗人的审美胸怀。在韦应物空寂的诗中,我们能够洞见到诗人的心灵境界,那种旷野间的疏离感、寂寞感以及对人生的质疑,等等,景物已然是诗人心灵的写照。
三是,时空转换:
杜甫《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璧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李商隐《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时空转换,是诗人在思想意识里进行的审美活动,把此时、此地的情和景与彼时、彼地的情和景都呈现在同一个情境之中。眼前的景引发了对诗人情思的共时性想象,表现为一种内审美的形态特征。杜诗仿佛具有“乾坤万里眼”,能够视通万里,诗歌将诗人的心灵世界完整地呈示出来,没有逻辑性的解说。李诗,连用了两个“巴山夜雨”,造成了回环复现的艺术效果。桂馥在《札朴》卷六里说:“眼前景反作后日怀想,此意更深”,不同空间的反复对照,使得诗人心灵主体性得以自由的呈示与展开。
二、禅宗与两宋诗:景物意理化
禅宗对于人的“心灵”本体的发现,促成了意境的生成。然而当人的主观精神主体性一味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心灵主体性便开始向知性(智性、意理)主体性转变。诗人的目光逐渐从外在自然而走向了内心世界。与此相应,原始的、本真的自然便为诗人们所遗忘了。呈现在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往往是“书本中”的自然,诗人们更以技巧和意理为创作旨趣,张扬着自我主观精神的主体性,从而遮敝了自然给予心灵的多样性。取消了自然多样性的宋诗,最终走向了唐诗的反面,最终导致了诗歌意境形态的式微。
尽管宋诗中的景物主体化进程在进一步的发展,但诗人往往赋景以“意”、以人的行为,意景交融,景物“心灵”化异化为景物“意理”化。景物心灵化、主体化的生成需要充分尊重景物的本体性,而景物本体却最终走向了工具化的存在,这便形成了宋诗的一个悖论:景物主体化的进程在进一步发展,同时景物偏离了本体走向了工具,造成了景物的“本体-工具”二元性。
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诗人常常赋景物以人文生命,如《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茅檐”、“花木”与人的活动紧密关联,而水绕绿田、山送青色则饱含着诗人的主观感受。这首诗中的境并非自然地呈露着,而是沾染着诗人的观感、趣味与生命,已经在人文视野的审视下获得了某种转化与提升。前二句以田园风光衬托出清高的隐者形象,后二句拟人手法展示出新奇的自然景色。“护田”、“排闼”语出《汉书》,但王安石却将校尉“卫护营田”与樊哙“排闼直入”的人的动态化为“一水”“两山”的意识与行为,景物因而主体化了,化为人的心理变迁。而在唐诗中,诗人往往赋景以情,使景物充分的主体化了,主体也充分景物化了,情与景实现了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又如其《夜直》:“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也体现了这个特点。
又通过赋景物以人的行为、动作,来传达某种理性意识,如《江上》“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第二句中“低徊”本来指人的徘徊沉思,这里却用来表现含雨的暮云低垂而缓慢地移动,情趣横生,静中有动。三、四句藉此生发哲理意谓人生前途遥远,道路无穷,下启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所谓宋诗意境的“意”本体,是相对于唐诗意境以“心灵”为本体的特征而言的,指把审美主体的“意”作为意境锻造的最终实在和根本。
“意”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两层意思:一为意志之意;一为意念之意。在艺术表现中显然是意志的意。《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就有“心之所之谓意”,把意看作是由主体内心所产生的行为动机和感情志向。郑板桥在一幅题画竹里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霜气皆浮动于疏枝密枝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非眼中之竹也”,其中的“画意”就是由作者所随机生成的审美目的、审美意识。宋人的诗歌创作与意境的营造常常“意”在笔先,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意识感的审美目的论传统。
在以意为本体的诗境中,虽然意景交融,主体的意充分景物化,景物也充分人性化了,但却未能生成主体间的交流与对话。“月与高人本有期,挂檐低户映娥眉。只从昨夜十分明,渐觉冰轮出海迟”、“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不似李白《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杜甫《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那样情景缠绵缱绻,而是景物代人思考,最终得意而忘景,景物本体走向了工具化。
意本体实质上是景物的意理化。它沿着景物主体化方向发展,但最终背离了景物本体性存在,将景物当成了工具,从而由主体化回复到了工具化。景物主体化的前提是景物的本体存在,然后才有景物的情感化、主体化出现。其表形特征是主客间的互动与对话。而意理化却是脱离了景物本体存在,将景物工具化。意理化中的景物不是情人而是雇工。当然,意理化中也有好诗。这些诗以哲理见长,也能警策读者。苏轼、王安石之辈多有此能。但宋诗多体现智,而唐诗多展现灵。智在技巧之中,灵在天地之间。
中国诗歌意境生成与演变的规律与奥秘,正在于由心灵主体性向知性(智性、意理)主体性的嬗变,由“心灵”本体到“意”本体的嬗变。
宋涛的自然意理化,是诗歌意境的异化形态。据笔者统计,与意境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进程相协又相悖,宋诗在景物心灵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意本体转向,并体现了向景物玄化的同归。虽然它与先秦诗歌景物玄化的侧重不同,却仍体现出了一种历史性的倒退(据对《唐诗鉴赏辞典》和《宋诗鉴赏辞典》的统计,宋诗名句为713句/1253首,即56.90%,较之唐诗名句的962句/1105首,即87.06%下降了30个百分点)。作为普遍性,在宋诗中,诗人或不写景,情景两无,纯以意胜;或者写景,而景物又成为诗人达意的工具。景物本体存在的合法性因之被取消。作为特殊性,在宋诗意境中,由于以意为本体,景物则兼具“工具一本体”的二元性。意本体与景物本体间的此消彼长构成了诗歌演变的脉络。以江西诗派为界,在其前,伴随意本体的生成与发展,景物本体性逐渐退场,意大于景;在其后,宋诗的中兴又使得景物本体在意本体的基础上复归,意景平衡。以意为本体,景物最终将被玄化、工具化,盛唐时期的情景交融、蕴藉空灵遂成绝响。
[参考文献]
[1]张晓红,试论2I世纪中国影视文化的“消解倾向”[J]学术交流,2009,8.
[2]徐大威,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看宋代意境型诗歌的意本体转向,[C]//王建疆,自然的空灵——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和流变,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193.
[责任编辑:李允